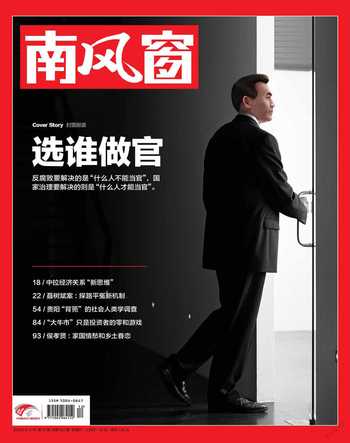中国变身“资本净输出国”
2015-09-10雷墨
雷墨

从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角色来看,2015年将是一个具有节点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中国的对外投资额很可能首次超过吸引外资的数量,转身为资本净输出国。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力始于2005年,10年间的绝大多数年份增幅都保持在两位数以上。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只比同期中国吸引外资量少35.6亿美元。
李克强总理刚刚结束的拉美四国行,再次凸显了中国在对外投资方面的强势作为。就拿中国与巴西签署的总额达533亿美元的35个投资协定来说,无论投资金额还是项目数量都算得上大手笔,一举将中印一年来首脑互访的经济成果和中国对巴基斯坦46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甩在身后。
关于中国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逆市增长”总是被强调的一个特点。比如全球咨询机构安永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提到,2011年至2014年,全球直接投资年缩减8%,但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增长达16%。

事实上,“逆市增长”的特点并非中国独有。中国对外投资的增势与全球直接投资格局的变迁基本契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全球直接投资总额的占比上,新兴市场经济体从1980年的6.2%上升到2012年的30%。而2012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对外投资中,来自金砖国家的数量占比超过60%。印度储备银行去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3年,印度对外投资增长了35倍,其中70%的投资额发生在2008年至2013年之间。
从国内背景来看,中国对外投资增长始于2001年提出的“走出去”战略。不过,最初的“走出去”着力点主要在拓展贸易方面,2005年中国对外投资才开始呈快速上升势头。当年中国对外投资额为123亿美元,与2004年(55亿美元)相比剧增124%!
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额达878亿美元,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韩国又松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迪利普·达斯认为,中国政府在对外投资扩张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自提出“走出去”战略之后,中国对外投资在质和量上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他提到,中国对外投资井喷式增长得益于一些特定的因素,比如中国有意识地融入地区和全球经济、参与全球价值链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等。
在中国对外投资历程中,政府“有形之手”发挥的作用毋庸置疑。经合组织曾在一份评估中国对外投资的报告中表示,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战略,在解释中国对外投资发展上,一直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不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经济问题学者丹尼尔·罗森认为,中国的对外投资政策不能不根植于中国经济的现实,“事实上,中国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正是中国经济需求的结果”。比利时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的邓肯·弗里曼表示,制度的确在中国对外投资发展中很重要,但制度的角色更为复杂,远非限制或促进对外投资那么简单,“不只是政策影响投资,投资者的行为也影响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对外投资大发展,是政府政策与经济活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李克强总理访问拉美四国的成果清单,预示着拉美地区将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一个重点。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增幅,拉美地区是132.7%,远超大洋洲(51.6%)、非洲(33.9%)和亚洲(16.7%)。而同期对欧洲的投资则下滑15.4%,对北美投资小幅增长0.4%。但2014年,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直接投资分别增长23.9%和1.7倍,增幅远高于对发展中国家,也高于当年对外投资总体增幅(14%)。中国对外投资态势的大幅变动,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原因,但也体现了中国对外投资行为的强势特征。美国鲁比肯战略集团董事本杰明·肖伯特,曾在一篇文章中把中国对外投资描述为“追赶型”。这也是中国对外投资动态变化的原因之一。
从存量看,中国近年来对外投资流量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美国传统基金会与美国企业研究所共同推出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系列报告,都提到这样一个趋势,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欧盟等发达经济体,海外工程建设则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2014年度的报告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排名前五的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和英国。韩国学者迪利普·达斯注意到,中国投资发达经济体意在获取高科技,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努力,进一步刺激了中国的对外投资。”用本杰明·肖伯特的话说,中国企业利用随时可获得的资金,来弥补技术和服务上的短板。
5月16日,国务院公布《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以发展中国家作为重点国别,并积极开拓发达国家市场。在访问拉美期间,李克强总理也提到“国际产能合作”,提议把中国的装备制造能力与拉美的基建需求结合起来。“中国全球投资追踪”2014年的报告显示,过去10年在海外工程建设对象国上,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尼日利亚、沙特、委内瑞拉、巴基斯坦和阿尔及利亚。从目前情况看,拉美未来的份额很可能会增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投资项目主管卡尔·索文特认为,对于国家经济来说,拓展投资的范围和布局,意味着诸如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促进经济融合这样的经济重构有了更多选择,资源配置也得到了优化。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去年中国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612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全年累计投资额为1160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的海外利益已几乎遍布全球。
中国对外投资的另一面是,截至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为6463亿美元,在全球排名第11位,与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序存在明显落差。但这一现实并未影响中国对外投资行为被过度“关注”。无论是吵吵嚷嚷一个多世纪都没走下纸面的克拉地峡运河,还是已经动工小半年的尼加拉瓜运河,都由于中国公司的介入而被外界用有色眼镜聚焦。中国向来突出对外投资的“经济属性”,合作对象也希望能得到经济好处,但中国的“政治动机”总被有意无意地指摘出来。
美国若不重视中国的投资,就不会与中国谈“双边投资协定”问题。但美国对中国企业的警惕也有目共睹。根据2007年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有权对任何事关“国家安全”的投资和并购展开调查。可该法案并未对“国家安全”下明确定义,也就是说美方有几乎无限的干预权。该委员会2013年审查的97件投资并购案中,针对中国企业的最多(21件)。2013年中海油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后不久,加拿大政府通过《2013经济行动计划法案》,提高了外国国企在加投资门槛。而且该法案把国企的定义修改为:外国政府拥有、控制或者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的企业。根据这一定义,加政府几乎可以把任何一家中国的大型企业定义为国企。
目前欧盟还没有类似的限制性法案,但政界也出现了中国是“拯救者”还是“掠夺者”的讨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索菲·默尼耶认为,中国投资的爆炸式增长给欧洲的决策者造成了两难:一方面,中国的并购可能会挽救濒临破产的欧洲企业,有利于就业和地区经济;另一方面,中国投资也可能带来国家安全担忧,导致无法确保能获得上述利益。这种独特的政经逻辑,在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行为中也时有体现。悉尼大学教授詹姆斯·莱利在题为《中国的经济谋略:将财富转化为实力》的文章中称,政治影响力会随着经济关系的不对称性增加而上升,鉴于中国的经济体量,在贸易、援助或投资上的微小变动,都可能对较小、更具依赖性的经济体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