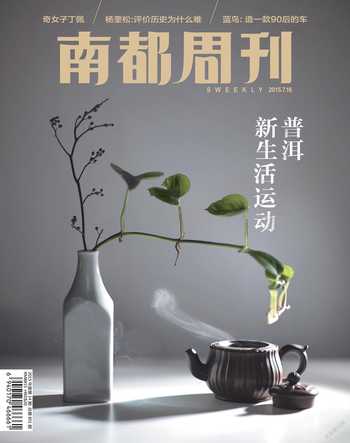杨奎松 历史评价的尺度
2015-09-10许智博
许智博
六月中旬的北京,蓝天白云的好天气让人心情舒畅。位于北京东南的首都图书馆B座的电影放映室里,柔和的灯光将焦点打在一米多高的演讲台上,肢体语言不多的杨奎松身上的浅灰色衬衫几乎没有一褶皱痕,从一个侧面显示着这个正在讲课的主人的严谨。在他的讲台对面的阶梯座椅上,二百多位通过网上报名抽签“抢”到门票的读者和历史爱好者竖着耳朵,听他将自己的观点娓娓道来。
这位年过六旬的学者是国内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圈里的名人,也是中国党史的爱好者们熟悉的作者,了解他研究方法的人愿意称他为“当代史学界的福尔摩斯”,他在中共党史和中外关系史领域的成就和声誉是顶尖的,“南高北杨”是对他学术地位的衷心褒奖。

从野蛮到文明的推演
这次为期一周的课程是杨奎松第一次在高校之外的公共场合讲课,“课题”也并非他以前在著作中探讨的题目,用为他开场“站台”的梁文道的话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听到的东西,会是我们请来的先生从来没在别的地方讲过的事情,是他花了很大的心机、很多的心血原创的一个崭新的研究计划,参加我们这个系列所有的读者们,你们都在看着一个新的知识或者学问上面的探讨方案的诞生。”
如果将门票上的讲课者名字隐去,单看“人为什么食人?”“希特勒为什么特别恶?”“如何认识美国的人权?”这些课题,恐怕熟悉杨奎松的人很难猜到讲课的人会是他。
不过“上课”的过程中很快就体现出了他的学养,高句丽的历史版图、日本的战争电影和美剧、ISIS的罪行、《圣经》的旧约与新约里映射的人类历史、华盛顿蓄奴、中国孩子在埃及旅游时刻字的新闻、哲学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的论述,几乎随便一个“梗”都能被他旁征博引编排进自己的论述里。
一个在中共党史领域的权威学者,为什么要像一个数学家要去讲解加减法一样,将讲课的课题定在学科的“基本面”,“屈身”做一次关于“抽象的、晦涩的”(梁文道语)历史评价尺度的探讨?用杨奎松自己话说,这些问题从他两年前去哈佛做交流研究的时候就一直在思考:“特别涉及到我们今天历史评价的这种混乱,完全没有标准,你会发现很多历史学家受现在国力上升的影响,把过去的说法全变掉了,原来是批判式的、检讨式的,甚至是反思式的,现在基本都成了一种自我辩护式的,从一个强国的角度很强势地要去‘对抗’。”
“这反映了我们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的、评判历史的尺度或工具。”杨奎松说,“而历史在我看来,无论如何,它有一定导向性和规律性。”
杨奎松将这样的讲课归为“启蒙的问题”。在这次首图连续七天的全天讲课之前,杨奎松曾在出版社的协助下挑选了一批高素质的读者,进行了一次像高校讲课那样用历史学专业学术词汇的“试讲”,因为听课的人学科背景不同,身为老师的他很快感觉到了他与“学生”们之间的尴尬,“很多人听不懂我讲的东西,又不好意思走,只能坐在那里,但我从他们的眼神里就能明白,他们跟我没法互动。”
杨奎松在试讲之后很快修正了自己的“方案”,他花了不少时间,做了一目了然的PPT,与之前单纯用史料讲述论点相比,他添加进来很多发生在现在的新闻、人们熟知的典故,让“课程”更加通俗。尽管讲课的题目看起来一节“抽象”、一节“具体”,似乎从字面找不到连贯性,但其实都是被他精心编排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是想通过讲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告诉大家,不光中国人是这个样子,外国人也是这个样子。”
“唯一需要注意的一点,这也是我在这次讲座当中反复在讲的一个问题,我们过去老讲野蛮就会挨打,中国百年以来,特别是西方和中国碰撞的历史,中国是受欺负的,没错,但是这次讲,其实我突出要强调一点,就是落后也存在另一个危险——落后也会野蛮。”杨奎松说。
在短短的几节讲课里将“了解之同情”的思维方式灌输给没有接受过历史学学术训练的听众并不容易,杨奎松甚至还像一个统计学者一样,在PPT里加进了大量的图标、数字对比,讲课时像抖包袱一样,时而纵向对比,时而横向对比——那些数字凸显出的“史实”显然更具备说服力,巧妙地引导着听课者去理解他含蓄而略带晦涩的观点。
他以自己八十年代初进入中央党校进行历史研究时遇到的困惑作为开场白,告诉着听众“评价历史为什么难”:当年轻的他读毛泽东在1938年发表在杂志上的《论新阶段》时,面对毛泽东当时对国民党的高度评价,非常吃惊,因为这些论述和之前他受过的历史教育完全不一样,他跑去问当时的党史教研室的主任,得到的回答只有一句:“对阶级敌人就是要搞阴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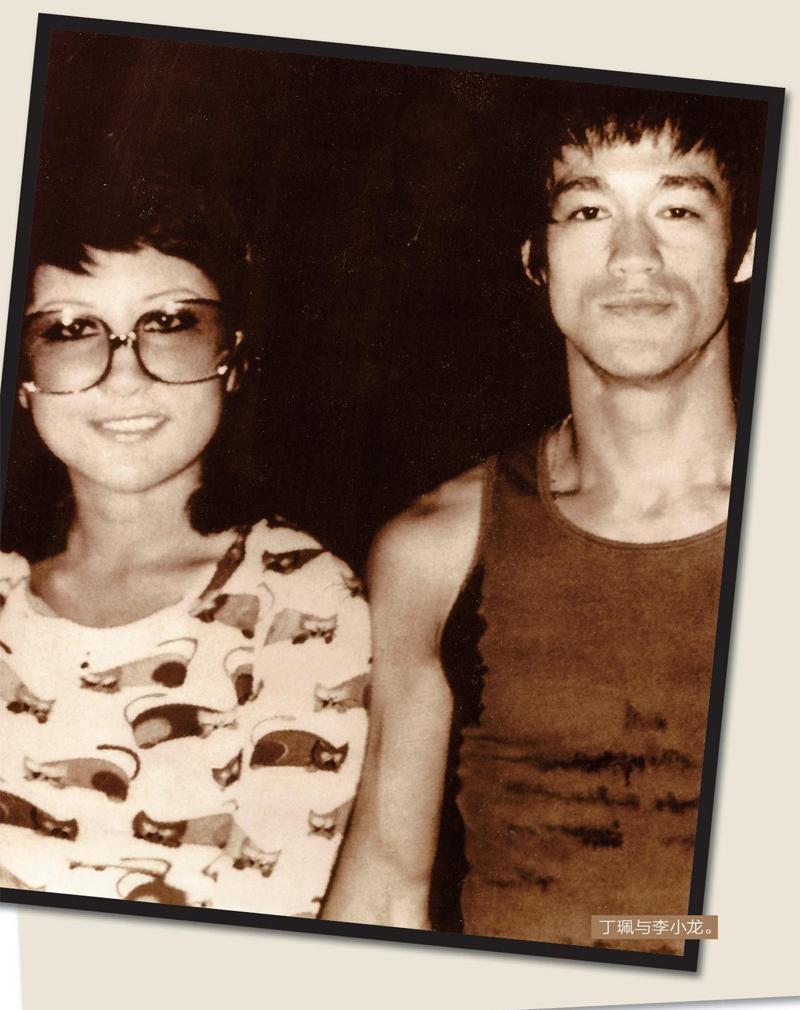
正是因为不满足这个答案,促使着年轻的杨奎松认真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尽管在当时的党史研究部门,很多持传统观点的人对他的研究“不太承认”,有人甚至说“中共党史如果按杨奎松这么搞就完了”,但这一切仍然不会减轻杨奎松心里的学术研究满足感。
三十年后,杨奎松用一星期的时间为很多专门请假、逃课来听他讲课的人将人类的历史从原始、野蛮到现代、文明整整“推演”了一遍,直到最后一节课,他才水到渠成地亮明了主题:我看历史评价的标准。
“人的历史”
从十几年前起,杨奎松在给学生们讲现代中外关系史的课程时,就会在黑板上画一个同心圆,圆心是“人”,每向外拓展一环,便是这个人在社会角色中利害关系更加递进的另外一个关系,从血缘、家族、信仰、地域,一直到职业、阶级、族群、党派、社会等级以及国家归属。
而今,这个同心圆再次出现在这次的“公共课堂”的PPT里。杨奎松为“人”画出这么多的圆环,只是为了说明,在历史里,人做出一个决定的出发点的多样性。
讲课讲到这里,杨奎松的语调都会有些轻微上扬:“其实每一个人在做研究的时候,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提醒我,我们在做任何历史研究的时候,我们在探讨任何一种历史问题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向我们的前人客观、中立。站在局外,抱着一个超然的态度。”
“研究历史,核心就是研究人。”这是杨奎松多年的从未改变的观点。“人是目的”是康德的主张,康德的人道主义观念曾给年轻时的杨奎松带来深刻的影响:“在人类文化启蒙的历史中,反反复复都在提‘人’的问题,但现在我们从小接受的爱国、民族教育里,人要服从国家,‘人’的问题变成了‘国’的问题,这二者之间有一个调和问题。”
在这次讲课的最后一讲,杨奎松洋洋洒洒的两个小时讲述,给出的评价历史的标准有三个:历史就是还原,要回归到当时的时空或情境,而不要拿来跟现实作对照,跟情感做连接;我们不能代替历史人物思考,用不着对历史当事、对已经发生过的历史负责;任何历史都是在某时间节点发生,所以要就事论事,根据具体时空条件和当时环境来评价,绝不能拿今天的条件去做对比、做褒贬。
杨奎松主张历史研究要进得去、出得来:“我讲这个时空实际上有点像我们做CT,做CT的时候,机器实际上按照精细的一条轴线,也就是我们讲的时间线在运行。但同时机器在不断地做扫描,‘横切面’就是我们的空间。所有的这些横切面你可以把它积累起来,然后还原成历史的空间,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时间段的那个横切面,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那个历史本身的前进或者退步,或者各种各样实践发生的情况。”
“我们对史实本身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尊重,这个尊重是什么?不是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上,站在我们今天的价值观的角度,对历史做简单的评判。或者说我们站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我们对历史本身做一个我们自以为正确的讨论,而是我们应该首先尽可能地换位思考,我们要尽可能地站在一个特定时空的条件下,去考察历史发生的原因和经过。”杨奎松强调说,“研究历史不能从价值出发,这是我要讲的。”
八节课很短,但这些串联起来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杨奎松治学数十年的持续思考过程:“最初做研究只是满足于把事情解释清楚了,但慢慢你就不满足了,在这些片片断断的东西解释完了以后,背后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做研究把史实还原了,还原了以后,只是一个片段、一个局部,这个部分跟其他部分有什么关系没有?从这个角度讲,我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宏大的、比较‘通’的思考,只不过这个思考是一步一步来的。现在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个局部研究之后都做一个理论性的归纳,那么我干脆就把这么多年思考的事情归纳起来,做一个史观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