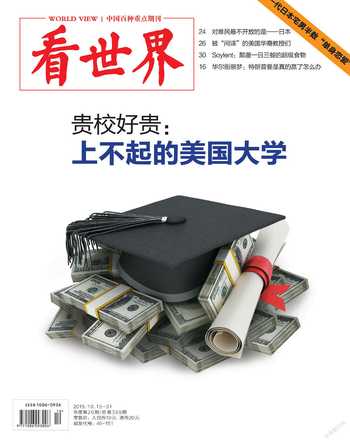澳大利亚少年吸毒致死背后
2015-09-10陈周
陈周

布里奇和他的小儿子普利斯顿·布里奇
9月13日,澳大利亚电视节目《60分钟》报道,2013年,16岁的澳大利亚少年Preston Bridge服用了合成致幻剂后出现飞翔的幻觉,跳楼身亡。他死后,父亲布里奇追溯致幻剂生产商来到中国合肥,以澳大利亚黑帮老大身份“卧底”,暗访合肥的致幻剂供应商。暗访的视频《Undercover-in-China(卧底中国)》在电视台播出,一时掀起轩然大波。该事件中相关致幻剂现象也将海淘时代的全球毒品网络推到风口浪尖。在造成16岁少年的死亡链条上,跨国供应商、对于新型致幻剂的监管困难、欧美泛滥成灾的校园嗑药文化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正如布里奇所说,“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布里奇是澳大利亚一个比较成功的生意人,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2013年,布里奇的小儿子普利斯顿·布里奇(Preston Bridge)16岁。他要去另一个城市的高中上学。这一天他还和母亲吻别。当天晚上,他跟一群学生一起开派对庆祝,在派对上,他服用了一些街上买来的合成毒品,叫做25i-NBOMe。随后,他出现了严重的幻觉,觉得自己会飞,从阳台一跃而下。父母再见到他时,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身上插满管子。两天后,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承受丧子之痛的父亲布里奇向澳大利亚政府部门反映无果后,开始在网上跟生产这类物质原料的公司接触。他号称自己是黑帮老大,打算进货。他说,这是一个父亲为了孩子而寻找真相的旅程,自己不能看着别的孩子步儿子的后尘,必须要做点什么。
布里奇找到中国合肥的一家致幻剂制造商。他伪装成一个携带巨款急欲采购的毒品贩子,和这家制造商取得了联系。澳大利亚当地电视台的制片人协助他,用眼镜式摄像头偷拍下了一段20分钟的纪录片。制造商的“工作人员”向布里奇介绍各种致幻剂,包括夺去他儿子生命的25i-NBOMe。
节目称,在中国,这些合成致幻剂打着“研究用药”的旗号,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算非法。而一旦一种致幻剂被法律禁止,就会马上改变化学成分,制造出新的致幻剂逃避法律。实际上,在中国严格的毒品控制之下,“所有只要是用于神经中枢、产生中枢性变化的、非医疗性用途的药,不管其化学结构是什么,都是违法的”。
然而,更现实的问题是,近两年,在我国每年新发现的吸毒人员大概有60%至70%都是吸食新型毒品。合成致幻剂最大的危害就是出现幻觉,导致跳楼、暴力等行为。而除了16岁的普利斯顿·布里奇,这类毒品在欧美已经夺去了很多青少年的生命。
从中国到澳大利亚,这类毒品是如何瞒天过海远渡重洋的?
承受丧子之痛的布里奇相当关心这个问题。澳大利亚海关很早就用缉毒犬阻止毒品进入,澳大利亚的缉毒犬还出口到了世界各地。然而发生在布里奇儿子身上的悲剧,让人对致幻剂是否能通过澳大利亚海关发出了疑问。
致幻剂中国供应商信誓旦旦表示自己有独特的方法通过澳大利亚海关。首先新型合成致幻剂一般能躲避过缉毒犬的检查,因为它们的训练一般只能覆盖传统毒品的气味。其次供应商在每个致幻剂的包装袋中混入不同的物质,使其有独特味道,最后他们还将小包的致幻剂置入密封的容器中。只要七天,货就会从中国送到澳大利亚“你家门口”。致幻剂供应商甚至保证,就算致幻剂真的被澳大利亚海关查封了,他们可以赔偿买方50%的损失。澳方的回应也揭示了目前体制的相应漏洞。澳大利亚司法部长宣布禁止进口所有合成药品,但合成药品往往伪装成浴盐或其他相似产品入境,缉毒犬也确实很难嗅出合成药品的存在。
澳大利亚并不是当下电子商务时代唯一的毒品“包邮”目的地。面对日新月异的合成毒品,各国的计划都没有变化快。在被鉴定为毒品和列为非法之前,新型合成毒品早已借助国际运输网络销往各个地方,成了年轻人聚会上的“新玩法”。合成致幻剂变化太快导致打击困难,法律改变的速度远没有化学合成的速度快。出现一种致幻剂,管制之后,生产商就会改变其化学结构规避法律风险。导致布里奇儿子死亡的就是这样一种新型毒品。
这种名为25i-NBOMe的致幻剂,在中国俗称“开心纸”,可以随意买到。但该毒品并没有列入中国国家食药监总局的易制毒化学品名录中,原因在于,任何新型化学物只有在人体试验发现有害后,政府才会研究决定列入管制目录。
知识传播迅速、材料易得和法律滞后,有些暂未被禁的新型毒品动辄打着“新药”名义被出售。这种做法都是在打法律时间差。在中国,“开心纸”就打着“研究用药”的旗号在卖。显然,这是毒品管理的迟滞延后,而这又是个世界性难题,新型毒品与毒品管理和司法打击使用毒品之间,常常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毒品的认定以及对贩卖使用毒品的定罪定刑方面也是难题多多。
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药理学者亨得森提出了一个概念:Designer drugs,指的是那些合成的或在实验室内可制成的,但又是被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管制的药物的类似物,后称为设计药物或毒品类似物,也被称为新型毒品,包括中枢兴奋类、致幻剂、兼具兴奋和致幻物质(摇头丸)和中枢抑制类物质。即便是FDA,也难以对层出不穷的新型毒品进行监管。
由于不少国家法律都强调“法不禁止即许可”,对新型毒品管理难度也在加大。像近几年来美国流行的新型毒品“浴盐”,是种卡西酮类衍生物,早在1969年就被人工合成,但到了2004年,它对人的神经造成的严重伤害才引起重视,之前迈阿密男子尤金袭击65岁流浪汉并啃食其脸部,就是因服用此物。由于“浴盐”危害日益严重,最先是美国禁毒署(DEA)出面加以禁止,于2011年7月发布对此类物质为期一年的临时禁制令,尔后FDA才将其列入新型毒品名单。
布里奇目前已经回到澳大利亚,但他仍没放弃对致幻剂售卖的调查。他认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为这些药物不仅贩卖到澳大利亚,也贩卖到世界各地”。布里奇点明了“互联网+”和校园毒品问题复合之后的严重性。全球化时代下的校园毒品网络早已超越国界,使得青少年获取毒品更便利,校园毒品问题也因为便捷的货源而发展到令人咂舌的程度。普利斯顿·布里奇的死亡,从因果链条上说,中国供货商只是在最远的一端。给他“开心纸”的同学,随意组织毒品派对的校园文化都是罪魁祸首之一。

2012年,俄亥俄州沃伦县警方逮捕了一名17岁的贩毒团伙头目,此人被指控操纵其手下在两所中学向学生兜售高纯度大麻。每月可获利2万美元。2010年时,人们就在当地一所中学内发现有人贩卖高纯度大麻,价格为每克13至14美元,而该区域早先贩卖的都是些低纯度大麻。警方立即派出卧底探员扮成买家,假意购买大麻,从而顺藤摸瓜并最终捣毁了这一校园贩毒团伙。
“他居然像企业家一样,掌控着这个颇为复杂的团伙。”反毒品行动小组负责人约翰·伯克说,“而且嫌疑人平时看上去就是个循规蹈矩的学生,在学校里既不是运动明星,也绝非调皮捣蛋的小无赖。他此前没有表现出任何能引起警方怀疑的地方。”警方表示,这名17岁的“毒枭”指使手下在三个地方种植大麻,每隔几周便能收获一次。而且他们种植的大麻在品质上属于最好的,可以提炼出高纯度大麻,平均一株一次的产量就可卖到5200美元。警方还发现,这伙毒贩将客户锁定在校园里。他们认为,在过去数年中,这名少年毒贩手下有6名在校或已毕业的学生为其工作,这些人专门向当地两所中学的学生出售毒品。“此人一再严令手下不得在校园内进行毒品交易,因为如果在那里被当场抓获的话,面临的惩罚会比在校外更加严重。”当地检察官戴维·福恩谢尔表示
17岁的贩毒团伙头目不是孤例子。近些年来,美国吸毒问题开始呈现低龄化倾向,校园毒品问题变得日趋严重起来。美国警方2008年5月在加利福尼亚州一所大学的数个学生联谊会内缴获了大量毒品,另起获数把枪支和至少6万美元现金;自加州警方2007年发起代号为“突然行动”的缉毒活动以来,涉案学生人数已累计达75名。2014年,费城抓住了两个大麻毒贩,一个25岁,一个18岁,都是费城郊外一个非常昂贵的私立高中毕业的白人学生。他们贩毒的对象就是郊区中高阶层的富裕白人学生,原因是他们自己经历了“找不到大麻的日子,想要为高中生办一点实事”。这话虽说听起来很滑稽,但他们确实是做了“实事”。他们建立了一整个系统,保证周边所有私立学校都有接头,而且给他们下面的学生贩子下指令,一周必须要卖出多少。
不夸张地说,美国大多数大学和高中都有自己的毒品经销网络。一个或者几个“学生毒贩”组织起自己的一帮人马,从网上或者其他人手里获得货源,然后在校园里分销。一个学期下来能获利不菲,而且还能形成自己的熟客系统。学生之间,对这类“学生毒贩”也是心照不宣,因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用到他们。
学生消费毒品大多在派对上,而学生之间的买卖大多发生在自习课。因此,自习课时,美国老师被训练和要求确定每位学生的行踪,还必须在30秒内做到观、听、闻。观学生的神情,听他们的声音,闻他们的口气,目的就是分辨学生是否有喝酒、抽烟等反常行为,一旦学生语无伦次或口齿不清,老师就会多问几个问题,多聊几句话,他们就会露馅。
十年前,一款和阿德林非常接近的药物在美国校园风靡起来,成了考试周的必备品——当然是除了咖啡、红牛和扎大腿的赶锥以外的必备品。在几个校园的调查显示,差不多有20%的大学学生习惯性使用阿德林来长时间学习或者考试。美国缉毒署发现从1992年到2003年,把处方药当毒品的年轻人数量翻了三倍,远远超过在美国其他人群中的增长量。毋庸置疑,这和在体育赛事中使用兴奋剂一样。
不过美国学生并不感觉服用阿德林是一个大不了的事情,甚至有人直说:服用阿德林其实就是一种很酷的,解决你学业问题的方法。这就回到了美国大学生活的真谛:“社交——睡眠——学业”形成了一个三角的三个顶点,任何凡人都只能选择其中两个顶点,放弃另外一个。而不愿意放弃社交和学业的酷孩子们,只能放弃睡眠,用各种乱七八糟的药物在没有睡眠的情况下维持社交和学业。于是,滥用药品的校园文化使得各种药片之间的界限在孩子们心中模糊起来,瘾品和毒品之间的切换对于这帮学生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在美国竞争极为激烈的一些大学里,含有安非他命的药物已经成了好成绩的必备品。不过,它们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毒品——毕竟,学生可以在美国大学的诊所里,用低廉的价格买到它们——它们仅仅是治疗多动症(ADHD),增强大脑专注力的处方药。
有些专家表示,这种对于药物的开放态度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帮助了一些有多动症的孩子获得学业上的成功——起码,他们可以不受歧视地使用这些药物,并且过上和一般孩子一样的生活。比如,一位在马里兰州立大学的校园医生表示,他经常能看见有些多动症的孩子通过服用这些药物,大大改善了生活,而他也认为这是好的。但是这位驻校医生表示,他几乎不能分辨那些假装自己有ADHD多动症的学生,和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而当阿德林这类药物逐渐失效或者不过瘾时,孩子们很快就会转向大麻或者其他毒品,因为嗑药在校园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和文化。学生们互相交换和交流各种药品和毒品的信息,完全“干净”的孩子反而是异类。另外,嗑药逐渐成了“酷”本身。学生们基本都会尝试大麻,而大麻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很多研究表示它会使得未成年人的智商明显下降,并且让他们上瘾。尤其是到了大学里,家长和学校都放宽了对大麻的限制,吸大麻也没有在高中时那种叛逆和酷的标签,更多是一种对于大学文化的随波逐流。
在当今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大多数人把所谓的“软”毒品和“硬”毒品明确地区分开,前者虽然非法,却受到某些人的容忍,而后者同样非法,却被认为是极其危险的。最有名的软毒品是大麻,不过,其他属于软毒品的药物诸如摇头丸和K粉,常被用在狂欢派对上,它们由此被称作“派对毒品”。在酒精毒品派对已经成为校园文化的今天,很多青年恣意使用“派对毒品”让自己嗨起来。这样的派对也是社交的重要部分。在这样的文化下,16岁的普利斯顿·布里奇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因此失去生命的孩子。痛失爱子的布里奇也深知这点,他创建了一个组织,名为Sideeffect(副作用),专门教育澳大利亚的年轻人,让他们知晓合成药品的危害,同时,也在征集药品走私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