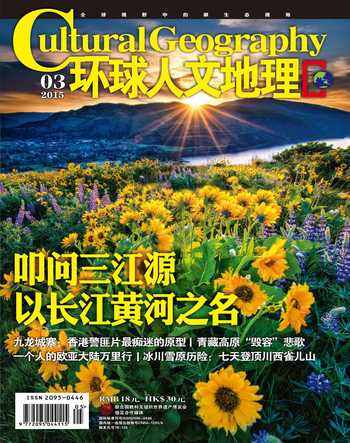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的骗局
2015-09-10于坚
于坚
1954年生。1970年开始写作。著有诗集、散文集20余种,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现为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正是一个个王元箓,前仆后继,使敦煌香火不断。正是王元箓式的献身,保管着古敦煌……斯坦因知道,王元箓坚持的世界观固若金汤,无法摧毁,只能利用。斯坦因的“取经”让这些通灵的经文从神器变成博物文件,作为文明标本死去……无数匿名于沙漠的工匠艺人创造了敦煌。他们像恒河沙数一样,风将他们吹去,他们又从别处回来。
当宗教式微,敦煌这个千年前就完成了的伟大高峰才水落石出。
“历时千年,包含魏、隋、唐、五代、宋、元凡六个大的时期,内容除大乘佛教的传说外,山水台阁、人物车马、花鸟图案、塑像之类,无一不备,真是天造地设唯一无二的艺术博物馆。”(向达)
但是,这个伟大的博物馆并非起于一个深谋远虑的宏伟计划,道法自然,这场在沙漠深处如喜马拉雅般崛起的中国艺术活动一直自生自灭。谁有能力供养匠人,谁就可以前来开凿洞窟。这一代人的窟倒塌了,另一代人的窟再次开始。最后,只有那些最坚固、最美丽的窟能穿越时间。穿越时间就是在时间中匿名,匿名于万物之中。道法自然,就要顺应时间。在唐的辉煌之后,敦煌一日日走向匿名。匠人们创造的敦煌道法自然又超越自然,超越自然又“复得返自然”。敦煌不是虚名,而是存在。存在就是能够成为自己,秋天成为秋天,河流成为河流,敦煌成为敦煌,然后又回到万物,周而复始。
1907年春天的浩劫
1907年3月12日,当那个用几匹骆驼驮着盛着饮用水的马口铁水箱、测量仪器、照相机等辎重,在沙漠中疲于奔命的英国人斯坦因来到敦煌的时候,“看守”它的是一个名叫王元箓的道士。在斯坦因看来,这位“胆小怕事、还不时流露出一种令人讨厌的狡猾的表情”的“阿Q式保管员”与伟大的敦煌博物馆极不相称,一只蚂蚁看守着一头大象。但是,王元箓确实在保管敦煌,他被当地人叫做“王阿菩”。王元箓式的保管在中国已经持续了数千年,他不过是依据传统,模仿前辈,也在敦煌主持了一个窟的塑建。正是一个又一个的王元箓,前仆后继,使敦煌香火不断。正是王元箓式的献身,保管着古敦煌。敦煌从来不是博物馆,它是不朽的神龛啊!
斯坦因很看不上王元箓修建的窟,就艺术价值来说,它完全不能与过去时代的窟相提并论。王道士那个窟里的塑像我也看了,呆板僵硬,因为过于诚惶诚恐。如果王元箓是美术系大学生,他绝不敢在敦煌面前轻举妄动。但是,王元箓是一个信徒。对于信徒来说,为神造像只在于虔诚的程度。不存在好坏,“不好”的神像谁敢造?谁又造过啊!只有现代人能分辨神像的好坏,在古典时代,艺术的是非不在美学上,只在于内心看不见的灵犀是否天真、诚实。敦煌的诞生和持续首先是虔诚,狂热的宗教热情导致了伟大的艺术,敦煌并不是伦勃朗先生的客户订单,匠人们绝不会左眼瞟着颜料,右眼瞟着卡塞尔双年展策划人,亵渎神的时代还很遥远。落日下,敦煌像沙漠一样灿烂,似乎正坦然迎接沙漠的吞噬。匠人们在匿名中创造着伟大的作品,这些作品从来没有观众,没有媒体,只有信徒。
直到西方人到来,敦煌与世界的关系才改变了。敦煌不再是神龛、神器、 神的匿名寓所,而是博物馆的价值连城之物。斯坦因绝不会对敦煌诚惶诚恐、顶礼膜拜,但他也欣喜若狂,对于他来说,敦煌是一只就要不幸被流沙吞噬的大金柜。
斯坦因设下的骗局
如果不是斯坦因,世界永远不会知道中国道士王元箓。
斯坦因名垂青史,被西方视为伟大人物“同时代人当中一位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人物”(欧文·拉铁摩尔),他看见的敦煌是大英博物馆未来的一部分。
史家对王元箓颇有微词,他被暗示成一个贪图小便宜而使伟大文物流失的罪人。敦煌道士王元箓完全没有博物馆的概念。他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虔诚的信徒。王元箓不知道博物馆,迎神容易送神难,敦煌属于神,谁会动它?谁又敢动它?往昔时代的灭佛,灭的只是神的在场,谁能灭神?神灵像万物一样自生自灭。自生自灭,也是神在世或者隐匿的方式。王元箓其实是一个匿名者,像千千万万的善男信女一样,他仅仅是在为自己的一生追求一个善果,为此他清贫而虔诚。斯坦因发现,用金钱或者考古学、博物馆来说服王元箓是无效的。史家将这一点说成是王元箓的无知愚昧,而在我看来,这是世界观的不同。伟人斯坦因无法改变小人物王元箓的世界观,于是他玩小聪明,导演了一出骗局,他说服王元箓将敦煌手卷卖给他的理由不是一个博物馆理由,而是一个良心、道德感和宗教虔诚上的理由。
斯坦因知道,王元箓坚持的世界观固若金汤,无法摧毁,只能利用。“他想,如果他对王元箓提到大多数中国人热爱的护法圣徒玄奘的名字,也许会触动王的感情。”“果然,经他一提,道士的眼睛就立即放光了。”其实斯坦因完全无视王元箓的世界观,还视这种世界观为愚昧、落后。他诱使王元箓相信自己就是一个当代的西方玄奘,负有让敦煌手卷重归印度的使命。斯坦因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告诉王元箓他是如何地热爱玄奘,“追随他的足迹,跋涉万里,越过杳无人迹的高山和荒漠……经过千辛万苦才到达玄奘去过的寺院。”是的,探险家斯坦因吃了不少苦头,但他没有告诉王道士的是,他的“取经”将让这些通灵的经文在博物馆中从神器变成博物文件,作为文明标本死去。事实上,斯坦因骗取的敦煌经卷后来在大英博物馆里的命运正是尘封,而玄奘取经却是要使这些经卷在大地上传播,在人间活起来。
超越宗教的圣敦煌
断碣赋碑,都付予苍烟落照。无数自以为是的疯狂造像以及对它们的物化都已经被时间之沙吞没,万有归一,都是恒河沙数。印度犍陀罗的佛龛,如今只有些残片,佛教后来在印度不传,宗教式微了,附着于它的一切也烟消云散。尽管从前的激情也许超过敦煌,但在印度,没有留下“敦煌”这种东西。莫高窟独立于瀚海。
敦煌起源于宗教的激情,如果只是教条主义,那么早期匠人的顶礼膜拜已经完美。但是,敦煌的创造并没有到亦步亦趋为止。与其说敦煌那些匿名的作者是一批艺术家、工匠,不如说他们是文人。这些伟大的文人创造了“敦煌”这种东西,曹衣出水,敦煌超越了它的宗教起源,超越了它的实用性。
敦煌乃是最后的、终极的。敦煌,文教之圣地也。那些佛教徒,那些匿名于狂沙的伟大艺人创造了超越宗教的东西——圣敦煌。
人们穿越沙漠来到敦煌,顶礼膜拜的是圣泥塑、圣壁画、圣铁线描、圣兰叶描、圣中锋、圣钴蓝、圣土红、圣朱砂、圣赭石、圣铁红、圣雄黄、圣湖绿、圣石青、圣石绿、圣铁黑、圣泥金、圣砖、圣竹简、圣书、圣吴带当风、圣曹衣出水、圣第45窟、圣第154窟、圣第99窟……
圣敦煌。
无数匿名于沙漠的工匠艺人创造了敦煌。他们像恒河沙数一样,环绕着自己的作品,风将他们吹去,他们又从别处回来。
入夜,敦煌的天空满天星子,一颗颗旋转着,就像被解放的沙子。下面,黑暗里,莫高窟在黑暗里,就像一个沙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