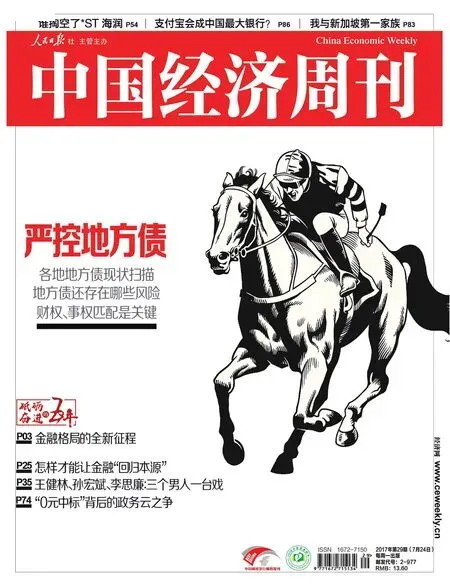对话陈九霖:金融衍生品交易需要监管,但不能因噎废食
2015-09-10郭芳
郭芳
“公司为了生存,只好借助进入成本比较低的石油衍生品赚钱”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再回看当年的中国航油石油期货交易事件,你有哪些反思?
陈九霖:对于当年的中国航油期货亏损事件,我从未讳疾忌医,文过饰非。我一直认为我犯有严重过失:用错了人,听信了专业机构的建议,没有及早斩仓。
《中国经济周刊》:当年国资委对央企的金融衍生品投机交易是明令禁止的,中国航油当时开展石油期货贸易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陈九霖:中国航油(新加坡)开展石油期货贸易始于1998年,即始于2004年中国航油(新加坡)石油期货亏损事件发生前的6年。当时,主要是套期保值,也有投机获利的操作。那时操作石油期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生存的需要。经国家商务部(原对外经济贸易部)等批准,中国航油(新加坡)于1997年恢复运营时的实际运营起始资金不到150万人民币。而购买一船航油的价款就达600万~1000万美元,一船航油的运费也需要30多万美元。那时,国家严格监管资金进出,也没有提出“走出去”战略,资金出境非常困难。在没有资金周转的情况下,公司为了生存,只好借助进入成本比较低的石油衍生品赚钱。
“有的上级单位甚至要求中国航油(新加坡)做出经验来,以便推广”
《中国经济周刊》:当时相关监管部门或主管单位对此是否知情?
陈九霖:由于期货业务性质本身的要求,中国航油(新加坡)开展石油期货贸易自一开始就履行了必要的审批手续。公司董事会签署了开展石油期货和衍生品交易的决议,期货交易员的遴选、期货交易账户的开立、ISDA Master Agreement(国际互换与衍生品组织主协议)等,都得到了董事会的批准。做过这方面业务的人都知道,没有董事会的授权,期货业务是开展不起来的。
自1999年起,在母公司的主动引荐和撮合下,中国航油(新加坡)开始先后为国航、东航、南航等公司操作石油期货,后来导致中国航油(新加坡)损失5.5亿美元的期权交易,就始于中国航油(新加坡)为国航操作的石油期权交易。
当时,应国航要求,中国航油(新加坡)为其开展期权交易,其对家为英国石油,中国航油(新加坡)居间赚取差价。基于石油期权交易赚取的巨额利润和为国航进行相关操作的经验,中国航油(新加坡)期货交易员提议公司自己开展同样产品的业务。中国航油(新加坡)进行投机性石油期货业务,还在中国航油(新加坡)上市时的招股说明书中做过明确说明,并毫不含糊地列入公司重大风险提示:“公司所开展的投机性石油期货、期权和其他石油衍生品业务,可能为公司带来巨额利润,也可能因为交易员操作不当而招致重大损失。”
2003年中国航油(新加坡)年报专门列表披露了公司石油期权业务,年报是经过董事会和母公司提前审批后才对外公告的。在发生亏损事件的2004年,上级单位曾经询问过中国航油(新加坡)开展石油期货业务的情况,由多家单位组成的检查组巡视过海外中资企业开展石油期货业务的情况。2004年8月,他们巡视中国航油(新加坡)时,中国航油(新加坡)主动报告了期货、期权业务情况,检查组也查过中国航油(新加坡)的期货盘位,其后并未劝阻中国航油(新加坡)停止期货。有的上级单位甚至要求中国航油(新加坡)做出经验来,以便推广。
“市场做得大,交易管得好,才是正确的监管之道”
《中国经济周刊》:在中国航油(新加坡)之后,不少央企也因金融衍生品交易造成了巨额亏损,盈利的很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九霖:我国企业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亏多赚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人才缺乏、客场作战、语言障碍、系统不全等,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毕竟,就国家层面讲,石油期货市场是发挥话语权、影响石油价格的重要场所之一;就企业而言,期货市场是把脉市场、捕捉商机、套期保值,甚至是可以获利的地方。对于石油期货业务的监管与风险监控,关键是要做到有规则可行、有实时监管机制、有危机处理手段。
《中国经济周刊》:在你看来,相关监管如何完善?
陈九霖:其实,有关机构早已注意到对石油衍生品合约的监管问题,但是,其措施要么不当,要么不到位。如何恰到好处地监管我国企业或机构从事石油衍生品交易的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政府机构和监管当局。
监管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上。对于参与衍生品交易的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应从公司管理制度、财务制度、业绩考核制度和市场应对措施等方面入手,完善其投资管理和风险控制体系。
同时,还要不断地通过明确监管机构、制定市场准入标准和强化场外石油衍生品合约的财务报表内信息披露制度等手段,逐步摈弃现行的行政化监管手段,形成向市场化、法制化结合的道路。
具体措施包括:明确石油衍生品合约监管的主体监管机构;对石油衍生品合约的主体资格实行市场准入制度;充分发挥石油期货的自律监管,完善三级监管体系等。
长期以来,我们以国家行政调控的方式来承担石油价格风险的代价过于沉重,最终我们必须走市场化、法制化结合的道路。从现实看,我们应采取“管”“放”结合的策略,即当前需要监管好我们的企业与机构“走出去”进行石油衍生品业务交易,但同时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石油金融市场。市场做得大,交易管得好,才是正确的监管之道。否则,管到没有交易又有何益呢?
“我希望在实业或投资领域,做出一个能源帝国来”
《中国经济周刊》:出来之后,你先是接受了组织聘请你担任葛洲坝国际工程公司的副总经理,又重回体制,当时外界都很意外,舆论上也曾轰动一时,当时你选择重回体制是基于什么考虑?
陈九霖:首先,我觉得这是组织上对我的关心,我应该领情。同时,也体现了组织上对我的一种认可,至少是对我过去所做的努力的认可。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这也是组织上对新加坡判决的一种姿态。如果说组织上完全认同新加坡的判决,如果说中国航油事件的责任完全在我本人,如果说我像新加坡当局所描述的那样“恶意扰乱新加坡金融秩序”,这种任命是不会有的。
《中国经济周刊》:在葛洲坝任职期间,你曾针对石油领域发表过不少文章,你在这个领域还有“野心”?
陈九霖:坦率地讲,在能源领域我还是有不了情,我还是希望在能源领域里发挥我的一技之长。我把过去多年的积淀和思考形成文字供大家参考,哪怕写得不对也是一个观点和角度。有些文章还是产生了不错的影响,有些甚至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要批示。我也在亲力亲为,希望在实业或投资领域,做出一个能源帝国来。我相信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
《中国经济周刊》:你有没有向组织申请过重回石油领域?
陈九霖:在我出狱之后,国资委给我安排工作的时候,我提出过想要回到中国航油集团去,担任哪怕一个处长、一个助理,或者是什么职位不要也行。但当时中国航油集团的老总可能有些担心,没敢接受我,我也可以理解,所以,我也没有再回去。
“现在这个平台可能更能发挥我的作用”
《中国经济周刊》:在葛洲坝国际待了3年之后为什么又选择了离开?
陈九霖:我原来有两种思考:一种是在体制内继续发展下去,如果那里有一个适合我的舞台,我还有10年左右的时间能做出一些事情来;另一种是走民营体制的路子自己当老板,我觉得也未尝不可。最后,我权衡来权衡去,觉得现在这个平台(约瑟投资)可能更能发挥我的作用。
《中国经济周刊》:在体制里这么多年,再从体制出来成立约瑟投资公司自己当投资人,适应吗?
陈九霖:刚开始也有一些不适应,所以,我也一直在考虑我和其他投资人的差别。与他们比较,我有三方面的弱势但同时也是优势:第一,我在民营企业工作的时间很短,刚刚起步,刚开始自然有些不适应,但我在中央企业工作的时间很长, 26年都在中央企业,这也是我的优势;第二,我在国外工作了11年,对国内情况的了解可能比对国外情况的了解要少一点,这是我的一个弱势,但未来我在国内工作的时间也会很长,两者结合又是我的优势;第三,我的起步比较晚,其他投资人起步比我早,甚至他们没有到国有企业工作过,直接就在民营企业开始创业,但如果我能做好规划设计,能少走弯路,也是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