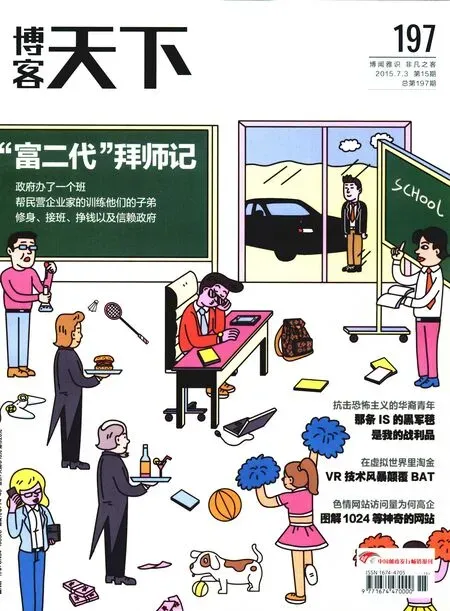这里,关押着全球最臭名昭著的罪犯
2015-09-08MarkBinelli时青靖
文 Mark Binelli 译 时青靖
这里,关押着全球最臭名昭著的罪犯
文 Mark Binelli 译 时青靖
多年来,美国唯一一座联邦超级设施的内部始终是个谜,基本不为人知。但是,一宗里程碑式的诉讼案终于将这个残酷世界暴露在公众面前
罗德尼·琼斯告诉我,在监狱里每个人都有一个绰号。琼斯也在里面混时间,早年开始,他就表现出精神病的迹象;12岁时第一次试图自杀,喝了一整瓶“高乐氏”清洁剂;后来沉迷于致幻药“天使粉”和可卡因药丸“快客”,转而通过抢劫来维持自己的癖好。
琼斯已经出狱3年,至少堪称成年后的创纪录佳绩,但他说起话来仍然有点云里雾里,因为他惊奇地意识到过去的老街坊都已变得高雅起来。
对琼斯来说,过渡到自由生活并非易事,他尽力坚持了下来。他说,因为已经决定不再回到度过最后8年刑期的地方—美国最高监管感化院。它位于科罗拉多州佛罗伦萨落基山脚下的一片荒漠里,在口语中简称ADX,是全美安全措施最严密的监狱。
这处建筑的设计目的是防止越狱,俗称“落基山的恶魔岛”,专门监禁最穷凶极恶、罪无可恕的囚犯,用美国联邦监狱局前局长诺尔曼·卡尔森的话来说,他们是“一小撮绝对不把人命放在眼里的家伙”。邮寄炸弹主角泰德·卡钦斯基和亚特兰大奥运会爆炸案主犯埃里克·鲁道夫把ADX称为“家”。9·11事件嫌疑人卡里亚斯·穆萨维也被关押在这里,连同1993年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的策划者拉姆齐·尤塞夫、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主犯特里·尼克尔斯、内衣爆炸案制造者奥马尔·法鲁克·阿布杜穆塔拉布、前黑帮大佬、博纳诺犯罪家族老大文森特·巴西安诺以及迈克尔·斯旺戈正在这里服刑。迈克尔·斯旺戈是一位制造过连环杀人案的医生,曾经毒死60名病人,被判处连续3个终身监禁;芝加哥最大黑帮GD(Gangster Disciples)的主要人物拉里·胡佛被判6个终身监禁,苏联间谍、FBI叛国特工罗伯特·汉森正在苦熬15个终身监禁刑期。
与上述臭名昭著的囚犯一样,被视为具有严重行为风险或潜逃风险的犯人最终也被关进ADX,例如琼斯这种人,由于一年内在路易斯安那州某中级戒备的监狱里受到3次袭击指控(都是跟其他囚犯打斗),2003年他被转入ADX,与卡钦斯基同在一个监狱分区。
在ADX,犯人每天约有23个小时处于禁闭状态,琼斯从未感到如此与世隔绝。在他的监区里,其他犯人连着几个钟头尖叫、撞门。琼斯说,精神病医生不准他服用治疗情感障碍的处方药,告诉他说,“在这儿我们不开让人感觉良好的药。”琼斯经历了剧烈的情绪波动。为了应对,他在牢房里锻炼身体,直到累得不想再动为止,有时会划伤自己。对此,警卫用四根老式束缚带把他的胳膊和腿绑在床上,这一过程叫做四点固定法。
2009年的一天,琼斯在院子里放风时发现了迈克尔·巴科特,一位来自家乡的朋友。见到熟悉的脸孔令人开心,但也麻烦。巴科特是文盲,智商只有61,还患有严重的妄想症。因为在得克萨斯某监狱的一宗谋杀案中
关押着全球最臭名昭著罪犯的ADX,是美国安全措施最严密的监狱他是负责望风的,所以被送进ADX,而且过得不太好。他多次要求转到别的监狱或接受心理治疗,均被拒绝。他确信监狱局想毒死他,拒绝进食和吃药。“除非你眼瞎或是疯了才注意不到这个有毛病的人,”琼斯摇着头说,“他几乎无法在正常环境中生活,理解水平几乎为零。”
巴科特以前的精神病检查都记录在案,于是琼斯去了监狱里的法律图书馆(一个装有电脑的房间),查到了一家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组织的地址,之前他听说过该组织,它的名称是“哥伦比亚特区囚犯项目”(D.C. Prisoners’Project)。因为巴科特不会写字,琼斯代他执笔,发出一份咨询信件。“我认为在进到ADX之前应该有一场听证会,”琼斯以巴科特的口吻写道,“他们没有为我听证。”他继续说,“我需要一些帮助,因为我掌握事实!请帮帮我。”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封信拉开了历史上针对美国联邦监狱局的最大一起诉讼案的序幕。
身为哥伦比亚特区囚犯项目的主管,德波拉·高登每年要处理大约2000件申请,但在2009年10月,巴科特的信件却引起了她的注意。“我想我可能错过了一些东西,因为在我看来,监狱管理局竟然可以这样公然违法、违宪,实在不可思议。”她说。高登指的是按照监狱管理局规定,禁止将“明显患有重大精神疾病”的囚犯安置在ADX之类的监狱。
像哥伦比亚特区囚犯项目这种组织倾向于将其改革努力锁定在州立监狱—用高登的话说,是联邦政府拥有“取之不尽的资源”,她的组织从未考虑过接受如此重大的诉讼,因为与联邦政府对簿公堂、向监狱管理局发起挑战是难以获胜的,“不符合任何人的战略目标,”高登说,但巴科特的诉状事实清楚,令她犹豫不决。“我不确定我们是否有机会。但法庭似乎必须看看这个案子。”

ADX坐落在科罗拉多州佛罗伦萨的一片荒漠里,俗称“洛基山下的恶魔岛”
ADX从1994年建成至今,不仅是唯一一座联邦超级监狱,也是美国刑法系统登峰造极的表现,在这里,抽象的改邪归正梦想完全被控制机制所取代。纵观美国历史,从19世纪的一群被铁链锁住、默默做着苦工的囚犯,到恶魔岛的物理隔离,关于如何惩治“恶人中的恶人”,一直存在很多不同观点。在18世纪末的美国,单独监禁取代体罚成为通用的惩治方式。这一实践最初是1787年兴起的,倡导者是一群自称“费城减轻公共监狱中的痛苦协会”的改革者。在本杰明·富兰克林主持的沙龙里,人们阅读的一本小册子呼吁建立“悔改小屋”,用孤独抚慰罪犯的心灵—该群体认为,相对于“绞刑、示众、杖刑、鞭刑”等不人道手段,这是一种开明的选择。费城东方州立监狱1829年开始运营,其中的囚犯全被隔离在一间间独立囚室中,里面有天窗、马桶,囚犯可以走进私用户外运动场,进行各种交易—取用饭菜,阅读圣经,另外一些州采取所谓的宾夕法尼亚系统(Pennsylvania System),同样对囚犯进行分离监禁,但很快都放弃了。1890年最高法院裁定,严禁对科罗拉多死刑犯使用隔离刑罚,同时指出,“即使仅仅经历过短暂的禁闭期,相当数量的囚犯仍会陷入一种半痴呆状态,几乎无法被唤醒,另一些人则变得极其疯狂,还有人甚至自杀,而那些在考验中表现较好的人通常未被成功改造。”
这种理念很快变得不合时宜,并且从1930年代开始,联邦系统中最棘手案件不断冒出,一些恶性刑事案件的主犯均被安置在恶魔岛上—一处由军事设施改建的监狱,直到1963年因维护费用太过昂贵,这座岛上监狱最终被封闭。到10年监禁期临近结束之际,许多犯人已经被转移到伊利诺伊州玛丽恩联邦监狱里的新型“控制单元”,被单独监禁。1983年,在同一天,两名狱警分别遭到暗杀,杀手是雅利安兄弟会(Aryan Brotherhood)的成员,此后,玛丽恩监狱被改建为第一座现代化全封闭设施,整个建筑完全与世隔离。
1989年初在加利福尼亚鹈鹕湾,各州仿效玛丽恩模式,开始建设自己的封闭监狱。隔离措施的重新使用与大规模监禁时代及州立精神卫生设施的广泛关闭不谋而合。超级监狱成为控制人员日益拥挤、心理日益动荡的监狱人口的最可取方法。这种不幸巧合所产生的后果是美国形成了一个越来越严
精神病医生不准他服用治疗情感障碍的处方药,告诉他说,“在这儿我们不开让人感觉良好的药。”酷、越来越功利的监狱网络,其设计宗旨是把绝大多数州和联邦囚犯监禁起来,所使用的方法令不少美国人大为震惊。根据大赦国际组织2014年的一份报告,目前全美超过40个州拥有超级监狱,每天都有8万名美国囚犯正在关禁闭。
诺尔曼·卡尔森在玛丽恩攻击案时期担任监狱管理局主任,负责主持联邦超级监狱的建设,后者最终将取代玛丽恩监狱。佛罗伦萨是科罗拉多州一座衰落的矿业城镇,居民们努力游说,希望政府将耗资6000万美元的监狱建在市区,最终他们向监狱管理局捐赠了600英亩土地。
ADX有8个单元,可容纳500名囚犯。犯人待在面积为12×7英尺(1英尺约30厘米)的牢房里,四周是厚厚的混凝土墙壁和双层滑动金属门(外门密封,所以囚犯看不到彼此)。一扇窗户,离地大约3英尺高,但只有4英寸(1英寸约2.5厘米)宽,除了一窥天空,别的东西基本都看不见。每间牢房里有一套水池-厕所用具、自动淋浴器,囚犯睡在水泥板上,上面铺一层薄薄的床垫。大多数牢房还有电视(带有内置收音机),囚犯可获得书籍和期刊,以及特定的工艺品制作材料。普通囚犯每周有最多10小时户外锻炼机会,可以走出牢房,独自走走,或到室内“体育馆”(那是一间没有窗的屋子,里面装有单杠,可做引体向上),还可以集体到院子里休闲一番(每个囚犯的活动仍局限在单独的笼子里)。所有饭菜都通过内门上的狭缝递进牢房,(囚犯与警卫、心理医生、牧师或阿訇的)任何面对面互动也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大赦国际的报告称,ADX囚犯“通常每天只能跟人说上几句话”。
罗伯特·胡德2002-2005年在ADX担任监狱长,他告诉我,第一次来到监区的时候,他被“非常严酷的环境镇住了”,不同于他曾就职或参观过的任何其他监狱,这里没有噪音,没有混乱,没有犯人在走廊上行走。当囚犯向他抱怨时,他会告诉他们,“这个地方不适合人类居住,”他回忆道,“一天23个小时待在一个房间里,只有一道狭长的窗口,你甚至看不到落基山脉—让我们直说吧:这种设计不是让人改过自新,而是为了终结、完蛋。”
胡德如此坦率,并不意味着为人残忍。ADX的建立显然是为了关押那些往往已被判处多个终身监禁的囚犯,因此,他们决不在乎杀死警卫或其他犯人。不过胡德说,在他任职期间,提出了与犯人发展尽可能亲密的一对一关系—他称塞尔瓦托·格拉瓦诺、绰号“公牛萨米”的黑手党大佬为“非常可爱的家伙,不管你信不信”,并且,出于对马拉松长跑的共同兴趣,与“邮寄炸弹的恐怖分子”(指泰德·卡钦斯基)私交不错—他的目的在于以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化犯人,使后者在狱中表现良好,日子更好过一些。但他也需要他们的理解,虽然身为监狱长,他没有权力改变他们的约束规则。在过去,胡德曾经把ADX形容为“净化版地狱”,令人难以忘怀。
5年前,针对联邦监狱局的大型诉讼案听起来不切实际。但在目前的情况下,ADX案似乎正处于风口浪尖,因为美国监狱对禁闭手段的过度使用已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审查。弥漫在禁闭隔间的空虚气氛“已经使一些囚犯产生了深层次的‘存在性不安’”。
高登认为,起诉监狱管理局仍然将是一场持久战,需要找到一位比她人脉更广的合作律师。于是,她找到了阿诺·波特(Arnold & Porter),这家业内知名的律师事务所擅长受理高调公益案件,他们在丹佛的合伙人艾德·阿罗对此案颇感兴趣,他的一位至亲曾在监狱里待过,其他亲属则患有精神疾病。
为了尝试了解案情,几乎每个星期他都驱车两小时到佛罗伦萨。多年来ADX的内部条件一直是个谜;大赦国际的报告指出,从2002年起,ADX官员拒绝了媒体的所有访问要求,也不许囚犯接受采访,除了在2007年接待过一次限制性游览项目。(监狱管理局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也不准访问网站。)阿罗以为能找到几个以某种方式躲过监查的犯人。“令我最为震惊的是问题的严重程度,”阿罗说,“ADX是整个国家监测最密切、囚犯评估最频繁的监狱。就问题的影响程度而言,我无法理解监狱管理局竟然对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置若罔闻。”阿罗想知道,美国最严厉的监狱如何变成了一座精神病院?为什么对其中的人员束手无策?
阿罗曾经采访过25名ADX犯人,2011年10月,他遇到了可以为此案代言的人。这位特殊的犯人名叫杰克·鲍威斯,52岁,在双方第一次会面时拒绝落座—多年独处一室,已经让他在其他人旁边坐立不安。不过,阿罗立即发现鲍威斯非同凡响:头脑清晰,言语利落,没有系统性暴力的历史。
“如果你看过杰克的犯罪历史,”阿罗说,“看到导致他被送入ADX、陷入这种不可思议的疯狂状态的种种稀奇古怪又令人不快的际遇时,你不可能相信眼下他所经历的一切与禁闭关押毫无关系。”那天离开监狱时,阿罗心想,如果要寻找一个令人信服的角色把这起诉讼案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没有比杰克更合适的人选了。
杰克·鲍威斯在纽约州诺维奇长大,父亲是越战老兵,动不动就打他。14岁时鲍威斯从家里跑了出来,几年后因盗窃罪被捕入狱。1982年他被释放,当时他21岁,结了婚,搬到密歇根州霍兰德市,在那里他创建了一家建筑公司和一家美容院。但在1980年代末企业破产了,他开始抢劫银行,根据1990年的判决,至少作案30次。他从不携带武器,总是把一张字条悄悄递给银行出纳。他认为是妻子(现在是前妻)告发了他。
他被判处40年刑期。在亚特兰大的美国监狱服刑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名叫爱德华多·王的犯人,是一个与中国有组织犯罪有牵连的海洛因走私犯。“不错的家伙,”鲍威斯在一份作证录像中说,“我的意思是,相对而言。”王和鲍威斯喜欢下棋。“但时间并不是很长,短短几个星期,”鲍威斯说,“在出事之前。”
一些高职院校受传统教育模式影响较深,不能正确定位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在对旅游专业学生进行教育教学过程中,仍然过于重视理论教学,而相对忽视实践教学。现阶段,很多高职院校旅游专业大都将目标定位于管理类人才的培养,导致学生对就业有过高期望,而不愿从基层岗位做起。但大部分旅游相关企业急需大量一线员工。这种培养目标定位不符合旅游业的实际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旅游专业毕业生的就业。
王成了雅利安兄弟会成员的目标,他们威胁说,如果不给钱就杀了他。鲍威斯警告王说情况很严重,但王犹豫不决。一天下午,一伙人跑到他们的楼层,对着王猛刺几刀,鲍威斯则被刀逼着,押到隔壁牢房。当他们跑开后,王跌进鲍威斯的臂弯,鲜血从脖子上喷涌而出。“帮帮我,”他说。鲍威斯竭尽全力总算把王背下几层楼,来到监狱医院,王死在那里。
超级监狱成为控制人员日益拥挤、心理日益动荡的监狱人口的最可取方法。这种不幸巧合所产生的后果是美国形成了一个越来越严酷的监狱网络

监狱内景。囚犯可以看电视
在谋杀案调查过程中,鲍威斯被转移到一间保护单元。不过,在他调换房间不久,一张雅利安兄弟会成员的脸就出现在他牢房的食物传递狭槽。“如果你供出我的孩子,”男人说,“我就砍掉你的头。”但鲍威斯在雪城有个十几岁的儿子,他想与之重新联系,因此,为了换取一个在他看来可能会减刑的机会,他同意为政府出面作证,他指证了4名雅利安兄弟会成员,其中3人被判终身监禁。
鲍威斯被监禁前没有精神病史,但在王被杀后,他开始显示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表现为担心遇袭、时常焦虑,梦见手持凶器的室友把自己逼进监狱的囚犯隔离区。到1999年,他还未收到减刑通知,越来越确信监狱管理局正在计划将他转移出保护区,于是他决定逃走。
他把一个假人放在床上,躲在放风院子里的炉子后面,利用自制抓钩爬到一座建筑旁边。在屋顶上,他跳过16英尺高的电网,然后把联邦快递的纸盒绑到胳膊和腿上,翻过第二道带刺铁丝网。一到外面,他就偷了一辆汽车,开往雪城看儿子。

9·11事件嫌疑人卡里亚斯·穆萨维也被关押在ADX
儿子不接他的电话,他尝试去看望同父异母的妹妹。(她不在家,但当他看到邻居费力地操控割草机,他便帮她割了草。)两天后警察将他缉捕归案。《雪城旗帜邮报》(The Syracuse Post-Standard)在当地监狱采访鲍威斯,问他是否会重操旧业。这篇文章像是一位绅士大盗的特写,读起来轻松愉快,颇具人文色彩,鲍威斯的肯定回答却在唱反调。“没了人生的正常感觉、情绪和感情,”鲍威斯说,“你还有什么?”
2001年10月,由于被认定存在越狱风险,鲍威斯被转到ADX—他曾指认的3名雅利安兄弟会成员全部都在这里服刑。鲍威斯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恶化了。他被贴上告密者的标签,更具破坏性的是被视为雅利安兄弟会的敌人,甚至连不属于该组织的囚犯都避免跟他搭话。鲍威斯说,警卫也对他另眼相待。他解释说,如果整个监狱里的人都跟一个囚犯作对,“这就像是一边倒。如果说他们在试图冷静对待其他人,但是临到你这儿,他们就不会冷静。”
2007年,一位名叫何塞·维加的囚犯被安排住进鲍威斯下方的牢房。维加曾在另一个监狱用刀片攻击副监狱长,之后被关进ADX,被诊断为抑郁症,因为有生病和搞破坏—把粪便和尿液泼在工作人员身上—警卫都不待见他,鲍威斯如是说,但他们两人开始通过排水管交谈(相邻牢房的囚犯可以沟通,具体方法是使用卫生纸卷把水从洗脸池下方的U形存水弯管里吹出来)。多年来第一次,鲍威斯认识了一位可称为朋友的人。他们会聊聊监狱、彼此的家庭、法律问题。维加已经失去了看电视的特权,所以鲍威斯将自己的耳机贴近水槽排水口,大声播放音乐,以便让他的朋友也能听到。

在ADX,囚犯每天约有23个小时处于禁闭状态,其甚至被称为“净化版地狱”
有个警卫时不时招惹维加,维加确信监狱工作人员在夜间潜入他的牢房袭击他。鲍威斯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沉重的牢房门被打开,鲍威斯不可能听不到。但他说,警卫确实扣住了维加的信件,还故意把后者的食物掉在地上。一位警卫告诉维加,他也可以自杀,因为事情不会有什么转机。“他们开始做掉他,”鲍威斯说,“很像你看到职业摔跤选手,那种组队角力,其中一人将对手抛给下一个队友、下一个、再下一个。”
2010年5月1日早上,维加被发现死在牢房里,他用床单把自己吊死了。维加死后,鲍威斯剃了头,开始用他所描述的“阿凡达条纹”装饰自己的身体—灵感来自詹姆斯·卡梅隆电影中蓝色外星人身上的条纹。他用刀片把皮肤划开一些小口,然后把复写纸屑抹在伤口上,鲍威斯身上布满了刺眼的长长纹身,沿着手臂、腿到脖子、头、眼睛下方,还有喉结周围,随处可见。2011年的一张照片显示出他在形象上的惊人变化:1990年进入联邦监狱系统的那个故作笑脸、头发蓬乱的年轻银行抢劫犯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看上去刚刚走出噩梦的人。
据高登说,历史上监狱方面有一种对付诉讼的传统,就是简单地把涉案犯人转移到另一个监狱,使案件不了了之。因为预期这种情况还会重演,高登和阿罗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原告队伍,人员之众使移送策略变得不再可行:最初的投诉来自6名囚犯,包括鲍威斯和谢尔比,还有11个后备人选,疾病、种族和背景各异。(法律团队也代表何塞·维加的家人提起诉讼,罪名是虐待致残和意外死亡。)
2013年,阿罗和监狱管理局的美国代表律师花了两天时间对鲍威斯进行质询,全程录像(后者在ADX的大部分经历由此为人所知)。视频中的鲍威斯身穿标准的囚服,坐在桌子后面,双手被铐住。有一次他告诉律师,已经记不清上次跟许多人待在一间屋子里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几年前。他思维缜密、小心翼翼,显然聪明睿智。听着他叙述一桩桩可怕的往事,你基本可以理解人们为什么断定他神志清醒。
一位新的联邦地方法官就职上任,对可能的和解加以监督。阿罗和高登向监狱管理局列出了27点需要解决的事项,包括诊断和治疗的具体要求,以及成立一个监督委员会,确保这些要求得到满足。(诉讼不包括任何财务和解项目。)经过近一年的谈判后,高登在今年1月告诉我,“我认为我们非常接近于达成和解。”阿罗虽然也越来越乐观,却在3月对我说,他还不能预测是否会有和解或审判。
不过,在和解谈判的同时,监狱管理局单方面变更了某些(虽然不是所有)要求,并开始在ADX实施。比如增加了新的精神卫生规划,额外聘请了几名心理学家,在亚特兰大新开设了一间分部,专门关押安全性很高的精神病犯人。根据之前的预测,诉讼中提及的一些囚犯已被移出ADX,包括鲍威斯,去年,他被送到了图森一间高度安全的监狱。
鲍威斯无法适应新设施的开放环境。阿罗认为监狱管理局是好意,但可悲的是,对于一个过去13年来大多独自一人孤独度日的犯人来说,新习惯难以养成。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囚犯牢房的门都不上锁,但鲍威斯很少冒险进入公共领域,心情糟糕透顶。在一次与工作人员的争吵中他打了对方,之后便被单独关押。在单人牢房里,为了尝试环锯术,他拿着一把用电池改造而成的钻头,想方设法在颅骨上方钻了一个孔。
戴维·谢尔比,曾经吃掉自己手指的一名ADX囚犯,也被转移到北卡罗来纳州巴特纳的一处安全设施。他有6英尺高,300磅,戴着监狱发的厚框眼镜,圆圆的脸刮得干干净净。(在ADX,他的胡须散乱,貌似蛮荒地带的幸存者。)去年秋天我去看他,在讲述从前一起暴力事件前,他停了下来,轻轻地说:“我希望,我没有让你感到不舒服,先生。我现在按时吃药,所以你是绝对安全的。”■
本文由《纽约时报》资讯与版权公司授权《博客天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