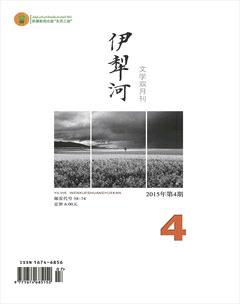21世纪中亚文学研究扫描
2015-08-31贺元秀
谈到中亚文学,首先不得不对中亚的地理概念做一个界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全部或部分属于中亚地区的国家共有七个,即:阿富汗、中国、印度、伊朗、蒙古人民共和国、巴基斯坦和苏联。就中国来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河西走廊、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地都属于中亚地区范围。中亚是一个纯地理名词。自古以来,中亚即各个不同的国家,其中一部分地区是中国的领土,其他地区也和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当前学术界为了论述的方便,更加普遍的认同狭义“小中亚”的界定,即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五国所占据的地域称为中亚。在这里,中亚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复杂的”文化概念。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位置,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当今比较流行的共识是世界文化可划分为四大体系:欧洲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和汉文化体系,犹如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所说:“世界历史悠久、地域辽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我认为:季羡林先生所说的世界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涵盖了中亚地区。所以中亚是处于世界四大文化体系相互碰撞、交流、影响、交融的地方。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中亚文学在自己的发展中免不了受到外来文学的影响,体现出多元性。21世纪以来,随着中亚各国的相继独立和盛产石油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第二),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中亚这片神奇而多彩的土地;而随之从事中亚文学研究的学者队伍也开始壮大,中国社科院、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新疆大学、兰州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国内高校都设有中亚研究所,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出版了不少学术著作,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可以预见:目前还是我国东方文学研究薄弱环节的中亚文学研究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中亚文学特征及其研究特点
谈起中亚历史文化,不少人会敬而远之。这是因为中亚历史文化非常丰富而复杂,正如有一位研究中亚历史的学者所说:研究中亚历史,好比一个人站在摩天大楼上往下看,只见大街上人来人往,一群一群的人聚集起来,忽又解体、散去、融合,往复循环,如一场杂乱无序的运动。
倘若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纵向考察,在中亚这个大舞台上出演一幕幕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影响深远的历史文化节目的主要部族有雅利安人、塞人、月氏人、乌孙人、汉人、粟特人、波斯人、希腊人、马其顿人、塔吉克人、鲜卑人、突厥人、突骑施人、葛逻禄人、契丹人、蒙古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俄罗斯人等等,其中欧罗巴人中的雅利安人本是中亚的原始居民,作为游牧部族,他们四处迁徙,曾在印度等地成为统治者,可是在中亚本土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大的长久的政权,所以中亚本土总是受到外来民族的控制。最早对中亚历史进行控制的是操伊朗语的东伊朗人。从波斯人建立的公元前阿契美尼德王朝(存在220年)征服中亚开始,经过公元前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后建立的亚历山大帝国(只存在18年)、希腊人建立的塞琉古王朝(只存在59年)和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只存在59年,希腊人建立的三个王朝共存在136年)到波斯人建立的安息王朝(存在472年)经过贵霜王朝、囐哒、西突厥汗国、阿拉伯帝国的倭马亚朝和阿拔斯朝,再到中亚当地民族和塔吉克人建立的塔赫尔王朝、萨法尔王朝、萨曼王朝和古尔王朝(四个王朝共存在260多年),从以上叙事中可以看出来从公元前550年—公元1215年波斯人先后控制中亚1700多年,直到今天东波斯人的后裔塔吉克族建立了中亚五国之一的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族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中国新疆也有分布。所以塔吉克族是中亚最古老的土著民族之一,显然波斯文化已经内化为中亚文化的血肉。从公元583年—公元1231年,突厥人在中亚先后建立西突厥汗国(公元583年—公元657年)、迦色尼王朝、喀喇汗王朝、塞尔柱克王朝、花剌子模王朝;成吉思汗西征后掀起的蒙古风暴催生了突厥语化伊斯兰化的察合台汗国、帖木儿王朝、哈萨克汗国、哈萨克三玉兹、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至此可以看出来,从中国北方西迁的突厥人及其后裔先后控制中亚将近1000年,深刻影响了中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以致中亚文化具有突厥语化的特征。阿拉伯帝国的倭马亚朝和阿拔斯朝对中亚虽然控制了180年左右,但它强行推广留下的伊斯兰教文化长久深刻影响了中亚文化乃至中国新疆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文化,使中亚文化带有伊斯兰教化的特点。两汉时期、隋唐时期、元代和清代由于不同程度的控制中亚,中国文化对中亚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18世纪—20世纪,由于沙俄和苏联控制中亚,俄苏文化对中亚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中亚五国独立以后开始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中亚文化表现出古老性、复杂性、多元性。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讲,中亚历史文化的古老性、复杂性、多元性决定了中亚文学的古老性、复杂性、多元性。纵观中亚文学研究史,我们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中亚文学的研究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中亚文学多元性的比较研究
由于中亚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位置,世界四大文化体系相互碰撞、交流、影响、交融的地方,从中亚文学中,我们不难看出波斯文学、古代印度文学、古希腊罗马文学、阿拉伯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俄罗斯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从中亚古代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英雄史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印度的《五卷书》、波斯文古代经典《阿维斯塔》和著名史诗《列王记》、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的影子;19世纪随着中亚地区成为沙俄殖民地以后,俄罗斯文学开始影响中亚文学;由于中亚地处丝绸之路,商业的发展和流通和唐朝在中亚建立自己的统治,使得中亚文学与中国文学产生了更紧密的联系。中亚五国独立以后,中亚当代文学受到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使得中亚的文学成分变得更为复杂。我们也感受到祆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的文化因素在中亚文学中闪烁,共同影响着中亚文学的发展。不同宗教在中亚的历史、文化、文学中交替更迭,使得中亚文学的多元性更加明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波斯和阿拉伯宗教文学渗透在中亚文学中,对中亚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影响是极深的。中亚五国是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各国主体民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吉尔吉斯族、土库曼族、塔吉克族的民众几乎都信仰伊斯兰教,这使中亚文学带有明显的伊斯兰化倾向性。现代学者对中亚文学多元性的比较研究也不在少数,比如戴佩丽著《突厥语民族的原始信仰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再娜甫·尼合买提的《印度故事在哈萨克文学中的演变》(新疆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张定京、木合塔尔·阿布勒哈克的《突厥与哈萨克语文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的《玛纳斯奇的萨满“面孔”》(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等。
2.中亚民间文学的类同研究
由于中亚五国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土库曼族都属于阿勒泰语系的突厥语族,在历史文化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民间文学发展方面尤为突出;而且其中的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四个民族与我国境内的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有着深远的渊源关系。在民间文学中出现很多类同现象。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歌、英雄史诗、爱情传奇等内容,其中又以史诗在文坛上的地位最为重要。史诗具有拥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丰富的历史事实、浩繁的社会内容、深刻的主题思想、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等特点,作品以战争为内容的英雄史诗居多,比如哈萨克民间文学中公元10—11世纪的《阿勒帕米斯》,10—12世纪的《库布兰德》,14—15世纪的《英雄的塔尔根》,16世纪的《英雄哈姆巴尔》,17世纪的《英雄的叶斯别姆别克》,18世纪阿布赉时代的《夏班巴依英雄》《别根拜英雄》《贾尼别克英雄》《哈邦拜英雄》《布甘拜英雄》《哈尔哈英雄》等,19世纪的《阿尔卡勒克英雄》;乌兹别克族的著名史诗是《阿勒帕米西》《玉素甫和阿赫迈提》;吉尔吉斯文学中的重要史诗要数《玛纳斯》;塔吉克波斯时期的著名史诗《列王记》……这些英雄史诗在今天的民族文学中仍占据着重要地位并对当地的群众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哈萨克方面最重要的要数十月革命以后穆赫塔尔·阿乌埃佐夫著《阿拜之路》,是哈萨克现代文学中第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史诗性小说。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对柯尔克孜族文学的研究成果颇多,他长期从事突厥语民族的英雄史诗、叙事诗研究,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并且出版专著《口头传统与英雄史诗》《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中亚民间文学》等等,为相关学者研究中亚民间文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借鉴。乌兹别克文学中由德国学者卡尔·赖希尔著,我国柯尔克孜族民族学者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翻译的《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11年10月)一书中,就对乌兹别克史诗《阿勒帕米西》做了部分介绍,另外卡尔·赖希尔对中国民族文学中的史诗也多有研究,出版过《乌兹别克斯坦的口头叙事诗》》《歌唱往昔:突厥英雄史诗与中世纪英雄史诗》《朱玛拜·巴扎罗夫演述的卡拉卡勒帕克口头史诗》等十余种专著,还有近百篇的论文发表在各类刊物上;塔吉克文学中的民间文学由来已久,9世纪以前,塔吉克文学的来源之一就体现在古伊朗语的文学创作《阿维斯塔》中,书中保留了许多民间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的成分,对塔吉克文学发展影响极大;“20世纪30年代,苏联学者从塔吉克民间歌手口中搜集记录到了具有浓郁塔吉克色彩的史诗《呙尔奥格里》的文本,史诗《阿勒帕米西》也是塔吉克流传的文本”。塔吉克史诗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菲尔多西著、张鸿年译《列王记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6月),莫拉维(鲁米)著、张晖译《玛斯纳维启示录(波斯)》(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元文琪《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等。土库曼著名的史诗是《先祖阔尔库特书》《旅途中的伴侣》等,成为土库曼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
3.中亚民间文学的变体研究
中亚五国中,有四个民族与我国的民族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与我国境内的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在民间文学的发展方面同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许多重合或是一致的地方。比如《阿勒帕米西》作为中亚民间流传最广的英雄史诗,“从爱琴海到阿尔泰、从伏尔加河到乌拉尔山脉的广大地区的突厥语各民族都有它的文本流传并且以散文体的故事形式、英雄传说形式和韵文体叙事诗及史诗的形式广为传播。”它的变体在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等民族中都可以搜集到,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苏]日尔孟斯基的著作中:《阿勒帕米西及其他英雄史诗》(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另外,这部史诗的阿尔泰变体《阿勒普—马纳什》与吉尔吉斯的英雄史诗《玛纳斯》在情节和部分母体上有些相似之处,学者们对此也进行了研究,主要表现在:[苏]波·别尔科夫《阿尔泰史诗与<玛纳斯>》(俄罗斯文,莫斯科,1961年),郎樱《玛纳斯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热·克德尔巴耶瓦《玛纳斯史诗的发展历程》(俄罗斯文,1980年)等;再如《呙尔奥格里》也是中亚流传极广的传奇叙事诗,以纯韵文或韵散结合的方式流传于土库曼、塔吉克、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等民族中,但在流传过程中又吸纳了各民族文学自身的特色与精华,于是又都具有自己的特色。专门研究《呙尔奥格里》的[土耳其]孜克里亚·卡拉达乌特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总结了该叙事诗在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等民族中的流传和变异,通过对情节和结构的系统研究,对诗中各种变体出现的情节类型进行了详尽的归纳,这些在他的论文《呙尔奥格里的产生:突厥语诸民族变体比较研究》(比什凯克,2002年)中有所体现;此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哈萨克史诗《阔布兰德》,它在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各民族中都有广泛的流传。这部史诗最早的文本由俄国学者伊利蒙斯基从一位民间歌手口中记录下来,苏联的学者穆赫塔尔·阿乌埃佐夫、塞比特·姆卡诺夫、阿·奥尔洛夫等学者都对其进行过系统研究。
二.21世纪以前中亚文学译介和研究概况
1.21世纪以前中亚文学译介概况
21世纪以前,国内外对于中亚文学的译介有一些成果,有些译作至今仍有较大的影响力和研究价值。国内哈萨克文学的翻译作品主要有:哈拜翻译的哈萨克著名作家阿拜的作品,如《阿拜诗文全集》(民族出版社,1993年),《阿拜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5年9月),穆坎诺夫等著、衷维昭、草云、船甲翻译的《在荒地—哈萨克作家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1月),[苏联]阿·耶戈乌巴耶夫著、夏里甫汗译《哲人的芳名和学者的著作流传千古—<福乐智慧>哈萨克文译本序言》(《<福乐智慧>研究译文选(一),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
21世纪之前,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作家作品的翻译主要集中在对艾特玛托夫的作品的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界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位作家,他的成名作《查密莉雅》1958年问世后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1961年第10期的《世界文学》杂志上刊发了这部作品。1973年“文革”期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其中篇小说《白轮船》。“文革”结束后,艾特玛托夫的大部分作品陆续被翻译出版。这些作品主要有:单继达选编《艾特玛托夫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力冈、冯加译《艾特玛托夫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艾特玛托夫小说集(上、下)》(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冯加译《断头台》(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我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力冈译《白轮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力冈、冯加译《查密莉雅》(外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等等。1987年,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由陈学迅翻译的艾特玛托夫的文论集《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为中国研究艾特玛托夫及其文学创作提供了理论支持。另外,由郎樱翻译整理的《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玛纳斯>》一书于1990年出版,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汉文有关《玛纳斯》著作,被称为中国“玛纳斯学”的奠基作。1992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到1995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郎樱主编的《玛纳斯》。
对塔吉克、乌兹别克和土库曼文学的翻译作品相对于前面的两个民族来讲并不是很多,乌兹别克的译作主要有:卡赫哈尔等著、王连成译《乌兹别克短篇小说集》(时代出版社,1953年12月),朱尔菲娅·依斯拉依洛瓦著、卉妍译《朱尔菲娅诗选》(作家出版社,1962年1月),[苏]哈米德·古利亚姆著,季耶、大鹏译《双重身份的人》(北京出版社,1988年6月),阿斯卡德·穆赫塔尔著、衷维昭译《姐妹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3月),萨德里丁·艾尼著、千羽卜洛译《布哈拉》(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7月)。塔吉克古典文学作品的译介相对于现代文学作品的译介更多一些,比如潘庆舲翻译《鲁达基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潘庆舲翻译的菲尔多西的作品《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10月),张鸿年翻译菲尔多西的名著《列王记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6月)。另外,在俞灏东、何乃英主编的《东方文学作品选》(北京出版社,1987年6月)中也有一些译作。
21世纪之前,对土库曼斯坦的文学译介在苏联时期的成果更多一些,如钦吉兹·艾特马托夫著、郭锡爵译《土库曼诗人马赫图姆·库利》(民族文学研究,1992年第2期),撒哈雷诺夫等翻译的土库曼短篇小说集《爱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1月),邹绛翻译的《凯尔巴巴耶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凯尔巴巴耶夫著、王民泉等翻译的《白金国的爱素丹》(时代出版社,1951年7月)以及凯尔巴巴耶夫创作、江犂翻译的长篇小说《决定性的一步》(时代出版社 1954年)等。
2.21世纪以前中亚文学研究概况
21世纪之前,国内外学者对于中亚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相对来说成果较多的还是要数对哈萨克文学和吉尔吉斯文学的研究。国内的哈萨克文学研究的成果表现在:1988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哈萨克族古典文学》、郭得茂的《论哈萨克族谎言歌》(西域研究,1991年第3期),韦建国的《纳孜古里:哈萨克民间文学中女性形象的超越》(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扎哈拉·奴拉德勒的《哈萨克民间长诗中的女性形象》(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再娜甫·尼合买提的《印度故事在哈萨克文学中的演变》(新疆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哈拜的《谈阿拜的翻译诗》(民族文学研究,1986年12月),穆塔里甫《哈萨克民间长诗流传方式的调查》(民族文学研究,1987年第3期)等等。国外的哈萨克文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哈]迈里克·哈布杜林《哈萨克民间文学》(学校出版社,1974年),[哈]艾·孔鄂拉特巴也夫的《哈萨克民间文学史》(阿拉木图母语出版社,1991年),[哈]尼·克里木别托夫的《哈萨克古代文学》(阿拉木图学校出版社,1986年),[哈]S·萨德尔巴也夫《民间文学与美学》(阿拉木图作家出版社,1976年),[哈]木合塔尔·马哈乌因的《哈萨克汗王时代的文学》(哈萨克斯坦出版局和母语出版社,1992年9月),X·伊布拉也夫的《英雄史诗的世界——哈萨克英雄史诗的诗学》(阿拉木图科学出版社,1993年)等。
吉尔吉斯斯坦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获诺贝尔奖提名,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作为一个在文化血缘上与中国有密切联系的作家,他对中国的一些当代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国对他的研究开始于八十年代,相关论文已有百余篇。如北京大学俄语系的任光宣于1995年在《当代外国文学》第4期发表了《从<断头台>到<卡桑德拉印记>——论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金琼于1996年在《外国文学研究》第4期发表了《试论艾特玛托夫的当代意识与历史意识——重读<风雪小站>》;黄涛梅于1997年在《国外文学》第1期发表了《追寻艺术之母——论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对民间文学的引用》等等。这些论文大部分是艾特玛托夫的作品赏析,或对作者创作风格、作品形象、作品体现的悲剧意识宗教意识等进行分析,但研究尚不成规模。21世纪前,对吉尔吉斯斯坦文学的另一个研究热点是东干族文学研究。中国的东干学研究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最早论及东干文学的是中央民族大学胡振华教授的论文《苏联回族文学概述》(宁夏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另外,杨峰的《东干文化与东干作家文学漫议——<苏联东干族小说散文选>译后记》(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阐述了东干文学的特点。郎樱女士在《玛纳斯》的研究上颇有建树。近半个世纪中,她撰写学术著作、学术论文和学术报告40余种,大大深入并拓展了我国《玛纳斯》史诗的研究领域,为中国“玛纳斯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1991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玛纳斯>论析》。1999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再次与她合作出版《<玛纳斯>论》。另外,在陶德臻著《东方文学简史》(北京出版社,1985年5月),梁立基、陶德臻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6月),何乃英主编的《东方文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和肖之兴翻译的塔吉克加富罗夫著《中亚塔吉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8月)中对塔吉克族各时期的文学发展简况都有所论述。
三.21世纪中亚文学译介与研究概述
1.21世纪以来国内外对中亚文学的译介
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于中亚五国文学的译介更加重视,出现了一大批翻译作品和丛书,其中哈萨克文学的翻译作品主要有:阿拜著、栗周熊、艾克拜尔·米吉提译《阿拜箴言录》(民族出版社,2008年7月),穆哈哈里·玛哈泰耶夫著、哈依夏·塔巴热克译《远飞的大雁》(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1年7月),贾合甫·米尔扎汗主编、哈依夏·塔巴热克等译《哈萨克族文化大观》(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哈依夏·塔巴热克译《哈萨克民间达斯坦》(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涅马特·凯勒穆别托夫著、叶尔克西译《永不言弃》(民族出版社,2010年2月)。
吉尔吉斯斯坦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在21世纪之前基本翻译成中文出版,但在21世纪以后也有新的版本出现:如谷兴亚翻译的《崩塌的山岳:永恒的新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草原与群山的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另外,新疆人民出版社在2011年以维吾尔语出版了艾特玛托夫的一系列作品如:《断头台》《查密莉雅》《崩塌的山岳》《一日长于百年》《早来的仙鹤》《漂亮的大眼睛》《卡珊德拉印记》《悬崖上猎人的哀叹声》等。21世纪东干文学进入人们的视野,2001年,丁宏翻译了伊马佐夫的《亚瑟尔·十娃子生活与创作》,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林涛翻译了拉洪诺夫的《中亚回族的口歌与口遛儿》以及伊马佐夫的《中亚回族诗歌小说选译》,由香港教育出版社出版。2011年李福清编著的《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塔吉克文学的译介主要集中在对塔吉克民间文学和中古波斯文学的翻译上,对古典文学的翻译作品主要有:[波斯]萨迪著、张晖译《果园》(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张晖翻译的《鲁达基诗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丁岐江《波斯趣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波斯]扎赫拉·恒拉里著、张鸿年译《波斯故事》(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波斯]莫拉维(鲁米)著、张晖译《玛斯纳维启示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波斯]萨迪著、杨万宝译《真境花园》(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塔]布·格·加富罗夫、阿·姆·米尔佐耶夫、吴秀琴译《塔吉克民间传奇故事精选》(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7月)等;乌兹别克文学的翻译主要集中在对纳沃伊作品的翻译,例如:阿里舍尔·纳沃伊著、吴国璋译《法尔哈德和希琳》(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6月),艾里西尔·纳瓦伊著、铁依甫江·艾里耶夫整理,张宏超译《纳瓦伊格则勒诗选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对土库曼文学的翻译在我国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只有极少数的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如米娜瓦尔·艾比布拉、阿布都诺夫·甫拉提翻译的《马赫图姆库里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是土库曼文学翻译的代表。
2.21世纪以来国内外对中亚文学的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哈萨克文学的研究成果相对其他几个民族来讲显得更为厚重一些。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于哈萨克文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其中国内方面的专著主要有:赵嘉麒主编《哈萨克文学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毕樳主编《哈萨克民间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赵嘉麒、翟新菊主编《哈萨克文化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贺元秀主编的《哈萨克文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贺元秀、乌鲁木齐拜主编《哈萨克文化新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吴孝成、赵嘉麒主编的《20世纪哈萨克文学概观》(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黄中祥著《哈萨克英雄史诗与草原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5月),帕提曼著《哈萨克民俗文化》(民族出版社,2008年10月),常世杰、叶新元主编《哈萨克族民歌选编》(伊犁人民出版社,2006年),张定京、木合塔尔· 阿布勒哈的《突厥与哈萨克语文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等。论文方面主要有:张治安的《哈萨克文学的历史成就与现实走向》(宁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郑振东的《略论阿拜·库南巴耶夫的历史地位》(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黄中祥的《哈萨克英雄史诗中所反映的萨满观念》(民族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黄中祥的《哈萨克族巴克思在其民间文学传承中的作用》(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毕樳的《哈萨克神话传说里的波斯成分》(民族文学研究,2002年第1期),郑振东的博士论文《阿拜研究》(南京大学,2001年5月)等等;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法]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哈]哈尔召巴依·珠玛坚沃夫著《卡拉卡尔帕克地区的哈萨克文学》(阿日斯出版社,2006年),[哈]塞里克黑拉巴耶夫著《哈萨克文学史》(阿拉木图出版社,2004年),[哈]巴尔塔拜著《突厥语族文学史》(阿拉木图市阿勒斯出版社,2009年),吾塔尔阿里·布尔克特著《突厥学》(阿拉木图市阿勒斯出版社,2003年)等。
在吉尔吉斯斯坦文学研究方面,我国对艾特玛托夫的研究继续深入,相关研究论文有300余篇,尤其在2008年达到高峰。这些学术论文主要从艾特玛托夫思想研究、创作研究以及与中国当代作家的对比研究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了作家创作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对理想的追求以及严肃而朴实的现实主义与理想色彩。不少论文将艾特玛托夫与张承志、高建群、路遥等中国当代作家进行比较论述。河北师范大学史锦秀教授于2007年出版专著《艾特玛托夫在中国》,以原创性的思路、翔实的资料和科学的分析,将艾特玛托夫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比较文学研究的崭新领域。东干文学在国外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在苏联时期就形成一定规模。本世纪之初,北方民族大学的林涛、黄燕尤、武宇林等人发表一系列介绍吉尔吉斯斯坦东干口头文学以及书面文学的文章。兰州大学的常文昌教授带领本校研究团队在东干文学研究领域取得可观成果,发表了30余篇学术论文,出版专著《世界华语的“新大陆”——东干文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其中详细介绍并评价了多位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族诗人和作家。他的《亚斯尔·十娃子与汉诗》在吉尔吉斯斯坦出版,并得到吉尔吉斯科学院东干研究所所长M·X·伊玛佐夫的高度评价。兰州大学青年教师、文学博士杨建军也发表了一系列东干文学研究论文:如《论中亚东干文学的多元文化渊源》(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中亚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世界华裔文学中的伊斯兰文化带》(兰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等等。另外,上海政法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常立霓在东干文学研究方面也有一些成果,比如《中国“东干学”研究述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中国西北方言口语的艺术宝库——多元语境中的东干小说语言》(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等。东干文学研究在国内虽然仅有20年的历史,但不可否认已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吉尔吉斯斯坦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热点是对史诗《玛纳斯》的研究。世界闻名的英雄史诗《玛纳斯》是生活在两国的柯尔克孜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财富,是对人类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玛纳斯》研究会副会长郎樱因在《玛纳斯》史诗研究方面做出巨大贡献,于2011年荣获吉尔吉斯斯坦“达纳克尔”勋章。中央民族大学柯尔克孜语言文学专业的创始人胡振华教授的研究成果令人关注;另一位在该领域颇有建树的是柯尔克孜族研究员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他用汉文和柯尔克孜文撰写过多篇有关《玛纳斯》的研究著作或论文,如《<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民族出版社出版,2006年)、《呼唤玛纳斯》(柯尔克孜文论文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2006年)、《16世纪波斯文<史集>及其与<玛纳斯>史诗的关系》(民族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玛纳斯奇的萨满“面孔”》(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等;同时,他还从事《玛纳斯》史诗的翻译工作,翻译成果共计十万余行,为史诗《玛纳斯》研究做出了贡献。
塔吉克民族作为中亚最古老的土著民族,在其漫长的发展进程中与其他的民族不断渗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并且,“它最大限度的保存了东伊朗的民族成分和伊朗语”。塔吉克人作为东伊朗人,它与波斯人的祖先——西伊朗人有着人种、语言和文化上的亲缘关系,因此,学者研究塔吉克古典文学,就将其与波斯古典文学联系起来研究。塔吉克现代文学开始于十月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的塔吉克文学又受到了苏联文学的影响。2000年以来,国内外出现了不少研究塔吉克文学的学者,如张鸿年、潘庆玲、张晖、杨春航、吕静涛等等,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学者像塔吉克族学者西仁·库尔班、塔比勒迪·乌守尔、阿蒂坎姆·翟米里等。国内关于塔吉克文学的相关研究著作主要有:穆宏燕著《波斯古典诗学研究》(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1月),张鸿年著《列王记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张鸿年著《波斯文学史》(昆仑出版社,2003年),王建玲、南美玉主编《蔷薇园:萨迪人生教诲录》(海潮出版社,2011年2月),刘兆祥、安睿主编《蔷薇园:萨迪智慧枕边书》(海潮出版社,2011年2月),许序雅著《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孟昭毅著《丝路译花》(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何乃英等主编的《新编简明东方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论文主要有:[塔吉克族]阿蒂坎姆·翟米里著、[维吾尔族]伊明·阿布拉翻译的《当代塔吉克族书面文学概况》(民族文学,2001年8月),蒋宏军、蒋方珍的《试论中国塔吉克族情歌》(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1月),西仁·库尔班的《塔吉克族口头文学简析》(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4月),张鸿年的《菲尔多西的列王记》(中外文学交流,2005第7期)等;国外的研究著作数量不多,主要有:[俄]巴尔托里德等著、耿世民译《世界汉学论丛·中亚简史》(中华书局,2005年12月)中对塔吉克文学有所涉及。
21世纪以来,乌兹别克文学和土库曼文学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现当代学者对乌兹别克斯坦文学的研究仍然主要集中在对纳瓦依的研究上,比如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古典文学和十二木卡姆研究学会主编的《伟大的诗人纳瓦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海热提江·乌斯曼著《对中国辞书中“纳瓦依”条目解释的思考》(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4期);另外,载于《乌兹别克斯坦》一书中的《苏联时期的乌兹别克斯坦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和孙壮志、苏畅、吴宏伟等编著的《列国志:乌兹别克斯坦》等书(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中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文学也有所涉及。对土库曼文学的研究比较多的还是对著名诗人马赫图姆库里的研究,主要有:赵中干的《土库曼诗人马赫图姆库里》(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施玉宇主编《列国志:土库曼斯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等。
除上述对国别文学的研究成果外,还有许多著作中部分涉及到了中亚五国文学的内容,国内方面比如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中亚文明史》、王治来的《中亚通史·古代卷(上、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马大正,冯锡时的《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著《中亚民间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张铁山著《突厥语族文献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等著作中对中亚文学的有关内容都有所介绍。国外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哈]巴尔塔拜著《突厥文学史》(阿拉木图市阿勒斯出版社)、[哈]吾塔尔阿里·布尔克特《突厥学》(阿拉木图阿热斯出版社,2003年)、《古代民歌和传说》(阿拉木图作家出版社,1985年)等,其中对中亚文学的有关内容或设有专章陈述或做了简要介绍。
四.中亚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学者对中亚文学的研究虽然有一些成果,但是从中亚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
第一、语言障碍为文学研究设下了屏障,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是我国跨境的少数民族,懂得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兹别克语、塔吉克语的学者队伍中除了少数民族学者之外,汉族研究者和其他少数民族研究者的数量是极少的。同时,由于文学翻译的限制和滞后,很多中亚文学作品还没有及时译介到国内来,我国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等跨境居住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学作品被译成汉语作品的数量也不多,因此说,语言和文学翻译是中亚文学在中国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瓶颈。
第二、从中亚历史文化发展的方面来说,历史上中亚地区曾受到波斯、古希腊、阿拉伯、中国、突厥、蒙古、沙俄、苏联等统治,使得中亚语言文学的成分一直以来比较复杂,国别文学研究的界限变化不定,为中亚文学的研究造成一定难度。
第三、20世纪90年代初,中亚五国相继独立以后,主要精力放在国内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上,虽然每个国家都分别出台了不少激励文艺发展的政策,但由于苏联时期对于中亚民族文学的忽视和当代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暴力恐怖主义势力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对中亚五国的影响,造成了中亚文学与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不能全面深入的交流。
综上所述,中亚文学是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尚未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加上其他原因造成现在中亚文学研究相对滞后。中亚文学本身的丰富多彩性以及与古代印度文学、波斯文学、古希腊文学、阿拉伯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俄苏文学、西方文学的渊源关系和紧密联系,为我们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中亚文学研究的前景是广阔的,有待我们去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