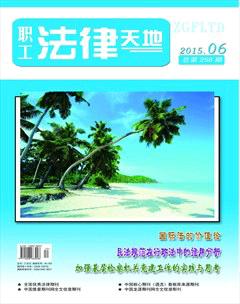死刑存废问题之探析
2015-08-27王单媛
王单媛
随着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进入二审阶段,“毒驾入刑”“拐卖儿童犯罪中的买方也将被追责”等话题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此修正案延续了刑法修正案(八)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将死刑的范围缩小化,在修正案(八)的基础上又减少9个罪名,由之前的55个减少为46个,其中包括5个经济类的犯罪,即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两个社会管理秩序方面的犯罪,即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两个军人违反职责罪,即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同时,草案中明确指出了要提高对死缓犯执行死刑的门槛。我国现行刑法第五十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在刑法修正案(九)的草案中,把“故意犯罪,查证属实”改为“故意犯罪,情节恶劣”,这一修改体现了创新刑事立法理念,将进一步发挥刑法在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社会生活方面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刑法修正案(九)的修改体现了立法机关对死刑的鲜明观点,而死刑存废问题在我国由来已久,一直是学术界讨论不息的话题之一。关于死刑的起源,学界并没有统一明确的说法,有人认为死刑是神赋予的权力,国家代表神的意志实施死刑。《国语》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从现有的资料看,刑是法的最初形态,源于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但可以肯定的是,刑罚意义上的死刑是随着法的产生而产生的。如此看来,“报复时代”(奴隶制时期)的仇杀就是最早的死刑。“由于刚脱胎于原始复仇习惯,带有浓厚的复仇色彩,甚至以复仇为其唯一目的。”事实上,早在原始社会,仇杀现象既已存在,但其在当时只能作为死刑的雏形,因为死刑作为刑罚的方式,其存在是以法的存在为依据的。随着法的产生,仇杀被纳入了法律,被合法化、规范化、制度化,从而成为了早期的一种刑罚手段。在当时,血亲复仇以“集体负责”的方式构成了适用刑罚的依据,而同态复仇是刑罚的主要原则。需要注意的是,奴隶主处死奴隶的现象不应看作是死刑的适用,因为在奴隶社会,奴隶没有“人格”,奴隶只是作为法律的客体而存在,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在当时不属于法律所要调整的“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在严格意义上讲,当时死刑的适用范围不包括奴隶。因此,当时法律所要调整的社会矛盾主要是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奴隶主阶层利用死刑威吓和惩罚威胁其利益的人;另一方面,死刑可以满足弱势群体依靠国家力量实现报复目的的需要。可见,死刑在当时是作为统治手段和报复的手段而存在的。死刑的基本特征——“以命抵命”的报复本质从同态复仇中被人们保留了下来。在随后的封建社会发展时期也呈现着大体相同的特点。
从死刑的漫长渊源发展历史来看,其在我国的延续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突发的,而是带有很强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适应性。许多实践证明,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水平之下,完全废除死刑是不明智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死刑适用的范围可以无限度的扩大,而是要严格地进行控制、有限度地使用。死刑具有最强的威慑力。死刑代表死亡,代表了生命的终结,让人不由得心生恐惧、望而却步,深信死刑是不能够触碰的。所以,人们会自愿地把法律当成自己行为的底线,以此为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人们普遍认为,为了能够更好地预防犯罪,必须使用死刑这种绝对惩戒的方式,通过死刑所具有的威慑力和震慑力从而达到较强的预防作用。毛泽东同志早在1927年所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明确指出:“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
但是,死刑也必须受到及其严格地规制,否则将会与我国的人权事业的发展背道而驰。我国现行刑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死刑予以限制:
(1)从适用条件上限制。《刑法》第48条第l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将适用死刑的条件界定为“罪行极其严重”,也即犯罪性质、犯罪情节、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的统一,有效地对死刑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从刑法分则看,对于可以判处死刑的犯罪及其情节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刑法分则中,除极个别的以外,死刑都是作为选择刑来规定的,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刑罚方法共同构成一个量刑幅度,加强了慎用死刑的可操作性。
(2)从适用对象上限制。《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法律明确规定将“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婦女”这两类人排斥于死刑适用对象之外,进一步限制了死刑的适用范围。前者主要考虑未成年人尚处于世界观形成初期,心理可塑性强,容易受到不良犯罪思想的蛊惑,应着重教育改造。后者体现了刑罚的人道主义原则。
(3)从适用程序上限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条规定,死刑案件只能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基层人民法院无权审理死刑案件,当然也就无权适用死刑。《刑法》第48条第2款前半段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规定了严格的核准程序,客观上限制了死刑数量,保证了办案质量。另外,《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3款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不上诉的,和判处死刑的第二审案件,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规定正是对死刑的适用慎之又慎的表现。
综上所述,在当今中国,死刑的废除并不是明智之举。但我们应该坚定地相信,死刑的废除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死刑终将成为历史发展的牺牲品,最终湮灭在人类发展的滚滚潮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