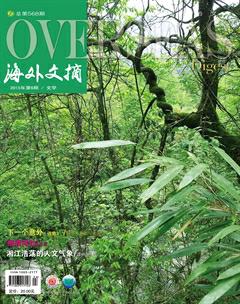我的散文观
2015-08-18陆令寿
陆令寿
就在这个月的11日,我已到了退休的年龄。虽还未正式接到通知,但我的人生又到了一个新的拐点。回首往事,感慨万千。
5年前,在军旅奔走了35个春秋的我毅然脱下军装,主动去蹭旅游这艘“游船”,完成从“军旅”向“民旅”的转变,这似乎有点不智和轻率。然而,这几年的游历游思,似乎证明当时的选择不仅契合了我对事业的追求,而且把工作与爱好较为完美地结合起来———当一个人把工作当爱好、把爱好当工作时,无疑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日月行天,落了还会升起。世间万物,来是偶然,去是必然,来去皆顺其自然。在部队,军营是我的精神栖息地,我唱的主旋律是“军歌”;到了地方,旅游的岗位成了我创作新的源泉,我又唱起了“民歌”。当年,莫言老师曾戏称我“左手抓政治,右手搞文学”。那时,我以小说创作为主,观照的对象是那些出生入死地战斗在执勤和处突一线的基层官兵,我的处女作《阿根从军记》在《钟山》发表后,又创作了中短篇小说集《春日迟迟》和长篇小说《鳑鲏郎》。《鳑鲏郎》曾经获得解放军文艺奖。随着岗位的变化和职责要求,我没有时间去啃大部头,于是便学着写散文。在军旅生涯结束时,我结集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换一种活法》,向我终生眷恋的军营告别。转业到地方,我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去搞湖北特色的“三万”,即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在土苗聚集、山高坡陡的巴东县清太坪镇,扎扎实实待了92天,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写下了20余万字的“春天里的日记”———《巴山寻根》,这本日记体的散文集由余秋雨题写书名出版。在我成为旅游人之后,我的脚步跟着岗位的需要走,跟着季节的变化走,跟着大众的旅游潮流走,在欧洲、在北美、在东南亚,在国内29个省市及台湾、澳门地区,足之所至,心之所舒,手腿脑并用,不仅用文字,也用图片满足读图时代读者立体的审美需求,力求每一篇游记有异地魅人的景观,有搏动的生命,以观照读者的灵魂。这些年,我走到哪儿、拍到哪儿,写到哪儿,发到哪儿,有些刊物还给我开了“游记专栏”。于是,便有了《远行,给你一个故事》。
创作,对于每一个作家来说,它永远在路上。今天,在这样一个极其难得的作品研讨会上,各位老师对我的散文作品进行了中肯的解读,剖析中有赞扬也有批评,我很清醒地看到:赞扬里鼓励的成分大于作品实际的品质,批评里指明了我今后改正的方向。这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我深知,我的作品还很稚嫩,有的还比较粗粝,比较肤浅,真正拿到桌面上来与读者见面时,我心里很忐忑,很愧怍,生怕浪费了读者的时间和精力。要真正写出无愧于时代的散文作品,还要下很大的工夫。散文是直逼灵魂的写作,是情感的创作,一定要写出真情实感,来不得半点虚假。三十多年前,我听过王原坚老师的讲座,他说,写作一定“要写从心头上流过的东西,只有从心头上流过的东西才是好东西”。感动读者一定要先感动自己。写好散文细节也很重要,感人的细节才能抓住读者。各位大师的作品之所以能赢得读者,在于他们把细节写得很生动。诚如林非老师所说:“不能把细节虚弱在广漠的社会和宇宙之中。”再一个就是要蕴含哲理和思考。我们的祖先一直倡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理解真正意义上的旅行,是边行边思。
少小离家的我,一个远离故土的游子,似乎更愿意把那些遥远而陌生的地方,作为我终生追寻的另一个故乡。
只有带着灵魂去旅行,用心去感受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旅行中的故事才能无比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