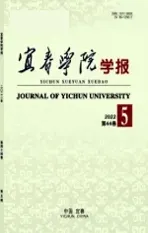景颇族原始宗教与群体认同
2015-08-15徐祖祥
李 叶,徐祖祥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群体”作为社会学分析的一个具体单位,主要是指人们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联结起来,进行共同活动和感情交流的集体。“认同”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主要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情感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群体本身就含有某种特定的认同因素。群体认同包括宗教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以及混融和超越了民族认同、宗教认同的区域认同。
宗教其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必须要以某一民族或群体作为载体,因此,关于宗教与民族认同关系的研究,学术界侧重于将宗教视为民族的一个基本特征来进行论述,如泰勒《原始文化》中的“有那么一种情况,一个民族具有其特有的服装,特有的工具和武器,特有的婚姻法和财产法,特有的道德学说和宗教教义。”[1](P9)以及斯大林有关民族的定义,我国早期民族学界的学者也基本沿用了这一方式来对其进行研究。景颇族原始宗教作为一种全民信仰的原始—氏族部落宗教,与传统文化几乎完全一致,宗教群体与民族群体完全统一。因此,景颇族原始宗教中的宗教教义、禁忌习俗、神话传说等也就成为了整个民族集体记忆、道德规范的重要来源,并且融入到景颇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春播秋收、冬藏,还是婚丧嫁娶、起房盖屋、生病、械斗,都要杀牲祭鬼。”[2](P361)原始宗教所承载的整个民族的民族渊源、历史记忆、伦理道德通过“杀牲祭鬼”的方式不断得以强化,代代传承。景颇族原始宗教以董萨为媒介而进行祭献天鬼、地鬼、家鬼的宗教仪式,既是宗教观念的现实展现,同时也是景颇族群体认同的强化过程。
一、景颇族原始宗教与宗教认同
景颇族原始宗教作为景颇族传统文化的根源,集中体现了景颇族民族意识,是信仰原始宗教的景颇族民族群体相互认同、亲近的精神纽带。“在民族的生成与发展过程中,一些在民族原始时期形成的心理特征和生活习惯,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保存下来,从而成为具有社会和文化意蕴的民族群体的初级意识,也可称之为‘民众意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种‘民众意识’能够引导民族群体生存的发展方向,并促进本民族内部的凝聚与团结。”[3](P3)这里的“民众意识”即民族意识,景颇族的“民众意识”便是通过原始宗教这一集体无意识的方式保存、传承下来的,是景颇族先民进行生产生活的重要精神、技术指导。信仰原始宗教的景颇族信徒往往对本民族的原始宗教和信仰原始宗教的其他成员产生一种亲近感,自然也就对其他民族的宗教和信仰其他宗教的民族产生一种排斥感,于是,该群体自然萌生了对自己宗教的认同感。
景颇族原始宗教是一种基于万物有灵的鬼灵信仰,这种信仰伴随着景颇族民族的形成而产生,是景颇族先民与自然界关系互动的经验总结,贯穿于景颇族民族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景颇族的春播秋收,婚丧嫁娶等都离不开原始宗教。如景颇族春播撒谷前进行的“能尚”祭祀,也叫开秧门节。“能尚”是景颇族全寨的神庙,供奉着与全寨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鬼。每年祭祀两次,第一次是在撒谷子前,第二次是在秋收前。主要由董萨主持祭祀。目的是为了祝福寨子在一年中,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也健康、平安;寨子要团结,很多规章制度在祭“能尚”的时候制定,寨子的人不许违背,约束力强。以前祭“能尚”由山官 (大、小之分)带着来祭 (现在大多是由村上领导组织的),官家婆娘准备水酒,接着就通知大家献能尚(董萨选好日子),大家自愿凑东西,比如鸡蛋、钱等,然后全寨不干任何事,集体到能尚那里,请董萨去念。选日子的时候,属虎、属牛、属龙的日子,要选那些比较有力的属相。天神、地神、山神、雷神、财神等各种神 (7种)都有自己的位置,第一个位置是山官家的家神,第二是天神,最后是饿死鬼等各种不好死的鬼,用叶子包着肉祭献。现在牵头祭能尚的,依然是官种后代主持。祭能尚有7个鬼桩,4个董萨,哪个神桩献什么,献多少 (需要多少只鸡……)根据董萨占卜决定,牛或鸡 (一年杀一样,不能年年杀鸡,也不能年年杀牛)还不杀的时候拜一次,董萨念一遍,念完杀了煮熟的时候又念一遍,拜一次,开始吃,吃的时候还是由村领导讲话,宣布一些寨子里的事,好的鼓励,不好的批评,吃完就全部一起回家了。由于祭“能尚”关系到整个村寨的兴旺丰收,因此全寨都村民都会去参加,以前凡是新搬迁进来的村民,要一起参加过祭“能尚”才能算是这个村寨的人。
祭“能尚”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形态,与景颇族的民族文化基本合为一体,早已内化成了景颇族“民众意识”的核心纽带。祭“能尚”的时候通过对以山官家神 (鬼)为主的各种神 (鬼)的献祭,把基于原始宗教信仰基础上的景颇族信徒宗教认同,上升到了对整个景颇族群体的认同。这种建立在原始宗教上的宗教认同,作为景颇群体认同的重要因素,在景颇族每年两次的集体献祭中不断得到强化。
二、景颇族原始宗教与民族认同
纵观历史,少数民族中的原始宗教与原始文化往往是浑然一体,难以割裂的。特别是像景颇族这类直过民族。毫无疑问,原始宗教变成了景颇族社会生活包罗万象的纲领,成为其全部的精神生活。“民族是以一定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民族认同是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文化和其他成员的亲近感以及对民族命运的关注。”[4](P66)其中,“民族成员对其他民族成员的亲近感”也必须要通过对自己本民族民族文化的亲近与认同才能实现。因此,民族文化在民族认同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景颇族原始宗教作为深入景颇族民族群体内心,惯性极强的一种精神文化,处在了景颇族民族文化的中心位置,并与景颇族民俗紧密相连,关系着整个景颇族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成为了景颇族民族认同的重要衡量标尺。以景颇族特有的节庆活动目瑙纵歌为例。
景颇族目瑙纵歌,是聚集起来一起唱歌跳舞的意思。目瑙纵歌来源于景颇族的一个神话传说。
传说开天辟地时,“目瑙纵歌”舞蹈只有天上的太阳姑娘会跳。一次,太阳王在太阳宫举行盛会,邀请大地万物参加,大地派百鸟作代表前去。到达太阳宫,百鸟向太阳姑娘学习各种优美的舞蹈动作,尽情与太阳姑娘狂欢,与太阳姑娘结下深厚的友情。盛会毕,百鸟从太阳宫返回大地,落脚在一块平坦的草地上。草地四周风景秀丽、气候宜人,遍地百花盛开、蜂蝶沉醉,旁边一条清澈见底蜿蜒曲折的大江,两岸生长着茂盛的果树,果子黄灿灿的十分诱人。百鸟恋恋不舍在那里欢歌跳舞,犀牛第一个引吭高歌,嘹亮的歌声吸引了各种飞禽走兽前来狂欢;凤凰带队在前,五彩缤纷的羽毛闪闪发光非常漂亮;孔雀领舞,开屏展翅跳起优美的舞姿;山绿鸽子扯开歌喉一边唱起婉转动听的歌谣,一边跳起从太阳姑娘那里学来的“目瑙纵歌”舞蹈。其他动物也纷纷排成长队跟在后面跳起来,一派热闹的景象。这一切恰巧被景颇族祖先麻丁约看见,他被深深地感染,一边模仿百鸟的舞姿扭动起来,一边唱祭“目代”神史诗,还与头人扎瓦容扎一起带领其他景颇族人民跳起欢快的舞蹈。不久,苏瓦木独专门举行盛会,邀请所有的景颇族狂欢纵舞。
之后,景颇族人民无论是在生产丰收、出征凯旋归来,还是在头人升位、祭“目代”神等时候,都要砍4棵笔直的树劈成长方形,用带有红、黑、白、蓝、绿、黄、紫等颜色的物质在上面绘画各种线条,顶端绘画太阳、月亮及迁徙路线等图案,做成‘目瑙示栋’桩竖立在房前院场中,由“瑙双”(汉语为领舞者)戴着装饰犀鸟头颅、插有孔雀羽毛的帽子,身着长袍,双手舞动雪亮的长刀,后面紧跟着瑙巴、瑙知等,在古老大铓和大木鼓的伴奏下,带领众人舞蹈,“瑙双”、瑙知、瑙巴就是犀鸟、凤凰和孔雀的形象代表。[5](P44-45)
关于景颇族目瑙纵歌来源的神话传说,首先,其本身便是景颇族民族文化中的一类,几乎跟景颇族原始宗教完全吻合,其终极指向都是景颇族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如果从民族群体的角度看,所谓原始宗教,不过是民族思维、民族生活方式、民族历史经验的框架与民族自我表现方式而已。一句话,是一个民族存在的一种神话象征。”[6](P150)神话传说为目瑙纵歌找到了神圣存在的合理性,保证了景颇族民族精神、传统文化有根可循,也为景颇族这一群体找到了精神导向。其次,目瑙纵歌来源的神话传说中详细描述了景颇族的山川河流、气候风景、花鸟草木,反映出了景颇族民族思维、生活方式,同时体现了景颇族对自身民族共同的生产生活地域、生活方式的认同。此外,神话传说作为原始宗教的一种形态“运用它所具有的信仰体系、文化功能和社会生活方式,使之在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语言的基础上,形成稳定而牢固的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将一个特定的人群逐渐凝聚为一个民族。”[7](P56)从而增强了景颇族的民族认同。再者,目瑙纵歌作为景颇族全民性大型祭祀活动,其舞步路线是景颇族民族迁徙的路线,很多动作来自于景颇族先民刀耕火种的生产生活动作,如割草、烧火、扬谷等,目瑙纵歌重现了景颇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是景颇族先民历史的再演绎。“历史是一个民族的人们追寻自身过去的独特的、超越时空界限的记忆。”[8]历史记忆的保留才能使一个民族产生共同经历一段历史的历史认同感,只有在清晰的历史记忆认同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孕育出某一民族的民族认同。每年正月十五举行的目瑙纵歌是对景颇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像”记忆。目瑙纵歌通过物化的形式把景颇族民族历史记忆融入到原始宗教大型歌舞之中,从而使目瑙纵歌这样一种原始宗教祭祀仪式变成了景颇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特征。
除了目瑙纵歌,还有景颇族的新谷节、结婚、丧葬、进新房等等民族特有的风俗与节庆活动,都是合为一体的景颇族原始宗教与原始文化在景颇族社会生产生活各领域的延伸与具体化。
景颇族原始宗教以文化的形态,融入到景颇族群体生活之中,把景颇族整个群体有力地凝聚在以原始宗教为根本,传统文化为具象表现形式的景颇族民族精神之中。
三、景颇族原始宗教与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的基础源于民族认同,而宗教认同又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因此国家认同是群体认同的最高层次。对于原始性氏族—部落宗教的景颇族原始宗教而言,“宗教情感与民族情感往往交织渗透在一起,因此,宗教已成为民族自我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系民族凝聚力的纽带”,[9]民族认同几乎完全等同于宗教认同。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当今世界没有哪个族群或族群成员可以离开国家而单独生存,无论是在经济依赖和政治安全的意义上说,还是在地理学的意义上看,概不例外”,[10]景颇族“宗教往往是认同意识的核心,对于族群边界的确定具有重要意义”。[11]因此,景颇族原始宗教与国家认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景颇族原始宗教作为一种原生性氏族—部落宗教,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得以保存,并成为民族宗教的基质,对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具有天然的认同感。“传统中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自文明以来,就都不是封闭的传统,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中,在继承与纳新的互动中存在与发展的。”[7](P60)正是这种互动,使中国各民族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而构成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景颇族原始宗教中的国家认同主要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祖先崇拜、伦理道德的归附以及“送魂经”对中国疆域内的祖先居住地的回归来体现。
基于万物有灵观念形成的景颇族原始宗教,把鬼分为以太阳鬼最大的天鬼,以地鬼最大的地上的鬼和以“目代鬼”(山官家供奉的鬼)最大的家鬼三大类。景颇族在供奉家鬼的时候,除了山官家供奉“目代鬼”以外,其他普通民众都是供奉家堂鬼。所谓的家堂鬼,就是指自己祖先的灵魂。根据景颇族的风俗习惯,只要是家里的老人不在了,都要请董萨来通宵念“送魂经”把他的灵魂送到老祖先在的地方,如果送不走的或者送走后又回来“咬”家人的,就要为他做一个家堂,把他的魂供奉起来。如果是娶了媳妇,那便也要连丈人家的鬼一起供奉起来。等到孙子辈的时候,就要将自己爷爷、父亲的魂一起送走。家里供奉着家堂鬼,每逢进新房、结婚、小孩出生、吃新米等都要祭献,平时一年祭献两次。祭献家堂鬼的祭品一般是鸡、猪、牛等,祭品要大于给山神鬼的。景颇族对家堂鬼供奉、祭献,是中国传统祖先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景颇族的原始宗教是融摄于中国传统祖先崇拜下的一种独具民族特色的宗教文化形态。除此之外,景颇族创世史诗中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认为其他各民族都是自己的兄弟。以孔明为其祖先的孔明崇拜,加之景颇族原始宗教本身便只是一种氏族部落的宗教,因此,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景颇族原始宗教只不过是中国多元宗教文化的一部分。
从社会功能方面来看,任何一种宗教都具有伦理道德的劝诫约束功能,景颇族原始宗教也不例外。景颇族原始宗教中尊敬长辈、团结互助、长幼有序、诚实守信,不偷不抢等,这些道德伦理又通过景颇族的“神判”得以在民族群体中一一落实。原始宗教的“神判”发挥着现代文明社会法律的作用,保障了景颇族群体的团结稳定,同时促进了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和谐稳定。
纵观景颇族原始宗教中的神话传说以及“送魂经”内容,不难发现景颇族代代传承的民族发源地以及活动区域皆是在中国疆域之内。每次宗教仪式,如目瑙纵歌的舞蹈路线,送魂路线等都在不断深化着本民族集体记忆的同时,又无形中强化着本民族的国界意识,明确着自己的政治身份,是本民族国家归属感、认同感的滋生、强化过程。
结语
宗教与民族关系问题,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与民族关系,是我国民族团结发展、繁荣稳定的关键环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景颇族原始宗教的存在形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其在景颇族群体认同中的作用依然存在。因此,积极引导景颇族原始宗教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大景颇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宣传力度,提高景颇族民众的文化自觉,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宗教和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瑞丽市史志办 编.瑞丽景颇族[M].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2014.
[3]张曙光.民族信念与文化特征—民族精神的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宫玉宽.我国少数民族民族认同中的宗教因素[A].牟钟鉴编.宗教与民族(第五辑)[C].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5]盈江县史志办.景颇族民俗与文化拾遗[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6]高长江.宗教的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7]金泽.宗教与民族研究的三个问题[A].牟钟鉴 编.宗教与民族(第四辑)[C].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8]梅萍,林更茂.民族精神与和谐社会的价值认同[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社会,2007,(6):150-153.
[9]王颖,秦裕华.关于新疆民族文化认同与宗教认同[J].新疆大学学报,2008,(6):76-79.
[10]钱雪梅.从认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J].民族研究,2006,(6):16-25.
[11]菅志翔.宗教信仰与族群边界——以保安族为例[J].西北民族研究,2004,(2):175 -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