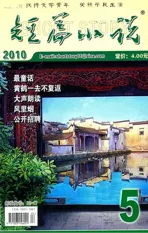养猪场的杀人事件
2015-07-21朱敏
◎朱敏
养猪场的杀人事件
◎朱敏
据同村的好多人说,朱彪最后一天在家的日子过得风平浪静。大清早吃完饭,碗筷还横七竖八地放置在炕桌上,碟子里剩下几块肥肉,油腻腻地泛着白光,醋碗里的醋浮着一层白沫,碗沿上挂着一条绿色的辣椒丝。还有吃剩下的馒头,上面滴滴答答地落着几点醋汁,乌黑乌黑的。一片狼藉。栓虎后来这样形容。还不叫姓朱呢,吃相都是个猪样。有人附和着开玩笑。大家听了哈哈一笑,但笑完就开始骂朱彪:这家伙,走哪也不吭一声。这句话才是他们的真实意愿表达,说明他们想朱彪了。
没错,朱彪已经失踪好多天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大家都胡乱猜测着,新疆、兰州、内蒙,或者青海,之前,他也去过这些地方,买猪、卖猪,赊账、要账,反正他在这个村里就是个能人,走南闯北,大家伙也都习惯了。只是这一次,有些特殊,他走之前竟然没有和他们打招呼,不仅没有和他们打招呼,也没有和他老婆桂月打招呼。他失踪的第二天,栓虎又去找他喝酒,已经是晌午了,太阳热烈地照在院子里,菜园里的菜被晒得有些疲乏,绿油油的叶子失去了鲜艳的光泽。水井台上湿漉漉的一片水渍,桂月穿一件水红色的连衣裙,正撅着屁股洗头。
“朱彪呢?”栓虎高声地喊道。
桂月抬起头,头发丝上的水珠子不断往下滑,她用手背抹了一下脸,嘴角露出一个淡淡的笑:“谁知道呢,昨天下午出去,再就没见人回来。”
“你没打电话问问?”栓虎跨过围栏,从地里随手摘了一个西红柿,走到水井台前,拿水瓢舀了点水,把柿子洗了洗,喂进嘴里,啃了一口。
“打了!关机。”桂月又把头沉在盆里,用手扑拉着水往头发上撩,溅得水珠四射。
“我打一下试试。”栓虎蹲在花池沿上,从口袋里摸出手机,太阳光太刺眼,他用手遮在手机前面拨号。“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手机里清晰地传出话务员悦耳的声音。“奇怪,大白天关机。”栓虎自言自语着。他不甘心,又打了一遍,还是关机。他从花池上跳下来,打算走。
桂月喊他:“等等,帮我冲一下头。”
栓虎返回身,接过桂月递来的水瓢,慢慢地把水倒在桂月头上,桂月用手搓揉着头发,白皙的脖颈裸露在太阳底下,又白又嫩,像一段洗掉泥巴的藕。栓虎笑:“嫂子,朱哥不会是外面有人了吧?”
桂月把头发上的水撸干,拿起椅背上搭着的一条毛巾擦头,边擦边笑:“有了才好呢,我就省心了。”
栓虎也笑:“放心吧,谁都可能有人,就我朱哥不会,他那个死心眼也就只对你好。”
桂月:“那谁知道呢!”
栓虎:“嫂子,说了你别不信,上次我们几个去KTV,傻强叫了几个小姐,朱哥当场就翻脸了,拿起衣服就走,拉都拉不住。”
桂月:“这个呀,我信。”
栓虎:“话说回来,朱哥就是爱喝点酒,爱打个麻将,其他的坏毛病真没有。”
桂月已经擦完头发,齐耳的短发湿漉漉贴在脸上,她微微弯了腰,使劲甩头,头发梢的水珠子在太阳光下,像一颗颗珍珠玛瑙,被轻盈盈地丢了出去。
听了栓虎的话,桂月笑得有些得意:“要不然我嫁他?”
栓虎:“也是,想当年多少人稀罕你啊!一个个像苍蝇寻着卖豆腐的一样……”
“谁是苍蝇?谁是卖豆腐的?”桂月骂着,顺手拿起墙角的扫帚丢了过去,栓虎一个蹦子跳开,笑着走出院子。门口的大黑狗立马狂吠起来,引得后院的狗也开始叫。
桂月端起水盆冲着狗泼过去,骂道:“叫啥呢叫,再叫就把你卖了。”
狗被泼了个落汤狗,缩进狗窝里,只把狗头露出来,呜咽着,再不敢大声叫唤。桂月在村里,可是独独的一枝花,没嫁人时,家里就有钱,上面只有一个哥哥,从小被爹妈娇生惯养,再加上又长得漂亮,大眼睛,双眼皮,棱鼻梁,巧嘴巴,属于人见人爱的姑娘,正如栓虎说的,村里的小伙子个个稀罕她。她偏偏看上了没爹只有一个寡妇妈的朱彪。虽说朱彪长的有模有样,但家里穷,结婚时不仅拿不出一分钱彩礼,连结婚时穿的衣服、买三金的钱都是桂月问爹妈要的。桂月嘴巧,哄着爹妈说:“看人要看长远,你别看朱彪现在没钱没势,往后的朱彪,没人能比得过。”
真让桂月说着了,两人结婚后,朱彪仰仗着老丈人的关系从信用社贷了款,把家里的几亩果园全部挖了,建成养殖场,专门养猪。猪四个月出栏,卖给兰州、西宁的猪贩子,再买新猪种。几年后,他成了村上甚至镇上有名的养猪专业户,养殖场也扩大了好几倍。这不仅让桂月脸上有光,桂月爹妈的脸上有光,甚至是和朱彪一起长大的哥们儿弟兄都觉得脸上有光。他们几乎天天和朱彪腻在一起,喝酒、打麻将、胡聊天。有一年,朱彪还在家里挖了个鱼池,养上新鲜的活鱼,打算弄农家乐,结果也只乐了哥们儿弟兄,一个夏天,吃光了鱼塘里的几百斤鱼,后来,桂月说,她从老南街经过,一闻见烧烤摊前的烤鱼味,她就想吐。
朱彪的养猪场是独门独院,四周全是果园,中间开了条小路,直接通到县城新修好的一条大路上。朱彪经常出门,十天半月的不回家,桂月也不心慌,把两个娃娃往娘家一放,每天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的,就去镇子上打麻将。麻将桌上的时间过得飞快,一晃天黑,在麻将馆里吃了饭,再继续打,常常深更半夜才回家。
这样的好日子持续了几年,朱彪和桂月也风风光光地过了几年,虽说有钱了,但朱彪从来不在人前摆谱,该咋样还咋样。唯一不同的是更大方了,只要在外面饭馆吃饭,都是朱彪请客,从来轮不到第二个人掏钱。桂月也不计较,她对钱就没概念,从小到大也没为钱的事难肠过,所以由着朱彪胡吃海喝。
事情变糟糕,大概是从出现猪瘟那年开始,先是猪价猛地降下来,以前也遇到过这种事情,猪贩子来拉猪时,朱彪就留着没卖,心想过段时间价格肯定回升呢。结果,耗了两个月,价格又降了好几块,朱彪有些急了,几百头猪,一天的饲料就近千块钱,再加上人工工资,银行贷款利息,各种费用加起来,再强大的内心也经不住这么耗。还没等朱彪联系猪贩子呢,猪瘟又来了,从每天死几头猪,到死十几头,几十头猪,几百头活蹦乱跳的猪就这样一天天被抬出去。猪场也慢慢空了。年底的时候,猪场整个没猪了。银行贷款却来催账了。朱彪没办法,只好又找老丈人,以前是在农村信用社贷的款,现在去商行贷款,贷了新款还旧款,才勉强过了个年。
养猪场空了一年,朱彪再不敢轻易养猪,猪把朱彪的心伤了个透透的。后来,朱彪又养过牛,一头牛近一万块钱,买了十头牛,半个月全死了,找来兽医,才发现是以前瘟猪留下的病菌感染了牛。大家都以为朱彪垮了,结果半年后,朱彪喜气洋洋地从外地拉来几车小尾寒羊,栓虎帮着卸羊,大概数了数,有二百多只。栓虎问他哪来的钱,他说是赊的,半年后付款。栓虎咂咂嘴,也就他朱彪有这个胆量,乖乖,一只羊一千,二百只羊就二十万,哪辈子才能挣二十万啊。
这不,羊刚进圈不到一个月,朱彪不见了。
大家都猜测朱彪到外地躲账去了。除了这个理由,也再找不出别的说法了。
朱彪失踪的第二天,桂月把鸡窝棚里的十几只下蛋母鸡让哥哥开了个三轮车全部拉到了娘家,她对哥哥说:“让妈把鸡杀了,给几个娃娃擀鸡血面吃。”哥哥以为妹妹因为朱彪没回家在生闷气,也没多说话,直接拉了鸡就走。
朱彪失踪的第三天,桂月把两只大黑狗送人了,一只送给了娘家,一只送给了栓虎。栓虎高兴得不行,问桂月:“嫂子,你不会反悔吧?咋好端端把狗送给我啊?”
桂月脸上还是带着笑,笑里又带出些恼:“不要放下,废话咋那么多?”
栓虎哪能舍得放下,拉起狗就走。这两条狗可是朱彪从青海带回来的,类似藏獒的血统,个头大,虎背熊腰,叫声浑厚,能震住人。
桂月还是出去打麻将,一天不落。麻将桌上也有人问桂月朱彪到底去哪了,桂月满脸的无辜,摇摇头,拇指和中指灵巧地甩出一张牌,说:“七饼。”慢慢的,也就没人问了,都开始同情桂月,说朱彪不负责任,要跑也该带着桂月一起跑啊,哪能自己一走了之呢。
朱彪失踪的第十天,桂月把家里的二百只羊便便宜宜地卖了,只收了市场价的一半。所有人都眼红,但等知道时,羊已经出圈了。
大家都暗暗地说:“桂月这次是真生气了。”
刘蒜头说:“可能是信用社又来催贷款了,我那天看见田主任和桂月在镇上说话呢。”
翠翠说:“羊卖了,场子又空了,日子咋过呢。”
翠翠男人骂翠翠:“你好好活你的,操心都操不到点子上。”
这样的讨论天天在暗地里进行。在这个小村子,朱彪失踪了,比什么国家大事都重要。人们的生活里似乎已经离不了朱彪,他的存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存在,而是一种象征,梦想、富贵、希望、仁义等等。
似乎唯一不放在心上的反而是桂月。她就像一条鱼,以前怎么鲜活地游动,现在还怎么鲜活地游动。大家开始佩服桂月,到底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姑娘,就是能沉住气,要是一般的媳妇,早都寻死觅活地跳河去了。
半个月后,朱彪的寡妇妈也坐不住了,不知从哪得了个音信,她扔下了家里的鸡鸡狗狗,背上了一个小包袱要上新疆找儿子去了。临走前,她还来看了一眼媳妇,安慰桂月说:“娃啊,别急,妈这就出门给你找朱彪去,找到他,看我不打断他的猪腿。你就在家安心等着吧。”桂月拉着婆婆粗糙枯瘦的手,险些掉下眼泪,临出门时,她嘤嘤地哭起来,她说:“妈,你别去了,你从来没出过门,一下子就走这么远,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咋办呀?”老婆子也被媳妇说难过了,抱着媳妇好好哭了一场,临了,还是要走。桂月租了个车,把婆婆送到火车站,给买好卧铺票,买了一大袋吃的,又送进站,看着火车把婆婆徐徐带走,这才转过身,一步一摇地回了家。
最后找见朱彪的是警察。
原来他哪都没去,就在自己家里。
之所以找见朱彪,是因为有一个人先崩溃了。不是丢了丈夫的桂月,是喜欢上桂月的王强。王强也是本村人,有老婆,有孩子,和爹妈住在一个院子里。除了种地,也没啥正经营生,农闲的时候,喜欢到镇子上打麻将。自从朱彪失踪后,王强就变了,天天窝在家里睡觉,把被子往头上一蒙,好像世界从此和他没啥关系了。只要有人提起朱彪,王强的脸色就变了,苍白得像挂了秋霜的茄子。
中秋节晚上,正好是朱彪失踪一个月整,王强的爹提着一瓶酒进了王强的屋子。王强的媳妇和娃娃都不在,回娘家看爹妈去了。王强的爹把酒放在桌上,把王强从炕上一把扯起来,说要和王强喝酒。王强从被子里探出头,软塌塌地爬起来,爹已经把炕桌摆好,也没有下酒菜,爷俩就干喝。三杯酒下去,王强就憋不住了,两只手抱着头痛哭,眼泪鼻涕地胡乱抹。爹小声劝他:“强子,有啥事你给爹说,爹早都看出你心里有事,这样藏着掖着不行,纸包不住火,迟早要露馅。”被爹这么一说,王强的心理防线彻底坍塌,他这才一五一十的把事情告诉了爹。当天晚上,王老头一点都没有迟疑,拉上王强就去了镇派出所,又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警察。第二天一大早,警察就到了桂月家。
警察和王强来的时候,桂月并没在家,和表妹逛商场去了。王强指认了藏尸地点,就是院子里的鸡窝棚。朱彪被挖出来时,面容还好好的,像睡着了一样。头顶上有一道血口子,血迹干了,乌黑乌黑的,让人又想起那天早上吃剩下的馒头上面掉的醋汁。围着看热闹的人很多,大家全都默不作声,一时间这样的结果让人很难做出反应。大家这才明白为啥桂月要送走鸡,送走狗,卖了羊。
尸体被运走,有人第一时间给朱彪的妈打电话,没敢说朱彪已经死了,只说找到了,让她赶紧回来。接电话时,老婆子正走在乌鲁木齐的大街上,话筒里传来“羊肉串,现烤的羊肉串”的叫卖声。警察让王强给桂月打电话,王强颤抖着声音问桂月:“你在哪呢?”电话里,桂月的声音还是那么温柔,她说:“我和翠翠在商场呢。”警察给王强使眼色,王强努力地平复了一下心情,说:“你等着,我过去找你,有事给你说。”桂月竟然没有起疑心,她笑着答应了,然后挂了电话。
警察过去时,桂月正从二楼的滚梯上下来,旁边站着翠翠,两个面容姣好的女子,两个风华正茂的女子。没有人想到她们中的一个是杀人犯,而且杀的是自己的丈夫。真的没有人想到。王强也跟在警察后面,桂月看见了警察,看见了王强,她竟然没有惊慌,还笑了笑,把手里的购物袋递给翠翠,径直向警察走了过去。
事后,有人传出消息,说王强和桂月早就好上了,只是大家都蒙在鼓里。那天晚上十二点了,桂月给王强发信息,让王强马上来家里一趟。王强以为又是朱彪不在家,骑上摩托车就来了,进屋一看就傻眼了,朱彪躺在地上,头上全是血。两人在鸡窝棚里挖了坑,把朱彪偷偷埋了,从第二天开始,又风平浪静地过日子。
朱彪的妈从新疆回来,带着两个娃娃去监狱看桂月,桂月给婆婆跪下,抱着她的腿哭:“妈,我对不起你,娃娃就托付给你了。”
没有人知道桂月为什么要杀朱彪,也压根想不到桂月会杀朱彪,他们曾经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对。至于王强,简直是横插了一杠子,不该有的插曲。听栓虎说,桂月被警察带走时,只对王强说了一句话,她说:“我算看错你了。”
责任编辑/乙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