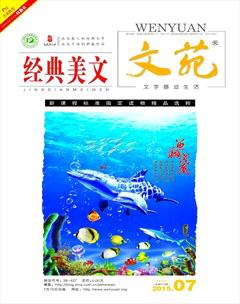衣魂
2015-07-14周芬伶
周芬伶
有一个衣柜,寄放在记忆阴芜角落,当我离去,它或许正在伤心哭泣。
衣柜是家庭权力的角力场。听说一个男人离婚的理由是每天打开衣柜时的梦魇,他太太的衣服张牙舞爪占领几乎全部的空间,而他仅有的三两件衣服紧贴柜角,被挤压成饼状块状,这大大伤害他的男性自尊,与其每天都要面对衣柜沦陷的恐慌,他选择的是拥有自己的衣柜。
他为什么不反攻,跟着太太添购衣服抢占地盘?只因他是个名士派,不屑借衣服装点门面,结果赢得了风范,却失去了衣柜,可见要在风范和衣柜之间取得平衡是件多么困难的事。
如果真要选择,女人恐怕会先抢占衣柜再说,抢赢的总是女人,许多男人面对女人在衣柜中开疆拓土的威力早就弃甲而逃。男人不屑与女人争夺衣柜空间,可并不表示他不在乎,他的权力欲望扩展在别的地方,他總是会反攻的。
刚结婚时,在那个群居的房子,我并没有自己的衣柜,单薄的几件衣服寄居在丈夫与四叔合用的衣柜,四叔的衣服占去一半空间,丈夫的皮衣、西装、夹克也颇有体积,我那红艳的嫁衣,虽然抢尽颜色,但薄纱的材质容易被欺压,原来光华慑人的小礼服被挤压得风仪尽失,形成虚幻的存在。我只能打游击战,生存的方式是无孔不入,皮包、丝袜、手套有缝即钻;有一阵子嗜买睡衣,只因它的材质薄体积小,抽屉的边角,吊衣橱的下档,或摊平或折叠,我选择这种悲凉的存在方式,因为意识到在这里生存不易。
母亲生长在旧式大家庭,深谙权力之道,她连夜亲自坐镇,从南部到北部押送一卡车家具和家庭用品,上自床组梳妆台,下至针线剪刀,无不齐备,可惜房间太小摆不下衣柜,她为我抢占的基地,总算稍稍扳回一城。可不久我那些小东西纷纷从柜子上败阵下来,有人嫌它碍眼,收的收,藏的藏,为此暗吞不少眼泪。
不久,我的房间也沦陷了,小叔进驻,丈夫与我退居三平大的小房间,重整格局,勉强塞进一个小衣柜,衣服总算找到归宿。其时孩子已出生,衣量暴增,衣柜里尽是婴儿衣服用品,丈夫与我的衣服只能是配角。可孩子的衣物甜美可爱,任谁都会甘心相让。仅余的空间就让我偏爱的长洋装翩翩飞入,里面还有一些私密的收藏;母亲送我的蓝色小化妆箱,里面装着象征圆满的龙银和一些母亲佩戴过的首饰,戒指上的珍珠已微微发黄,上世纪50年代的镶工颇有味道;我最爱那一双母亲结婚时戴的手套,象牙白的色泽如新,上面爬着同色系的锦绣和珠花。母亲爱美我也爱美,母亲的掌型饱满圆短,我亦如是。戴上手套时指尖是空的,玩弄那一截空令人晕晕然傻笑。有些事真的神秘不可说,爱的血流不可说,物的余情亦不可说。
当感情美好时,拥挤也是幸福,孩子、丈夫与我挤在狭窄的空间,自有挨紧的甜蜜与热闹,更何况丈夫信誓旦旦将给我们一个宁静无争的家园。我紧抱着这誓言,任孩子的玩具衣物淹到床上来,衣柜一打开总有什物掉下来,我们犹能翻滚嬉笑,写作时依偎着衣柜,挪出一尺见方的空间,在稿纸上创造另一个想象的次元。
为了善用空间,我的衣服尽选那价高质优的中上品,每年还得咬牙切齿淘汰几件过时的旧衣。幸存的几件都是精选,可也华美得像装饰品;譬如一件白色小外套,钉着金色扣子,配上白底紫花的长纱裙,只穿过一次。那一次听说是舞会,到场时发现大家都穿得很随意简素,一时对自己过度装扮恼怒极了,后来只有让它在衣柜中上吊自杀;还有一件樱桃色的麻纱长洋装,布料掺着一点丝质,细看暗闪着珍珠光泽,款式很简单,精彩处在后头,活动的系带成X形交叉,从背脊一路爬到腰间,只要抽紧带子,曲线展露无遗。我总以为那件衣服不是我的,而是属于另一个浪漫妖娆的女人,一如电影中的红衣女郎,只可远观,不可了解,真想看到某个人穿上这件衣服,暗中跟踪她欣赏她;另有一件黑色绣花V字领长洋装,是居住在美国那一年买的,胸口开得很低,美国的女装大半如此,长度很惊人,踩上三寸高跟鞋还拖地,如此不实穿却流连再三。服装店就在埃蜜莉·狄金逊生前住过的房子附近,后来看她的画像,才明白为什么执迷于这件衣服,与她穿的衣服十分相似,是新英格兰的黑,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从上世纪延伸到本世纪,倘若衣眼也有魂魄,辗转流离,怕也脆弱得不堪轻触。我供奉那袭衣魂许久,并添购一双黑色缎面镶水钻高跟鞋,水钻沿着X形细带交错,围着足踝闪着泪光,美得令人心碎。有一次盛会,穿上那袭黑衫搭配缎鞋,整个人似乎也变成一缕幽魂,许多人的眼光落在我脚上,水钻确有夺人心魄的力量,我的心快要跳出胸腔,衣缕变得千斤万斤重,衣眼真有魂魄么?它不能忍受轻佻的注视,我在宴会中途就逃走了,锦衣夜行,多么可悲的命运!
我怕别人太注意我,可也忍受不了别人的漠视,真矛盾!这样就很难抓到装扮分寸,我的服装语言就是如此不切主题,失心丧魂。然而,一缕缕衣衫垂挂在衣柜时是如此安适,仿佛已经找到灵魂的依归。谁知道,当我的衣服住下时,我的心灵已然远走。
心灵是漂泊者叛逆者,婚姻令女人的心灵更加叛逆,美丽的衣裳只是暂时的伪装,衣柜也只是最后的栖息地,不久它将以薄纱之翼起飞,随着衣魂飘荡,飞至广漠无人之处。
现在我独自拥有一个大衣柜,体积有以前的两倍大,只装我一个人的衣服。穿衣不照镜,开橱不浏览,生活变得干净无心,我不怀念以前的华服,只是有时翻到孩子刚出生时穿的小袜子,会趺坐下来呆看许久,我真的曾经拥有一个美丽的小婴儿?他痴恋着母亲的怀抱,我痴恋着他的一切,他真是我的?我生的?我养的?还有那些钉满珠子亮片的印度灯笼裤、阿拉伯织花毛披肩、重约一斤的密钉珠花围巾……,那真是我的?我买的?我穿的?
我遗失了一个衣柜,那里有我不忍回首的华美收藏、绮罗往事;还有一袭袭装载过虚荣身躯的锦绣云裳;屈辱的压迫和空洞的誓言。我无意加入家庭权力的角力,女人需要的不是一个床位和些许的衣柜空间,她需要的更多。有时我想到那双似乎闪着泪光的镶钻缎鞋,当我离它而去,它还在继续行走,以我不知道的步伐,走向我不知道的未来。
摘自花城出版社《窥梦人——新世纪台湾散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