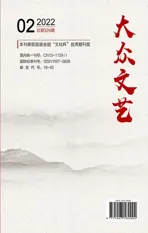穿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张枣诗艺探究
2015-07-12郑艳娟黑龙江大学150080
郑艳娟 (黑龙江大学 150080)
钟鸣曾评价当代的诗人,曾有两位诗人的诗不曾有败笔之作,一位是柏桦,另一位就是张枣。而对于张枣,他对自己的诗歌有着自己的坚持与原则,越是这样,他对自己的要求越高,他曾学习多种语言,为的就是如何能够更好地作现代汉语诗歌,即便是这样,他不曾降低自己诗歌创作的标准。也是因为这样,他对他曾写过的很多诗都不满意,都废弃了,这一点颇像马拉美。有人称,如果马拉美能够少一分宁为玉碎的心,可能更伟大。这一种情况可能也会发生在诗人张枣身上,但是即便不是这样,张枣也无疑是一位优秀的不可多得的天才诗人,他在22岁不到的年纪就已经写出了《镜中》《何人斯》这样的鼎力之作,而他的好友诗人柏桦对他的评价更高,在2010年张枣逝世,柏桦写下了近三万字的回忆性评论,最后,他痛苦与惋惜地称张枣的离去,给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的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自早期白话诗以来,新诗的“现代性”追求主要体现在学习西方的诗歌,这一论断早在朱自清先生的文集中就有明确的表示,虽有胡适等人提出的以中国的民谣入诗,然而最直接的方法和渠道还是师从外国诗人。我们在研究现代乃至当代的诗人,我们不难发现,很大一部分诗人在早期阅读过程中都接触到西方的诗歌,比如艾略特、波德莱尔、史蒂文斯、雪莱、惠特曼等诗人的诗,以及中国新诗的创作历程,使得包括张枣在内的80年代诗人既兴奋又迷惘,无疑,汉语诗的“现代性”问题是他们的关注点。在张枣,这个来自“人杰地灵”的湖南,活动于四川成都的青年诗人眼中,显然他的诗歌追求是有自己的观点的,也就是将中国的传统与诗歌的现代性结合。这个诗学观念早已不新鲜,早在白话诗开始,就有一批一批的诗人践行着这个理念,比如说朱自清、戴望舒、卞之琳等。然而当诗歌发展至当代,张枣却将其应用的更加纯熟,这种风格已经变成诗人的血液,同时也演变成了他的诗歌的血脉。在最初一接触张枣的诗歌时,有一种非常模糊却又很舒服的感觉,他的诗歌有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东西在里面。这种感觉很微妙,但是你是可以感受的到它的存在的。他的传统是一些意象的运用,或者也可以称之为“情景交融”的意境的存在,但是他的表达却是很现代的,很前卫的,有断裂的地方。张枣的这种诗歌风格曾被以创作口语诗的韩东高度认可,他称张枣的诗歌根植传统文化的土壤,却会带你领略到异国文化的风情,他的“化欧化古”的诗风堪称卞之琳再世,其好友柏桦也如此评价他的这位天才诗人朋友,“但在颓废唯美及古典汉语的‘锐感’向现代敏感性的转换上又完全超过了卞先生”,可见,在融汇传统与现代于诗歌一体的造诣上,我想张枣还是略高一筹的。在他的一首意境唯美的诗《镜中》里: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这首诗歌重构了我对于好诗的定义,在这首诗中,好诗的标准抛却了寻求终极意义这一层面,无关现实与理想的指涉,也无关写作者的姿态或者他们是什么目的,对于我,好诗就是无论时间怎么变迁,人们都会一如既往的喜欢阅读它,品味它,至于品味出个什么结果,那并不重要。我个人认为诗歌能保持这样恒久的魅力的典范就是张枣的这首《镜中》,我看过很多版本的对于这首诗的解读,其中的一个版本是:此诗“讲述一个匿名者的故事”,“一个女子的越界行动”,诗中女子 “她的感应力大到可以叫梅花应念而落,与其让巨大的悔意埋葬一生,不如在惩罚临前做点什么”,于是催生了女子的勇气。也许是,诗中“皇帝”的字样代表一种规训或者是一种约束力,所以有回答问题时的羞惭与低头,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看似女子勇敢越界的论断;版本之二是诗人刘春在他的论著《一个人的诗歌史》中张枣一章对《镜中》的理解,按刘春的原话说:“当然,如果一定要说出个子丑寅卯,我们可以把它当做对美的膜拜与思考或者对理想生活的描绘与憧憬,而我更倾向于另一种解释:一个过去年代的书生对着镜子回想起往事时的怅惘与懊悔,他‘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对《镜中》这首诗的解读就更丰富了。
我个人也很喜欢刘春版本的解读,但是我更倾向于对这首诗整体流露出一种很微妙的感觉和情绪的关注。首先,诗中的人物,是“匿名者”也好,“书生”也罢,总之他/她看似实际存在其实是很模糊的,也就是说他/她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两个人,三个人;可以是女人,同样也可以是男人;可以是照镜子之人,也可以是旁观者。其次,这种很微妙的真切而又模糊的感觉和情绪,来源于诗中开头和结尾对时间的分辨率的描写。这是很抽象的,但是诗人却让时间具体到了梅花飘落的物象上。一个人,不管他/她是谁,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此时此刻,能恰好感觉到梅花的飘落,而梅花飘落的姿态应该是轻盈曼妙的,而这个飘落的很缓慢、很唯美的过程正是回忆一生中后悔的事所用的时间,时间在这一刻能够被清晰的分辨出来;到了诗的结尾,当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了。每一瓣梅花的飘落,他/她都能清楚的感觉到,因为他/她在追忆,直至时间久的后知后觉梅花已经落满山头。而我把这种微妙的感觉和情绪归因于诗人张枣一直强调的传统精神与诗的现代性的融合的诗学观念,
张枣诗歌“化欧化古”的风格,使他的诗歌书写穿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对于传统坚持,除了对诗歌意境的追求,另一方面是在语言上对“母语”的关注,他肯定一种“寻找母语”即对汉语现实的关注。从另一角度上,诗人对诗歌长久以来的“现代性”的探索也作出了尝试,自新诗发轫以来,首先是对语言的一个“现代性”的诉求,这是向西方诗歌开放,与西方接轨的必然性。从创作主体来看,这也可称之为诗人张枣的“写作的焦虑”:诗歌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之间的关系?如何使诗歌写作获得“有效性”?我想通过张枣的诗歌,我们可以获得一种解答。
[1]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颜炼军.张枣随笔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3]宋琳、柏桦.亲爱的张枣[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4]刘春.一个人的诗歌史(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