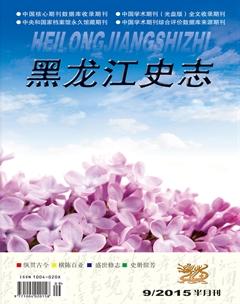试论中西方“变形”思想意蕴之差异
——《变形记》与《向杲》比较研究
2015-07-10李园
李园
(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 湖北 黄石 435002)
试论中西方“变形”思想意蕴之差异
——《变形记》与《向杲》比较研究
李园
(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 湖北 黄石 435002)
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与蒲松龄《聊斋志异·向杲》中的向杲都是人异化为物的故事,但两者却有着深刻的差异:《变形记》体现的是外在的物的世界和异己的环境对人的挤压,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而《向杲》则体现了中华民族“善有善报”的良好愿望,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文章从思想意蕴角度对《变形记》与《向杲》进行比较研究。
《变形记》;《向杲》;思想意蕴;变形;比较研究
一、在外界环境下,是否丧失自我
《变形记》这部小说通过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大甲虫的荒诞故事,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做出深刻揭示,是典型环境下的丧失自我的悲鸣和寻找自我的失败。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俱来的普遍现象。卡夫卡曾说:“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托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那里,我们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在这里,人变成了“物品”,“物件”,任由其生活的环境支配。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看似荒诞不经,实际上却荒诞中透露着真实,由于外在物的世界和异己环境的挤压,寻我自我失败,人已经丧失自我,沦为“非人”。[1]格里高尔在生活的重压下寻找自我价值,但最终却彻底失败了,变成了一只人人恐惧,厌恶的大甲虫,其生活方式也和甲虫一样,表现了,寻找自我的失败,丧失自我的悲鸣。《聊斋志异·向杲》中的向杲却与格里高尔不同,蒲松龄塑造的向杲,是一个异化成老虎为堂兄报仇的有情有义的男子,堂兄向晟被当地财大气粗的庄公子打死了,向杲想为堂兄报仇,但多次尝试后都已失败而告终。向杲作为人无法报仇雪恨,受尽了庄公子的欺辱。向杲想过去官府告状?但是庄公子却和官府勾结,官府与地方豪强勾结,在此,蒲松龄向读者揭露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向杲想自己私自杀死庄公子,但是庄公子周围有很多护卫。后来向杲在偶然间救了一位道士,这个道士给了他一件破破烂烂的衣服,因缘际会,他穿上之后就奇迹般地变成了一只老虎,最终咬死了庄公子成功地为堂兄报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向杲作为一名底层的普通老百姓变成老虎都是黑暗的社会现实逼迫的,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丧失自我,虽然有老虎的外形,但他不是纯粹的虎,因为在它复仇的时候完全具有人的思维;老虎的外形,人的的心理活动,而且它的目标很明确,复仇之后,机缘巧合之下,又恢复了人身的向杲。其实,不管是人形的向杲还是虎形的向杲,都是一回事,是向杲的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互相补充的存在形式。因此,向杲并没有丧失自我,而格里高尔在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下却丧失自我,变成了大甲虫,最终格里高尔的生活习惯和思想也和甲虫相似了,完全丧失自我。
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走向不同
《变形记》里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是一个十分冷漠、无情的“物”的世界。他为老板工作是因为父亲破产,欠老板的债无法偿还,这就决定了他在公司中的地位,他不能象其他人那样享受充足的睡眠,他不敢把怨气向老板发泄,只能背着生活的重担,忍受这种种难以言说的屈辱,谨慎地工作。他的老板“总是那样居高临下地坐在桌子后面对职员发号施令”,他与老板之间没有人情的温暖,只有冷冰冰的“物”,“债务”和“雇佣”的关系。格里高尔与同事的关系也是非常糟糕的;和客户之间,更是“萍水相逢”,“总是些泛泛之交,不可能有深厚的友情,永远不会变成知己朋友。”[2]格里高尔在变成大甲虫之前与家人的关系是怎样的,关于这点,卡夫卡在小说中并没有向读者作出交代,但作者却描写了格里高尔变成大甲虫之后家人对他的态度:嫌弃他、怕他、厌恶他。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格里高尔的生活环境是一个没有亲情和温暖的冷漠的“物”的世界。血浓于水的亲情在格里高尔生存的环境里完全丧失了,格里高尔勤勤恳恳地为家人的生活而奔波,但是当他在外界的挤压下“异化”之后,家人赤裸裸地抛弃了他。而向杲不同,向杲为堂兄向晟报仇,体现了他和堂兄之间的兄弟情深。当向杲得知哥哥被打之后,急忙赶去现场,结果很可惜,他去晚了,哥哥已经被打死了,满腹冤情的向杲心急如焚,最终在道士的帮助下大仇得报。那么,这位道士为什么会帮助向杲呢?原因是这位道行高深的道士在村里求斋时,善良好心的向杲经常给他饭吃,于是道士与向杲比较熟悉,就助他报仇。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向杲的生存环境中,人与人之间互相关怀,体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除此之外,向杲家人对他的关心也体现了亲情的温暖,由于向杲为堂兄报仇期间好几个晚上没有回家,家人正在为他担心着急时,看见他回来,都高兴的慰问他。这体现了向杲的家庭中有亲情的温暖与关怀,与格里高尔的家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东西方“变形”的艺术象征之差异
读完卡夫卡的《变形记》时,也许我们会有这样一个疑问:主人公格里高尔为什么变成了大甲虫,而不是别的动物,或者为什么卡夫卡偏偏选择了“大甲虫”这个象征意象,而不是其他一些昆虫,如瓢虫、毛毛虫、苍蝇或者蚊子呢?经过几番思考之后,得出结论:卡夫卡之所以选择“大甲虫”这个艺术象征,是有其深层含义的,他并不是随便找个昆虫来描写的。“大甲虫”是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艺术象征,它象征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异化”处境,它象征了自我的一种怯懦,逃避和封闭。卑微的小人物是无力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抗衡的,它只能躲进甲壳中,忍受孤独,冷眼世界,在孤独中绝望,在绝望中死去,这是格里高尔的悲哀,更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悲哀。[3]作者卡夫卡选择“大甲虫”这个隐喻式象征,是觉得“甲虫”最符合格里高尔的形象,甲虫与苍蝇和蚊子相比,它有一个笨重的“大甲壳”,这个笨重而坚硬的“甲壳”象征了格里高尔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和生活压力,而且还象征了格里高尔看似外表刚强,实则内心脆弱。与此同时,“壳”也象征了一种阻碍,它像一堵无形的墙一样阻碍了格里高尔与外界的人际交流。那么,问题来了,向杲又是为什么化为“老虎”,而不是别的动物呢?庄公子打死了向杲的堂兄,向杲具有强烈的复仇之心,可能蒲松龄认为“老虎”这个意象正好符合向杲的人物形象,老虎凶猛,有勇有谋,化虎食仇人,既能报仇雪恨,又能保护自己。除此之外,中国人有“老虎情结”,在中国,老虎被誉为“百兽之王”,不仅是因为它额头上与生俱来的“王”字,更是因为它威武,力量的形象。中国人从原始时代开始,就对老虎怀有一种崇拜的情结。原文中作者幻想向生化虎报仇,强烈赞扬受害者个人反抗的精神,表明了蒲松龄先生对黑暗恶势力现实的憎恨。[3]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中的“虎文化”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虎”这个艺术象征最符合向杲的人物形象,代表了力量与正义,符合中华文化中大众的审美需要和心理倾向。
综上所述,同为“变形”,但中西方的“变形”在思想意蕴方面却有着深刻的差异,这主要是中西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差异使然。
[1][2][3]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下)(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17-121.
[4](清)蒲松龄著,中山大学中文系《聊斋志异》选评小组评注.评注聊斋志异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213-215.
李园(1990-),女,陕西商洛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汉语修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