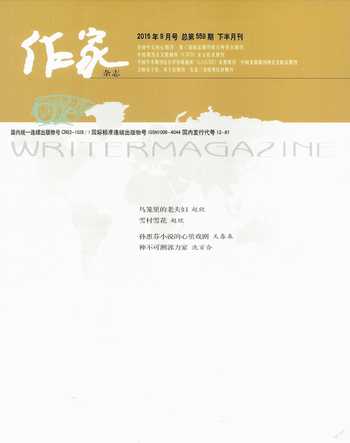意的自然呈现:皎然“作用”说论略
2015-06-30王明强包玉颖
王明强 包玉颖
摘要 皎然作用论内涵来自佛典,是指向诗意而言。在佛典中,“作用”的基本意涵是性与体自然呈现出自身之相。运用到诗学领域,也就是诗意的自然呈现。中唐时期,诗歌创作从以风神情韵擅长到以筋骨思理见胜转型,诗歌创作中的“意”逐渐凸显,天机渐失。皎然的作用论为主意的诗歌创作提供了通向“风流自然”艺术境界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作用 意 自然
皎然在《诗式》卷一中有“明作用”条目:作者措意,虽有声律,不妨作用,如壶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时时抛针掷线,似断而复续,此为诗中之仙。拘忌之徒,非可企及矣。
皎然是将“作用”引入诗学领域的第一人,在《诗式》中共计11次出现“作用”这一术语。“作用”有着特殊的诗学思想价值,但其具体内涵长期以来却隐蔽不彰。目前大陆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作用”就是“艺术构思”,这以郭绍虞先生为代表。但以“艺术构思”来解读《诗式》中的“作用”,很难将其诗学思想融会贯通。究竟如何来正确把握“作用”的内涵,笔者认为应从其理论产生的背景、“作用”的基本含义以及皎然在诗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三个方面来考察。
一
任何一种理论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诗式》就是诗歌转型需求的必然结果。皎然《诗式》完成于唐中期贞元年间,而这一时期正是唐代詩歌由盛唐向中晚唐转型,也是整个中国诗学转型的重要时期。
中唐以前,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其创作范式是追求“自然英旨”,讲求“直寻”,任情任性。其理论代表是钟嵘的《诗品》。钟嵘诗学侧重诗的自然天成,其诗学思想核心有二:一是诗歌缘起上的“感兴”论,一是诗歌创作上的“直寻”。
中唐以后,诗歌创作逐渐走向以筋骨思理见胜的道路。尤其是宋诗,重法度,讲技法,重视苦思。皎然的诗学思想正是基于诗歌创作实践的转型上。对于皎然的“四变”,李壮鹰概括说:“览《诗式》全书,似可看出:皎然以苏、李诗天籁自成,不见作用为最高。《古诗十九首》初见作用,为一变;谢灵运尚于作用,为二变;齐梁诗雕绘偶丽,为三变;沈、宋创制律诗,为四变。”很显然,四变中,诗歌创作从自然天成向人为雕琢转向。到了皎然所处的中唐时期,诗歌创作追求诗格、诗境,苦思立格、苦思取境的诗学观念萌生。对于诗歌创作的这种转向,皎然明显持否定态度。这在他的五格论诗中得到具体体现。“不用事第一格”是皎然最为推崇的任情任性,不假雕饰,自然天成的诗歌最高境界,却几乎没有列举唐人诗句。在“作用事第二格”中也仅列举唐人诗8家,到了“有事无事第四格”则选唐人诗多至29家,在“有事无事情格俱下格”中更是多至35家。显然,在皎然看来,他所面对的诗歌创作已是江河日下,与西汉之初及以前的浑然天成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人类的发展历史是人为逐渐掩盖天机自然的进程,反映在诗歌创作上,亦然。也正是面对这样的诗歌创作实践,皎然要为恢复诗歌的自然天成打通道路,这也正是他创作《诗式》的目的之所在。
正是忧患于“洎西汉以来,文体四变,将恐风雅寝泯”,作者才“辄欲商较以正其源”,而其目的正是“使无天机者坐致天机”。通观皎然《诗式》全书,其基本诗学思想就是人为与自然的统一,即人为而不失自然。
谢诗在当时是以自然著称的。但其自然是人为之后的自然。康乐公正是由于“尚于作用”,才达到了“风流自然”的境界。在皎然看来,“未有作用”、浑然天成的诗歌最好,但在诗歌创作日渐从混沌走向雕琢的情况下,如何“使无天机者坐致天机”,提高诗歌的艺术境界,这就需要“作用之功”,就需要“尚于作用”。可见,“作用”是实现诗歌创作人为与自然统一的枢纽,通过“作用”,诗歌创作就可以达到“如壶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的自由境界。那么,“作用”作为诗学理论,其内涵究竟是什么呢?这要首先来探究“作用”一词的基本含义。
二
作用一词原指“有功能,起功用”之意。比如《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五引《说文》曰:“筋,体之力也,可以相连属作用也。”但仅仅“艺术构思”是无法达到“如壶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的自由境界,也无法实现诗歌创作的“风流自然”。因此,“作用”一词定另有内涵。
“作用”一词后来大量出现在翻译的释典里,其意义有了新的含义。皎然是一位诗僧,长期浸润于佛学之中,其诗学思想受到佛学影响是无疑的。
很明显,《诗式》的成书与编定都与禅学思想脱不了干系。那么,“作用”在佛典中到底是何意?我们从佛经中取例加以剖析:
唯声为体,其名句文,但显佛教作用,非佛教体。(《圆觉经略疏之钞》卷八)
所谓“作用”就是佛本体的显现。禅宗认为人人皆可为佛,“作用”也就是人自性的显现。被公认为中国禅宗正系的洪州禅最富有特色的理论就是“作用见性”。“作用见性”也作“性在作用”,据说印度异见王与波罗提尊者在一次谈话中最先语及。
作为成佛依据的佛性必须通过人的外在行为展现出来,这就是“作用”。具体说来,就是眼作用为见、耳作用为闻,鼻作用为辨香,口作用为谈论,手作用为执捉,足作用为运奔。禅宗虽认为人人皆具佛性,但一旦“以业识惑病所拘”,就不能“神变作用”。
在佛典中,“作用”与“功能”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作用不仅仅是发挥功能,而是要“生相”。否则,“生相未来但起功能非是作用。”而且生相是“无有等无间缘”,不是“现在顿取过去渐与者”,不是“异时取与”,而是“现取果”,是自性的当下显现,是当下完成态,是自性的一种自由的无障碍的显现。作用并不是平常所能达到的,而是顿悟佛性之后的境界。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佛典中,“作用”已超越于“功能”义,指“功能”的完成态,而且是功能的自由、自然的完成态。更概括地说:是指物之“性”与“体”自由、无障碍地呈现出自身之“相”。
三
我们来分析一下皎然在运用“作用”这一词汇时的具体指向。皎然提到“作用”共 11次,除“作用事”是指向事外,另外都是指向“意”:
作者措意,虽有声律,不妨作用。(《诗式卷一·明作用》)
连贯起来看,“作用”要“放意”“ 措意”,“深于作用”则可以“意度盘礴”。由此,可以初步判定:在皎然诗学思想中,“作用”应该是针对诗中的意而言。
中唐时期,诗歌创作由情向意转型,陆时雍对杜少陵诗作的评价可为我们提供一点佐证:
少陵五古,材力作用,本之汉魏居多。第出手稍钝,苦雕细琢,降为唐音。夫一往而至者,情也;必然必不然者,意也。意死而情活,意迹而情神,意近而情远,意伪而情真。情意之分,古今所由为矣。少陵精矣、刻矣、高矣、卓矣。然而未齐于古人者,以意胜也。假令以古诗十九首与少陵作,便是首首皆意,假令以新安石壕诸作与古人作,便首首皆有神往神来,不知而自至之妙。(《诗镜总论》)
面对中唐时期的诗歌创作,如何形成诗歌丰富的意旨,是皎然思考的重点。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钟嵘《诗品》与皎然《诗式》作一比对。钟嵘以“情”论诗。在《诗品》中,“情”是诗歌的源动力,诗歌要“穷情写物”“骋其情”“情寄八荒之表”。与钟嵘推崇情不同,皎然不但对诗歌中的“情”加以限制:“雖期道情,而离深僻”(《诗式卷一·诗有四离》)。而且明确提出 “思致”“尚意”:“虽欲废巧尚直,而思致不得置;虽欲废言尚意,而典丽不得遗。”(《诗式卷一·诗有二废》)。 相对于钟嵘论诗以“情格”居上,皎然五格论诗明显以意格为主而以情格为辅。因此,在诗学思想的核心指向上,钟嵘是“情”,而皎然是“意”。联系到“作用”在佛典中的基本内涵,在皎然的诗学思想中,“作用”应该是诗歌中意自由、自然地呈现。
“意”与“情”不同,正如陆时雍所言,“夫一往而至者,情也;必然必不然者,意也。意死而情活,意迹而情神,意近而情远,意伪而情真。”相对于尚情“直寻”的诗歌创作,主意的诗歌创作就要进行较为艰苦的艺术构思:
或云,诗不假修饰,任其丑朴,但风韵正、天眞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无盐阙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又云,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不然。葢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诗式卷一·取境》)
但苦思并非就能创造出艺术性高的诗歌。即使精心构思,精雕细琢,倘“情少”“无含蓄之情”,“无作用”,没能呈现出具有内涵的诗意,也不是好的艺术作品。经过苦思,且“深于作用”,才能达到“意度盘礴”的诗歌境界。既要“词归一旨”,又要“兴乃多端”,也就是诗意的丰富性和意味的无穷性。也就是皎然所推崇的诗意“两重意已上”。
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向使此道尊之于儒,则冠六经之首,贵之于道,则居众妙之门;精之于释,则彻空王之奥。但恐徒挥其斤而无其质,故伯牙所以叹息也。(《诗式卷一·重意诗例》)
倘能如此,也就达到人为与自然的统一。这也就是皎然对主意的诗歌创作所提出的理想和追求:
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诗式卷一·诗有六至》)
面对中唐时期主意诗学观和苦思立格、苦思取境的诗歌创作实践,面对诗歌创作中“意”的逐渐凸显和天机渐失,皎然的作用论为当时的诗歌创作提供了通向“风流自然”艺术境界的桥梁。
四
那么,皎然的“作用事”又如何解?对于皎然五格论诗中的不用事、作用事、直用事、有事无事到底作何解,学界多有争论。
考之皎然五格论诗所引诗例,作为“用事”实例的陆机诗是列入“直用事第三格”。按照皎然的论述,征古是否为用事,区别的标准是“古事”与“诗意”是否完全对接。陆机引用古代完整的故事来申述规谏之义,是移用了古代的整体意象,所以就是用事。而谢灵运以自己之意来综合张良、邴曼容、谢安来形成自己的意象,则并不是用事,而是比。
综合起来看,皎然所谓的“用事”就是“直用事”,而且“直用事”的诗作艺术境界并不高,只能列入第三格。
所以,不用事就是“兴生于中,无有古事”,创作方式是“直寻”。这一点与钟嵘的诗学思想是一致的。
再考之皎然“作用事第二格”所引诗例,可以看出,“作用事”用典,不是直接移用古事的整体之意,而是经过融会,使古事与诗意浑然一体,是皎然所言的“比”,亦非“用事”,也就是皎然所说的“语似用事义非用事”。这是皎然所推崇的征古、用典的方式,所以他说“弱手不能知也”。综合融会古事,浑化无迹,使之有“作用”,呈现出丰富的诗意,方能列入第二格。否则,“有功而情少”“无含蓄之情”“无作用”的诗句则“宜入直用事中,不入第二格”。“直用事第三格”以下皆是“无作用”的诗作,也就是诗意流于刻露,没有得到自然的呈现。
参考文献:
[1](清)叶燮:《己畦文集》,卷八康熙刊本。
[2](唐)释宗密:《圆觉经略疏之钞》,清宣统三年刻本。
[3](唐)释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明万历三十五年刻本。
[4](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四部丛刊三编本。
[5](唐)釋智周:《成唯识论演秘》,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王明强,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副教授;包玉颖,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