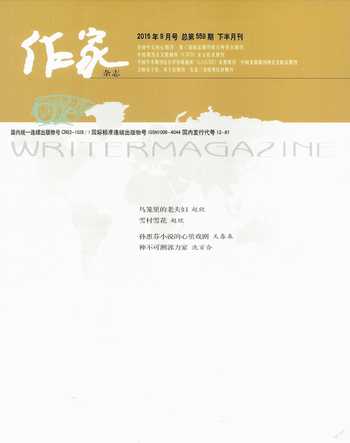试论中唐骚体的创新方面
2015-06-30穆伟
摘要 中唐骚体文学既有对原初骚体的继承,又有自己独有的艺术特色。在继承的同时中,唐骚体文也有自己创新的方面,如在内容上:涉及文人因科举考试或因仕途背井离乡、远离家人,而产生的对故土亲人的思念为内容比较多。在艺术上作品中议论化的成分加重;出现了一批哀怨愤懑情绪后升华为昂扬向上的豁达情调的作品;语言上也更多的多样化。而且这一时期的骚体也受到了传奇的影响。
关键词:中唐 骚体文学 创新方面
骚体,即楚辞体,是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它诞生于战国,经由汉魏唐宋,一直到流传直到清末,形成了一整套相对独立的完整体系。虽然汉以后,骚体文学一直没有成为主流的文体,但它却历经几千年顽强的保存并发展了下来,并在每一个朝代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及士子心态。艺术源于生活,文学艺术也不例外,它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孤立的存在。文学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背景,中唐特殊的社会形态,对骚体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十分大的影响。安史之乱是唐代由兴到衰的转折点。从国力上来看,此时的唐朝已经远远没有了初唐,盛唐时期那种强盛的气派;从治国策略上讲,藩镇割据使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只能维持表面上的统一。从国情上来讲,8年的安史之乱,使人民饱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之苦,中唐以后政府黑暗,沉重的负担使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这个时期,内忧外患的国情使那些曾经历过“大唐盛世”的文人们开始直面盛世后衰落,深刻的反思,希望找到变革的方法,实现国家中兴。他们献计献策并付之以实际行动。如对安史之乱后日益加剧的藩镇割据,文人们主张以武力削平藩镇。除了政治操作之外,中唐士人还发起了著名的古文运动,复兴儒学,想通过对社会思想的重建达到国运的振兴。文人们的这些忧患意识与屈原在面对楚国灭亡时的情感遭遇是很相似的,由于在情感上的共鸣,使骚体文学在中唐文人们的感慨与怨愤声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较之初唐、盛唐出现了更多的骚体作家作品,实现了骚体文学在中唐的兴盛。
中唐骚体文学是有唐以来骚体创作的巅峰时期,文人们在继承原初骚体的同时,又积极探索新变,起到了很好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为后世骚体发展影响深远。
中唐骚体文学的创新方面主要体现在内容和艺术两方面。
一 就中唐骚体文学的内容而言
首先,由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此时的骚体带有更加浓重的政治色彩。“安史之乱”后,士人们目睹此时国家纷乱的局面痛定思痛,中国文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开始对盛世的衰落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找到变革的方法,实现国家中兴。如李翱的《幽怀赋》中写到:“自禄山之始兵兮,岁周甲而未夷。何神尧之郡县兮,乃家传而自持。税生人而育卒兮,列高城以相维。何兹世之可久兮,宜永念而遐思。有三苗之逆命兮,舞干羽以来之。惟刑德之既修兮,无远迩而咸归。当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赢师。能顺天而用众兮,竟扫寇而截隋。况天子之神明兮,有烈祖之前规。划弊政而还本兮,如反掌之易为。苟庙堂之治得兮,何下邑之能违。”割据的局面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战事连连,国将不国,作者心中并不存在对自己卑微身世的伤感,而是对于现实国家危在旦夕的担忧。全文贯穿始终的是国事。再如,《释怀赋》“邪何德而必好兮,忠何尤而被疑。彼陈辞之多人兮,胡不去众而讯之。进草言而不信兮,退远去而不获。弗验实而考省兮,固予道之所厄。”作者谴责那些治国之人昏庸,使那些真正想为国出力的士人们被陷害直至入狱,他为君子鸣不平,为国家命运忧虑。
其次,涉及文人因科举考试或因仕途背井离乡、远离家人,而产生的对故土亲人的思念为内容比较多。科举发展到中唐已经相当成熟,士子们十年苦读,只为科举进身,为此他们不得不远离故土亲人,参加考试,由此产生的对亲人家乡的思念,常常用骚体的形式写出。此外,仕宦中也有不少不得已离开故土赴任或是被贬的,他们身在异乡,有家难回,所以也常常把对故乡亲人的魂牵梦绕之感用骚体表达。这类内容在李观、白居易、欧阳詹等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如欧阳詹的《出门赋》,作者回想起当年离开家时父母妻子的叮咛嘱托“严训戒予以勿久,指蒲柳以伤秋。弱室咨予以遗归,目女萝而起愁。”家中的亲人都盼望着自己早些回去,一想到这里,诗人思乡思念亲人的情感立即跃然纸上“心眷眷以缠绵,泪浪浪而共流。”父母妻子盼己早归,但是由于赶考不顺利,自己已陷入两难境地:“逮前程之尚遥,顾所离而日远。事纷擎以争拔,情交庆而不和。退藩篱则弱羽恋于云路,激龙门则纤鳞限乎尺波。”“身违日日之晨昏,恋凄凄而莫遣;亲益年年之赢老,思摇摇而若何。”诗人强烈的思乡之情溢于言表。
二 就中唐骚体文学的艺术而言
首先在表达方式上,这个时期的骚体出现了明显的议论化倾向。中唐的骚体作家们提倡以意为主,议论的成分多。如刘禹锡《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便直接说:“古之为书者,先立言而后体物,贾生之书首《过秦》,而荀卿亦后其赋。”柳宗元《读韩愈(毛颖传>后题》也斥责骄体的“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这个时期议论化已成风气,作家常常在骚体作品中直抒胸臆,如皇甫湜《东还赋》,在艰苦的生活面前,他说:“安读书之下炜兮,乐儒行之环堵。苟吾道之无爽,又何陋焚斯土。顾言行之有常,虽蛮夷兮可处。”以为环境恶劣并不足惧,重要的是坚守大道。李翱的《幽怀赋》与《释怀赋》两篇作品就像政治论文:《幽怀赋》指出了国家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方案,文章开门见山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自己是“虑行道之犹非”,而非“咸磋老而羞卑”,用颜回为论据来论述“悦中怀之自得兮,终老死其何悲?”的观点。提出國家应该弃弊政、修刑德,这样才能长治久安。虽然诗人敢于面对黑暗的社会,也想为国家的中兴付出自己的全部,可是却没有人可以理解他,怨愤之情犹然而生;《释怀赋》是一篇为正人君子鸣不平的论文。皇甫湜《伤独孤赋》也提出了对人生的看法:“闻古人所孜孜兮,贵身没而名存。颜冉不登下寿兮,无百里而愈尊。齐梁赵楚之君非不富且贵兮,人不得而称之。”韩愈的《阂己赋》“惟否泰之相极兮,咸一得而一违。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时。聊固守以静侯兮,诚不及古之人兮其焉悲。”作者愤懑于自己失志后,用否极泰来来鼓励自己,表示自己目前的状况只是时候未到的结果。刘禹锡《何卜赋》作者在文中用了很多例子正反两面论证,最后将自己的不得志,归结为时机,认为时机在人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琢嚎之毒荃,鸡首之贱毛,各于其时,而伯其曹。屠龙之伎,非曰不伟,时无所用,莫若履稀;作俑之工,非曰可珍,时有所用,贵于研轮。络首糜足兮,骥不能践。前无所阻兮,跋鳖千里。同涉于川,其时在风,沿者之吉,溯者之凶;同载于野,其时在泽,伊撞之利,乃谬之厄。故曰,是耶非耶,主者时耶!”
其次,中唐骚体在句式上更加灵活。一方面表现在出现了七字句句式,而这在原初骚体中是没有的,但是在诗歌盛行的唐代,七字句句式被普遍使用,如柳宗元《招海贾文》中的“黑齿栈解鳞文肌,三角骈列耳离披。反断牙跨钦宏崖,蛇首稀欲虎豹皮。群没互出灌遨嬉,臭腥百里雾雨弥。君不返兮以充饥。”而这种七字句的使用,不得不说是对原初骚体的一种创新。另一方面表现在骚散结合。虽然在楚辞中也出现过骚散结合的作品,如《卜居》《渔父》等,但这类作品数量上少之又少,而且散的部分一般出现在作品的小序部分。而中唐骚体中的散句,常常出现在文章中间,如柳宗元的《解祟赋》:“今汝不知清己之虑,而恶人之哗;不知静之为胜,而动焉是嘉。徒逗逗乎狂奔而西慷,盛气而长磋。不亦辽乎!”
再次,中唐骚体中出现了一批哀怨愤懑情绪后升华为昂扬向上的豁达情调的骚体作品。刘禹锡就是这方面作品的领军人物。由于现实的种种,刘禹锡也有哀怨,但却能被他开朗的性格所化解,他的这一性格与柳宗元十分不同,就以《囚山赋》与《楚望赋》相比,柳宗元把山水看成是关押自己的囚牢,愤懑之情不能已;而刘禹锡虽然也无奈于自己被贬不得志,但却没有达到把山水看作囚牢的程度,愤懑过后仍可“自得其乐”。再如,他被贬时所做的《滴九年赋》,被贬九年仍未有被起用的征兆,作者心中无限的愤懑与不平,但文末他又自我调节到:“不可得而知,庸讴得而悲?苟变化之莫及兮,又安用夫肖天地之形为?”。在《砒石赋》中,作者把自己比作宝刀,这把刀由于很长时间没有用,所以生了些锈迹,但是只要一经砒砺,便会“故态复还,宝心再起”“即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认为没有必要被贬谪之事哀怨消极,是金子总会发光,只是时候未到,这些都表现了作者顽强的意志、不屈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何卜赋》将自己被贬不得志归结为时,认为时在人的一生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并用否及泰来的道理来安慰自己,平静地等待时机的到来。除此之外,中唐时期骚体在语言上也更加的多样化了,如韩愈的作品以散句为主,而刘禹锡、皇甫湜等人的作品里虽也有很多散句,但骈句运用的也很广泛。
此外,这一时期的骚体文学也受到了唐传奇的影响。传奇在中唐异常繁盛,出现了许多的传奇作品。由于一些传奇作家也创作骚体作品,所以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的传奇与骚体相融合的作品。传奇的写法对骚体的影响很深。
唐代著名的唐传奇作家沈亚之的作品中有8篇为骚体,如《古山水障赋》就是一篇典型的传奇与骚体相融合的作品。此赋在描绘画中景物的同时作者还通过想象赋予其人的情感,画中的景物变成了栩栩如生的真实的景物,好像将看画的人带入了画中,进行了一番游览。作者将传奇虚写的移情的手法用于到了辞赋的创作中。
类似的作品还有沈亚之的《梦游仙赋》《湘中怨》,郑琼罗《叙幽冤》,洞庭龙君《宴柳毅诗》,独孤遐叔妻白氏《梦中歌》,湘中姣好女《答郑生歌》、《风光词》等作品。
综上所述,中唐骚体文学受到时代文化的影响,产生了很多新的变化。中唐骚体文学,题材内容广泛详实,情感内蕴复杂深厚,艺术特色丰富多样。
参考文献:
[1] 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 蔡靖泉:《楚文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 许结、郭维森:《中国辞赋发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4]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 郭建勋:《楚辞与中国古代韵文》,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6] 郭建勋:《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7] 周殿富:《“楚辭源流选集”之〈楚辞魂—屈原辞译注图录〉》,《楚辞源—先秦古逸歌诗辞赋选》,《楚辞流—历代骚体诗选》,《楚辞余—历代骚体赋选》,《楚辞论——历代楚辞论评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8] 柯伦:《试谈唐代诗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4期。
[9] 陈思苓:《楚声考》,《文学杂志》,1948年第2期。
(穆伟,中央司法经管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