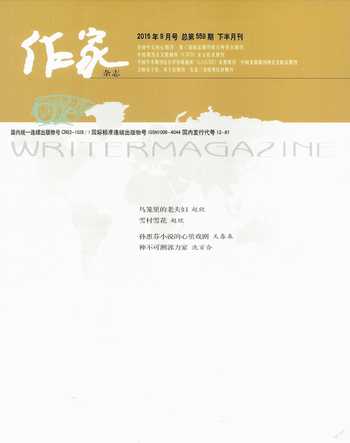孙惠芬小说的心理戏剧
2015-06-30天春来
天春来
孙慧芬是一个来自乡土的地道农家女,这决定了她区别于其她乡土女性写作的身份立场,以及表现领域的先天限制。乡村妇女在父权制传统顽固的乡村社会,活动的有限天地是在家族范围内,以及由家族延展到邻里的社群。即使在进入大都市之后,她们的第二性文化限制也是因袭的重负。日常生活中的挣扎与男性中心的心里对抗,成为心理戏剧的原初动力。孙惠芬的小说创作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文化宿命中,演绎着她们日常的心理戏剧,表现乡土女性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渴望、追求与坚守。
一
对于乡土作家来说,故乡是他们看世界的初始情景。在这个情景中,有着亲情维系的乐园记忆,也有着心灵创痛的个体情结,成为他们记忆的起点,也是他们创作灵感的源泉。孙惠芬的初始场景是男人缺席、三代女人拥挤在一起的狭小的家。这样的记忆使她的小说一开始就以家族伦理为主题,在家中亲属之间的情感依恋与心理对抗中,演绎出日常生活的心理戏剧。这些戏剧里都是素常的琐细小事,近乎于无戏的戏剧,但是情感的能量却是巨大的。
“母子共生”及“母女共生”关系早已成为人类文学史及心理学史里最为历久弥新的课题。作为乡土女儿的孙惠芬在书写乡土女性的时候,是无论无何也绕不开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母亲”。她的作品中,引人注目的便是“母亲”形象的反复出现,并且具有多种文化心理的内涵。《舞者》和《歌者》中的同一个母亲,是孙惠芬在自述和小说中提及最多的母亲形象,大部分性格刻画的细节是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她是现当代文学中,一个全新的母亲形象,也是一个全新的女性形象。她区别着男权社会价值理念的规范,又区别于现代文化塑造的新女性形象,同时又兼有新旧两种女性的优秀素质,无疑为“好女人”孙惠芬提供了直接的榜样,成为她自我生命塑造的模板和不竭的情感与活力来源。
作为新一代女性作家,孙慧芬自觉超越了文学史中母女关系的描写,在漠视男权文化规范的同时,又发掘出新的潜藏于平凡人生中的母子模式,那就是与母亲一生的“告而不别”。她纯粹以女性作家的本能和直觉,达到女性生命在彼此精神依存中的自我拯救。“我与母亲的告别,是从我七岁那年开始的。那种告别最初只是潜意识里的事情,就像树根下细细的萌芽。”[1] “我”好好学习,我要做小镇的女人,像二娘和四婶一样,以一种近乎疯癫的姿态开始了对母亲最初的反抗。懵懂、不经人事及逃离母子同体的自我放逐,使欲望将母女搁置为彼此相悖的状态中,呈现出自我分裂的精神现象。我的母亲也同样有对家园的寻找经历,却因无法挣脱男权文化的束缚,而处于家园失而不得的焦虑。“我”以不停地奔向外面的世界,来确定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及价值,去小镇制镜厂工作、发表文章和城乡间的往返,但仿佛生命里有一条无形的风筝引线,越想争脱越难争脱。这种奔逃未遂的母女关系,最终爆发为母亲的悲伤时刻,她因失去了家长的权威、不能为女儿操办一场像样的婚礼而伤心欲绝。虽然再也没有了家长束缚手脚,但在随着时代价值观念扭转的家庭中仍然没有权力,这样的文化夹缝处境使母亲举步为艰。作家在继续诉说母亲在家中的弱势地位时,笔锋一转,情节有了戏剧化的逆转,“母亲”的再次出场是以一种全新的社会化形象。这时的母女亲情也因此增添了一种交际的实用功能,外部世界的伦理价值观念在母女身上产生了曲折的内化效应。从“我”给表哥要回了驾驶执照事件开始,亲人们觉悟到我的“本事”,开始了对我大规模的侵扰。使我这个在小城刚有立足之地和平静心态的人,几乎被所谓的亲情窒息。它袭击了我的喉咙,让我无法正常呼吸,只有无力的看着自己千方百计的告别,最终是一种权利和亲情无法和解的对立。
《歌者》里的母亲是《舞者》里母亲的再次出场,是母女共生意识的又一次飞跃,在我远离俗世嘈杂,沾沾自喜于重新拾起人生的目标,却因为言语和文化语境的突然受阻,而不得不在母亲的怀抱里,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段“胎化”过程。“故事故事,像个兔子,兔子不跑,故事不了”。[2] 我在大连城里狭窄的两间房中,像困兽一样焦灼着理不清创作的头绪,是母亲用歌谣式的话语开启了我生命的又一扇情感之门,我的长篇小说《歇马山庄》就是在她看似不经意,实则煞费苦心的讲述中如期而至。这里好似口耳相传的母女对话,体现了一种传统的文化承继关系,母女的心因共同的情感体验,以不“太连贯的故事”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从而突破写作的困境,也是文化的困境。这里的母子共生关系,已经有了寓言的性质,是文化心理的诗性寓言。
“我”与“建筑师”的婚外恋情,从未曾和母亲提起过,母亲或许能从女儿在虚构与现实中挣扎的困苦中有所察觉,可善解人意的母亲还是一如既往,以最深邃的沉默来透析并敲击着女儿的心神不宁。当“我”情感意外受挫,母亲洞悉一切之后,面对女儿错误的情感取向和结局带来的疯狂,再度给予了不同常理的救援策略,以碎布头沉默地缝抹布,使女儿得到暗示,不同形状不同颜色布片缝合在一起,为“我”的一颗破碎的心找到了一艘“搭乘的风帆”。坚定浑然一体的母女亲情又一次通过无声的心灵交汇而救赎了彼此的苦難,女儿的最终成长及自我确认的道路中,再也无法脱离母爱这个力量的源泉,母亲已经是精神家园的象征。
在家庭女性关系的描写中,婆媳之间的伦理纠葛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所引发的议题成为了乡土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笔。孙惠芬的作品里突破了以往文学中被塑造成型的模式化恶婆疟媳的简单描绘,也不是赵树理笔下对旧式婆媳关系纯粹否定的刻画,而是将源自心灵深处的本体意识融入社会文化变迁当中,从而达到对女性意识的最深层次的洞幽发微。在《给我漱口盂儿》中,“奶奶”和“妈妈”之间的“斗争”从始至终,叙事者“我”,在“穷摆谱”和“没教养”的两极价值取向的戏剧性冲突中切入视角,对这场“无硝烟战火”进行内醒及文化心理的透视:“奶奶”和“妈妈”是一对具有不同文化符号的对立者,“奶奶”是一个一生中都以“体面”和“讲究”作为活动准则的传统文化权威的代言者,以每餐后漱口的行为模式,缔结了与乡村他者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妈妈”是“太不讲究”的代表,吃饭时嘴里无拘无束的“吧唧”声,正代表着个性意识的解放,是对“奶奶”也就是传统的规范制约的有意反抗。文中这两种力量呈现了一个此消彼长、相互制约的情势,一连串的家庭琐事让婆媳之间斗智斗勇,造成人物紧张的心理对峙,当“奶奶”发现“妈妈”知道自己心里那个秘密时,婆媳双方数个回合的拉锯战戛然而止,心理戏剧冲突达到了最高潮。“此时无声胜有声”,“我”见证了乡村妇女最基本文化人格的心理对抗。这是在孙惠芬的家常式叙事中,比较典型的戏剧化演述方式,体现为她多部作品戏剧观众的视角。
乡村家庭里的妯娌关系也是无比微妙的,她们相处的困难程度不比婆媳间的过招儿逊色。“妯娌”这个词,从字形的意义就已经规定了彼此关系的性质。左边同是女人,右边却又一个“由”,一个“甲”,同形颠倒的形态,暗示着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天然对抗,所以这个词语的形态,就隐含了妯娌之间无法融洽的伦理状态,已经呈现在漫长历史的基本文化情境当中。“只是女人之间的斗争,更微妙更复杂,因而也更艺术。一个眼神,一句双关语,一件小饰物,一声酸酸的语气词,都常常表现着很深的心机……女人总是要设法压同性一头。”[3] 在同一个家庭中会面对同一利益而生活的女人,这样心理较量更是频频不断。孙惠芬在《来来去去》中,把妯娌间怨恨、嫉妒、挑剔又相互扶持的心理狀态,进行了极深刻的揭示。这部小说记载了“申”氏家族里几个主要人物,在“进城”这个基本行动元的故事中,由于心理的微妙对峙衍生的情节,折射出的不同人生心路历程。其中,以对二媳妇厢琴和三媳妇小芸两妯娌间的心理剖析最为突出。厢琴和小芸同是申家被分出去单过的媳妇,却因各自际遇的不同,而成为无法化解的一对冤家,彼此排斥、互相攀比等争风吃醋的事件风波不断。
“挨着她的厢琴冷冷地咧了咧嘴。小芸的笑,使厢琴脸越发苦抽的厉害。乐,你当然乐,不管不顾别人去不去、别人有没有座,只要你去,你就有座,你从不把吃亏事留给自个儿,占了便宜就乐。下乡青年都一路货色!”[4] “厢琴却很敏感,她想不到小芸会报名吃亏,这太难得了。一时间她有些激动,有些喜欢小芸,她一面心里唱着‘铁树开了花呀开了花”[5]
妯娌之间的情感就是这样的莫名其妙,一会儿恨不得想你死我活,一会儿又因对方的小失意而极度同情,甚至发自内心的“喜欢”,孙惠芬塑造出来的细节,就像是来自内心本能的生物性驱使一样,重新点燃了人们探索人性奥秘的渴望。这种不落窠臼的立体化描摹,和不为流俗所动摇的稳健笔锋,可以说是脱离了主流文坛的艰难跋涉,在当代女性作家的创作里极为难能可贵。身为女性作家的孙惠芬,对于女性心理这样深度的反思和剖析,正是她具有强有力的女性观,最为准确生动的演述与注释。
二
“中国文学几乎从它的开端就是以浓烈的父权与夫权意识来完成‘香草美人或‘女人是祸水的主题阐释……”[6] 女人,这个“沉默的大多数”,背负着生命延续的重担在历史前行中过早地被父权文化所规范,以温柔、慈爱的面孔安分守己去奉行父亲、丈夫和儿子的旨意,并在父权的高压中一味顺从,以至于消解了生命的真谛。“想来想去妇女问题的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解放。”[7] 农村妇女的经济依属地位和情欲的长期禁锢,是日常伦理戏剧衍生的无意识土壤。这也直接决定了她们话语权的缺失,沦为纯粹物化的附庸。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是孙惠芬以乡村女性的姐妹情谊为主题的叙事,也是在被男权制度放逐的基本处境中,女性神话破灭的生存悲剧与精神情感的悲剧。在这个故事中,作者延续了她一如既往的心理剖析加细节描写的长处,将独守空房的两位新婚少妇不同寻常的友情,从建立到破灭的曲折的戏剧化过程细致入微地演绎出来。在男性权威缺席的状态下,潘桃和李平这两只刚飞入婚姻牢笼的金丝鸟的落寞心事可想而知,新婚是人生中的一次最大幅度的升飞,可是在“宴席散去,热闹走远”时,也就是丈夫进城打工走后,这种突然的精神失落使两个无所适从却怀有相同心事的女人,也在相对宽松的婚姻关系中获得一定的自由度,得以以一副“甘苦与共”的姿态走到了一起,开始了她们姐妹情谊的创世纪。两个被婚姻暂时搁浅的弱势个体,共同建立和经营彼此的无法实现的旧梦来填补寂寥的心理空间,把对方独守空房的欲望遮蔽转化为一种势均力敌的中间地带,来承载着自己对无法预知未来生活的恐惧和不安。可是一旦民工返乡——缺席的男人再次出场,各自的丈夫也就是男性统治者重新莅临,因李平的丈夫成子如期而至而潘桃的丈夫玉柱推迟回乡时间,友谊的天平立即失衡,潘桃在失意愤怒中终于爆发出恶毒的报复心理,向自己的婆婆泄露了李平曾做过“三陪”的秘密,结果乡村女性最初勇敢叛逆的觉醒再次消融进浓厚的男性秩序的阴云中,李平被丈夫大打出手并撵回娘家,这个承载着女权意识的同盟迅速瓦解,姐妹情谊的神话在丈夫返乡的时节,“合情合理”的以解体告终。戏剧情节发生了迅速的逆转,喜剧变成了悲剧,创世纪变成了失乐园。
中篇《“中南海”女人》是孙惠芬90年代的作品,这部小说又是一篇深入透析女性生命和天性被权力关系遮蔽的代表作,六个镇领导夫人生活在相同的政治和生活环境中,因各自男人的宦海浮沉来自我定位,实现自己的社会角色。在这部作品中,每一个被菲勒斯中心文化统领的衣着光鲜的女人背后,都谨小慎微地出演着一出在苦闷中爬行的心理戏剧,管书记夫人第一次和姜镇长夫人搭讪却未得到回应时,首先想到的是“她心里好悔,悔不该不听男人的话,遭了难堪。看来男人的话是不可不听的;”[8] 当丁镇长夫人“实在忍受不住孤清和空虚”,想去和表面看来平易近人的蔡书记女人聊天时,因突然造访而使蔡书记女人无比惊讶,蔡书记女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男人开会说错了话?又捅了漏子?……”;在这里,女人间话语权势的强弱完全是以男人们的官场勾心斗角的能力为前提,女性的依附性处境在嫉妒和攀比中越演越烈直至完全失去自我。在斗心眼的一幕幕情景穿插中,女人被镇压在以自己丈夫为代表的男权大山下无力攀爬,只能靠与同样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同性进行情感剥夺来维持自己的生命乐趣,以期得到一丝的平衡和自信。可是女人毕竟也富于血肉的个体,她们已如死灰的生命意识一旦被重燃,也就是小合唱队的组织和排演时,她们之间也滋生了“娜拉式”共鸣和觉醒, “这是中南海女人生活中最辉煌的阶段,在这些天里,她们那么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彼此那么紧紧地你依着我,我依着你,……”[9]可是这种缺乏独立人格的暂时同盟的命运注定是昙花一现的,在曲终人未散时,“女人”们就已经自觉回归到捆绑自己人性和话语的“妻性”轨道,“发生在这几天里的亲热和相互依恋,仿佛早已被大风刮走。”在小说结尾,男人们的突然调动又引起了女人世界里的一场旋风,她们终于又顺势跌进了女性逃之不得的被束缚的男性枷锁里。
“家庭,乃至家族,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便是以男性为标志、为本位、为组织因素的”。[10] 女人在森严的男权秩序里被“物化”,作为“交易”的功能成了女性世世代代无法更改的宿命。从历史上的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和亲”作“为国”“为父”或“为君”的物化载体,到近代满清皇族与蒙古的政治联姻,女人,在男性操纵的命运安排中经常以“等价物”的职能来完成男性话语的交换,以期凸显自己的生命价值。在中国辽南乡村的现代化语境下,由于乡土文化的凋蔽和对现代文明阐释的暧昧不清,乡村女性的话语本质具有更多的迷惑性。
乡村权力结构是混乱和复杂的,乡民的人际关系和文化心理在这样的文化处境中必然会有不同于常理的思维及处事模型。而话语权力缺失的乡村女性生活在男性利益和权势角逐的缝隙中,她們做为承载男人权力攀升的阶石自然成为无法逃脱的命运。在《歇马山庄的两人男人》中,刘大头作为村里的最高权力代表就是一出出以女性身体交换权欲的悲剧作俑者。他生命中两个最亲近的女人——老婆和女儿,都无一例外的成为他接近和稳固权力的工具,把22岁正值妙龄的女儿嫁给42岁的乡农委主任;把老婆贡献给历任乡长换取连任资格,都是刘大头之所以在村里横行霸道、欺男霸女却又无所顾忌的资本,就是这样一个臭名昭著,被包括鞠广大、郭长义在内的村民背地里恨得咬牙切齿的“恶人”,在被他占过便宜的鞠广大女人柳金香死后,决定要把自己的小姨子嫁给人生最落迫时的鞠广大续弦,如此举动让受害者鞠广大对于这份恩泽欢喜得措手不及,顿时改变了他在鞠心中的形象和地位外,还被鞠看成是刘大头恩赐给他一生中最为辉煌和成功的命运转机。“一种关系的连接,如何彻底地颠覆了鞠广大啊!……刘大头的霸气不但没让鞠广大反感,反倒让他也腰板挺直目光开阔了,因为他已经在努力把目光伸向那个世界了。”[11] “人的权利欲是永无止境”[12] 的,尽管当时的鞠广大的政治地位是处于乡村里底层的底层,可是一个女人给他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暖屋热菜这么简单的欲望满足,而是在他从来没有沾过边的却潜意识里无比渴望的权势亲贵!和刘大头做连襟,在他看来成了对曾“占”过金香的郭长义的最有力的报复,他在村里的地位陡然剧增,孙惠芬不露声色却入木三分地把乡土中国的权力规范和格局剖析的一览无余。
《南大沙》里的火样女子丁红,是不同于黑牡丹的敢爱敢恨、有血有肉的性灵女子,她知道她想要的是什么,也在拼命地为自己命运的不尽如人意而竭力反抗,可是作于沙西一村之长的女儿,她身上的负荷注定要比其它的女人多得多,于是她为了父亲,为了南大沙这片被沙东和沙西两村视为生命的海滩,为了村人的活路,也就是父亲能够继续坐在村长位置,她当然要责无旁贷、尽力而为,包括和渔业开发商陆连发四年来的不正当关系作为维系乡民和父亲利益的纽带,包括再次作为父亲和情人的政治和商业棋子,要她和沙东的村长儿子、那个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联姻,她的“勇敢”和“识大体”在于她深知她作为村里“救世主”的至高无尚的地位,让她对于这样为村民的荣辱也就是男权社会的认同而进攻男人转化为一种荣耀和自豪的资本,而和她相亲男人吕志刚明知是个阴谋,还要义无反顾地要她,因为他也深知“女人出嫁前父母是第一生命,出嫁后丈夫是第一生命。”[13]“女人是渔家生活中最重要又最不受尊重的家庭成员”,[14]像这样的现象,不仅仅是在渔村,整个辽南农村甚至整个乡土中国,作为妻子和女儿的女性用身体以婚姻的外在形式来为父亲或家族光宗耀祖,这是女性生命史上对男权认同和奉行的最愚昧却最无法回避的事实,丁红本身的生命欲求在暂时的觉醒和孱弱的反抗后因进攻的失利而不得不滑向男人秩序的环抱中……
三
孙慧芬小说中的乡土人物经常会出现有意的重复,导致乡土女性悲剧命运的人物关系也有相似性,加上上文论述过的戏剧情节的大同小异,都使她的创作带有基本原型置换变形的艺术特征。原型作为在文学作品中反复或经常出现的主题或映象,经常被历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创作所沿用。而在乡土文学的创作中,尤其是在乡土女性的叙事中,很少有人运用这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孙慧芬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实践者。或者说,辽南民间故事的原型也控制着她的叙事,不断置换出时代的人物形象,关系结构与文体形式。
(一) 男人:女性价值观的核心
弗莱曾说,文学作品是神话的移位,而孙惠芬的中篇《欲望时代》和长篇《歇马山庄》等作品里的一系列细节刻画就对这一观点有了经验式的印证。1997年孙惠芬在《芒种》杂志上发表了小说《欲望时代》,作家在这里还是利用她一以惯之的乡土女性视角来做一个空间换位,来审视都市女人们对于看似复苏的生命意识在无处不在的男性秩序中仍被搁浅的边缘化命运。故事中的“我”是一个已婚的政府办公厅的女秘书,“我”的大姑姐姐是一个40岁未嫁又性格孤僻的老姑娘,小姑妹妹是一个大学刚刚毕业的毕业生,家里的三个处于不同年龄和不同文化身份的女人,却怀有着相同的心事,那就是都义无反顾地爱上同一个已婚男人季和平——一个经常出入于家里的某个局里的书记员,这个男人周旋在姑嫂三人中,让本是和谐的一家人因三个情敌的对弈而硝烟四起。
我发现这个《欲望时代》的故事情节与孙惠芬在2000年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乡土长篇《歇马山庄》里的情节竟然有些异曲同工之妙,这种无意识的不同空间的伦理纠葛的巧合,让我们不得不对孙惠芬的心理无意识,进行进一步的探寻和思索。《歇马山庄》这个故事的主要情节是围绕着月月、买子和小青这“二女一男”三个年轻人的爱恨情仇为核心展开的,月月和小青本是在林家相处融洽的姑嫂关系,两个女性经常以姐妹式的交往方式私下里交流不为人知的隐秘心事,包括月月告诉小青国军的病情,以及小青将自己已经早就不是处女的隐私往事等,可是当二人的生活中出现了和她们彼此精神利益相关的同一男人买子时,姑嫂二人的交往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另一个女主角小青是一个城市卫校里刚刚毕业的新式女性,追求并占有买子这个男人便成了她调剂死水般的工作和心灵状态的一个手段。同时,与嫂子这个“对手”共同竞争买子便更助长了这个叛逆姑娘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持必胜的信念。她战略上以退为进、知此知彼,小施谋略。月月在以前还迷失在自己对不起林家的悔恨中,可是有了小青这样的挑衅,一下子顿悟并清醒,自己想要的和内心最真切的情感,于是便义无反顾地跳入这场毫无胜数却要血本无归的旋涡中,在月月和小青这场伦理上本无悬念的拉力赛里增添了更多彼竭我盈的味道,“都因为有了对方的参与才使她们共同悬入高空或坠入地下……”,[15] 作者并没有为月月这个“嫂子”,这个在恋爱竞争过程中本无位置和资本的的弱势一方套上伦理的枷锁,并让其与未婚姑娘处在同一起点上,从这种细节安排上来说,孙惠芬是有其独特用意的。
不同年代、不同创作阶段的作品有着这样的安排,这样的构思,这样的巧合,作为在孙惠芬内心深处的女性生命历史长河中不断翻腾的浪花,我们又怎么能忽视!这个情感故事的原型在哪里?孙惠芬在小说《歇马山庄》中,配合着月月和小青的困惑呈现给了我们一个醒目的答案。一个反复出现又极富有隐秘色彩场景,就是那个有着古老传说的姑嫂石缝,这个传说里有一家的嫂子和小姑同时爱上了一个染工,而在嫂子和染工的交往中,小姑因与嫂子有相同情愫所以使出一个小计谋,分别骗了嫂子和染工,来实现自己心中的爱,只可惜,事情败露,染工自杀、嫂子殉情。如此简要的一个传说,竟然深入到作者的灵魂,并融入进创作理念中,置换出一个又一个跨时空的女性伦理悲剧,这为我们阐释孙惠芬女性无意识表层之下存在的深层集体无意识,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空间。首先,虽然在传说中演绎出的两个故事中的姑嫂,没有像原型中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月月和小青失去了乡土社会最重要的女性生存资本:工作和家庭;城市里的“我”和大姑、小姑分别失去了自我和迈向前方生活的勇气……;而女人间的胜利一方,并不是最后要真正的和那个男人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传说中的小姑自杀,小青得到买子后发现那根本不是她所要追求的生活,“我”的小姑却也知道季和平是已婚男人的前提下仍和他鬼混。无论男女,他们都没有走向传说人物自杀殉情的结局。这无疑构成了一个反讽的意义结构,现代人的情感纠葛已经没有了生死相许的实质内容,更多的是同性之间的争锋,而且明显带有游戏的性质。两个故事中,付出真情的女性都是以失败告终,胜利者则是空虚和掌控手段高明的现代女性。她们追求“男人”的深层心理,只是一个男性中心意识支配下的女性远古意识的闪现,但是内容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其次,形式的不同和空间的泛化却是基于相同的模式,那就是由两个或多个女人爱上同一个男人的范本,而不是在现代通俗小说中,几个男人爱上同一个女人或多个男女之间的多角色关系,这一点在作者小说的女性意识构建上,运用这样重复的故事模式是极具深意的。孙慧芬彻底从温室女性“自恋”的倾向中走出来,清醒地认识到在男性情感场域的主流文化支配下,女性即便是从狭小的家庭生活中走了出来,走向了城市,有了一定的经济地位,但是她们传统的文化角色和文化心理,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对于传统文化秩序中男性中心的崇拜,仍是女性群体所逃离不得的课题。由此可见,在包括现代都市女性在内的广大女性群体,在欲望苏醒攀爬的过程中,仍难逃离千百年来女性被符号、被指涉的原始命运,孙惠芬怅然若失地徘徊在边缘身份的精神世界中,对女性集体无意识隐秘世界的揭示,为她的创作提供了更久远、更深入的心灵空间。也使她的乡村女性日常心理的戏剧,有了更深广的文化空间,具有时空同体的永恒原型意味。
(二)文明:女性想象的方舟
“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言语的交际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它往往渗透着民族的文化精神,并成为这一民族某一时代的文化镜像之一。”[16] 在上述我们所分析的神话原型叙事中,那些置换在现代故事的女性意识发展的人物关系的演绎,就是这些“被抛出”的“大多数”的深层文化心理,的确是不能被忽视的当代乡土文学隐晦的风景。所以,这一由神话原型转换出来的文化心理寓言,是孙惠芬小说乡村女性日常心理的戏剧最有深意的高潮设置,标志着她的创作真正走向了成熟期。
首先,孙惠芬以神话原型镜像映射中最表层的女性,是一部分未走出家庭的传统女人。她们和神话传说时代的生活方式相去未远,主体意识的缺失使她们的生命意识苏醒和情感的追寻过程是非常隐秘的,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奴隶角色导致了对男性无条件的顺从,是她们思想中至高无尚的精神追求,便是以对男性身体的占有象征家庭及社会地位,这样带来女性间无法和解又难以名状的嫉妒、猜疑,作为女性集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常常出现在作家的笔下。比如在中篇《姥姥》里,大姥姥和小姥姥一生斗争的根本原因,就是对姥爷的拥有问题。“当事人规定,大姥姥、小姥姥每人十天睡姥爷,……虽只一个轮回,小姥姥就再也没从姥爷房中搬出……。”[17] 如果说家庭内部尤其是旧式家庭里,同一男人的两个太太之间对男人的占有争风吃醋是一个常见的故事模式,那么不同家庭的女人间对于男性的占有所带来的心理负荷的失衡所导致的反目,则是孙惠芬以同一个故事模式容纳了现代生活的情爱特质。《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和《女人林芬和女人小米》里的两对个女主人公“始乱终弃”的友谊,由建立到破裂的故事都是典型的例子。《歇》中的潘桃和李平在丈夫外出打工的岁月里,因独守空房的落寞为起因逐渐的相知相吸到无话不谈,彼此努力地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温暖对方因男性的缺席而孤寂的心灵,可是结局却是李平丈夫成子如期回归而潘桃丈夫玉柱延期回归,无名的怒火燃烧的潘桃心生嫉恨,致李平和友谊于绝境。《女人林芬和女人小米》中的林芬和小米也有着一样的情感历程,两个离婚女人相互扶持又相依为命,在彼此达到“不要相信男人”“再也不嫁男人”共识之后,因男人冷力和林芬情感的逐渐浮出,导致两个女人的友谊无法挽回的最终破裂。
其次,她镜像中的第二层人物,则是在经济的大潮中,觉醒了的当代乡村女性。她们在自我意识逐渐苏醒后,在物质生活的贫瘠和压抑、制约之下,改变自身悲凉现状几乎已经成为她们的成人礼,她们有了最初向上攀爬实现自我价值的意识萌动,于是乡土女性对于政治权利的追逐便成为一股强劲的风尚,而乡土政治权力的掌控者男人,便是她们挣扎攀爬的主要目标,但是她们越要挣扎攀爬就越深地陷入被男人围困的境地,这是孙惠芬呈现给读者的乡土女性的第二重精神困境。《伤痛城市》是一篇以“我”的眼睛看待姑姑、姑夫一家在城市生活的精神困顿和不堪的伤怀之作。姑姑这个“一缕发丝就可煽动万千男人的漂亮女子”,在三十年前不顾世俗和家人的阻挠,义无反顾地投向姑夫这个有妇之夫的男人的怀抱,最根本的原因不在于姑夫本人有多大的魅力,“姑夫其貌不扬却才华横溢”,最根本的是姑夫当年“在小城当着权威无比的粮食局长”。《岸边的蜻蜓》里梅花对于老姨夫的爱也是如此,老姨夫有妇,梅花有夫,而梅花口中爱的陈词却是“老姨夫是厂长,走南闯北,知识广,让你觉得有靠头……”“物质这东西也怪,得到越多,越觉得不够。你懂吗,我觉的整个厂子都是我的,我也有了皇后一樣的感觉了……”[18] 寂寞的女人,可悲的女人,从自我定位的方向失衡那天就注定了她们自我救赎的失败,男性的权力符码仍高高地悬挂在女性仰视的天庭,使她们的身体在登上第一级欲望的台阶后,又迷失在男性权力承载的欲望牢笼里。
而最后一层,则是孙惠芬对乡土女性的生命觉醒、突围和陷落进行了全程的追踪关注,以《欲望时代》中的人物为代表,是的一批脱离了乡土、走出了家庭的女性。她们的命运又如何呢?身体和精神是不是如她们所愿的那样,得到了真正意义的解放?这是孙惠芬要呈现给读者的第三重女性精神的困境。这一点几乎从她的大部分作品中都能找到引证,几乎可以称之为孙惠芬塑造的经典乡土女性形象。从小说《歇马山庄》的月月和小青对于买子普通话的看重,和月月三嫂秀娟对于三哥“有识青年”的义无反顾的选择,都是最集中的体现。《吉宽的马车》里的许妹娜和《春冬之交》里的小兰等代表的孙惠芬作品里的众多女性,哪个不是为了嫁给城里人做了孤注一掷的抉择,而她们的结局却是:许妹娜实现了人生的这个目的,得到的确是倍受欺凌的日常生活,和最后离婚的结局;小兰在抛弃农村的恋人和嫁妆时,连许妹娜那样的实现理想一瞬快乐都未曾拥有;她们都决不后悔,城里人的生活她们用什么作代价换取都值得!于是她们便用自己的身体承载着生命骤变的神话,而在飞升的想象坠落后,留给自己的只有一生的落寞和不安……
孫惠芬对女性集体经验三重困境的纵向剖析是显示了其浓厚的创作功力,原型和寓言的套层表意结构,作为点睛之笔更加深入地透析了乡土女性力图争扎却不得解脱的处境,她的女性意识逐渐由摸索徘徊而走向真正的自觉,戏剧化人生处理的冲突再一次高潮迭起,这是当代乡土文学中一个叙事的奇迹。
参考文献:
[1] 孙惠芬:《歌者》,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4页。
[2] 孙惠芬:《歌者》,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72页。
[3] 季红真:《女性启示录》,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4] 孙惠芬:《孙惠芬的世界》,大连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08页。
[5] 孙惠芬:《孙惠芬的世界》,大连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17页。
[6]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303页。
[7] 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第五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版。
[8] 孙惠芬:《孙惠芬的世界》,大连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第142页。
[9] 孙惠芬:《孙惠芬的世界》,大连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第167页。
[10]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1] 孙惠芬:《民工》,作家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87页。
[12] 伯特兰·罗素:《权力论——新社会分析》,吴友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13] 孙惠芬:《伤痛城市》,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9月版, 第174页。
[14] 孙惠芬:《伤痛城市》,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95页。
[15] 孙惠芬:《歇马山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39页。
[16] 林宝卿:《汉语与中国文化》,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17] 孙惠芬:《姥姥》,《小说林》,1998年第6期,第135页。
[18] 孙惠芬:《民工》,作家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