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凤凰涅槃之歌
2015-06-26童孟侯
童孟侯/文
新凤凰涅槃之歌
童孟侯/文
他没有上过摄影大学,可他后来是上海多所大学摄影专业的客座教授;
他原来是机器厂一个早班翻中班的地地道道的车工,可他后来成为杂志社专业的摄影记者与编辑;
他的祖籍是上海青浦,青浦练塘镇政府要为他建立一个影像作品典藏室,这是政府为摄影人建立作品典藏室的上海第一人。

杨元昌——1980年代,上海涌现出一位具有大胆创新、坚持探索的当代摄影的先行者。他的当代影像艺术的观念及作品影响了一批摄影人,为中国摄影艺术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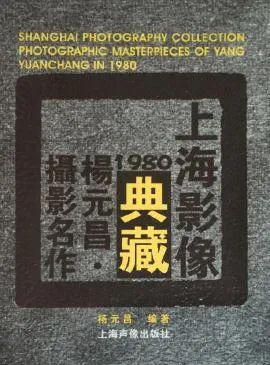
杨元昌摄影名作典藏集。
想没想过或许是“火烧旺铺”呢——不想了,三个决定不改了
1987年的一个清晨,杨元昌刚刚从床上坐起来,睡眼惺忪,突然听见窗外有个单位里的同事大叫:元昌,单位里火烧啦,快点去啊,火烧啦!
杨元昌赶紧套上外衣,跳上自行车就往嵩山路赶,一路踏一路想,莫不是我的暗房着火了?因为暗房里的插头是整个《现代家庭》杂志社最多的,用电量也是最大的。还有,暗房里的胶卷最容易燃烧,比纸张燃烧的速度快多了。如果是那样,难道是我闯的祸吗?
赶到嵩山路,杨元昌被眼前的惨象惊呆了,木结构的杂志社小楼已经烧得漆黑一团,断墙残壁,连扶梯都七歪八倒。
杨元昌推开消防队员要往小楼跑,要往四楼跑,那里有他的暗房,有他的编辑室。消防队员一把拦住他。眼下,大火已经基本扑灭,所幸的是消防队就在离《现代家庭》杂志社几百米远的地方,它们很快赶来救火,强大的水龙浇灭了大火。
杨元昌急不可耐:我要从暗房里抢出我的胶卷和底片,让我上去!
消防队员问他:还能抢得出来?你都看到了。
原来,《现代家庭》杂志社聘用了退休的老王头值夜班,白天回家休息,晚上过来当门卫。值班室就设在杂志社的门口,厨房间则在25米远的里头。
夜深人静,老王头开始干私活儿:先是洗袜子,然后打开煤气用水壶烧水。水开了,他并没有把开水冲入热水瓶,而是让它沸腾着,然后把刚刚洗完的两只袜子贴在滚烫的水壶外壁上——他用这种方式把两只袜子烤干。
嘴上喝的和脚上穿的贴在一起,卫生吗?老王头不计较;白天来上班的编辑记者不知道还有这一着,眼不见为净。
老王头笃悠悠在值班室喝茶看报,他已经把厨房间烘袜子的事情忘记得一干二净。不多久,烘在水壶外面的袜子干了。湿的袜子能粘住水壶,干的袜子粘不住,滑落下来,刚好掉在灶头上,掉在蓝色的煤气上。很快,一只袜子被火焰烧着了,第二只袜子也烧着了,灶头的周围是抹布、油瓶等等。
这一切,坐在25米远的值班室里的老王头莫知莫觉,他喝他的茶,他看他的报,等到烟雾弥漫到值班室,紧接着熊熊大火扑面而来,老王头已经不能冲进厨房间灭火。火势异常凶猛,飞速从一楼烧到二楼,从二楼窜到三楼,从三楼喷到四楼……而这个四楼,正是美术编辑杨元昌的编辑室和暗房。
消防队的警报拉响了,呜啊呜啊呜,红色的消防车只有几分钟就赶到嵩山路,水龙立刻喷向《现代家庭》杂志社的小楼,大火终于变成袅袅的烟雾……
等到允许杨元昌和他的同事们进入烧毁的杂志社,杨元昌冲上四楼一看,顿时泪流满面:这里是他工作的地方,锁在铁皮箱里的两个照相机,一个135的,一个120的,都不能用了,铁皮箱都被火烧得变了形,里面的照相机可想而知。
杨元昌所有的胶卷和底片,都放在另外一个用木头做的箱子里。一共有多少底片呢?一圈胶卷36张,10卷就是360张,100卷就是3600张,他存放在木箱子里总有500个胶卷,那么起码有18000张底片!他曾经从这18000张底片里精心挑选3000多张底片,特地把它们剪辑下来,夹入专门的底片簿。这些底片有的是专门为杂志拍的封面和内页,有的是他业余拍摄的摄影作品。
眼下,木箱子没了,一切灰飞烟灭,他想火中取栗都没有机会,只能从救火用的大水中瞎捞瞎摸。18000张底片是他杨元昌拍摄了整整22年的心血啊!也是《现代家庭》杂志从创刊以来的全部摄影资料,眼下,全毁了!
杨元昌真想冲上去一把揪住老王头:你赔我的胶片!你赔我啊!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是我的一家一当,老王头你赔啊!
《现代家庭》杂志社为摄影编辑杨元昌配备了新的照相机和放大机,可是他呆呆地看着这些新相机,孤独地坐着,沮丧地叹息,一坐就是半天:是不是老天爷要我杨元昌放弃摄影创作?是不是意味着我杨元昌搞摄影是没有前途的?否则老天爷为什么把我所有成果毁于一旦?为什么?为什么啊……
数天之后,杨元昌做出了两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他要为烧毁的杂志社拍一组照片,那些经过火烧烟熏的墙壁和木柱,出现了非常难见的肌理和木纹,非常空灵,非常抽象,就像他锁在铁箱子里被火烤过的照相机,虽然壳子还在,但是不具体了。
这组别出心裁的照片后来发表在杂志上——作为杨元昌对大火毁灭后的场景的纪念,作为杨元昌最后一次摄影创作。
第二个决定:为了保险起见,从此以后再也不把自己的胶卷底片放在单位里,而是全部放在家里保存。为何?这个世界上还缺少粗枝大叶的老王头吗?还缺少那些叫人哭笑不得的无知的“纵火者”吗?
数年以后,杨元昌作出了另外一个决定:辞职。
这个杂志社的摄影编辑兼记者岗位,11年前杨元昌是多么艰难地争取来的呀!那时候,你杨元昌还在大隆机器厂当车工,还在工会当干事,但是你的一门心思就是摄影。你的摄影技巧在同辈爱好者中算是好的,你在创作摄影作品的时候也很有自己的想法,区政协还决定让你这个机器厂的职工当了区政协委员,让你代表全区摄影这个行当。
那时,《现代家庭》杂志正准备创刊,要招聘唯一一个摄影编辑,全市三十几个摄影爱好者都来抢这个极其宝贵的岗位。最后,你杨元昌从竞争者里脱颖而出,从大隆机器厂调到杂志社,从业余到专业。
眼下,看到这样的场景杨元昌摇摇头,他彻底灰心丧气。大火可以烧掉他的黄金白银,可以烧掉他的字画印章,绝对不能烧掉他这个摄影人的胶卷底片,那是他的命根子!如今全都烧掉了,他这三十几年不是白活了吗?仅仅烧掉照片不要紧,有底片,还可以再印。烧掉了树叶还有树枝,烧掉了树枝还有树干,烧掉了树干还有树根,总有一天可以再发芽的。可是,把他保存的所有照相底片都烧掉了,那就是烧掉了根本,他何以为生?
心里是否燃烧着另外一把熊熊烈火——燃烧吧,三种拾回都拾了
后来,他离开了杂志社,杨元昌开了一家广告公司,生意还不错,不是亏本,而是赚钱。因为杨元昌对广告设计制作那一套不是外行,广告人需要摄影技术、绘画窍门、书法基础……杨元昌都懂,有的还很精。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杨元昌还在大隆机器厂当工人的时候,他这个摄影“粉丝”认识了上海油雕院图书馆另一个摄影“粉丝”老顾,两个人很谈得拢。于是,杨元昌毫无障碍地“潜入”不对外开放的油雕院图书馆,摸到了“上层建筑”。那个岁月,中国的油画雕塑还是老一套,中国摄影套路更是陈旧不堪。然而,夜郎自大。
也许,杨元昌是上海第一个欣赏到现代西方大摄影家摄影作品的摄影人。他在图书馆里浑身热血沸腾:哦,原来摄影还可以这么搞,原来摄影还必须有思想,决不仅仅是留影。如果摄影人没有丰富的内心,不可能抓到人间那些精彩的瞬间。一趟外出采风,即使拍了一千张照片,没有思想,镜头决不可能和那精彩的瞬间“撞车”。
从此,杨元昌按照外国摄影画册的路子,开始摸索,开始模仿,然后才开始自己的创作。一起搞摄影的朋友觉得奇怪,大家一起背起照相机,一起去拍照片搞创作,一起到某个地方,为什么杨元昌拍的照片和我们越来越不一样呢?
有一次,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摄影策展人来到上海,希望挑选到一批上海摄影人拍摄的摄影作品,然后拿到国外去展出,让世人了解中国,也了解中国摄影。上海摄影家协会便发出征集通知,请上海的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把最好的照片寄去。结果,外国策展人从几千张摄影作品中挑选出30张,其中10张是杨元昌的。
后来,香港搞了一个国际摄影年赛,由柯达公司赞助,向全世界征集优秀摄影作品。月评的时候,杨元昌是月冠军;年评的时候,杨元昌是年冠军;最后,他是那一届年赛的总冠军。
他还获得过中国青年摄影“十大杰作”称号……
杨元昌曾经拍过一张获奖作品,叫《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个题名当然是受了张贤亮同名小说的启发。那天,他到浙江的一个乡村采风,突然看见一个院子的大门边坐着两个无所事事的男人。
杨元昌便琢磨:这两个男人接下来会做什么呢?如果有人从这扇没有门的大门进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有个女人进去,这两个男人会有什么反应?
于是,杨元昌便躲在一个角落里,静静地等那一幕的发生。过了十分钟,一个年轻女人拎了一个水桶,从外面走来,当她跨进门槛的一刹那,杨元昌用他的135照相机嚓嚓抓拍了两张照片。
照片冲出来了:那个女人衣着简陋,显然是一个辛勤的劳动者。她很丰满,但是身上的曲线一点儿都不美;她很年轻,但是很疲惫。坐在门边的两个男人死死盯着那女农民,那种贪婪的目光和那种垂涎欲滴的神态毕露无遗,两性之间奇异的吸引被杨元昌咔嚓一声记录下来。
这是一幅关于人性的生动写照,可是,当时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没有一位摄影编辑敢接受这精彩的作品,也许编辑们在心里接受了,欣赏了,但是他们不敢发稿;即便发稿了,在总编那里也不会通过三审。刚开始改革开放的年代,虚伪的极左的大气候摆在那里,“文化大革命”的流毒还远远没有从人们的骨髓中拖拉出来……
杨元昌跟朋友交谈的时候说过这么一番话:搞摄影创作,主要不是看摄影器材的好坏,不是看摆拍有多么精细,而是看照相机后面的眼睛,后面的脑子,摄影技术再好,没有脑子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有个朋友突然问他:元昌,你从此以后不再搞摄影创作了吗?你就搞广告公司了吗?开个广告公司谁都能办到,搞个摄影创作却不是人人能办到的。
唉——杨元昌长叹一声:不拍了,不拍了。
朋友反问:你真的不拍了?《现代家庭》杂志社被大火烧毁之后,你不是心急慌忙问别人借了一个135的照相机,把烧毁后的场景拍下来了吗?难道你仅仅想留一点记忆?不是,你是放不下,你是在悼念你的那些底片!
杨元昌心头一惊,他没有回答朋友的质疑,他不知道回答什么好。
那位朋友继续道:你保存的底片虽然烧掉了,但是一万多张底片总有几张没被烧尽,总有几张没有被水泡烂,你何不“挽救”一下呢?它们是你的宝贝。
朋友说得对啊,杂志社的一把火虽然早就被扑灭了,但是他心中另外一把火什么时候停歇过呢?那把火就是风风火火的摄影创作!
杨元昌悄悄开始了他的“挽救”行动。果然,他从哪些被火烧过被水泡过的底片里,找寻到十几张残缺不全的,有的只有上半张,缺少下半张;有的烧掉一只角,其他依稀可见。杨元昌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残疾”的底片拿去放大,然后稍加修饰……哦,他的摄影作品回来了好几张!

杨元昌摄影作品《采石女工》。
他像得到宝贝似的,把这些劫后余生的照片挂在家里,然后坐在写字台前细细欣赏,就像欣赏自己新生的儿子。他不时为自己的作品鼓几下掌,不时伸一下腿,退后一点,继续欣赏作品……他感觉到自己的脚尖碰到了写字台下面的一个肥皂箱子,声音是噗噗的,也没有什么重量。
那个纸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他记不得了。拿起手工刀划开纸箱子一看,杨元昌手中的小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我的天哪!天助我也!那是整整一箱子当初放大放坏了的照片,足有1000张!杨元昌捧起这些照片热泪盈眶,他亲吻着它们,把它们贴在自己的脸上。这1000张不是坏的照片,而是放大时没有放好的好照片啊!
杨元昌通宵达旦地整理起这些照片,“坏”里挑好,粗里选精,挑选那些质感好的,有层次的……其实在父亲眼里的儿子,没有一个不英俊的。经过几个月的寻找、翻拍、扫描、修复、放大……他从中选出100张他还算满意的作品。
刚刚完成这一巨大的“工程”,杨元昌突然想:我的底片虽然烧掉了,但是很多杂志报纸都发表过我的摄影作品,我为什么不把我第三个失散的“儿子”找回来呢?
说找就找,于是,杨元昌赶到那些报社、杂志社和图书馆,寻找他曾经发表的照片,翻拍,放大,修饰……果然,就像当初拍的照片一样,虽然不是那么清晰,但是作者的思路特别清晰。
这是杨元昌在搞广告设计?不,身在曹营心在汉啊!
冬天里有无一把火熊熊燃烧他心窝——也许吧,三个台阶都上了
2004年,上海摄影家协会找到杨元昌,请他出山,请他重归摄影,请他主持《上海摄影》杂志的工作,担任副主编和艺术总监。
《上海摄影》是一本专业的权威的杂志,非同小可。很多人都怀疑,淡出摄影前沿队列已经整整11年的杨元昌,他的眼光,他的水准,还能够适应新时代的摄影观念和审美思潮吗?杨元昌行吗?
不可否认,1980年代的上海文化,是真正具有开放意识的文化,也是上海当代观念摄影的萌芽时期,各类摄影风格相互争艳,成为当代中国摄影最亮丽的风景。摄影家的共同特点就是具有独立的社会价值判断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独立的国际文化接轨的审美能力、洞察社会动向和生命意识的能力,杨元昌就是那个年代的代表人物。
眼下的杨元昌,其实从没有放弃过对摄影的梦想,也从来没有掉队,他提出的观念摄影就是一个例证。所谓观念摄影就是非具象、超现实的摄影,摄影阐述一种新的生命价值观念,新的社会政治、道德、公共事务观念的一种摄影趋向——这可是当代艺术中最活跃最前卫的艺术方式。
杨元昌的摄影观念依然是超前的,那么,他能实实在在地撑起《上海摄影》这本杂志吗?那是两码事。
杨元昌默默地把广告公司交给了朋友,只身上任《上海摄影》。
从此,他把培育辅助摄影人和摄影家为己任,帮他们发表过无数摄影作品,帮他们开过无数次摄影个展,帮他们解决过无数创作中的困惑……
11年以后,杨元昌接手后出版的66期《上海摄影》,不仅经受了中国最苛刻的摄影人群的挑剔,还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尊敬,获得了中国摄影界同仁的高度评价。
就这么一晃,11年过去了。
2012年,杨元昌的好朋友、著名摄影家尔冬强对他说,元昌啊,你为别人策展,为别人出版摄影画册……那么你呢?你自己呢?你是不是应该为自己搞个摄影个展出本画册?你已经60多岁了。
2012年4月28日,在田子坊的尔冬强艺术中心,杨元昌的第一个个展《拾回的记忆》隆重开幕,同时也出版了杨元昌的第一本画册。他的照片都是黑白的,那幅名作《师徒》,占据了正面的整堵墙,漫天风雪中的师徒俩给展厅定下了基调:某个风雪交加的清晨,杨元昌走过马路的一个小工地,看见师徒两个正顶着严寒施工,就在他们俩抬起头喘口气的一瞬间,杨元昌拿起照相机抓住了那一刻。师徒两人的眼神,“令我们涌起敬意、怜惜和惆怅,心神不安”。
个展中展出的那幅《姐妹俩》,什么都没有说,却什么都说出了,片子有一种悲伤和温暖,是那种还没有长大就已经有了慧根的人生。
那幅《母亲》,出现了朴实坚强的母亲和孩子们,艰辛的人生,自然的光影,使观者获得了一种根本的感动。
“隐忍和感伤,是杨元昌的基本要素,是他的一贯风格。每一幅照片都有一种完美的修养和力量感(——作家卓玛)”。
没想到杨元昌摄影个展的头一天,人头攒动,杨元昌的同学、学生、好友、同事,还有摄影爱好者、记者、电视台摄像……从四面八方赶到田子坊。
杨元昌展出的照片平均定价是2000元一张,当场就被订掉60张——有几张作品两三个人“抢”。他们当场把预订费都付清,唯恐不及。
著名作家陈村去看了个展,他感叹道:大音希声,大作不秀,他的那些作品都可以命名为《无题》,犹如真正的人生从来无题。经他的拍摄,它们获得了永生。只要是经典,必然经得起折损。杨元昌浴火重生的摄影是大师之作,不畏惧时间,也不畏惧损耗。
杨元昌穿了一件红色的像火那样的中装,他激动不已,不停地向观众点头致意,向他的前辈鞠躬,想不到这么多年他默默无闻,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磨难,仍然有那么多的摄影人记着他,承认他的作品。
东方电视台把杨元昌请去,作了长时间的采访。而后,在黄金档播出了30分钟摄影家杨元昌访谈。
杨元昌自己都没有想到,几十年后,他竟然火了起来!
2014年,上海声像出版社来找杨元昌,表示愿意为他出版一本精致的摄影画册。这一次,杨元昌爽快地答应了。他告诉出版社编辑:一个摄影家一生一世,其摄影名作一般不会超过10幅,让人们记住的让社会认可的让摄影家点头的摄影作品,甚至只有五六幅。不要认为捞到篮里的都是菜。所以我想出版一本《上海影像1980典藏•杨元昌摄影名作》,只收集几十幅我的摄影作品。
出版社编辑点头,表示同意。
杨元昌说:既然是典藏,那么应该是限量版的,是让藏家收藏的,所以这本东西只限量发行300册。
出版社编辑点头,还是表示同意。
过了几天,编辑就打电话来:杨老师,您的摄影名作选刚刚开始征订,还没有印刷,预订数已经达到五六百本,怎么办?
杨元昌说:就印450本吧,不能再多了,多了就烂。
《上海影像1980典藏•杨元昌摄影名作》出版,虽然供不应求,但只印了450本,并且不再加印。
杨元昌是上海摄影界的名人,他是上海人,祖籍是上海青浦。一天,青浦练塘镇有关领导找到了老乡杨元昌:杨老师,我们练塘镇要为您建立一个展示馆。
杨元昌说:我是一个普通的摄影家,不要这样大张旗鼓吧?
有关领导说:我们练塘是一个古老的水乡,您是知道的,我们想让游客看看我们既秀美的又有文化品位的水乡,不想把我们练塘搞成只是买买土特产、吃吃河虾河鱼、喝喝绿茶红茶的地方,希望杨老师支持我们的文化建设。
杨元昌依然低调:不要为我搞什么馆了,我是个很普通的青浦人,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有关领导说:我们已经把练塘镇风水最好的老建筑“圣堂”留给了您,决定要建一个杨元昌摄影名作展览馆,永久保存。这是我们青浦人民的骄傲!
杨元昌摇摇手:不行不行,陈云是伟人,他在青浦的那个馆叫纪念馆,我怎么能叫馆呢?绝对不行。
有关领导见杨元昌松了口:杨老师,那么您觉得叫什么名称比较好?
杨元昌不知不觉上了“钩”,说:要么叫杨元昌影像作品典藏室吧?我有一些从大火中“抢”回来的摄影作品,还是有点珍贵的,可以在那里展出。
有关领导说:好!一言为定,就叫“典藏室”。您的作品不是在那里“展出”一下就撤了,而是永久保存。杨老师,下个星期我们就开始设计图纸,请您来一次,我们共同商量。设计方案一旦敲定,我们立刻动工改造装潢!
杨元昌跑到练塘一看,那个“圣堂”是整个练塘镇风水最好的道观,始建于宋朝的老建筑,因为年久失修,几乎要废弃了。它的门前是一座明朝造的石头桥,桥的下面是一个石壁,石壁后面才是“圣堂”,总面积达到四百多平方,分为前堂和后堂两部分。
杨元昌又“低调”了:这么大的“圣堂”怎么能我一个人占了呢?我的摄影作品就放在后堂的二层楼展出,只要100平方就足够了。其他的地方,可以开展览会,轮流展出摄影家尤其是我们青浦的摄影家摄影爱好者的作品,发扬光大。
杨元昌的朋友们学生们又来劲了:杨老师,我们用最好的红木来制作匾,门口挂的馆匾,上刻“承艺堂”,后堂挂一块匾,上刻“杨元昌影像作品典藏室”。您的摄影作品我们用目前世界上最经典的铂金印相技术来制作,内中含有金子的成分,保证照片永不褪色。您摄影作品的镜框我们用最好的橡木来做。至于整个典藏室的设计布置,我们会请最好的设计师参与设计……
杨元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中国有几位摄影家享受如此待遇?
传说中,凤凰是人世间幸福的使者,它背负着积累与人世间的所有的不快和恩怨,投身于熊熊烈火中自焚,经受巨大痛苦和轮回之后,凤凰得以重生。
杨元昌就是涅槃的凤凰,他更生了,他永恒了,在光明的火红的摄影世界,他尽情地歌唱,展翅高飞!
此刻,杨元昌却想起了妈妈跟他说过的一句话:做人要做好,真有本事不要怕出不了名。诠释一下妈妈的话:如果没有本事,当然很难出名;如果有了本事,出名并不难。如果没有本事也不要紧,做人先要做端正了。
回首征程,杨元昌在大隆机器厂呆了11年,又在《现代家庭》杂志社工作了11年,又在广告公司干了11年,如今在《上海摄影》杂志社也做了11年。巧了,都是11年。那么,这4个11年象征着什么?象征着8根坚实的饱含磨难的柱子吗?象征着4双筷子吗?象征着他人生四个重要阶段的“饭碗头”吗?也许是,也许都不是,也许是他心中熊熊燃烧的那把烈火从未熄灭,也许是温文尔雅的杨元昌对摄影艺术始终的追求和呼唤: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摄影是他的生命,怎么能不要啊!

杨元昌摄影作品《人生·自我·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