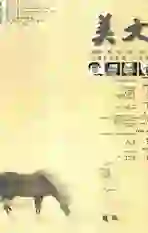在桥上看风景的卞之琳
2015-06-25彦火
彦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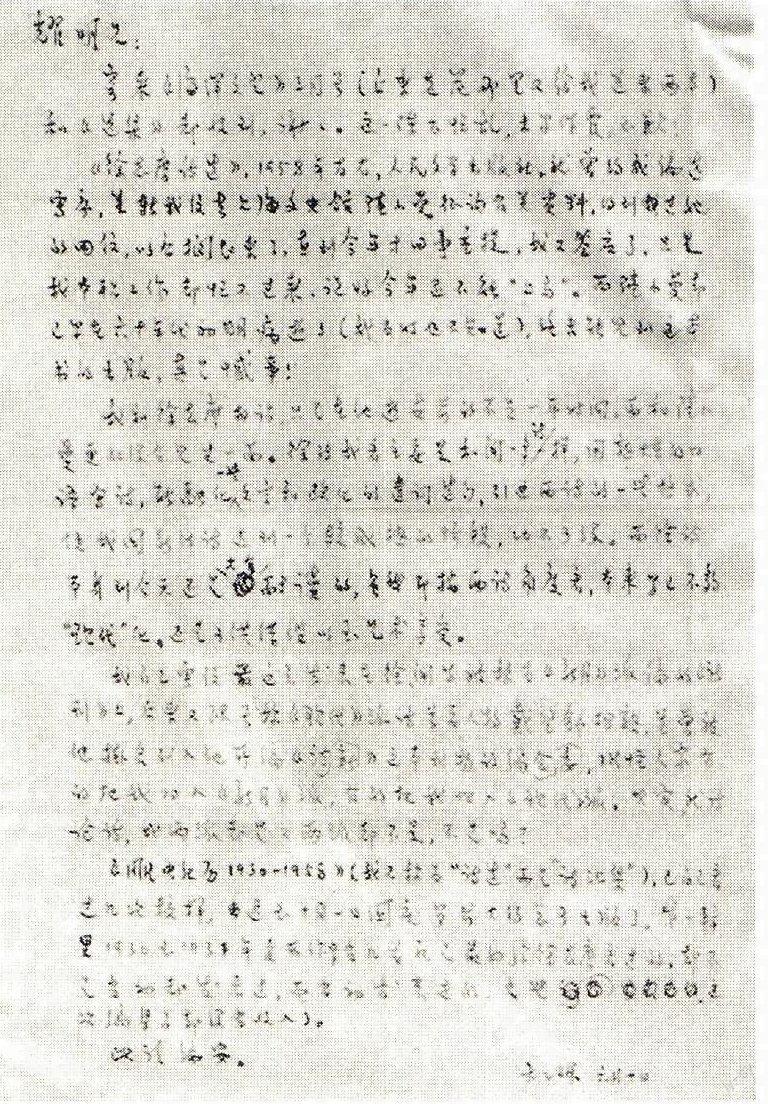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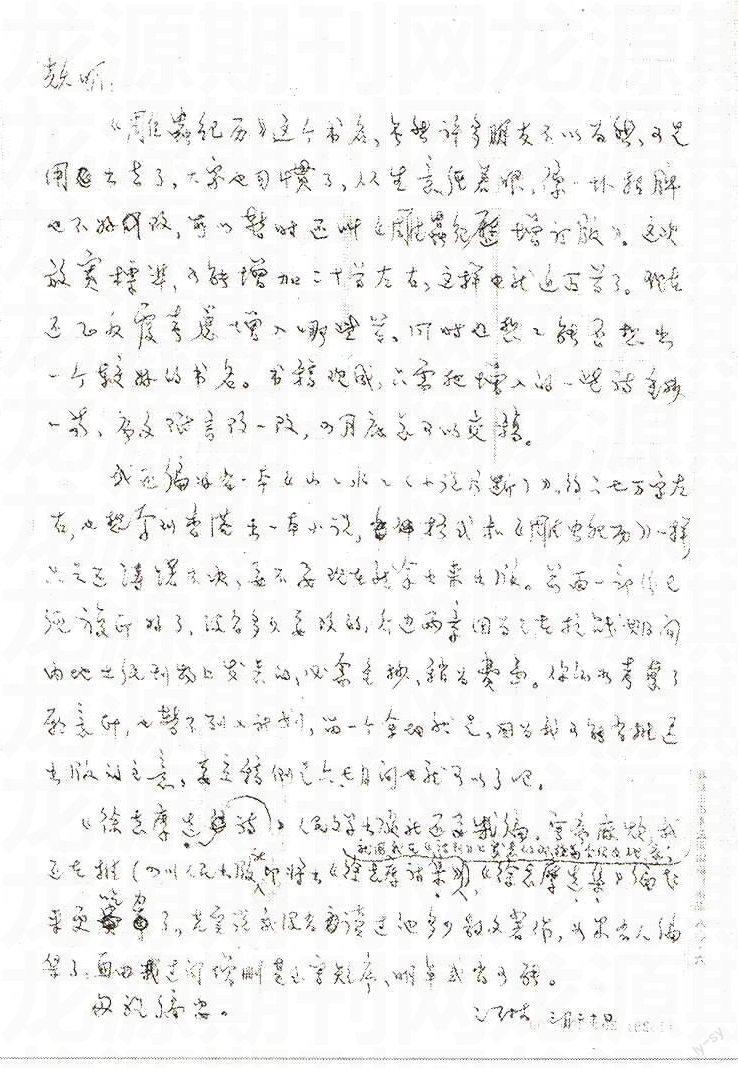
在桥上看风景的卞之琳
在港台及海外,卞之琳的诗一直为诗歌爱好者所传诵,从未间歇。我觉得在中国老一辈的诗人中,可以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除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马悦然曾经提到的艾青,卞之琳应是不二之选。
艾青是中国现实派诗人的大纛,卞之琳则是现代派诗人的一面猎猎旗帜。
余光中对卞之琳的哲理诗,大为激赏。余光中在一篇以《诗与哲学》为题的文章指出,“现代诗中企图表现哲理的作品不少,但成功的不多。”他称颂卞之琳是此中的佼佼者,是“一位杰出的现代诗人”。
余光中举卞之琳早年的短诗《断章》为例,认为虽然寥寥四句,却“是一首耐人寻味的哲理妙品”: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不少海内外评者均论及这首短诗,余光中更是说得透彻:“原来世间的万事万物皆有关联,真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你站在桥上看风景,另有一人却在高处观赏,连你也一起看了进去,成为风景的一部分,有如山水画中的一个小人。”“同样一个人,可以为主,也可以为客,于己为主,于人为客。正如同一个人,有时在台下看戏,有时却在台上演戏。”
卞之琳这类哲理诗,比比皆是。
卞之琳 (1910-2000) 是原名,他的笔名是季陵。今人对卞之琳的名字耳熟能详,倒是把他的笔名淡忘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笔者因写《当代中国作家风貌》一书,并编辑卞之琳的《雕虫纪历》(香港三联书店繁体版),与他交往较多。最近整理与他来往的信件,拢共有近二十封之多,其中不乏逾千字的长信。他的字很像巴金的字,像一尾尾小蝌蚪,有点潦草,细辨之下,还是分明可读的。
卞之琳给我的信,涉猎的范围很广,其中包括他的生平、创作生活、代表作、对新诗的创作体会和主张。
卞之琳写新诗,既写自由体,更多写格律体,与“新月派”及后起的“现代派”都有缘,既直接受过西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式“现代主义”诗(包括后期象征主义诗)的若干影响,也保持了我国古典诗的主要特点。
卞之琳既然曾经师法闻一多的新格律体,那么他应是属于新月派的诗人,为什么又有人将他列为现代派的诗人?笔者曾就此征询过他,他在回信中解释道:
我自己写诗最初是发表在被称为“新月派”的徐、闻等人编的《诗刊》上,后来又跟“现代派”首要人物戴望舒相熟,并曾被他挂名列入他所编《新诗》这本刊物的编委会,难怪人家有的把我归入“新月派”,有的把我归入“现代派”,其实,就诗论诗,我两派都是又两派都不是,不是吗?
“两派都是又两派都不是”,这句话好像很难理解,其实并不。所谓“两派都是”,是说卞之琳曾与这两派发生关系;所谓“两派都不是”,是卞之琳又能脱出两派的窠臼,走出自己的道路,在诗歌的创作上,突出了自己的风格。
在卞之琳早期的创作活动中,有三个人与他关系最密切,他们是徐志摩、沈从文和闻一多。
徐志摩是最早发现卞之琳富有诗才的人。一九三一年初,徐志摩到卞之琳就读的北京大学教英诗,在课外看到卞之琳的诗作,并且带回上海与沈从文一起读了,大加赞赏,不由分说,分交一些刊物发表,还亮出了卞之琳的真名。
卞之琳深谙化古、化欧之道,知道如何承继传统诗、借鉴西诗,以探索中国新诗的进一步建立。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一次诗歌问题的讨论会上指出,中国古典诗词只有吟唱的传统,而五四以来的白话诗受到外国诗的影响,才有“为了念”的传统。他说:“这种新传统到今天也不能说不属于我国的民族传统,而照这种新传统写出来的新诗形式也就不能不是我国的民族形式。”
他在《雕虫纪历〈自序〉》一文就更明确地指出:
我写白话新体诗,要说是“欧化”(其实写分行,就是从西方如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那么也未尝不“古化”。一则主要在外形上,影响容易看得出,一则完全在内涵上,影响不易着痕迹。一方面,文学具有民族风格才有世界意义。另一方面,欧洲中世纪以后的文学,已成“世界上的文学”。现在这个“世界”当然也早已包括了中国。就我自己论,问题是看写诗能否“化古”“化欧”。
卞之琳这段话,意即中国新诗的道路,除了要有纵的继承,也要有横的移植,并且将继承和移植融会贯通,这就是所谓“化古”和“化欧”之道;此外,还说明了只有将自己的民族传统与世界文学的意义联系在一起,才可开拓中国新诗的发展。卞之琳自己是身体力行的。
卞之琳的成就还是不止于诗歌,他是北京大学的西语教授,翻译了不少西方名著,包括《莎士比亚悲剧四种》《英国诗选》等等。
卞之琳的美诗妙译
蜜蜂的细腿已经拨起了,
多少只果子,而你的足迹呢,
沙上一排,雪上一排,
全如水蜘蛛织成的水纹?
──卞之琳《足迹》
屈指一算,卞之琳已走了十二年了。说起与他的交往,除了我做现代中国作家研究之外,还有一段因缘。
当年我任职香港三联书店的时候,为他出版《雕虫纪历——1930-1958(增订版)》,期间为出书的事与他通过好几封信。
卞之琳在“文革”复出后,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他出版了《雕虫纪历——1930-1958》,书出版后转瞬间销售一空,洛阳纸贵。人民文学出版的《雕虫纪历——1930-1958》,卞之琳把过去写的诗,特别是1939年以前的部分删得太多,难以窥见卞氏诗风全貌。
其实卞之琳删除的诗,大部分是他为“私生活中一个隐秘因素”写的诗,——这些诗可读性相对较高。
后来我在北京出版家范用的荐引下,提出出版《雕虫纪历》的增订版。因为人民文学的《雕虫纪历》已销到香港,笔者曾探询卞之琳,香港版是否改一个书名,况且他把自己诗作以“雕虫(小技)”自喻,是否谦虚过了头?
卞之琳对书名很执着,理由是《雕虫纪历》已打响了招牌,不好改,倒是他同意香港版的《雕虫纪历》增补上较早删除的部分,至于人民文学版书末所附英文自译诗十一首,则予删除。
事后我对这做法,颇感到美中不足。
卞之琳补上三十首的诗,很是珍贵,照卞之琳的说法,“其中《群鸦》和《芦叶船》则完全因为从1934年先后曾在上海和北平的出版社在刊物上登过预告,就以这两首的题目作书名,后来并没有出书,而这两首也只分别在另两本集子里出现过一下。”
更难能可贵的是卞之琳把题赠张允和,而因战争爆发未及出版的《装饰集》也收录了进去,卞之琳在《附记》中,说是“砍了一首大部分,只留了个尾巴,独成一首小诗。”
至于被砍掉的一大部分是什么,相信只有卞之琳自己,以及他为之苦恋一世的张允和女士才知道了。走笔至此,我不禁想起他香港版《雕虫纪历》的压卷篇──《路》的结尾:
也罢,给埋在草里,
既厌了“空持罗带”。
天上星流为流星,
白船迹还诸蓝海。
关于卞之琳的“隐私”,也只好“给埋在草里”,像流星一瞬即逝,像帆船消失在蓝天尽头。
另一个美中不足的是,卞之琳西洋文学根底很深厚,他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也是翻译家,他的译诗肯定很棒。在香港版的《雕虫纪历》删除“自译诗”,未免可惜,都怪我当时没有坚持保留这一部分。
谈到译诗,卞之琳很有自己的一番见解,他在《翻译对于中国现代诗的功过》一文中,指出时人在译诗时,大都不扣原文,“只顾迎合时尚来译诗,一旦成风,反过来又影响诗创作,彼此互为因果,就形成恶性循环。”
试举以下卞之琳自译的两首短诗,英译与原文紧扣,仿如组构珠贝上下的两叶瓣,开合自如,浑然一气:
第一盏灯
鸟吞小石子可以磨食品。
兽畏火。人养火,乃有文明。
与太阳同起同睡的有福了,
可是我赞美人间第一盏灯。
The First Lamp
Birds engulf hard pebbles to grind the grain in their crops.
Beasts fear fire. Men keep fire, and so arises civilization.
Blessed are those who arise at sunrise and sleep at sunset.
Yet I praise the first lamp that opens on a new world.
无题五
我在散步中感谢
襟眼是有用的,
因为是空的,
因为可以簪一朵小花。
我在簪花中恍然
世界是空的,
因为是有用的,
因为它容了你的款步。
The Lovers Logic
Walking listless, I feel grateful
That the buttonhole is useful
Because it is empty,
Because it can hold a small flower.
Fixing the flower makes me remember
That the world is empty,
Because it is useful,
Because it allows your graceful walking.
第一首诗虽短小,寓意深刻,意象繁富。译来十分考功夫,卞之琳译笔流丽潇洒,琅琅可诵。第二首分明是爱情诗,原是留空的襟眼,因可以簪一朵小花,而变得有用,偌大的世界,因为你的款款步履而变得有价值。译诗扣紧原文,韵味自成,不啻是美诗妙译。
苦恋一世的卞之琳
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
我往往溶于水的线条。
你真像镜子一样的爱我呢,
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
──卞之琳《鱼化石》
卞之琳的爱情哲理短诗之中,最为人传诵的,除了《断章》,还有《鱼化石》。
《鱼化石》与《断章》一样,全诗只有四句,却有丰富的内涵,也同属爱情诗,是为张允和而写的。
卞之琳在《鱼化石后记》的解读表示,诗的第一行借用了保尔·艾吕亚(P. Eluard)的两行句子:“她有我的手掌的形状,她有我的眸子的颜色。”与司马迁的“女为悦己者容”的意思相通;第二行蕴含的情景,从盆水里看鱼化石,水纹溶溶,花纹溶溶,令人想起保尔·瓦雷里的《浴》;第三行“镜子”的意象,仿佛与马拉美《冬天的颤抖》里的“你那面威尼斯镜子”互相投射,马拉美描述说,那是“深得像一泓冷冷的清泉,围着镀过金的岸;里头映着什么呢?啊,我相信,一定不止一个女人在这一片水里洗过她美的罪孽了;也许我还可以看见一个赤裸的幻象哩,如果多看一会儿。”
而最后,鱼化成石的时候,鱼非原来的鱼,石也非原来的石了。这也是“生生之谓易”。也是“葡萄苹果死于果子,而活于酒。”
诗人反问:“诗中的‘你就代表石吗?就代表她的他吗?似不仅如此。还有什么呢?待我想想看,不想了。这样也够了。”
四行诗可以引申出一大堆繁复的意象和埋藏那么丰富联翩的遐想,我想古今中外也只有卞之琳才有这份的能耐!
性格极度内向的卞之琳,也许存心与读者捉迷藏,不好直截地表明真正心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呢。还幸,卞之琳在1978年出版的《雕虫记历·自序》曾隐隐约约吐露了这段感情,使读者才可寻到他感情生活的一些蛛丝马迹:
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显然彼此有相通的“一点”。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做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仿佛作为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
其实,徐迟远在1943年,在《圆宝盒的神话》一文便指出,“……献给一个安徽女郎的《鱼化石》,这一片《鱼化石》中的怀抱着并且照出了令世界各时代的恋。”
这个安徽姑娘不是别人,正是安徽张氏四姊妹之一的大才女张允和。
卞之琳虽然精通中西文化,著述等身,但却拙于口才,寻常讲话结结巴巴,很不伶俐,加上内向性格,使他在感情上吃尽苦头。正如张允和所说的,卞之琳是一个极不开朗极为内向的人,是一个不善于、也不敢于表达自己的感情的人。唯一的途径,只有诉之文字和诗篇。
对卞之琳的倾情,我相信张允和女士不是全无所知的。张女士在答复苏炜询问时说道:“他后来出的书,《十年诗草》《装饰集》什么的,让我给题写书名,我是给他写了;他自己的诗,让我给他抄写,我也写了。可是我也给所有人写呀!我和他之间,实在没有过一点儿浪漫。他诗里面的那些浪漫爱情,完全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所以我说,是无中生有的爱情。”
溯自1937年,卞之琳客居澄州雁荡山大悲阁寺,特地编选了他的近作,题为《装饰集》,注明“献给张允和”的,这已间接表达了浓浓的情谊了,张允和不可能感觉不到的。这本诗集由戴望舒的新诗出版社出版未果,后来编入《十年诗草》,也是由张允和题的书名。
卞之琳为了表达对张允和的深款情谊,自己曾把《装饰集》抄录一遍,准备把这手抄本,赠送给张允和,最终也没送出去。
问题是卞之琳从未向张允和直接表达过爱意。如果他学习当年沈从文追求张允和的三姐张兆和的死劲──他深埋在地下单恋的种子,说不定有破土的机会。当年沈从文天天给她的学生张兆和写情信,张不胜其扰,把情信交给校长胡适处理,后来沈从文转到别的大学任教,仍然死心不息地给张兆和写情信不辍,终于打动美人芳心。
无疑,沈从文是情关的一员闯将,卞之琳缺乏的恰恰是这份胆识,不免遗恨绵绵。
从爱字通到哀字
沈从文曾在《三生》文章里,隐含揶揄卞之琳单恋张允和的鳞爪:“……然而这个大院中,却又迁来一个寄居者,一个从爱情得失中产生灵感的人,住在那个善于唱歌吹笛的聪敏女孩子原来所住的小房中,想从窗口间一霎微光,或者书本中一点偶然留下的花朵微香,以及一个消失在时间后业已多日的微笑影子,返回过去,稳定目前,创造未来或在绝望对孤寂中,用少量精美的文字,来排比个人梦的形式与联想的微妙发展……”
晚年的张允和曾说道:“那时候,在沈从文家进出的有很多朋友,章靳以和巴金那时正编文学季刊,我们一堆年轻人玩在一起。他(指:卞之琳)并不跟大家一起玩的,人很不开朗,甚至是很孤僻的。可是,就是拼命给我写信,写了很多信。”
换言之,这是卞之琳一厢情愿的单恋,这一恋情旷日持久,整整维持了一个甲子。打从1933年秋在沈从文家邂逅在北大读书的才女张允和开始,卞之琳便为她的丰仪所倾倒,此后,牵魂梦绕,一发不可收拾。
原来被闻一多称赞不写爱情诗的卞之琳,改变了初衷,为张允和写下大量驰名的爱情题材的诗篇,如他的代表作《断章》《鱼化石》《无题》等。
卞之琳的苦恋与时俱增,一层一层地积淀在他的心底,他的情诗原是地下感情熔岩的喷发,所以字字珠玑,行行深情。诗人这份深情虽蘸满心中流淌如泻的泪痕,却刻意令人深沉莫测。这也是他自况自喻的“古代人的感情”:“古代人的感情像流水,积下了层迭的悲哀。”(《水成岩》)而时间“磨透于忍耐!”“回顾”时还挂着“宿泪”(《白螺壳》)。
卞之琳有点守株待兔式地枯候“吹笛聪敏女孩子”的眷顾,再没有结识其他异性朋友,待到张允和1948年与汉学家傅汉思在北平结婚。七年后,1955年他才与现任夫人青林结婚。
婚后的卞之琳,仍然余情未了,念念在兹。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刚开放,我便收到一篇散文稿,是由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转给我。文章是给《海洋文艺》,我当时在该杂志任事。当我收到这篇文章时,怔忡老半天。因为整篇文章的笔迹是老诗人卞之琳的,作者的署名却是张允和。
后来我在北京见到卞之琳,我特地就此事探询过他。他腼腆地说:“因为我要保留她的手稿!”
那是个还没有复印机的年代。仅仅是为了保留她的手稿,已届七十多岁的诗人花了不少力气用硬笔一笔一画地誊抄了这篇稿。这篇稿比起诗人自己写的稿更工整清晰、更用心。
卞之琳逝世后,卞之琳的女儿青乔将其父于1937年为张允和手抄的一卷《装饰集》以及一册《音尘集》、一卷张允和手抄的《数行卷》,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数行卷》(七首诗)是张允和以毛笔蘸银粉、用秀丽小楷写的,卞之琳把这手抄本一直随身携带,直到他离世,可见对其真爱。
二十多年过去,卞之琳也已离世整整十三个春秋。他是带着这一段终生不渝的苦恋上路的。
以苦恋的长跑者姿态出现的卞之琳,最终的结局,在他的《白螺壳》已预见到了:
我仿佛一所小楼,
风穿过,柳絮穿过,
燕子穿过像穿梭,
楼中也许有珍本,
书叶给银鱼穿织,
从爱字通到哀字!
出脱空华不就成!
好一句“从爱字通到哀字”的沉痛喟叹,至于是否“出脱空华不就成”那样的洒脱,相信这只是卞之琳故作轻松的哀鸣而已。
也许心思纤细的女儿,深谙父亲可昭日月的一片苦心,她把卞之琳单恋私下的“定情之物”,让文学馆去珍藏,不让散失。时光荏苒,留下的,恍如鱼化石,凝住了一段天荒地老的痴情,永恒长存。
不管怎样,这段从来没绽过芽、开过花、更没有结过果的感情,长年在诗人心中激荡巨大的波澜,发酵并酝酿成醰然醇厚、流传不衰的诗篇,造就了一代大诗人。
有洁癖的卞之琳
卞之琳给我的二十多封信中,不乏长信。之前发表的短信,因为篇幅所限,内容较简单。倒是他的长信,涉猎的题材较广泛,内容也丰富得多了,从中更可窥他的治学态度、学养,以至他的人生取态。
我特选登一封较代表性的长信,全文如下:
耀明先生:
接到你六月十四日信,还没有顾到作覆,前天又接到七月份《海洋文艺》。
首先让我祝贺你们能发表到《时间》这首诗,我个人认为是艾青年来发表过的最好一首新作,也为国内若干年来少见的好诗。
其次,一定会使你感到扫兴的是:我出于诚摰的关切,劝你不要轻易写那本《中国作家散记》。诚如你自己所说,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你当然知道的,去年杜渐、苍梧出于一片好心,从我的随便谈话中整理出一篇访问记,未经我本人看过,发表了,有不少事实和说法错误(倒没有什么政治错误),害得我不得不以补充方式给《开卷》第四期发表一篇《通信》不着痕迹地把一些主要错误更正了。这篇《访问记》又被这里一种内部刊物转载了,在许多编辑部广为流传,每听人谈到,我总要请他找第四期《开卷》看看我那篇《通信》,这也许仅是我出于我一贯的洁癖(我常常甚至于自己一发表了什么就非常后悔),别人爱热闹可能无所谓。死者自己当然更无所谓了,可是也还有尚在的死者的亲友。(你寄给我的那本《选集》序文里,对我所作的评语可能很有见解,而也可能中肯的,只是一些事实错误,倒如我用过H·C的笔名之类,使我看来总觉得不舒服)目前内地一些高等院校中文系编印了好几种中国当代作家传等之类的小传,内容雷同,大多是经过作家自己审核过的,都是内部数据,当然也是公开的“秘密”,我这个循规蹈矩的死心眼人总认为不好寄给你们看,只好请原谅。如果你已经不得已写了那本书,出版前征询一下有关的人的意见,或者也是唯一避免好心好意使人不愉快的办法吧?
最后,我想征询你一点意见。月前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汉语翻译及其改编电影的汉语配音》,又写长了,约有一万一千字,送交了约我写稿的一个大型刊物。竟以“太深”的理由还给了我。其实,我还是做普及性工作,给学术性刊物,应是太浅了。我这次不怕人家说我“王婆卖瓜”,就一些例子对照一下朱生豪的“权威”译文,和我自己的译文,再通过上影译制片厂1958年根据我的译本给奥里嘉纲埃主演的那部老影片整理配音,作一番检验(这部黑白片今年重新公映,而且上电视,遍及内地各县,看的人次不少),看起来是些琐屑,实际上是讲的运用汉语译诗以至写法的基本工。我是鉴于我国多少年来写诗、译诗、读诗的大半丧失了对祖国语言的艺术性能的感觉力和鉴别力,而费此唇舌。文章全无政治问题,不论是任何地方,除非说琢磨祖国语言也就是一种政治。内地也不是没有发表的地方,只是我想先请你考虑能否给《海洋文艺》发表,或转告苍梧,他们的《八方》想不想考虑发表。你们是月刊,出得快一点,所以先问问你。
编安!
卞之琳 六月十八日
这封信是我在编《海洋文艺》月刊时卞之琳寄给我的,时间是1979年。
艾青的《时间》(共五十行),发表在1979年7月号的《海洋文艺》上,卞之琳读后,很为激赏,依稀记得这首诗的开首是这样的:“时间与空间/有一个共同的母亲/叫做‘无限。”
信中提到的《中国作家散记》,是我于1980年完成的著作,易名《当代中国作家风貌》(正续编,香港昭明出版社),台湾远景出版社后易名《当代大陆作家风貌》出台湾版,并由韩国圣心大学出版社翻译韩文版出版。
书内收有《诗人、翻译家卞之琳》,出版前,曾给卞之琳过目,也承他订正一些错误。
卞之琳是一个治学十分严谨的人,可以说达到一丝不苟的地步,这也就是卞之琳信中所说的“洁癖”。
信中他以1978年11月发表在香港《八方》文艺丛刊一篇访问记出现的谬误,警戒笔者。
卞之琳对《八方》的出错,很是耿耿于怀。由香港大学张曼仪教授编的《卞之琳年表简编》,也提到这一笔账:
1978年11月,香港《开卷》创刊号刊出古苍梧(古兆申)的访问稿《诗人卞之琳谈诗与翻译》。11月26日,写信给古苍梧对访问稿作出订正加补充,该信刊于《开卷》第四期(1979年2月)。
卞之琳是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他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便译了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时年十九岁。
此后,他还翻译大量西方诗人的作品和文论。1954年完成《哈姆雷特》的翻译,此后他完成“莎士比亚悲剧四种”,除了《哈姆雷特》,还有《奥瑟罗》《里亚王》《麦克白斯》。
信中提到他写的《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汉语翻译及其改编电影的汉语配音》长文,原先给《海洋文艺》发表的,主编吴其敏嫌太长,最终转由《八方》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