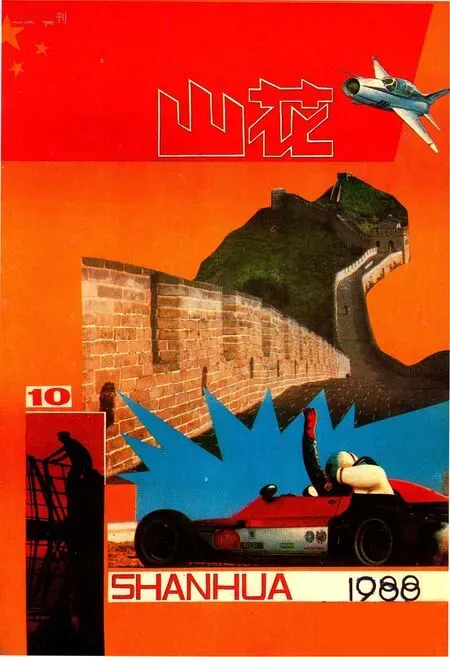“忧患”中的“朝鲜诗”境界
——论丁若镛汉诗的忧患意识
2015-06-19孙玉霞
孙玉霞
“忧患”中的“朝鲜诗”境界
——论丁若镛汉诗的忧患意识
孙玉霞
丁若镛(1762-1836)是朝鲜实学派的领军人物、“朝鲜诗”思潮的摇旗者。他高亢的“朝鲜诗”宣言与其“忧时忧民”的汉诗作品共同织成一面鲜明的旗帜,引导朝鲜学者正视朝鲜社会现实、关注百姓生存状态、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民族文学,将民族意识在文学乃至思想领域推向了新的高度。本文将研究的视角聚焦在被诗人内化于其诗作中的“忧患意识”,采用汉诗文本分析与文献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寻丁若镛笔下“忧时患民”、“思国思世”的“朝鲜诗”境界。
对百姓命运的深切关注与担忧
“以民为本”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孟子更是直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丁若镛深受孟子思想影响,在诗歌创作中常常表现出对底层百姓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注,生动再现了朝鲜王朝后期庶民们在乱政重压下艰难挣扎的生活惨景。字句间饱含着诗人“爱民”、“忧民”的儒者情怀,浸透着一个思想家面对末世乱象的担忧与焦灼。
丁若镛在其许多诗歌作品中,毫无粉饰地再现了当时庶民百姓的凄苦际遇,犀利尖锐地表达了对苛政酷吏的憎恶与批判。这类作品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哀绝阳》《有儿》《饥民诗》等汉诗。诗人在《有儿》中,描述了大旱之年,流民四起,一双惨遭父母遗弃的小儿女的悲凉、凄惨境遇:
有儿双行,一角一羁。角者学语,羁者髫垂。失母而号,于彼又岐。
执而问故,呜咽言迟。曰父既流,母如羁雌。瓶之既罄,三日不炊。
母与我泣,涕泗交颐。儿索乳啼,乳则枯萎。母携我手,及此乳儿。
适彼山村,丐而饲之。携至水市,啖我以饴。携至道越,抱儿入麛。
儿既睡熟,我亦如尸。既觉而视,母不在斯。且言且哭,涕泗涟洏。
日暮天黑,栖鸟群蜚。二儿伶俜,无门可闚。……
——《有儿》
诗人首先描写了一对小儿女失去母亲后的悲苦与无助。姐姐不过六七岁,弟弟刚刚学会说话。离开了母亲的怀抱,两个弱小的孩子不知该往哪里去。借孩子之口,诗人详细地描述了灾荒下百姓生存难以为继的惨景。父亲已经离家多日,母亲一人留在破败的“家”里守护着一对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幼子。米缸早已见底,厨房也已“三日不炊”。没有粮食,丈夫又不回来,这让家里的女人和孩子陷入了生活的绝境。接着,诗人细致入微地描写了陷入绝境后母亲的挣扎。她无助地抱着孩子们痛苦哭泣,可惜眼泪没能帮到这位绝望的母亲,反而惹得孩子们也哇哇大哭起来。没有粮食,大人可以忍,懂事的姐姐也在忍,可是还在吃奶的孩子怎么忍得了呢?弟弟哭闹着要奶吃,饥饿煎熬下,母亲的乳汁早已干涸。万般无奈,母亲只得牵上六岁的姐姐,背上吃奶的弟弟离开家门,上街乞讨。这是个流民遍地的大荒之年,母亲靠乞讨不可能养得活她和孩子们。“母亲带我们到集市上给我们买了糖吃,又带我们穿过了那条路,在路边轻轻地摇睡了弟弟。弟弟睡着了,我也躺下睡了。醒来后却发现母亲不见了……”孩子边说边泣,涕泪纵横。日暮西山,飞鸟们都要回家了。两个孤苦无依的孩子却无家可归……此情此景,情何以堪。本该在父母怀中撒娇受宠的孩子们,转瞬间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弃儿。我们能责怪他们的母亲吗?从“啖我以饴”,“抱儿入麛”的情节中,这位母亲撕心裂肺的痛分明可感。两个幼小的孩子,离开了家、又失去了母亲的保护,恐怕难以逃脱活活饿死的宿命;那个在绝境中挣扎徘徊、抛弃了亲生儿女的母亲又能如何苟活?看到如此惨景,人们不禁要问那些在丰收的年景里到处搜刮聚敛的官吏们在百姓需要救济的时候,躲到哪去了呢?那打着筹备荒年里为百姓提供救济的旗号征收走的“还政”米又到哪儿去了呢?
诗人笔下,苦难的百姓在苛政酷吏下的生存危机中丧失了基本的人伦。父母对子女之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它的美好与温馨常常触动人内心深处的柔软。诗人却要把这种美好与温馨在现实世界中的“撕裂”与“毁灭”清清楚楚、原原本本地再现给人们看。在这一弊政下的一幕幕人间悲剧里,诗人对底层百姓苦难遭际的切肤之痛跃然纸面,对苛政酷吏的彻骨之恨力透纸背。
对社会乱政的深度省察与思考
丁若镛汉诗被韩国学者宋载邵先生称为“针对李朝末期病入膏肓的社会现实开出的临床报告”。凭借着实学家特有的敏锐与深刻,诗人断言:诸多眼前事,“无一不失当”的病根就出在混乱不堪、失天理丧人伦的所谓“田政”、“军政”、“还政”以及腐败透顶的“吏制”上。
丁若镛剑锋所指的田政、军政与还政,是当时朝鲜王朝的基本国策。这些基本国策一方面为王朝统治者提供着维护其统治所需的大部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却因为制度本身存在的巨大缺陷,以及制度执行过程中的纰漏百出,成为各级官吏向百姓“寻租”、公饱私囊的“利器”。在丁若镛生活的时代,上至都城里的权门贵胄下至地方上的吏胥土豪,个个赚得个盆满钵满,朝廷的国库里却空空荡荡,无款可用。空荡荡的当然不仅是国库,底层百姓的家里更是“精简”到无米可炊,无衣可着的境地。
在《耽津村谣》里,诗人形象地勾画了一个催收田税的胥吏形象。诗人开篇写道:“棉布新治雪样鲜”。看着自己织出的“雪样新”的棉布,劳作者自然是满心的欢喜,大概还在心里盘算着是该用它给自己的孩子做件新衣,还是拿到集市上卖掉,换点儿银钱来让一家人吃顿饱饭呢。然而,诗人笔锋猛地一转,一个催收田税的胥吏凶神恶煞地跳了出来。诗人用“黄头”、“如星火”、“三月中旬道发船”分别描写了胥吏夺人财物时的衣着、隳突乎南北的动作和冠冕堂皇的托词。贪婪残忍而又道貌岸然的督税官吏形象就这样在诗人的笔下活脱脱地蹦了出来。
在《奉旨廉察到积城村舍作》《哀绝阳》《夏日对酒》等作品中,丁若镛又把抨击的矛头对准了朝鲜王朝的“军政”。自15世纪末起,朝鲜王朝的“军政”逐渐演变成一种税收手段。政府规定,所有符合兵役年龄却没有服现役的男子,必须缴纳相应数量的“军布”。为了增加税收,政府把兵役的年龄范围一扩再扩。最后,上至白发老者,下至襁褓男婴都被纳入了军布税的征收范围。诗人在《奉旨廉察到积城村舍作》中用白描的手法再现了这一令人称奇的军政之下,底层百姓家艰难的生存境况:年方三五岁的两个年幼的男孩子都已名列军籍,“两儿岁贡钱五百”令其父母不堪重负,也让年幼的孩子缺衣少穿——“儿稚穿襦露肩肘,生来不著裤与袜。”在《哀绝阳》中,诗人对军政的控诉又推向了新的高潮:在“芦田少妇”的长哭中,一幕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拉开了帷幕。贫苦的农家难以支付“舅丧已缟儿未澡,三代名签在军保”的军布重税,只得眼睁睁地看着酷吏们咆哮着牵走家中唯一的耕牛。丈夫在极度的愤懑中“磨刀入房”,自去其势……
猛烈抨击同样祸国殃民的“还上”之法也是丁若镛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诗人在《夏日对酒》中,直斥“还上”乃是打着赈济之名行抢夺之事,害百姓“万命哀颠连”的恶法。既然是借贷活动,理应两厢情愿。百姓不愿借粮,政府岂能强制?甚至要求百姓不“借”也要“还”?事实上,就在这一借一还之间,百姓的劳动所得有多少流入了官宦们的口袋,正所谓“赢余肥奸猾,一宦千顷田”。实学家的视野让诗人清醒地意识到,如此“还上”只会让民更苦,国更弱!诗人高声呼吁让“还上”成为名副其实的“赈济之策”。
混乱的土地制度逼农为丐,致使流民遍地;沉重而漏洞百出的税收制度使国库日空、民不聊生;颠倒黑白的再分配制度——“还上”让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身份等级制度下不合理的人才起用制度造成了巨大的人才浪费,令举国上下几无可用之才……丁若镛的汉诗仿佛一把把钢刀利剑,刀刀砍向祸国殃民的封建弊政,剑剑直指混乱不堪的社会制度要害。精辟透彻、发人深省,展现了浓重的时代特点和民族忧患意识。
对民族自觉的呐喊与企盼
“我是朝鲜人,甘作朝鲜诗”是丁若镛在晚年所作《老人一快事六首 效香山体》(其五)中高声喊出的“朝鲜诗”宣言。它上承李瀷、洪大容、朴趾源等实学派先驱的朝鲜民族意识自觉之衣钵,下开朝鲜民族文学崛起之先河,在忧国思世的实学浪潮中,将朝鲜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在这首诗中,诗人写道:“老人一快事,纵笔写狂词。競病不必拘,推敲不必迟。兴到即运意,意到即写之。……区区格与律,远人何得知。……梨橘各殊味,嗜好唯其宜。”呼唤朝鲜诗人摆脱汉字的格律束缚,用朝鲜人自己的方式酣畅、痛快地摹写朝鲜国家自己的现实,抒发朝鲜民族自己的喜怒哀乐。
在丁若镛的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半自由体式诗的偏爱。他的《龙山吏》《波池吏》《海南吏》《石隅别》《沙坪别》《龙潭别》等名篇都采用了五七言古体诗的形式。满目疮痍、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让丁若镛这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焦心顿足却有力不得施,只能以诗笔为重锤,为世人敲响嘹亮的改革洪钟。诗人焦灼的赤子之心突显于其大部分诗作中,构筑了其特有的“抑扬激越”的诗歌风格与“拯时济世”、“为天下国家”的“朝鲜诗”境界。
在创作实践中,诗人还非常注重素材的选择与主题的提炼。他不仅生动再现了李朝末期的种种社会病态,急切地呼吁改革,更在田园描写中渗透出茶山实学的底色,拓展了田园诗的创作素材。丁若镛笔下的田园不再是士大夫们闲适生活的世外桃源,而是劳作生产的一方乐土。
“弘哉灌溉力,千亩得油油。”
——《过景阳处》
“呼邪作声举趾齐,须臾麦穗都狼藉。杂歌互答声转高,但见屋角纷飞麦。”
——《打麦行》
“盆中纳茧数宜明,莫把胡儿信手倾。”
——《蚖珍词七首赠内》
这些与生产生活相关的“俗物”都被诗人选作田园诗的素材,丰富了其“朝鲜诗”世界的内涵与情趣,也充分体现了诗人对国家发展、民族崛起的殷切期待。
所谓不破不立,诗人要打破的是对中国的盲目崇拜、对中国诗歌的一味模仿,要树立的是对朝鲜民族传统的传承、对朝鲜社会现实和民俗民风民谣的重视。我们在《狸奴行》《豺狼》《海狼行》《虫食松》等多首寓言诗中看到了诗人对朝鲜寓言类文学传统的艺术传承;也在《长鬐农歌》《耽津农歌》《耽津村谣》等优秀的民谣风汉诗中看到了诗人对朝鲜民族风俗和生活实况做出的原生态的展示。诗人甚至将为当时正统文人所不屑的朝鲜“方言俗语”用音读、训读等方式“将俗化雅”,写入诗中。借此真实、生动地再现朝鲜民众的生活、思想与情感,表现出实学派诗人的果敢与睿智。
总之,丁若镛的“朝鲜诗”宣言是对当时朝鲜诗坛浮华、模拟文风流弊的强烈对抗,是一位思想家警醒世人、呼吁改革的需要,也是一种民族意识的觉醒。诗人要用自己的诗笔描写自己祖国的现实、解决朝鲜民族的问题,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作为实学的集大成者和李朝文坛的重要诗人,丁若镛的诗作与其实学思想交相辉映,大放异彩。诗人将“忧民”、“忧国”、“忧时”的忧患意识与“思国”、“思民”、“思时”的思考和改革意识浸润笔端、流淌在诗作的字里行间,构筑起“忧时患民”、“思国思世”而又充满民族意趣的“朝鲜诗”境界,带给世人精神的震撼与深刻、久长的思考。其汉诗凭借表现内容的博大、思想的精深、民族意识的自觉,在朝鲜文学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作品中渗透着的茶山实学思想对朝鲜近代思想的启蒙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释:
①丁若镛在《与犹堂全书》,《与金公厚履载》文中写道:“六月之初,流民四散,嚎哭之声,殷殷田田。婴儿之弃于道者,不计其数。伤心惨目,不忍视不忍睹。”
②丁若镛:《与犹堂全书(卷Ⅰ)》,韩国:新朝鲜社1934年版,第74-75、79页。
③孙玉霞:《朝鲜诗人丁茶山的诗歌创作研究》,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93页。
孙玉霞(1976— ),女,河北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韩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韩古典文学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