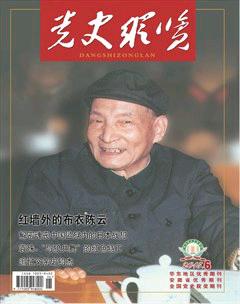袁殊:“与狼共舞”的红色特工(上)
2015-06-16卢荻
卢荻
袁殊是中国现代谍海风云中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其身份多面复杂,谍战生涯惊险离奇,人生经历跌宕起伏,可称得上是人世间绝无仅有的特工高手。袁殊除拥有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高官等诸多身份之外,其秘密身份却是一名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人员,并一度成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特工。他打入敌人内部,在扑朔迷离的谍海中“与狼共舞”,剑胆琴心,为中共获取了大量的战略情报,并成功地掩护了潘汉年及其情报班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朱德称其为“我党情报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
上海新闻界的一颗新星

袁殊,本名袁学易,化名曾达斋,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一个衰落的书香门第。父亲袁晓岚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后在国民党驻沪机关的工团工作。母亲贾氏,为前清官办盐商女儿。由于家庭经济困窘,袁殊幼年即不得不随母亲到上海投奔父亲。但时任国民党驻沪机关要职的袁晓岚却因与学生姘居而冷落贾氏母子。年少的袁殊不得不去卖大饼、油条,擦鞋,烧老虎灶,12岁时便被送进一家印刷厂做排字学徒工。袁晓岚虽然没有在经济上资助贾氏母子,却仍然关心着儿子的成长。经他的友人介绍,袁殊得以免费入读著名的私立学校上海立达学园,半工半读。据袁殊之子曾龙回忆,袁殊崇拜立达学园老师袁绍先、夏丏尊、丰子恺等,主张建立“无命令、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并参加无政府主义团体“黑色青年”。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运动,14岁的袁殊参与罢工、罢市、罢课大游行等活动,成为学校里一名活跃分子。
1927年初,袁殊参加了北伐军,受到袁父之友胡抱一(时任国民革命军江南别动军司令)的提携,成为其秘书。不久,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下级军官,并加入了国民党。
1928年初,袁殊脱离军队返回上海,不久就参加了高长虹主持的无政府主义文艺团体“狂飙社”,开始了在文艺界的活动。
1929年秋,因狂飙社解散,袁殊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一所新闻学校攻读新闻学,同时又广泛涉猎政治和历史知识领域,接触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初步接受了马列学说的洗礼。
1930年冬,袁殊因经济困难被迫回国,一度参加洪深领导的“联合剧社”活动。剧社在南京演出十分成功,引起南京市国民党党部注意。党部主任赖琏、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先后宴请剧社。袁殊于席上痛斥国民政府,发表左倾言论,与演员王莹同被视为左倾分子。

此时,袁殊对当时上海的报纸十分不满,认为这些报纸是买办阶级的工具,于是创办了《文艺新闻》周报,于1931年3月16日开始发行。这张小报推出不久,便以其独到的新闻眼光和大胆泼辣的风格而引人注目,发行量迅速上升。中共秘密党组织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负责人冯雪峰等人对这张小报给予了极大支持,不仅积极为其供稿,而且派党员作家夏衍、楼适夷具体参与其工作。连鲁迅、茅盾等文坛巨匠也不断在该报推出佳作,使这张小报风靡一时。据茅盾回忆,当时袁殊仍未加入左联,但与其成员关系紧密。左联成员投稿《文艺新闻》,及后更参与编辑工作,使之成为左联外围刊物。
其间,对袁殊个人政治生命与《文艺新闻》影响最大的,是对左联“五君子被害”事件的报道。
1931年1月17日,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李伟森在上海东方旅社开会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于同年2月7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由于国民党对消息的严密封锁,外界几乎无人知道左联五作家被害的情况。同年4月,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凶残,时任左联中共党团书记的冯雪峰找了多家报刊,希望能将这一信息发布出去,但各报慑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均不敢刊登。焦急之中,冯雪峰想到了袁殊刚刚创办的《文艺新闻》。由于当时冯雪峰还不认识袁殊,他便到陈望道处了解袁殊的情况。在陈望道的介绍下,冯雪峰找到袁殊,介绍了左联五作家被害的情况,希望袁殊能在《文艺新闻》登载这一消息。袁殊深知国民党当局对新闻管制很严,披露这样的新闻需冒很大风险,但其对国民党反动派残害进步作家的所作所为十分愤恨。为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嘴脸,袁殊心生一计,与冯雪峰密切配合,上演了一出双簧戏。首先,冯雪峰寄来一封署名“蓝布”的读者来信给《文艺新闻》,询问五作家下落。3月30日,袁殊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封读者来信探听他们的踪迹》为题在《文艺新闻》头版发表,立即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反响,引起各界对5位作家命运的关注。接着,冯雪峰转来两封读者来信:《作家在地狱》(署名曙霞)、《青年作家的死》(署名海辰),告诉读者,这5位作家“已被枪毙了”。4月13日,袁殊在《文艺新闻》上以《呜呼!死者已矣》的题目刊登了这两封来信。随后,袁殊又将这5位作家的照片登出,并发表了各类人物对他们被害的态度。这样,既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又使国民党当局找不到消息来源,无可奈何,从而保护了该报的安全。袁殊的机智和胆略受到广泛称赞,鲁迅对此大加赞赏说:“袁殊、适夷两个人年龄很轻,勇气很大。”并在《文艺新闻》上发表了《上海文艺之一瞥》及《湘灵歌》等诗文。《文艺新闻》因此销量大增,袁殊顿时成为新闻界的一颗新星。新中国成立后,茅盾在回忆中也对袁殊这种斗争方式表示赞赏。他说,《文艺新闻》以公正、中立,有闻必录之面貌出现,与国民党进行公开、合法的斗争,存在了1年零3月之久,是左联所有刊物中,维时最长者。这使得左联成员进一步认清合法斗争之必要,从而转变策略。
袁殊除了出版《文艺新闻》及《烽火》外,还组织“曙光剧社”,其表现受到中共赏识。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汉年的堂兄潘梓年邀请袁殊加入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袁殊成为“文总”常委,和潘梓年、朱镜我一同负责对下属文化团体的联络工作。稍后,他又参加了反帝抗日联盟、中国著作者协会,参与发起新闻学研究会等,成了左翼文化界的一位活跃人物。他积极发表著作和译作,在工人队伍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满腔热忱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
“白皮红心萝卜”式的中央特科成员

在与冯雪峰、夏衍、朱镜我的频繁来往中,袁殊主动向他们表达了加入中共的愿望。1931年10月的一天,当时正担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的潘汉年和他的助手欧阳新(化名王子春)在上海静安寺的一家白俄咖啡馆正式会见袁殊。潘汉年代表中共上海秘密党组织同意吸收袁殊为中共党员,同时根据隐蔽斗争的需要,将他调到中央特科工作。潘汉年对袁殊说:“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你的工作是保卫党的组织,今后要渐渐褪去红色,伪装成灰色小市民,寻机打入敌人内部。”潘汉年指定王子春为袁殊的单线联系人和指导老师,由其帮助完成特务工作。“剑胆琴心”则是约定的暗号。潘、王要求袁殊严守组织秘密,做一个“白皮红心萝卜”式的情报人员。从此,袁殊的名字从进步文化圈子中销声匿迹,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谍报生涯。
袁殊当时年方20,此前从未接触特科工作,对情报工作可谓一窍不通。王子春言传身教,使他很快就熟悉了情报工作的“游戏”规则与基本技能。掌握了秘密联络、传递情报等方面的基本技能之后,袁殊他们开始寻找打入敌人内部的途径。王子春耐心地帮袁殊梳理亲朋关系,使袁殊想起有个表兄贾伯涛在国民党中任要职,只是从未与之有过交往。贾伯涛是袁殊娘舅贾宝书的大儿子,由袁殊的父亲袁晓岚推荐到黄埔军校一期学习,曾任黄埔同学会会长,先后在湖北、上海警备司令部任职。在王子春的指示下,袁殊立即设法与贾伯涛取得联系,请求代为谋职。贾伯涛很快便将袁殊介绍给了上海社会局局长、中统头子、湖北人吴醒亚。袁殊在简历中说明自己“厌倦了左倾活动,想过安稳日子”。吴醒亚看了连声称“好”,当即要袁殊加入他的湖北帮,为他打探社会消息。
吴醒亚之所以肯任用在左翼文化活动中有一定知名度的袁殊,一是因为贾伯涛是蒋介石的大红人,不能不给面子;二是由于袁殊写的材料给他留下了好印象;三是因为吴当年从湖北到上海谋出路时,袁殊的父亲袁晓岚曾指点他去广州投奔陈立夫,结果得了势,受恩于袁家,想借此报答。这些社会关系,犹如一把无形的保护伞,为袁殊在险象环生的谍海风浪中遮风挡雨。
吴醒亚所负责的上海市社会局,表面上是要调节缓解社会矛盾,实质上则是以破坏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为主要任务。袁殊被安排为编外特别情报员,专事收集社会情报。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事业,建立自己的骨干队伍,吴醒亚拉拢一批湖北籍的人物组成了一个“湖北帮”,利用政治与同乡的双重关系为其效力。与此同时,他又伙同潘公展、吴开先组织秘密小团体“力社”和“干社”。“干社”在当时几乎与另一个著名的反共组织“复兴社”齐名,势力和影响都不小。袁殊被吴醒亚拉入了“湖北帮”和“干社”,并担任了“干社”的情报股长。而担任行动股股长的则是后来臭名昭著的汪伪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李士群20世纪20年代加入过中国共产党,被捕后自首叛变,因此王子春指示袁殊严密监视李士群的行动。
从1931年冬到1935年春这3年多时间里,袁殊在情报战线上四处活动,左右逢源,干得颇为顺利。
袁殊最初给吴醒亚的情报完全由王子春提供,都是些无重大价值的情报,诸如西南派系联合反蒋内幕之类的消息。一次,在王子春指示下,袁殊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搞到一个重大情报,为吴醒亚立了一“功”。王子春让袁殊趁机向吴醒亚讨个新闻记者的差事,以便开展工作。于是,袁殊被介绍到由著名报人严谔声主持的“新声通讯社”当了一名记者。利用记者这一特殊身份,袁殊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出入各种社交场合,了解与结识许多人。不久,他就因经常出席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新闻发布会而结识了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实际是日本外务省情报人员)。岩井被认为是“中国通”,专门负责搜集中国情报,正需要在中国人中寻找情报关系。袁殊有留日经历,能说流利的日语,岩井很快就看中了他。而袁殊为了获取日本情报,也有意识去接近岩井。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很快建立起情报关系。袁殊答应将通讯社若干不便发布的新闻材料提供给岩井,岩井则答应把领事馆将要发布的新闻信息提前告知袁殊,以帮助袁殊“抢新闻”。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经过一段时间的配合,岩井表示满意,随即向袁殊每月提供200元所谓交际活动费,于是袁殊就成了日本领事馆雇用的一名情报员,打入了日本外务省情报机构。自然,他的这些活动都是得到中共秘密组织负责人批准的。这为日后抗战期间,潘汉年领导对日情报斗争奠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袁殊为发展关系,与著名青帮头目杭石武结为所谓的异姓兄弟,又和帮会首领杜月笙等有密切往来。
受“怪西人”案件牵连被捕入狱

袁殊加入中央特科之后,与王子春紧密配合,进展顺利。随着袁殊获得的情报增多,两人由每星期见一次面改为每周两次。但是到了1934年底,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加上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中共上海秘密组织迭遭破坏,在上海工作了很长时间的王子春已难以继续坚持。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他被通知立即转移前往苏联,临行前甚至来不及通知袁殊,也无法向任何人交代和袁殊的关系。
到了接头之日,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袁殊两次未能与王子春见面。接头失败意味着“断线”。按照单线联系的组织原则,袁殊根本不知王子春当时的上级究竟是谁。焦急之中,袁殊决定去找知道他参加中央特科工作的夏衍,急切地表示自己和组织突然中断了联系,现在想恢复联系,请夏衍转交一封信给江苏省委或者任何一位上级领导人。夏衍望着袁殊焦虑的模样,答应了其请求。
几天之后,化名“小陈”的刘长胜来找袁殊。可过了不久,就改由学生打扮的“小李”来联系,负责传递情报。为此,袁殊多长了一个心眼,特地刻制了两枚闲章,一枚是“剑胆琴心”,另一枚是“流离载道”,他向上级声称:只有见到火漆封口加盖这两枚印章的信件,才是他的真实情报。
多年以后,历史的尘埃落定,袁殊才知道当时的复杂情况。原来,夏衍一时找不着中央特科的人,便把袁殊的信交给了组织关系在特科、工作关系已转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蔡叔厚。蔡叔厚觉得远东情报局正需要像袁殊这样的人,便请示决定把袁殊的关系转到远东情报局,但他并没把详细情况告诉夏衍,只含糊地说:“袁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你告诉他用新的联系暗号接头吧。”袁殊就这样在不知就里的情况下,参加了远东情报局的工作。
袁殊为远东局收集情报不久,就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怪西人”案件。国民党军统湖北站逮捕了中共党员关兆南。关氏在软硬兼施下叛变,随后带领军统特务诱捕了从上海抵达武汉与他联系的交通员陆独步。军统把陆独步押解上海,陆独步供出其哥哥陆海防,陆海防再供出共产国际中国总支部负责人、化名约瑟夫·华尔敦的罗伦斯。特务头目沈醉和两个特务,押着陆海防抓捕了华尔敦。法租界巡捕房见逮捕一个欧洲人,不同意马上引渡。面对巡捕房的审讯,华尔敦经验老到,拒绝回答一切问题,因此巡捕房无法确定其真实身份。于是,各家报纸均说:租界捕房抓获一名来历不明的“怪西人”。次日,陆海防再供出一些与他有工作联系之人,袁殊也因此被捕。
陆海防投降后,向袁殊展示其字迹,袁殊方才明白,一直与自己秘密联系,交付工作的上级,正是陆海防。由于已经有陆海防的旁证,袁殊便承认了自己曾为中共情报系统和远东情报局工作。当时直接经办“怪西人”案件的是戴笠系统的王新衡。王和袁殊本就很熟,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当袁殊暴露了中共的政治背景后,王新衡便竭力对袁进行拉拢。吴醒亚获悉袁殊被捕并已暴露真实身份后,也对袁采取拉拢的态度。显然,戴笠和吴醒亚都把袁殊看作是可以利用的人才,都想把袁殊收罗到自己的门下。因此,袁殊被捕后不仅没有受到皮肉之苦,相反却处处受到“关照”。在敌人面前,袁殊没有自首叛变与出卖组织和同志,因此并没有引起组织被连锁破坏。他在敌人面前采取了一种灵活、变通、圆滑的策略,尽量保护自己。
戴笠为了拉拢和劝降袁殊,特派武汉行营法官徐业道到上海对袁殊“做思想工作”。戴笠要徐业道向袁殊转达他的话说:“你的事我都知道了,等风波平息后,你可以加入到我们团体里来。你还年轻,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就此完结;要么参加蒋委员长领导的抗日工作。”徐业道要袁殊对戴的话明确表态,袁殊考虑过后,写下数十言:“我不认识怪西人,过去也不认识陆海防,但从事过共产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现在中日两国的问题是抗日问题,希望蒋先生领导全国人民抗日。”
不久,袁殊被押到武汉,由武汉行营法庭开庭审判。审判的结果是从轻发落:袁殊明明是被军统秘密逮捕的,判决时却被说成是“投案自首”,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兼容思想”的“思想文化罪”论处,判监2年9个月,按律减刑一半,只需执行刑期1年3个月。刑罚甚轻,主要是因为袁父向陈立夫求情,夏衍、蔡叔厚等人亦托人解救,甚至日本驻沪领事馆亦起了作用。
袁殊被宣判后,被转送到湖北省反省院服刑。该院院长黄宝石恰恰是吴醒亚湖北帮的“参谋长”,和袁殊也有些交情,因此,袁殊在反省院受到优待。袁父病故后,袁殊还被允许出狱处理后事,把袁晓岚灵柩送返湖北蕲春,方才回到反省院。被关押期间,他可以读书、写字、打球,可以写新闻短稿,还可以请假外出办事。1936年5月,袁殊实际“服刑”时间不足一年就被从反省院放出。黄宝石赠与其200元钱以及一张直通南京的船票,要求他晋见陈立夫。袁殊以路费已足,并未接受赠款。被关押和受到优待并没有改变袁殊当初参加革命入党的初衷,因此,他被释放后首先想做的事就是希望尽快找到党,希望能够继续为党工作。袁殊直到抵达上海,方才下船,会见亲人。
袁殊返沪后,未能联络上旧友,甚为焦虑,最后只好去找虽不是中共党员但同党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的孙师毅,通过他见到了刚从陕北来上海不久的冯雪峰。冯雪峰此次来上海的主要使命是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袁殊向冯汇报了近年来的情况。冯雪峰初步查明了袁殊在被捕期间的表现后,采取冷处理的办法,建议他先找一个教书的职业避一避风头再说。袁殊自然感到失望,表示想再去日本学习一段时间。冯雪峰表示同意,随后给袁殊送去50元路费。
袁殊动身之前,又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联系。鉴于袁殊曾是日方的情报人员,释放后又主动找上门来,领事馆极表欢迎,立即为袁办妥一切赴日手续,并送给200元路费;同时让袁到东京后再去找正在外务省供职的岩井英一联系。袁殊到日本后即去找岩井。岩井果然对袁殊给予了特别的关照:不仅为袁介绍学校,介绍一批学界与政界朋友,而且每月向袁提供150元的生活用费。岩井之所以对袁殊特别关照,当然不是出于所谓的朋友之谊,而完全是一种政治投资。袁殊自然对此心中有数,而他也乐于利用这样的“特别关照”为未来做打算。(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