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方块与马列维奇的“乌托邦”
2015-06-12韦承红
韦承红
迄今为止,尽管人们对抽象与前卫的讨论似乎已经多得让人厌烦。可当今观众在面对马列维奇(Klasimir Malevich)的《黑色方块》(Black Square,1905)时,反应却仍然大相径庭:顶礼膜拜者有之,不屑一顾者亦大有人在。然不论褒贬,当今世代的人们都难以再亲身体会它曾经带给世界的那种冲击,所幸我们还可以逆流而上,追溯到其诞生的时刻,尝试理解抽象主义最初所寄寓的希望。
故事发端于1915年年末。以马列维奇为首的共14名俄国前卫艺术家在当时的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举办了一场意义重大的展览。就在这次“0.10:最后的未来主义展”上,名垂青史(或臭名昭著)的《黑色方块》横空出世。在马列维奇一生的创作中,《黑色方块》是对其艺术理想最极致的诠释。展览标题“0.10”中第一个“0”,含义即是让艺术回归原点,“0”在马列维奇的观念中并不意味着消极的虚无,他曾说过:“存在物之动始于‘0而包含于‘0”。“0”既是“终极”的象征,同时孕育了无限的可能性。这件作品在多重意义上颠覆了西方艺术的传统理念。我们眼中所见的是白色画布上的一个黑色方块,笔触清晰可见,遗憾的是形状不太完美,因为我们能轻易发现方块的四边与画布的边缘并不平行,或许意味着形状本身并非作品的意义所在。而艺术家的意匠也不仅体现于画面中。在“0.10”展上,这件作品被高悬于墙的角落处,离地面数米之高——如此情形反倒更像是黑色方块高高在上地俯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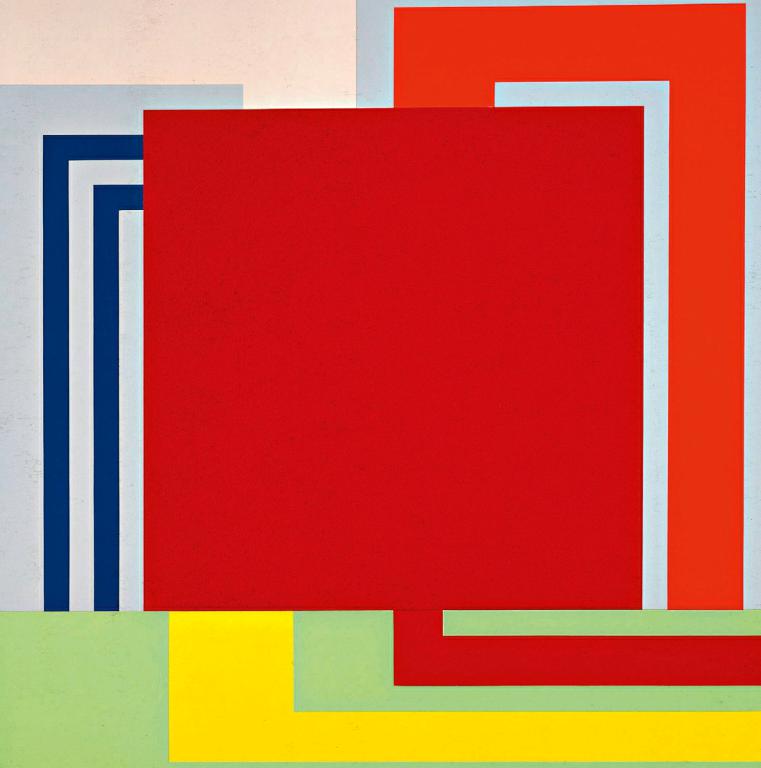
马列维奇在这次展览上为这样一件作品选择这个位置自是别有深意。按东正教传统习俗,这个角落正是信徒在家中放置最重要的一面圣像的“圣像角”(又称“红色角”)的方位。这一举措赋予了作品以某种厚重的宗教意味,但我们无需过于深入地解读黑色方块与东正教之间的精神联系,因马列维奇考虑得更多的应是颠覆而非继承。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一细节反映出视觉已经不是这件作品真正关心的问题(从这一意义看来,现今大多数画展都将该作以正面平视的角度展陈以便观众从近处细看,并不是一种理想的体验方式)。它的存在自身便是意义,这是《黑色方块》最“前卫”的一面。它不但摒弃了叙事性(narrative),也不是对任何客观物质世界之物的再现(represent),甚至称不上是“象征符号(symbol)”,因为它也不是任何一种既存概念的具象化,且排除了一切“技艺”因素的干扰——它是对“艺术”这一概念之传统价值体系的一次彻底的反叛。《黑色方块》极为准确而有力地表达了这批前卫艺术家的愿望:通过激进的、毁灭性的革命创造新的时代。早已湮没在各式标语口号的当今一代或许已经难以再被此类言辞打动,但对它的缔造者来说这绝不是耸人听闻的噱头,而是一场神圣的革命。但抽象主义艺术后来常常被打上脱离现实的标签,以至于这些误解自身成为了抽象艺术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然而就动机而言,脱离现实绝不是马列维奇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一批俄国前卫艺术家的初衷,而是他们在亲历了那场空前绝后的社会革命后,受到其政治理想的感召而自觉发起的一场艺术“革命”。马列维奇对“至上主义(Suprematism)”之理想与俄国十月革命之初对建设“乌托邦”式国家的理想之间无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乌托邦”原文是“utopia”,这个单词在希腊文中既有“美好之地”又有“不存在之地”两重意义。这个意味深长的单词被十六世纪英国作家托马斯?摩尔(Thomas More)借用为标题,写成了一本游记形式的文学作品;书中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基础,虚构了一个世外桃源,将之描述为一个拥有“完美”政治体系和道德观念的国家。其社会遵循小国寡民、财产公有的理念,其民众精神充实而自由且人人平等。《乌托邦》的核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之诸多弊端的反思与讽刺,它所描述的国家形态和对人性的理想成为了早期社会主义革命者的蓝图。依《乌托邦》中的描述,物质主义被认为是阶级、压迫、战争和犯罪等问题的病灶,是人性无法获得自由的根源。而这一思想也成为了马列维奇创立“至上主义”的原动力——他将对物质主义的反抗表达为反对艺术耽溺于对客观物象的模仿再现,主张“感受”才是艺术应当追求的纯粹和永恒之物。

“至上主义”理念中寄寓着马列维奇对平等和自由的理解。马列维奇在这里清晰地解释了“黑色方块”的意义:无物的“荒漠”中唯一真实的“感觉”。马列维奇认为,对物象的执着蒙蔽了艺术的纯粹——正如物欲对人性的扭曲;反对艺术服务于国家和宗教,是因为国家和宗教归根结底都是人对物欲之追求而造出的不同形式。因此,艺术必须摆脱客观性再现,不再服务于国家和宗教,才能返璞归真,获得真正的解放,去追寻自身的价值。说到这里,我们能够清晰地体会到,马列维奇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背后并不仅仅是在谈论艺术,而是对人性的折射和隐喻。“至上主义”阐释的虽然是艺术的自由,但其最终指向的是人性的自由。
当然,“至上主义”与早期的社会主义一样的确存在过于理想化的一面,他对于“感觉”之绝对性的肯定,对普世与永恒的追求仍然带有浓烈的宗教色彩。但这种追求,毫无疑问,是一种积极的探索,将这种探索简单地理解为对现实的“逃避”和“拒绝”,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在2015年,白教堂美术馆的抽象艺术回顾展以“黑色方块”作为抽象主义终极理想的一个符号;黑色方块是这场百年历险的起点、贯穿始终的线索与精神内核。展览用四个章节讲述了一个创世的故事:从无一物的“乌托邦(Utopia)”理想开始;用“建筑术(Architectonics)”逐渐搭建出新世界的框架;通过“沟通(Communication)”将这场“革命”的星火燃遍世界,最后却在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新大陆受到欢迎,降临到“人间世(Everyday Life)”,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一百年里,在不同社会语境之下,经过诸多艺术家的反复引用和转译后,“黑色方块”(抽象艺术)的意义已经变得复杂而多样化。今天,抽象艺术的精神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忘却的记忆,我们已然进入了“后抽象时代”。在悲观者看来,“乌托邦”理想最终还是在物质文明的淫威之下沦陷,是一种最惨痛讽刺;但乐观者或许看到的是,不论是否已经实现,对“自由”的追求,不论在艺术还是在我们自身都已经成为了一种深刻的自觉——“黑色方块”的历险还没有结束。(编辑:九月)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