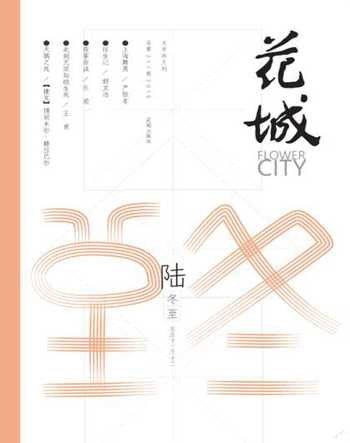更多的光线来自黄昏
2015-05-31鲍尔吉·原野
鲍尔吉·原野
蚯 蚓
蚯蚓多么温和,一生待在土里蠕动。它一辈子走过的路程也超不过100米,大地是蚯蚓的家。土,说起来是坚硬的东西,用铁锹挖一锹土,土上带着切痕。但蚯蚓能在土里行走,這又算一个柔软胜刚强的例子。有人说蚯蚓食土为生,如果这样就太好了,它永远不愁吃的东西。土虽多,蚯蚓却不见长胖,它懂得节制。或者,土吃起来很慢,蚯蚓沙沙地咀嚼,一天吃不了多少就饱了。
蚯蚓身体粉红,跟人的肉色接近。它的身体干净。这样的身体表明土地原本不脏,即使吃土也可以长出人肉的颜色。而人需要吃粮食和肉才长出人色。光吃菜,人脸偏绿,人身上的血红细胞减少,转为血绿细胞,接近于螳螂的气色。六十年代初,满街都是这种颜色的人,走路东倒西歪。
我见到蚯蚓先想到蛇。蚯蚓跟蛇有多少亲缘关系?它们相似但蚯蚓比蛇少一层皮。蛇皮,中药称蛇蜕。它是蛇的盔甲,而蚯蚓没有。上帝为什么不让蚯蚓长一层甲虫的甲呢?蚯蚓一定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帝。它藏在地里不出头也可能是怕被上帝发现。上帝惩罚谁,一般用两种方法,一是让它基因缺陷,二是让它干一些自不量力的事。然而基因有缺陷的生物大都本分,譬如羊不想吃狼肉并且远离狼。人的神经系统不敌毒品,这是基因缺陷,但有人尝试吸毒挡都挡不住。
蚯蚓没见过蛇,蛇只是一个传说。蚯蚓觉得下辈子变成蛇也不迟。这辈子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蚯蚓已经够好。它的天敌,比如鹰或鸡轻易吃不到蚯蚓。泥土的堡垒让蚯蚓十分安全,而蚯蚓也没想出去抓鸡或吃人。蚯蚓吃土的口感好像吃饼干,沙沙响。蚯蚓觅食无须像牛羊那样翻过一个又一个山坡,它抬头就有吃的,食品同时是被子、褥子,还是房子和床,总称土。蚯蚓喜欢土地的黑暗,静谧安详。土用臂膀护住蚯蚓,因为它没盔甲。蚯蚓偶尔也到地面上走一走,它觉得没什么意思,一来阳光晃眼,二来道路不平。蚯蚓在地面辗转不安,不如回到土里舒服。蚯蚓学不会蛇的灵巧。蛇哆嗦一下钻进草丛,再哆嗦一下钻进石缝。蚯蚓觉得蛇如果不吃药根本做不出这样的动作,这类似于麻痹震颤症。
有人听过蚯蚓的歌声,在雨后。说蚯蚓的歌声细弱如丝,像吹一片树叶子。蚯蚓唱歌做什么?雨浇湿了泥土,也浇湿了蚯蚓的身体。它听到沙沙的声响并非口腔咀嚼而来自雨,不禁惊呆,仿佛雨在吃土。每一片草叶都对雨滴做出回音,蚯蚓终于在沉默的大地听到了歌声,随之合唱。
不知道蚯蚓怎样在泥土里寻找自己的同伴。它生来孤独,如果有一天听到隔壁泥土松动,那一定是客人来访。两条蚯蚓缠到一起拥抱,有说不完的话,话题是土。蚯蚓想不出离开土还能说什么话。除了土,蚯蚓还谈到雨和庄稼的根须。蚯蚓在地下跟草和庄稼的根须握手,它们洁白的根须散发甜味。对蚯蚓来说,穿过这些根须相当于穿越森林。如果进入一片玉米地,蚯蚓毕其一生也走不出这片地下的森林。土里还有什么?蚯蚓见到最多的是蚂蚁。蚂蚁其实很凶恶,孤零零的爪子长在机器式的身躯上,头颅似乎没有一点理智。蚂蚁贪财,搬运一切东西。
蚯蚓走路离不开扭捏。其实它只会掘土,并没有学过走路。它不知学会走路有什么用处,蚯蚓哪儿也不想去。大地温暖安全,适合于一切爱睡眠的生物,其中有蚯蚓这样连皮都没有的,露出赤裸鲜肉的温和生物。
黑 蜜 蜂
黑蜜蜂无牵无挂,孤独地飞在山野的灌木上方。一只肚子细长的黑蜜蜂在岩石的壁画前飞旋,白音乌拉山上有许多壁画——古代人用手指头在石上画的图形符号。我觉得像是古埃及人来蒙古高原旅游画的。黑蜜蜂盯着壁画看,壁画上有一人牵着骆驼走的侧影,白颜料画在坚果色的黑石上。黑蜜蜂上下鉴赏,垂下肚子欲蜇白骆驼。古代骆驼你也蜇啊?我说它。黑蜜蜂抻直四片翅膀,像飞机那样飞走。
草原上有许多黑蜜蜂,长翅膀那种大黑蚂蚁不算在内。盛夏时节,草地散发呛人的香味,仿佛每一株草与野花都发情了。它们呼喊,气味是它们的双脚,跑遍天涯找对象。花开到泛滥时节,人在草原上行走没法下脚,都是花,踩到哪朵也不好。花开成堆,分不清花瓣生在那株花上。野蜂飞过来,如柯萨科夫——李姆斯基在乐曲里描写的——嗡,嗡,不是鸣叫,传来小风扇的旋转声。黑蜜蜂比黄蜜蜂手脚笨,在花朵上盘桓的时间长。我俯身看,把头低到花的高度朝远方看——花海有多么辽阔,简直望不到边啊,这就是蜜蜂的视域。蒙古人不吃蜜,像他们不吃鱼,不吃马肉狗肉,不吃植物的根一样。没有禁忌,他们只吃自己那一份,不泛吃。野蜜蜂的蜜够自己吃了,还可以给花吃一些。蜜蜂是花的使者,它们穿着大马裤的腿在花蕊里横蹚,像赤脚踩葡萄的波尔多酿酒工人。晚上睡觉,蜜蜂的六足很香,它闻来闻去,沉醉睡去。蜜蜂是用脚吃饭的人,跟田径运动员和拉黄包车的人一样。
草原的晨风让女人的头巾向后飘扬,像漂在流水里。轧过青草的勒勒车,木轮子变为绿色。勒勒车高高的轮子兜着窄小的车厢,赶车的人躺在里面睡觉,凭驾车的老牛随便走,随便拉屎撒尿。黑蜜蜂落在赶车人的衣服上,用爪子搓他的衣领,随勒勒车去远行夏营地。月亮照白了夏营地的大河,河水反射颤颤的白光。半夜解手,河水白得更加耀眼,月亮像洋铁皮一样焊在水面。那时候,分不清星星和萤火虫有什么区别,除非萤火虫扑到脸上。星星在远处,到了远处,它躲到更远处。虫鸣在后半夜止歇,大地传来一缕籁音,仿佛是什么声的回声,却无源头。这也许是星星和星星对话的余音,传到地面已是多少光年前的事啦,语言变化,根本听不懂。等咱们搞明白星星或外星人的话,他们传过来的声音又变了。
黑蜜蜂是昆虫界的高加索人,它们身手矫健,在山地谋生。高加索人的黑胡子、黑鬈发活脱是山鹰的变种,黑眼睛里藏着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他们剽悍地做一切事情,从擦皮靴到骑马,都像一只鹰。黑蜜蜂并非被人涂了墨汁,也不是蜜蜂界的非裔人,它们是黑蝴蝶的姻亲,蜜蜂里的山鹰。蜂子们,不必有黑黄相间的华丽肚子,不必以金色的绒毛装饰手足。孤单的黑蜜蜂不需要这些,它在山野里闲逛,酿的蜜是蜜里的黑钻石。
一位哈萨克阿肯唱道:
黑蜜蜂落在我的袖子上,袖子绣了一朵花。
黑蜜蜂落在我的领子上,领子绣了一朵花。
黑蜜蜂落在我的手指上,手指留下一滴蜜。
我吮吸这一滴黑蜜,娶来了白白的姑娘。
晨光在草原的石头缝里寻找黑蜜蜂,人们在它睡觉的地方往往能找到白玉或墨玉。黑蜜蜂站在矢车菊上与风对峙。它金属般的鸣声来自银子的翅膀。图瓦人说,黑蜜蜂的翅膀纹络里写着梵文诗篇,和《江格尔》里唱的一样。
黑夜如果延长,月亮会不会熄灭?
如果黑夜延长,月亮怎么办呢?会不会黯淡无光?夜只在夜里出现,就像葵花子在葵花的大脸盘子里出现,这个道理不言自明。如果夜延长了呢?小时候,我不止一次有过这个想法,但不敢跟别人说。它听上去比较反动,会给你戴上怀念旧社会的帽子,尽管我根本不了解旧社会。夜如能延长,不上学只是一个轻微的小好处,睡懒觉是另一个轻微的好处。我想到的大好事是抢小卖店。这个想法既诱人,又感到快被枪毙了,那时候,任何一处商店都归国家所有。任何“卖”的行为都由国家之手实施,个人卖东西即是违法。可是小卖店里的好东西太多,它就在我家的后面,与我家隔一个大坑。人说这个坑是杀人的法场,而我们这个家属院有一个清朝武备系统的名字,叫箭亭子。小卖店有十间平房,夜晚关门,闭合蓝漆的护板,好东西都被关在了里面,那里有——从进门右手算起——大木柜里的青盐粒,玻璃柜上放五个卧倒、口朝里的装糖块的玻璃罐。罐内的糖从右到左,越来越贵。第一罐是无糖纸的黑糖,第二罐是包蜡纸的黑糖,糖纸双色印刷。第三罐是包四色印刷蜡纸的黄糖。第四罐是包玻璃纸的水果糖。这三罐的糖纸两端拧成耳朵形,只有第五罐不一样,它达到糖块的巅峰,是糖纸叠成尖形的牛轧糖。我们都不认识这个“轧”字,但知道它就是牛奶糖。这里面,我吃过第一罐、第二罐和第三罐的糖,憧憬于第四罐、第五罐。家属院那些最幸运的兔崽子们也只吃过第一罐的黑糖,可能在过年时吃过一块,嘎巴一嚼,没了,根本记不住什么味道。他们其余时光都在偷大木柜里的青盐粒舔食。如果夜晚延长,我们可以从后院潜入小卖店,把打更的王撅腚绑上。我先抢第四罐和第五罐的糖,如果还有时间,再抢糕点——大片酥和四片酥,各一片。家属院的小孩有人说抢白糖,冲白糖水喝。有人说抢红糖,冲红糖水。烂眼的于四说他要抢一瓶西凤酒。因为他姥爷临终时喊了一声“西凤酒啊”命结。有人说抢铁盒的沙丁鱼罐头,我们没吃过,不抢。至于小卖店里的枕巾、被面、马蹄表、松紧带、脸盆、铁锹之类,我们根本没放在眼里,让抢也不抢。然而在我的童年,夜晚从来没有延长过。它总是在清晨草草收兵,小卖店一直平安在兹,我们每天都去巡礼,看糖。
月亮每夜带着固定的燃料,满月带的最多,渐次递减,残月最少,之后夜夜增多。如果夜延长了,月亮虽然不会掉下来,但会变灰,甚至变黑。黑月亮挂在空中,有很多危险,会被流星击中,也会被人类认为是月全食。它燃尽了燃料之后,像一个纸壳子在夜空里飘荡,等待天明,是不是有些不妥当呢?如果月亮不亮了,传说中的海洋也停止了潮汐这种早就该停止的活动,女人也有可能停止月经,使卖卫生巾的厂家全部倒闭。而海,不再动荡,不再像动物那样往岸上冲几步缩回,海会像湖一样平静。这也很好,虽然对卫生巾不算好。
人们在无限延长的夜里溜达,免费的路灯照在他们头顶。道路在路灯里延长,行人从一处路灯转向另一处路灯下。菜地里的白菜像一片土块,哗哗的渠水不知从何处流来又流到了何处。被墙扛在肩膀上的杏花只见隐约的白花却见不到花枝,如江户时代的浮士绘。路灯统治着这个城市,他把大量的黑暗留给恋爱的人。夜如果无限期延长,每只路灯下面都有学校的一个班级上课。下课后,赌博的人在这里赌博。多数商店倒闭了,路灯下是各式各样的摊床。人们在家里的灯光下玩,然后上路灯下玩。不玩干啥,谁都不知道夜到底什么时候变为白天。在夜里待久了,人便不适应白天,眼睛已经进化出猫头鹰的视力。他们可以在没路灯的地方奔跑,开运动会。他们开始亲近老鼠,蚊子取代狼成了人类的公敌。
如果亲爱的黑夜真的延长了,河流的速度会慢下来。河水莽撞地奔流容易冲破河堤。侧卧的山峰在夜里吉祥睡,在松树的枝叶里呼吸。星辰在此夜越聚越多,暴露了一个真相——每一夜的星辰与前一夜的星辰要换班,它们不是同样的星星。在星辰的边上,站着另一位星辰。猎户座、天狼星在天上都成双成对。连牛郎织女星也双双而立。夜空的大锅里挤满了炒白的豆子般的星星,银河延长了一倍。动物们大胆地从林中来到城市,它们去所有的地方看一看。比如超市和专卖店,它们坐在电影院的座椅上睡觉,猫在学校的走廊里飞跑,猴子爬上旗杆……
向日葵的影子
小时候,我家院子里种的向日葵夭折了七八棵,秋天只剩下一棵高大的老向日葵。它长到两米多高,好像一根绿色的电线杆子。为了帮助牧区的亲戚找到我家,我妈用蒙古文写信告诉他们“院子里长了一棵特别高的葵花”。
我常常趴在窗臺看这棵向日葵,它的躯干如同拧满了筋,筋外的绿皮生一层白绒毛。向日葵扁平的后脑勺也长满了筋包,原来像小舌头一样的黄花瓣枯干之后仍不凋落,萎在脸盘子的外圈。它的叶子如一片片手绢,仿佛想送人却没送出去,尴尬地举在手上。
向日葵的伴侣是它的影子。我家的小园子在秋天已一无所有。地上只剩下灰白色的泥土。土被连续的秋雨冲刷出一层起伏的花纹,似干涸的河床。立于院子中间的向日葵的影子如长长的黑色表针,从早晨开始缓缓地转动,仿佛探测园子里的土壤下面的秘密。我们这个家属院的地里有许多秘密。春天,各家种园子翻地翻出过日本刺刀,还有人的骨头。按说,翻地只翻一铁锹深,翻出来一些东西就不应再翻出来新东西了。但我们家属院年年春天翻出来新东西,这些东西仿佛年年往上长,最多的是人的肱骨和胫骨。有的人家把翻出的骨头捧子顺条堆在松木栅栏边上,仿佛炫耀他家的财富,那个时候的人真愚昧。我们跑到各家看这些骨头。有的小孩腰扎一根草绳子,把骨头别在腰上,到街里闲逛。这个小孩后来失踪了。
我总觉得向日葵的影子底下会有什么秘密。骨头不算秘密,虽然有人说骨头们每天会从地底上往上长一点,春天长到地面,它们要长出来。如果不翻动,骨头也许长出白枝白叶,也许红枝红叶,不一定。有人说这些骨头的宿主乃有冤魂,我沿着向日葵的影子往下挖一条细细的深沟,把土掏出来。这样,向日葵影子的细长身躯与大脸盘子就镶嵌在沟里。我见此很欣慰,如果蹲下看,地面已看不到向日葵的影子了。这是多好的事,我藏起了向日葵的影子。
万物和它们的影子应该是两回事吧,东西是东西,影子是影子。向日葵影子的生活是在模仿向日葵,为它剪裁一件透明的黑衣,追随它,须臾不得离开,直至黑夜来临。向日葵的影子没想到它竟掉进了沟里。我在向日葵的东面和西面挖了两条沟,都很细。西面的沟更长。太阳落山时,向日葵的影子掉进这条沟基本上爬不上来了。我一看到此景就想笑,这是它万万没想到的事情。黄昏的光线从辽河工程局家属院包括更西面的体育场和卫校方向的天空奔涌过来,几乎一点阻挡都没有。向日葵拖着一根影子的尾巴朝夕阳跑,过一会儿,慢慢的,影子中计了,它掉进了沟里,我在沟上面盖上早已准备好的草。看到没有,向日葵的影子消失了,它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影子的向日葵。虽然它老得豁掉了牙齿——它脸盘上的瓜子被喜鹊偷啄了很多,像豁牙子的老人。但它摆脱了影子该有多么轻松。房子和杨树都倚靠在自己沉重的影子里,房屋的影子由于沉重而倾斜。杨树的影子甚至在模仿杨树的断枝,像取笑它一样。
向日葵在自己的影子里站立,它在影子里站高、变矮、影子是它对往事的回忆。蚂蚁在向日葵的影子里爬,如同检查它的身体,或者说正把它的影子拆掉,搬到各个地方。每次我从窗台看到向日葵,它如同拄着拐杖的老将军,它离不开那根拐杖,拐杖就是它的影子。
向日葵的奇特在于把那么多种子结在自己脸上,它的大而圆的脸仿佛在笑,长时间凝视太阳却不会造成日盲症。然而它的脸上堆满了子女,多到数不过来。它看不到眼前的情景,它的子女在它脸上铺设了一座团体操的广场。蜜蜂般的花蕊脱落,向日葵的脸上布满黑色带白纹的瓜子。它们被称为瓜子,然而跟瓜没关系。瓜子们等待阅兵的口令。它们的横列已经齐得不能再齐,纵列更整齐,每一个肩膀都靠在一起。“正步走”的口令在哪里?瓜子们等待大喇叭传出这个口令。但没有,然后向日葵的头颅就低了下来,像所有罪人。那时候,盟公署家属院有一半的人是罪人,他们白天去单位低头请罪,回家的路上也不敢抬头。向日葵的头颅越来越低,它终于看到了地上的影子。影子里面有什么?为什么会有一个影子,向日葵仔细查看,脸盘子越来越低。
更多的光线来自黄昏
黄昏在不知不觉中降落,像有人为你披上一件衣服。光线柔和地罩在人脸上,他们在散步中举止肃穆。人们的眼窝和鼻梁抹上了金色,目光显得有思想,虽然散步不需要思想。我想起两句诗:“万物在黄昏的毯子里窜动,大地发出鼾声。”这是谁的诗?博尔赫斯?茨维塔耶娃?这不算回忆,我没那么好的记性,只是乱猜。谁在窜动?谁出鼾声?这是谁写的诗呢?黄昏继续往广场上的人的脸上涂金,鼻愈直而眼愈深。乌鸦在澄明的天空上回旋。对!我想起来,这是乌鸦的诗!去年冬季在阿德莱德,我们在百瑟宁山上走。桉树如同裸身的流浪汉,树皮自动脱落,褛褴地堆在地上。袋鼠在远处半蹲着看我们。一块褐色的石上用白漆写着英文:“The World Wanders around in the blanket of dusk,the earth is snoring.”鲍尔金娜把它翻译成两句汉文——“万物在黄昏的毯子里窜动,大地发出鼾声。”我问这是谁的诗?白帝江说这是乌鸦写的诗。我说乌鸦至少不会使用白油漆。他说,啊,乌鸦用折好的树棍把诗摆在一块平坦的石头上。我问是用英文?白帝江说:对,它们摆不了汉字,汉字太复杂。有人用油漆把诗抄在了这里。
我想说不信,但我已放弃了信与不信的判断。越不信的可能越真实。深信的事情也许正在诳你。乌鸦们在天空排队,它们落地依次放下一段树棍。我问白帝江,摆诗的应该只有一只乌鸦,它才是诗人。白帝江笑了,说有可能。这只神奇的大脚乌鸦把树棍摆成“The World Woande……”乌鸦摆的S像反写的Z。为什么要这样呢?是因为黄昏吗?
我在广场顺时针方向疾走。太阳落山,天色反而亮了,与破晓的亮度仿佛。天空变薄,好像天空许多层被子褥子被抽走去铺盖另一个天空。薄了之后,空气透明。乌鸦以剪影的姿态飘飞,它们没想也从来不想排成人字向南方飞去。乌鸦在操场那么大一块天空横竖飞行,似乎想扯一块单子把大地盖住。我才知道,天黑需要乌鸦帮忙。它们用嘴叼起这块单子叫夜色,也可以叫夜幕,把它拽平。我头顶有七八只乌鸦,其它的天空另有七八只乌鸦做同样的事。乌鸦叫着,模仿单田芳的语气,呱——呱,反复折腾夜色的单子。如果单子不结实,早被烏鸦踢腾碎了,夜因此黑不了,如阿拉斯加的白夜一样痴呆地发亮,人体的生物钟全体停摆。
人说乌鸦聪明,比海豚还聪明。可是海豚是怎样聪明的,我们并不知道。就像说两个不认识的人——张三比李四还聪明。我们便对这两人一并敬佩。乌鸦确实不同于寻常鸟类,黄昏里,夜盲的鸟儿归巢了,乌鸦还在抖夜空的单子。像黄昏里飘拂的树叶。路灯晶莹。微风里,旗在旗杆上甩水袖。
在黄昏暗下来的光线里,楼房高大,黑黝黝的树木顶端尖耸。这时候每棵树都露出尖顶,如合拢的伞,白天却看不分明。尖和伞这两个汉字造得意味充足,比大部分汉字都象形。树如一把一把的伞插在地里,雨夜也不打开。在树伞的尖顶包拢天空的深蓝。天空比宋瓷更像天青色,那么亮而清明,上面闪耀更亮的星星。星星白天已站在哪里,等待乌鸦把夜色铺好。夜色进入深蓝之前是瓷器的淡青,渐次蓝。夜把淡青一遍一遍涂抹过去,涂到第十遍,天已深蓝。涂到二十遍及至百遍,天变黑。然而天之穹顶依然亮着,只是我们头顶被涂黑,这乌鸦干的,所以叫乌鸦,而不叫蓝鸦。我觉得乌鸦的每一遍呱呱都让天黑了几分,路灯亮了一些。更多的乌鸦彼此呼应,天黑的速度加快。乌鸦跟夜有什么关系?乌鸦一定有夜的后台。
看天空,浓重的蓝色让人感到自己沉落海底。海里仰面,正是此景。所谓山,不过是小小的岛屿,飞鸟如同天空的游鱼。我想我正生活在海底,感到十分宁静。虽然马路上仍有汽车亮灯乱跑,但可不去看它。小时候读完《海底两万里》后,我把人生理想定位到去海底生活,后来疲于各种奔命把这事忘了。今夜到海底了,好好观赏吧——乌鸦是飞鱼,礁石上点亮了航标灯,远方的山峦被墨色的海水一点点吞没。数不清的黑羊往山上爬,直至山头消失。头顶的深蓝证明海水深达万尺。我一时觉得树木是海底飘动的水草,它们蓬勃,在水里屈下身段,如游往另外的地方,比如加勒比海。我想着,不禁挥臂划动,没水,才想到这是地球之红山区政府小广场,身旁有老太太随着《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音乐跳舞。
其实红山区政府的地界,远古也是海底。鱼儿曾在这里张望上空,后来海水退了,发生了许多事,唐宋元明清各朝都有事,再后来变成办公和跳舞的地方。黄昏的暮色列于天际,迟迟不退,迟迟不黑,像有话要说。子曰“天何言哉!天何言哉!”谓天没说过话,天若有话其实要在黄昏时分说出。
黄昏的光线多么温柔。天把夜的盖子盖上之前,留下一隙西天的风景。金与红堆积成的帷幕上,青蓝凝注其间。橙与蓝之间虽无过渡却十分和谐。镶上金边云彩从远处飞过来跳进夕阳的熔炉,朵朵涅槃。黄昏时,天的心情十分好,把它收藏的坛坛罐罐摆在西山,透明的坛罐里装满颜料。黄昏的天边有过绿色,似乌龙茶那种金绿。有桃花的粉色。然而这都是一瞬!看不清这些色彩如何登场又如何隐退,未留痕迹。金红退去,淡青退去,深蓝退去之后,黄昏让位于夜,风于暗处吹来,人这时才觉出自己多么孤单。黑塞说:“没有永恒这个词,一切都是风景。”
责任编辑 申霞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