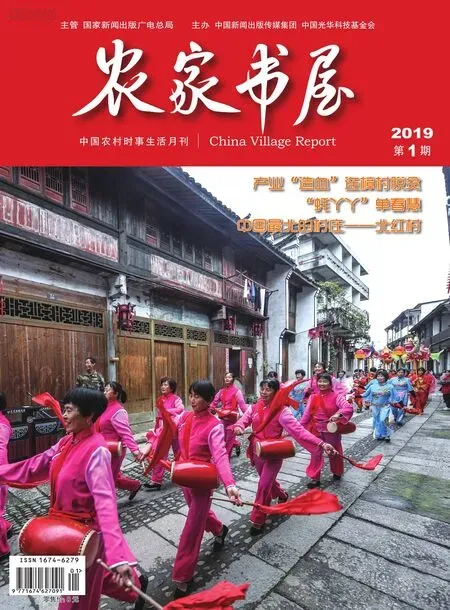《老农民》致敬农民
2015-05-30谢彦
谢彦
5年磨一剑的《老农民》于2014年12月22日登陆北京、山东、河南、黑龙江四大卫视。谈起《老农民》的创作过程,从《闯关东》《钢铁年代》《温州一家人》一路走来的金牌编剧高满堂用“行万里路”来形容。“这5年我不是行走在繁华的大街上、不是坐在咖啡桌旁、不是吹着空调、不是道听途说,是我用自己的双脚走路,用自己的肩膀担当,用自己的心和农民进行了一次对话。”
“工农商”三部曲
高满堂创作的《闯关东》,堪为中国电视剧的顶峰之作。而由高满堂编剧的“工农商”三部曲,用三段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故事来构筑60多年来的生活图景:穿越了共和国最初记忆的鞍钢工人,带我们走进那个如火如荼的《钢铁年代》;一个从山村走出来的家庭讲述着《中国故事》,成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情系黑土地的《老农民》,在那片沃土上演绎着生命和爱情、天地和感动……
《钢铁年代》堪称一部“工人礼赞”,由陈宝国、冯远征领衔主演的这部大剧,讲述了1948年到1964年间,从部队和全国各地前去辽宁鞍钢恢复建设的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的生活和情感。在这样风云变幻的宏大叙事里,幸福大院的几段家长里短散发出永恒不灭的人性温情。陈宝国饰演的尚铁龙和冯远征饰演的杨寿山,在情感、家庭、炼钢事业以及钢厂建设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二人一起经历光荣和耻辱、得到和失去,相互衬托又相互辉映,白头时才发现彼此早已是刎颈之交。
李立群主演的《中国故事》,实际是一部“温商传奇”,用一家人的命运串起了中国改革开放前10年的进程。《中国故事》展现的就是温州人在改革开放洪流中搏击的故事,用一家人的命运串起了中国改革开放前10年的进程。从山村走出来的周老顺一家立志要闯出一片天地,为此分隔天涯,踏上了不同的道路。女儿阿雨远赴他乡,孤身在异国打拼,历尽商海沉浮,尝尽人间冷暖,终于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周老顺一家所经历的起伏、波折、艰辛、成功,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
《老农民》则是一部“农民史诗”,这也是高满堂第一次触及农村题材。《老农民》从1948年写起,讲述了由北方农村的一场土地改革所引发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故事。全剧通过对以麦香村为代表的北方农村的全景式描摹和主人公牛大胆、马仁礼、灯儿等小人物的故事来构筑大时代的生活图景。剧中两位主人公牛大胆(陈宝国饰)和马仁礼(冯远征饰)一个是长工的儿子、一个是地主的儿子,你来我往互不低头,经历了互助组、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一直到2008年农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关注中国当代农村现实生活和农民精神世界。对于首次触及农村题材,高满堂说:“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大都是轻喜剧,讲述一个个时代的片段,缺少一部史诗性作品。中国有八九亿农民,为什么不用史诗性的东西去礼赞他们?”
作为“工农商”三部曲的收官之作,高满堂对《老农民》寄予厚望,“希望它能超越《闯关东》,成为我最好的作品。”谈到这部剧的创作初衷,高满堂说:“我们的8亿农民用了60年时间,完成了土地改革到土地使用权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想应该记录下来,把这段生活传承下去,给我们的子孙。大家知道我从来没写过农民,我写的都是年代剧。之所以把它放在最后,是我特别敬畏农民。但是我想老放着也不是一个事,于是用了5年的时间走了5个省采访了200多人,这给了我底气。”
以农谢幕
2014年4月24日,山东章丘朱家裕温度已很高,有了夏天的气息。但走进电视剧《老农民》的摄影棚,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时空,外面的阳光、蓝天和田野顿时远了。棚里搭出了一个古朴的中国农村,在戏里叫麦香村。窗子上写着“糖果”“罐头”“茶”的小卖部,写着“尊老爱幼,先下后上”的站台,邮局门上“人民邮电”几个大字是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有探班的媒体记者敲了敲一栋房子的墙壁,听了听声音,十分肯定地说 :“这砖头是假的。”
当时,逢上一场陈宝国和冯远征的对手戏。陈饰演的长工的儿子牛大胆,冯饰演的地主的儿子马仁礼,是本剧的两个主角,既是冤家,也是伙伴,上演了60年的恩怨纠葛。这场戏发生在1951年的马家大院,牛大胆住着马仁礼曾经的院落,一个完整的接地气的院子:堂屋、厨房,牛棚、鸡窝,门前两个大酱坛子,房前一棵刚抽出绿芽的树昭示着这是初春,树枝上挂着镰刀和篮子,旁边晒着一筐地瓜干儿。
在通告表上,这场戏被标注为“掸晾被子”,整场戏加起来可能不到3分钟,牛大胆推门出来,在门前绳子上摊开被子和褥子,马仁礼满脸堆笑拿着一瓶酒跑进来,牛大胆冷脸质问他:“你这是想拉拢贫下中农吗?”从做准备到拍摄,却用了将近一个小时。工作人员往地上喷水,把本就破旧的被子和褥子撕开点,露出里面的棉花,陈宝国和冯远征拿着剧本对词,商量怎么走位,试了几次后再试拍,最后才是正式拍。导演声音洪亮,在人数众多的片场更显得有穿透力,不时提醒工作人员:“别穿帮!别穿帮!”
深色褂子、大裆裤,涂黑的肌肤,陈宝国和冯远征是典型的上世纪50年代的农民造型,冯远征甚至还头戴一顶黑色帽子。这样的造型和化妆,每次需要50分钟到3个小时不等。陈宝国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演工农兵,而且一定要在最黄金的表演时期演。年轻时,他不太清楚原因,现在他明白了:“其实是想向我们的父辈致敬,回顾他们的生命历程。”这次接演了《老农民》后,他的梦想就圆满了。在他看来,牛大胆这个人物形象,是他饰演的人物画廊里一直缺少的人物,“我想把最好的表演状态留在这个戏里,才对得起8亿农民和十几亿观众”。在电影《1942》里,冯远征演一位农民,演完之后他下决心再不演农民了,“太苦了”。但看完《老农民》的剧本后,他不仅接演了,而且开始期待这部戏,“开机之后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因为这是个难得的好剧本”。
向农民鞠躬
一部《老农民》不仅来自于高满堂多年的生活经验,更来自于他在田间地头采访的亲身经历。
尽管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但在近期的影视作品中,以中国农民为主角的好作品数量甚少,此前赵本山打造的农村戏“乡村爱情”系列尽管收视颇高,但仍被不少剧评人认为没有切入到农民生活的原生态。而身为编剧协会会长的高满堂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不讳言农村戏创作之艰难:“‘农是最难写的,因为这么多年,农民所承载的负担太重,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应该为他们树碑立传,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忘记老祖宗。”而对于《老农民》这部戏,高满堂也曾立誓,如果写不好就退出影视圈。
“以小人物折射大时代”向来是高满堂作品的鲜明标签。谈及该剧的创作初衷,高满堂满怀深情:“中国有8亿农民,他们承受的东西、受的苦难太多,希望也很多,但专门为他们创作的电视剧却很少,应该有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献给他们。”为创作《老农民》,高满堂深入农村,走访了辽宁、河南、山东等地,采访了数百位农民。“写《老农民》是为了寻找一个民族已经丢失了的记忆。”他说,“在这个时代,有必要回过头去看一下过去的生活,看看农民是如何走过这60年的。”他称这部剧是一首抒情长诗,“写它的痛苦在于我们回忆了这段难忘的历史,但也欣喜它把历史和今天有力地焊接在一起。”
在高满堂看来,现在反映农民生活的影视作品,多是截取某年某月某时,反映的是一个片断。所以写这样一部横跨60年的史诗性作品,他觉得需要勇气,“面对真实的勇气,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编造历史。”他用的手法依然是由小人物折射大历史,对此他是自信的 :“这个创作方法不是新的,但如何用好它需要本事,我有这个本事。”
高满堂告诉记者,面对共和国65年历史,农民的人生负担太重太重,我们有理由为他们树碑立传,告慰我们的祖先。而60多年的跨度以及大体量的创作给高满堂最大的感触是:“我想一个民族的气质应该有它的深刻性。当我们再过十年二十年的时候,如果我们再不抢救60年的历史,恐怕这个历史就会消失。应该说共和国这65年里,5部农民电影,当我们期望着的时候,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该尊敬地向农民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