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书法
2015-05-30唐吟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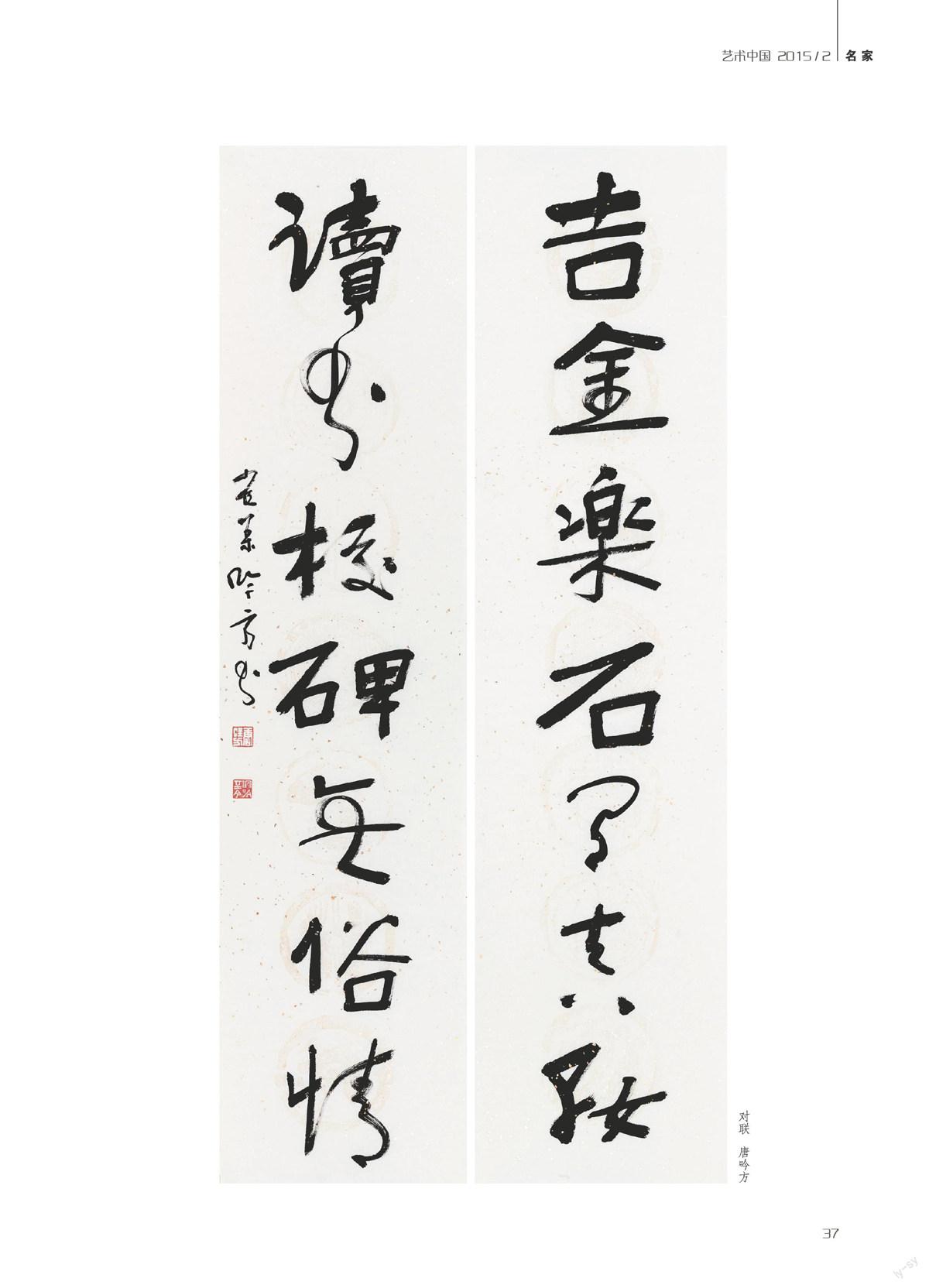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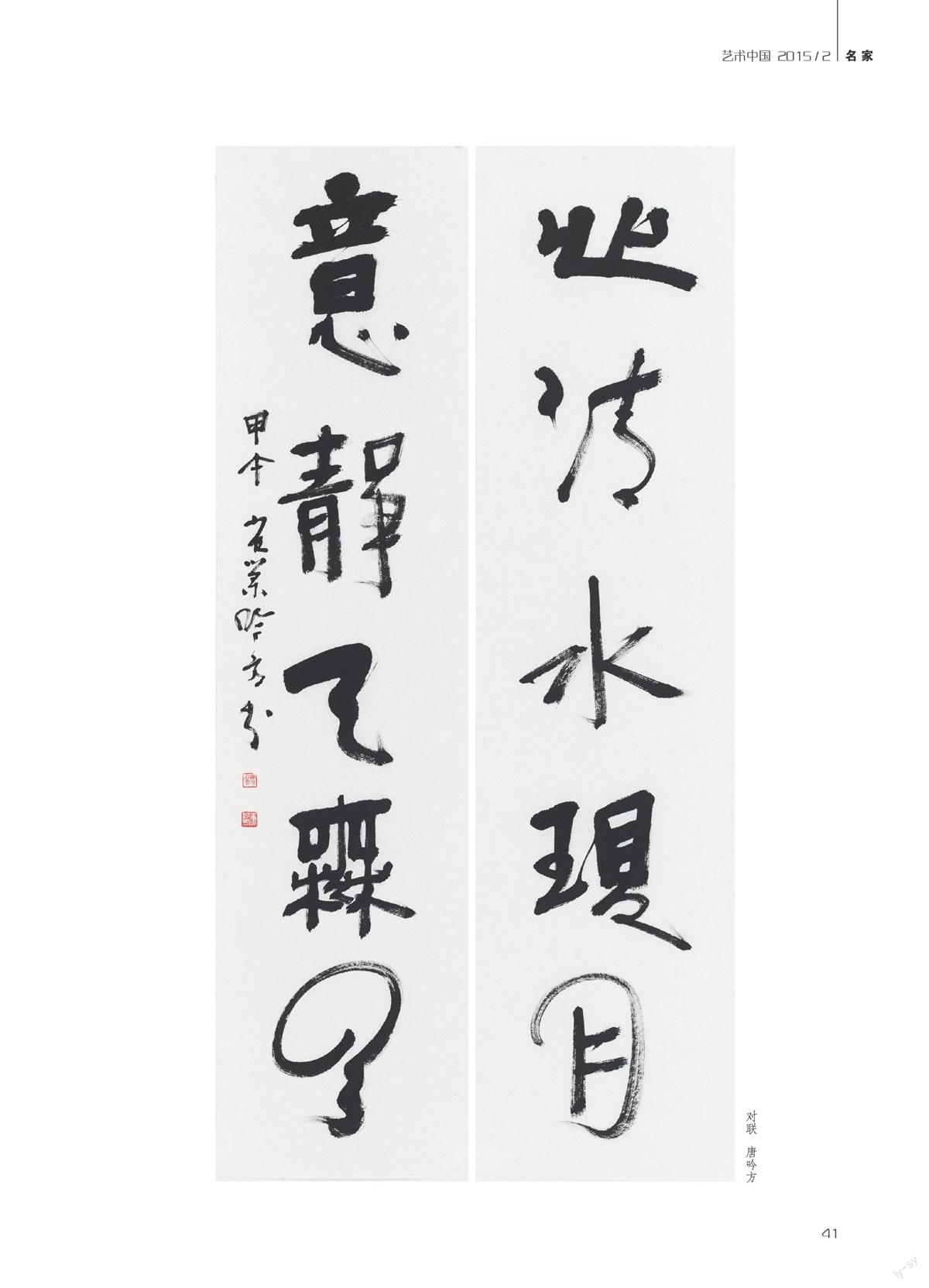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的中学美术老师带我到国画家沈红茶先生(1902--1985)家,从此就从师沈先生学画。建国前沈红茶先生和陈之佛、丰子恺,陆维钊、诸乐三、徐生翁都是画友,抗战前曾担任过杭州第三民众艺术馆馆长,抗战期间和学者、文字学家张天方一起流落到天目山,共创古文字画,兼任浙江省通志馆编辑,建国后一度在中学担任教师,50年代由于历史问题淡出画坛,文革结束后,恢复自由身,年近80,是浙北有名的老画家。沈先生知道我喜欢绘画,问我真想学好画吗。我回答想。他说“那你先把字写好,书法是画的基础。”我当时并不知道书法与绘画的关系,只因为沈先生德高望重,也就半懂不懂去做了,但对怎样写字,通过什么途经才能把字写好一无所知。所谓的练字,徒具形式,没有具体的指标。1984年我转师西泠印社的余正老师。余老师是篆刻家,要求我从篆书开始,推荐我选择王福庵书的《说文部首》为范本,练字的同时识篆书,临写时要悬腕。篆书在写法上相对简单,只用一种笔法,对臂力和笔力的增强有益,也在无意中暗合沈先生主张的绘画之道。篆书练习时续多年,我对规整一路篆书缺乏兴趣,但确实因此得到了锻炼,我的臂力大大增强。余老师自己的印风书风极严谨,对学生的兴趣爱好并不刻意规范,我喜欢汉简书法,他不反对,反而鼓励我尝试,只是时常提醒我要走得稳些稳些。在他看来,所谓的艺术,应该顺乎天性的发展,还强调艺术兴趣的重要性。因为有兴趣,自己会寻找途径进入。这样的施教方法,也就是因人而定。余老师对我的指点可以说是具体而微,在学书的最初阶段,由于余老师的引领,我对书法一直保持着高昂的兴趣,我喜欢汉简书法并投入一些精力,没有多久即有小成。1985、1986年之际,已有一些书法作品在浙江省内或全国竞赛中获奖,因而更加激发我的学书兴趣。
80年代中期正是中国书法趋向于“热”的一个特殊时期,书法赛事多,书法活动多,出版物多,投入的书法人口多。当时人们还没有90年代后对艺术的功利心,书法释放了被压抑得过久的对传统艺术的企慕之情,在我则混杂着青春期生命感的张扬。我大约每月到杭州去接受余老师的面教,大部分时间则是借助函授。余正老师那时正值中年,身处浙省艺术中枢,立足点和对艺术问题的看法敏锐而有前瞻性。他跟我见面时,经常出其不意提一些超出我思维的问题,我多半答不上来,为了应对老师的提问,逼自己不断想问题,后来意识到余老师用一种特殊方式培养我的思考能力。我一直觉得余老师的教授方式过于宽松,直到有一次余老师把邻县一位同学的作业误以为我的作业,写信严厉地批评我,才明白余老师对我的呵护。
我跟随余老师的同时,还向蒋孝游、江蔚云、张振维、孙正和等先生请教。蒋先生是从上海去安徽的画家,本是画家,却主持过中国第一部《美术年鉴》编纂工作,晚年从合肥回海宁后,创作之暇,仍不忘美术史志的撰述。我常去拜访他家,在艺术认识上得到他很多教诲,如果我日后对创作和艺术史同样有兴趣,应该追溯到蒋先生,是他给了我最初的影响。江蔚云先生是另一种风格,出身富家,酷爱艺术与收藏,善长古体诗词。他以章草盛名,在家做功课做得最勤的是篆书,许多人都说江先生草书成就最高,以我的看法,他的篆书水平绝不在草书之下。江先生的草书成就得力于他的篆书功底,故能静穆与古意兼而有之。浙东子才孙正和先生极其自负,但他服膺江先生的草书,把江先生和王遽常先生相提并论,称“江王”为江南二大章草大家。江先生住在嘉善,我每隔一段时间坐车船去看他。他老人家常常翻出自己的收藏给我欣赏,我的艺术品鉴能力半多得自江先生的熏陶,而我在江先生身上更多地感受是其为人为艺的古风。张振维先生是缶翁同乡、黄宾虹的学生,长期担任嘉兴图书馆馆长,学问好,被人称为“现代儒生”。我和张先生接触不多,作为前辈,他从来没有架子,他用鸡毫写字,书法似稚似拙,细观则老辣遒健,不言个性而个性自在其中。我当时好写竹简体行书,张先生没有因为我年轻而轻看我,反把我引为同调,还是我加入浙江省书协的推荐人。孙正和先生是新昌中学的老师,毕业于复旦生物系,又在北京大学读过研究生,年辈略低,从师者都是当代第一流名师,如张宗祥、王遽常、白蕉、邓散木、沙孟海、陆维钊、韩登安、钱君匋等等,接触名师太多,眼界极高,为人孤傲,以治楷书印闻名。我曾写信向他请教楷书印,他以为我要拜师,当即复信同意,我因为已拜余老师为师,不拟重师,去信说明原委,孙先生居然收回成命,仍旧给予热心指点,这大约是我学书途中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在信中常月旦当代成名人物,我从孙先生那里得到的教益是:不要迷信名家,艺术上要有自己的主见。
1988年由于王镛老师的提携,我进入中央美院国画系学习,专业是书法。这四年确立了书法的新坐标,大致是:怎样从造型艺术的角度考虑书法,怎样确立书法创作与当代的关联,书法的当代性通过怎样的途径得以实现,等等。在美术学院这样重造型重个体表达的环境里,类似的问题是我这样迷恋思考的年轻人无法摆脱的一种情节,但要实现却没有现成的样板可以参照。一些务实而动手能力强的同学已经明白这类关乎学理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拿出作品是最重要的。大学四年里我一直被这样一些问题困扰着,不像其他同学那样经过美院的学习创作上已经很丰满了。感谢老师们的宽容,这四年对我的影响至深,我立志要做一个有现代感的书家,而不是现代风向的追随者。但如何走,仍然迷茫。
在美院学习期间,已注意到工具材料和书法的关系。比如毛笔的选用直接关系到书写的效果,尤其是帖派一类书风。记得南京的孙晓云女士曾应邀来京为我们讲课,上课前,她特意跑到琉璃厂荣宝斋选购了一些狼毫笔分发给我们,她希望我们试试用狼毫临帖或写字的效果。孙女士的课是讲演性质的,但她给我们的“换笔”的确提示了工具是值得重视的要素,工具和书写最终获得的效果关系密不可分。也就是这一次,看她示范写字,她用自己从南京带过来的宣纸。这种宣纸推测经过裱装师涮过一遍豆浆或喷过过一次水,纸性已脱离生宣的性状,有点熟纸的味道,用狼毫来写字,更能衬托出笔致的弹性和质感。孙女士的这次演示,给我启示:在完整的书法概念里,工具的作用与字形结构、笔法、章法、墨法等要素一样不能忽视。
求学期间另一个收获是对“现代书法”的认识。从我对当代有限的创作样本作观察,发现在中国书坛,几乎所有致力于书法现代化创作的艺术家,他们最终无法突破自己的思维局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书法家。我曾仔细研读过“现代书法家”的文字表达,在有限的文字里不是语言晦涩难解,便有游离书法或蹈袭当代美术之嫌,不然就是逻辑意义上的陈述,无法贴合“现代书法”的义理。事实上,创作这种操作性极强的事受到的制约太多,而“现代书法”的原创性对所有书法家来说要求都很高,断非我们想像的那么青春热血。如果承认有“现代书法”一说,对每个创作个体而言,大概只有“现代书法”阶段。这个观察结果,包括和不少从事书法现代化创作的艺术家交谈,令我重新审视传统书法的价值。我的跟踪观察所获还包括: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里,创作个体的认知会有偏差,可能会较多地接受所处环境给予他的影响。另外,在今天,我们经常谈到的是技艺层面的问题,其实以我的观察阅读感受:在技术、艺术本质的认知追求外,艺术家的心理成长和看不见的思想部分容量的扩大才是最根本,发展到后来,后者对一个艺术家的成就影响更大。
1992年我进入《文物》杂志社做编辑,书法转为业余活动。活动空间由美术学院转向文博界。我的生活环境从美院走入一个更开阔时空,创作置于更加多元的评价体系中,接触不同文化背景人士的挑剔,这个过程是可能一个裂变的过程,可能是一个修正的过程,还有可能是退步的过程。以美院和文博界而言,这是二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艺术创作凭感觉,凭激情,凭想象力,几乎无成法可依;文博界讲究传统,讲究文脉,讲究历史的连续性,凭证据说话,路数完全不一样。我的工作有机会接触到文博界的一些前辈,和他们有些过从交往。最先接触的是故宫朱家溍先生。有次去他办公室,他听人说我是美院书法专业毕业生,非常纳闷,学书法还要上大学。见到我就问美院还有书法专业,我回说有的,是新开设的专业。朱先生又问学什么。我如实相告。一来一去的问答交谈当然说明不了问题,朱先生要我下次来带一张字让他看。后来我带字去面见朱先生,结果非常意外,他当着我面说“字写得可不好”,甚至说我的字有“乱世之相”。朱先生对书法创新深恶痛绝。他办公室的门上就贴着华君武的漫画《书圣病了》,画书圣王羲之捂着眼睛痛苦不已,画的大意是书圣阅丑书太多眼睛受不了,病了。这件漫画作品颇能说明老一辈对书法的态度:照古人写就是了,创什么新!而书坛的创新派书家则立志要扩大已有的书法图版,不图新何以存我。取向想法不同,追求也不一样,于是也有了分歧。朱家溍先生的批评,对我的触动很大,除了彼此之间执行的评价标准不同外,当然还涉及到诸如对传统书法的认识、笔墨功力、字外功等等问题。
许多年过去,我对朱家溍先生批评一事一直不能去怀。1992年后我重新转向对传统的学习多少与朱先生有关,他的批评让我重新审视书法家个人创作与书法史之间关系。此时少数有觉悟的师友已经开始践行,怎样在当下的语境里寻找返回古人自然状态下书写的途径。着落点其实已经发生变化,从“艺”重新返回到“人”,自然,“人”的修炼成为书法活动中的首务。这再一次印证了古人所说的“书如其人”重要性。
刘涛老师是我大学里的老师。学历史专业出身的他,身在美院,却是精英艺术的赞同者。每次我们见面,总劝我多临帖。刘涛老师近十多年来的书法活动大致围绕“临摹古帖”展开,他的做法是尽最大的可能接近书法史上的那些经典之作。他是艺术史学者,著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书法谈丛》等,以他的史观史识,以他对古代书法生态、书家的理解程度,在许多方面有先决条件接近理解经典。这些年来刘老师对于经典的传习,结果是他的书风远离时人,建立在共性的基础上的个性表达,符合传统审美观念,中和饱满,法韵兼备,文人气十足,意韵悠长。他的实践也对书法学习中的“入古”作出了新的诠释,证明“入古”与个性表达并不冲突,“入古”的过程反而有利于个性表达的完善。刘老师对于经典书法的致力,于是就有了新的意义。他是当代学林中少数有独立见解又得古法书韵的善书者之一。1992年后刘老师的书法立场对我的书法践行影响最大。
友人陈新亚提出的“书法的生活化”也是有体认有想法的追求。把书写引入日常生活,通过日常书写复原古人的书写状态,其本质是把有意识的书写转化为本能书写。我以为在当今实用书写与艺术书写分离的环境里,新亚的主张化解了创作与非创作的矛盾,是实现书写自由状态的有效途径。新亚自己踏实践行,其稿书绝佳,风度状态在当今书坛均属第一流。新亚屡屡劝我“书法的生活化”用毛笔写信记日记。
南京的老诗人忆明珠先生没有宣言,但他的书写实践早就是“书法的生活化”的现实版。忆先生从65岁后弃硬笔就毛笔,凡与书写有关的工作均由毛笔承担。他的手写体极其流畅随意有风韵,即使在85岁以后,走路已经不太灵便的情况下,拿起笔写蝇头小字,依然爽俊有神,与我向往的理想状态下的书写不谋而合。我与忆先生保持了20多年的书信交往,我建立在手写体上的书法创作常从忆老给我的书信中获得灵感。友人羊晓君则提醒我注意手写体大小字的一致性。如果说1992年后我的书法观念有一个转变,与我身处工作环境固然有关,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众多师友的督勉批评或或明或暗的指引与慧示。
最近友人朱京生给了我一份材料,是王伯敏先生写的黄宾虹先生去世前和他的谈话录,其中有些内容谈到书画家的生存状态和创作状态,说到底艺术问题最终归结为“人”的问题。黄宾虹先生没有引征据典,却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石涛吃四方饭,到处云游,头顶青天,脚踏白云,手中一管笔。到了晚年,无牵无挂。董其昌田地多,官做得大,牵挂也比别人多。”时代变了,书画家面对的艺术核心问题其实不曾变化。这一点我们和古人一样,是平等的。
30年前沈红茶先生给我讲的一句话“书法很重要,不打好书法基础,难言绘事。”我差不多花20多年的功夫才真正体验到这句话的含意。不过大道多歧路,书法才入门,绘画则万重山隔,真不知道几时才能像沈先生说的那样,有了一些书法基础,重续我的绘画前缘。
2012/5/25于北京仰山桥畔
2014/12/16增补于北京蓝旗营小区十号楼
唐吟方简历
唐吟方,初名吟舫。1963年出生,浙江海宁人。目前主要从事近现代艺术史、收藏鉴定研究及随笔写作,兼及书画印创作实践。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先后在东京、香港、上海、北京、苏州、秦皇岛、福州、海宁、宁波、南通、绍兴等地举办联展或个展。著有《汉字的艺术》(与刘涛先生合著)、《雀巢语屑》《浙派经典印作技法解析》《近现代名人尺牍》《尺素趣》等。
曾担任《文物》杂志文字编辑,现供职于北京《收藏家》杂志。曾出任过1998年度、2004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群星奖”的评审委员。文化部青联美术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书画院艺委会委员、西泠印社社员、黄宾虹研究会会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