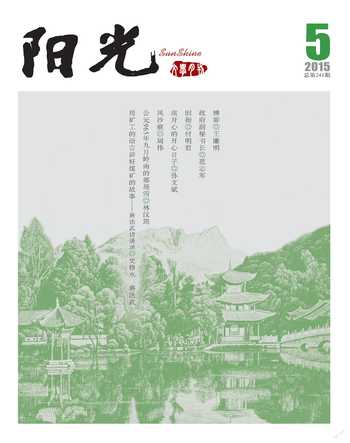旧街
2015-05-30付明君
付明君
一
旧街是矿区人口最密集的一个街道,在矿区的中心。
旧街这地方,低矮的平房一排挨着一趟,因为是在山坡上,故一排房比一趟排房高。远远望去,像坑木场的木头密集地有秩序地排列着,错落有致。每趟房有六户人家,一户挨一户,而每户都不到二十平米的卧室,外加一间仅六平米的两家共用的厨房。除去两家水缸和炉台,还有锅碗瓢盆占用的地方,几乎没有多大活动的空间了。用父亲母亲的话讲,到了做饭的时候,两家一起围着厨房转,都撞屁股。这就是矿工的家属房,这房子是公家的,允许居住,不允许买卖。我们这些矿工家属的孩子们,则在这样的大杂院里东家出、西家进,追闹着,锐叫着,不怨不怒。那时,即使各家的大人们出去做工了,房门都是敞开的。毫无戒备。用父亲的话说,“家家都穷的一样,也没什么可偷的。”
父亲是个美男子,剑眉朗目,端方而周正。但是父亲却有着鲜为人知的过去,据说父亲的第一任老婆是死在父亲的蹂躏下,至于怎样的蹂躏,我也不知,只听大人们有时暗暗怯怯地说,父亲的老婆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当时他的老婆哭喊着,父亲不让喊叫,说这样可以积攒气力,于是用毛巾堵住老婆的嘴,并用手挤压她的肚子,而且还让黄家街的黄婆娘死拉硬拽,硬把儿子拽了出来。可是父亲的前妻却因为大出血而死了。生下来就没娘的儿子,惹得父亲常常叹息,这小子,命像石头似的,太硬!于是“石头”便成了他的乳名。他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母亲先后生养了一双儿女。
说起来,母亲家在城里,也算是大户人家。她家的成分是富农,我的母亲,在姥姥的描述里,为人正直善良,当时是听媒人介绍说父亲是吃公粮的公职人员,且是八级木工。母亲不知道八级木工是什么概念,只感觉那是一个了不起的职称,嫁给父亲以后才知道所谓的八级木工其实就是一个木匠,而且是矿井里的搭棚支顶的木匠,为此母亲常常嗔怪媒人说,是他把自己骗给了父亲。母亲的媒妁之言的婚姻,并不幸福,经常遭到父亲的责怨、谩骂,甚至殴打。导致他们用恶毒的方式攻击对方的原因,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细节,而事后他们还能虚情假意地过日子。母亲原以为,找个丈夫顶门立户,遮风避雨,谁想到,竟是这样。世事难料啊。
在父亲身上,有一种典型的气质。闲散落拓,却也强势。在我们面前,尽显威严。父亲每顿饭都离不开酒,而且有酒必有下酒菜,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得有小灶,可是当时的家境是粗粮淡饭吃着都难,小灶更是难。母亲每日都为父亲的小灶绞尽脑汁,记得当时母亲没什么可做的了,就舀一把白面,放上葱末、花椒,味素,盐,用水一搅和,在锅里摊成面饼给父亲下酒,而我们在一边看着父亲吃得津津有味,却不敢动筷。母亲说,那是给爸爸吃的,爸爸上班辛苦。我们一家人全靠爸爸的工资养活呢。即使这样,还经常听到父亲酒后在埋怨母亲,说母亲不会过日子,说我每月给你的六十多元的工资,不知你掰扯到哪里去了?一到月末就向西边的魏家街的魏大嘴借钱,还说,吃不穷,花不穷,老鼠盗不穷,算计不到受大穷。唉!没办法,贫贱夫妻百事哀啊。一到这个时候,母亲总是细细地据理争辩,最后的结果是遭到父亲的数落。这个时候,母亲总是躲在厨房的炉火边暗暗抽泣。
我依稀记得母亲抽泣的时候,有时搂着我的二哥,外号二驴。有时我也往妈妈的怀里凑,但母亲就是不搂着我大哥。也许这个时候母亲的骨子里会觉得他不是自己亲生的。而石头哥总是在一旁陌生地看着我们。有时母亲会问我“我离婚了,你和谁。”我总是惊异地看着母亲。并不回答她的问话。但是她从没有问过我大哥。这个时候对门的英嫂闻声就会过来规劝,越劝我母亲抽泣得越是厉害,似乎终有了倾诉委屈的对象。待英嫂踱进里屋,不知说了什么后,父亲便停止了谩骂。英嫂就会隔门招呼我们进屋休息,母亲擦擦泪眼带着我们进屋后,英嫂同我母亲在说话。有时英嫂会对父亲说,你哪样都好,就是脾气大了些。我父亲坐在炕头上,静静地抽着卷烟。我注意到,这个时候,他抽的格外专心。他吸上一口,半晌,也不见再吸下一口。烟卷上已留下了长长的烟灰,我轻轻走过去,倒把他吓一跳。说,洗洗,上炕睡觉。我和哥哥们便上炕,把被褥铺妥当,然后各自钻进被窝里。英嫂看我们要睡觉了,便也慢慢踱回自己的屋里,睡去了。
英嫂是一个漂亮玲珑的少妇。你知道有一种糖果叫山楂饴吗?一种软糖,色状如山楂,上面撒满了白色的糖霜。在那个年代的矿区,这是我们最爱的零食。因为奢侈,偶尔才能得到。在矿区,英嫂的好模样儿,就是男人们含在口里的一块山楂饴,每每咂摸起来,都是丝丝缕缕的味道,甜甜酸酸,让人不忍下咽。
但是英嫂也有不幸的过去,头几年,英嫂的丈夫在煤矿做工的时候,煤矿冒顶,生生把他掩埋了,待抢救出来,已不省人事了。英嫂是干练的人,她说女人绝不能把那一份严峻生活内容刻在脸上。好比寒冬里开放的花,它的意志越坚强,其花瓣就越色泽艳丽、娇柔。这些话,我不懂,但是我想我父亲懂。因为,我常看见,父亲每次给我们分吃的时候,都拿出一份叮嘱我给英嫂送去。有时,他也自己送去,忽儿就出来了,待走到门口时,还要回头张望一眼并嘱道,趁热快吃吧。
那时候英嫂同母亲最要好。两个人常常坐在院子里说话,说着说着,两个脑袋就挤在一处,声音低下来,忽然就听不见了。有时母亲和英嫂坐在院子里,一针一针织毛衣。发出针针摩擦的声响。英嫂有时会停下来,告诉母亲针法。父亲这个时候也会走过来,每人递上一颗糖,眼睛却看着英嫂,问道,甜不甜?父亲有时也会在英嫂身边干咳一声,把容颜正一正,他在掩饰或在暗示什么,心里痒痒的走开去。她坐在那里,半低着头,一团线绕在她的两个膝头,她的一双手灵活地在空中绕来绕去。眼睛向下,待看不看的。我母亲从旁看着这一切,沉默了。
我父親最喜欢的事情,是工闲的时候扛上他那支心爱的猎枪去打野物。我们这地方山多,小河套也多,河套两边,又是另一番世界。成片的树林,疯长的野草,不知名的野花,星星点点,清新且美丽。春天的清晨,刚下过雨,我们相约着去河套里翻鹅卵石捉龙虾。在我们的方言里,龙虾儿有一个很奇特的名字,带着儿化音叫蝲蛄儿,很好听。这种生物,黑青,像螃蟹似的有两个大夹,不小心就会被它夹着。我们捉回来,放在水里煮了,只一会儿的工夫,就由青黑变成了殷红色,剥开坚硬的壳,露出泛黄的稀少的肉,香味扑鼻,是那个年代难得的美味。河套边,还有野芹菜,人们用锋利的刀割了,背回家。炒了吃或包馅儿吃。青黄不接的时候,人们也去河套边采鸭食,当然这是鸭子的食物,可是既然鸭子吃了毒不死,我们也能吃。秋天,万物成熟的时候,通往山林的小路上,人欢马叫,一片欢腾。对于我父亲来说,河套的魅力在于那片茂密的树林。常常,我父亲背着猎枪,在河套的树林里转悠,或者到更远的山上,一待就是一天。黄昏的天光从树叶深处漏下来,偶尔,有一只野兔快速跑着,随着一声枪响。忽然就静下来。四下里寂寂的,光阴仿佛停滞了。我父亲往远处看一看,眼神茫然。他在找什么?我说过,我父亲的身上有一种纨绔气质。这是真的。弯弯的村路上,一个男人慢慢走着,肩上扛着猎枪,枪的尾部,一只野兔晃来晃去,或者是一只野鸡。这是他的猎物。夕阳照在他的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通常情况下,我母亲对我父亲的猎物不表态度。哥哥和我围上来,七嘴八舌地叫着,知道这两天的生活会有所改善。还有对门的英嫂也会过来,同母亲说着什么,然后哧哧地笑,再然后,眼风一飘,很媚了,父亲则侧头看了一眼英嫂,心里就忽然跳了一下。他说,这天,真热。于是,舀水洗手,矜持地沉默着。这沉默里有炫耀,有骄傲,也有隐隐的燥热吧。
二
那时候,旧街最西头有一棵枣树,经了多年的风雨,很沧桑了。巨大的树冠遮挡着一大片荫凉,邻里的一些孩子,有时聚到树下,有的捉虫子或掏蚂蚁洞、跳格子,也有男孩子们在弹玻璃球。有时旧街的大人们也坐在这里,男人们吸着旱烟,女人们拿着绣了一半儿的门帘。若是夏天,也有人手里拿着像马尾巴的蝇甩子在驱赶蚊蝇。还有的把自家的戏匣子拿出来收听电台广播。街里骤然热闹起来。说话声、笑声、咳嗽声、嬉闹声、乱哄哄的,半晌也静不下来。
在枣树的不远处,有一自来水管,但是这自来水不是时时有水,而是由自来水公司每天中午和晚上定时放水,每到放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拎着水桶前来接水,那高低粗细不同的水桶错落有致地排着很长的队,前面的桶接满了,水龙头都不用关闭,后面的水桶马上就接替上。男人和女人一边排着队一边说笑。这个时候,总能看见石头担水的趟数最多。因为他不仅要给自家挑,还要给英嫂家的缸蓄满水,而且还备用两桶,留着浇菜园子的。这个时候,会看见他额间滚满了汗珠,身上散着热气,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而他的眉宇间却闪烁着明亮的精气神。总是一担水担走了,而另一担却由英嫂在那儿排着。
阳光照下来,四周一片光亮,不知道谁说了什么,人们都笑起来。一个男人跑出人群,后面,英嫂在追,笑骂着,把一小石子掷过去,也不怎么认真。我坐在树底下,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一切。总之,那时,在我的心里,男人和女人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了。它包含了很多,温暖、欢乐,有一种世俗的欢腾和喜悦。如果男人和女人有颜色的话,我想,它一定是暖色的,明亮、坦荡、热烈,像田野上空的太阳,有时候,不得不把眼睛微微眯起来,它的明亮里有一种很刺眼的东西,让人莫名地甜蜜且忧伤。
在人们的眼中石头是旧街上有文化的人。不是他比谁念书多,而是他学的扎实、厚成。石头哥生得俊朗,为人也厚道,在街里很得人缘。那时候,街里的街委会总是开会,各种各样的会,叫得上名目的,叫不上名目的,大的,小的。每次开会,总有我石头哥。开会的时候,石头哥总带上我。我现在依然记得,街委部的一间屋子墙上挂满了奖状和锦旗,木头的长椅,斑驳的酱色漆,我依在哥哥身旁听。讲話的人是街委会主任,也就是英嫂。
只见英嫂的嘴一张一合,很用力,可是我听不懂。我心想,她在说什么呢?忽然,从她嘴里蹦出一个词,她说,肯定,我们能——我心里一闪,啃腚。这回我听懂了。我一下子来了兴趣。啃腚。这事情有趣。我等着她的下文,她却再也不提啃腚的事了。可能是她忘了,我失望极了。下午的阳光从窗子照进来,细细的飞尘,在明亮的光束里活泼泼地浮动。我把头歪在哥哥身上,我困了。后来,直到现在,一提起开会,我就会想到那间屋子,挂满了锦旗和奖状,木头的长椅,阳光里的飞尘,还有,啃腚。真的。肯定。我只要一听见这个词,就会想起啃腚。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对于石头哥,我的记忆模糊而零乱。那时候,在石头哥眼里,我只是一个懵懂的小丫头,淘气的时候,给一根棍子就能把天戳破;安静的时候跟在他的身边寸步不离。一次哥哥同英嫂去镇里的电影院看电影,哥哥不让我去,说人山人海的怕挤散了,可我却哭闹着要同他去。无奈哥哥答应了。可到了影院,因离电影开演还有一段时间,影院的大门还没有开,我在外面冻得直哆嗦,上牙下牙帮直打颤,哥哥看见后一面把他的棉衣脱下来给我穿上一面说,不让你来非要来。话语中,含着嗔怪,也带着怜爱。我穿上哥哥的棉衣暖和了,没想到哥哥却冻病了。为这事,哥哥却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跟屁虫”,每次我要跟着他的时候,总做出乖巧的样子,常常惹得他笑起来。那些年,河套里还有水。石头哥常常带着我还有英嫂去捉鱼。我们把鱼放在一只罐头瓶里,捧着回家。有时,他会把我背起来,作飞机状,跑着,飞着,嘴里呼啸着。我惊叫起来。手紧紧捧着罐头瓶,几条细小的鱼,惊慌失措,四下里逃逸。哥纵声大笑起来。
石头哥考上民办教师的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可是我依然不懂大人们口里吃皇粮的意思。在我母亲简单而有秩序的世界里,上班,就是吃皇粮的意思,这是矿区妇人最朴素的判断和认知。石头哥在说起未来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种光芒,是自信,也是憧憬。刚刚参加工作,一切都是新鲜的。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规矩,不同的人事,在矿区,他是决意要施展一番了。那时候,他还没有结婚。之前,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谈过恋爱。不过,那些日子,家里的门槛已经被媒人踏破了。父亲很着急。哥呢,却是漫不经心,仿佛这事与他无关。后来我才知道,石头哥心里曾经爱着一个人。那个人,不是别人。是我们对门的英嫂。
对于石头哥的这场爱情,我始终不明所以。我只是从大人们闪烁的言辞中隐隐知道了一些模糊的片断。我只知道,那时候石头哥总被英嫂唤来唤去,帮她把洗好的湿被单抻展,帮她到井边抬水,帮她把鸡轰到栅栏里去。帮她掏炉灰,然后用扁担担出去,而在这时,石头哥总是乐颠颠地跑过去,听从英嫂的吩咐。还有一回,我记得,英嫂求石头哥把树上的一只气球摘下来。这只气球不是街里卖的红红绿绿的气球,而是用避孕套吹起来的气球。英嫂指着挂在树上的薄而透明的气球,它在阳光中飘飘扬扬,仿佛是树上长出的一个透明的大白果。英嫂脸色微红,神情娇柔,想必是有些难为情了吧。说“不知哪个野孩子淘气,挂上去的。”石头哥看了英嫂一眼,又抬头看了看树上的大白果,他稍稍犹豫了一下,很快,他往手掌心里吐了一口口水,像村子里那些野孩子那样,他开始了笨拙的攀爬。现在想来,当年,石头哥那样一个安静斯文的男孩子,酷爱干净,在二驴,也就是我二哥为了躲避惩罚身手敏捷地爬上树杈的时候,他也只能站在树下,仰着脸,低声下气地请求二弟下来。那一回,他居然为了一个气球,英嫂的气球,毅然地学会了爬树,像村里那些他鄙视的野孩子那样。我分明看见英嫂眼睛深处的纯净和柔软,在那个春天的下午,显得那么可爱动人。
当然了,是更早的时候。当年英嫂刚刚嫁到旧街,洞房里,少不了取乐戏闹的男人们,说着各种各样的荤话,把新娘子逼得走投无路。石头默默坐在角落里,看着羞愤的新娘子,像一只惊慌的小兔,在猎人的围攻下无力突围。灯影摇曳,石头心头忽然涌上一股难言的忧伤。多年以后,英嫂还跟母亲提起,感叹道,这孩子就是不一样呢,规矩。那时候,在我的屋里只是坐着,一坐就是一夜。英嫂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柔软,她是想起了那个羞涩的少年,还是追忆起自己似锦的年华?
那一阵子,我们矿区的话题总是围绕着父亲、石头、英嫂的事。人们的长吁短叹常常路途迢迢地传到矿区、传到旧街、传到我们的耳朵里,纷扰着我们的心。流言是慢慢传开的。说是英嫂跟父亲。这怎么可能。旧街的人都说,按辈分,父亲当是叔叔辈,虽说早出了五服,可再怎么,人家是娇滴滴的嫩瓜秧一般,父亲是一棵老瓜秧,再说了,父亲是有家室之人——也有人说,天天在一个屋檐下,做饭,撞屁股,能撞出什么好来?生活里,才子佳人,惯了就弄假成真了。有人就吟道:错把戏剧当生活——人们就笑起来。
还有人说,石头已经在矿区里干得风生水起。事业上的得意,更加衬托出情场的落寞。人们都感叹,世间的事,到底是难求圆满。
我愿意相信石头和英嫂,他们之间,真的热烈地爱过。也或许,一直到老他们依然在爱着。然而,然而什么呢,我也说不好。但是我也愿意相信父亲和英嫂只是旧街的一个流言,一个荒谬的传说……
我不知道,那么多年,石头哥是不是一直想着英嫂,那个俊俏的小媳妇。那么多年,他是不是曾经喜欢过别人。用我母亲的话讲,一个好端端的小伙子,怎么能娶一个比自己大一轮的水货。水货,用旧街的话讲,也就是二婚的意思。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字眼的含义。它后面包含的种种歧视、凌辱、哀伤、无奈,我全懂。母亲说,这简直是辱没门楣的事情,是一种耻辱,是对宗族的叛逆和玷污。这是一个不能妥协的立场。于是找来了严厉的父亲,任由石头哭闹、绝食,父亲只是不理。小孩子,示一示威罢了。况且,在这几个儿女中,石头的孝是出了名的。可是,父亲再想不到,石头会喝了农药。当终于救过来的时候,石头睁开眼,头一句话就是,我要英嫂。父亲长叹一声,泪流满面,“你也不想想,英嫂是你的吗?”
三
的确,英嫂不是石头的,也不是父亲的。那个冬天,英嫂出嫁了。嫁到河对岸的北街了。英嫂的丈夫,我是见过一面的。个子矮一些,跟高挑的英嫂站在一起,尤其显得矮小。出嫁那天,是腊月初八。雪后初晴,格外的冷。英嫂穿着大红的缎袄,烫了头,坐在炕上。响器班子站在院子里卖力地吹打。新女婿早早就来接亲了,可是被人为难,不让进屋,只知道露出白白的牙齿嘿嘿笑着。陪送的人再三劝道,让进去接走吧——不早了。这才进了去,把英嫂牵了出来。院子里,唢呐声更热烈了。英嫂推着披红挂绿的自行车,一步一步,走出旧街。因为英嫂化着浓妆,那一刻,我看不清她的表情。英嫂在想什么呢?街里街外,天上人间。那一天的事,现在想来,已经很模糊了。天色渐渐明亮了,披红挂绿的队伍和着高亢的唢呐,在冬日的村路上格外鲜明。英嫂在众人的簇拥下,推着车,慢慢走着,走着,一直走进她未来的悠长岁月。
后来,我总是想起英嫂出嫁那天回望石头哥的那一眼,眼里有泪水,饱含着多少不舍、难耐、心酸、欲言又止的无奈……她生命中盛开的花朵,娇娆、芬芳、迷人。在那一刻,已慢慢凋零了。作为一个女孩子,从那时候开始,我就隐隐地认识到,美好的,总是短暂的。我开始害怕看姑娘们出嫁。而在此前,我是那么热衷于看热闹,挤在人群里,心神激荡。
石头立在院子里,看着满地的鞭炮碎屑,空气里还有硫磺的刺鼻的味道,雪地上,乱七八糟的脚印,一道道车辙、交错着、纠结着,终是出了旧街。石头把胸中的一口气慢慢咽回去。然后跑回房间号啕大哭起来。
父亲休工的时候多是扛着猎枪在河套的树林子里消磨光阴。家里的事情,他懒得管。也管不了了。他只知道,即便天塌下来,有母亲顶着。这些年把他折磨得已不像当年的男人了,他知道,如果男人不像男人,这个家,女人也就不像女人了,这是真的。先前,母亲是一个多么懦弱的女子,在娘家,娇养得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见了人,不待开口,先自飞红了脸。说起这些,谁会相信呢。英嫂的事,要不是母亲做事果决,怎么能够这么干净?是她,把这杯苦酒自斟自饮了,还不露一丝痕迹。她知道,这种事,在自家最是张扬不得。尤其是旧街这屁大的地方,人们的嘴巴不齐,张口闭口,不经意间就伤了很多。她知道其中的厉害。她必得把这口气咽回肚子里。没办法的事,寡妇门前是非多啊,把一对活生生的人摆在眼皮子底下,这后半生可怎么做人?母亲脸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却托了人把男方家底都一一摸清,也把英嫂的思想说服了。这其中的坎坷煎熬,能跟谁讲?
四
老大不成亲,老二成亲,这在旧街是很丢脸的事。可是二驴哥的媳妇已显怀了,生米已成熟饭,这在旧街也是个忌讳。可是石头对象还没有呢,也不能等啊。如今,真是儿大不由爷啊!没办法,只有舍得脸面赶紧结婚吧。二驴哥和二嫂婚后两个月,二嫂就生了个大胖小子,家丁兴旺,母亲高兴得很。同人闲聊的时候,说着说着,就说起了新生的孙子。大胖小子,哭起来嗓门响着呢。早忘了这孙儿提早降临给家里带来的羞辱。相反,倒很庆幸。母亲照例是忙里忙外。看着一院子的尿片子,花花绿绿的晒满了铁丝柴火垛,甚至柳筐的弯梁上都是。把这旧院多年的阴气全给冲散了。孙子走到天边都是自家的根苗。再远,也是走不出这旧街的。母亲笑了。天是格外的好。母亲抬起眼,看着旧街上方那一片湛蓝的天,有一缕云彩悠悠掠过。这辈子她最得意的事,就是二儿子娶了妻生了子。起先,心里还有一点儿忐忑,生怕像老大似的死心眼儿。这回,母亲是彻底放了心。她捏一捏尿片子,太阳真好,只这一会儿差不多就要干了。
阳光照过来,铺了半张炕。二嫂倚在被垛上喂奶。屋子里有一股暖烘烘的奶香夹杂着尿腥的味道,让人昏昏欲睡。炕上,摆满了花花绿绿的线钱。这地方,生了孩子,人家都要送线钱。用线系了不等的钱坠,有五元,十元,二十,三十的不等。线送过来,都要在孩子的脖子上戴一戴,吉祥,长命,富贵,避邪。然后就挂在炕墙上。线越多,孩子的命越好。二嫂抬眼看了看线钱,层层叠叠的,让人眼花缭乱。这一回,乡间的人眼皮都活得很呢。两个儿子,就是旧院的两只胆,两条梁。老大虽然也不错,可是自从英嫂嫁出去后,就像丢了魂似的,几近呆傻。是什么也指望不上了。老二人缘好,顶替了父亲的职号上了班,是队上的队长,可别小看了这队长,在矿区,谁若是在他的手下干活儿,这其中的文章就难念了。可是,承了不薄的人情。受惠的人家总念着什么时候把欠下的這份情还上。比如说,有一回,我母亲病了,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受了风寒。左邻右舍都来看望。特别是下趟房邻居对窗户的邹婶,又是替母亲烧火又是喂鸡的。那个殷勤劲儿,怎么说呢,让人都感到不自在。同母亲比起来,邹婶,到底是年轻了些,难怪,父亲总是说邹婶像小娇娥。有时说说,俩人就追赶着满院子跑,邹婶把一把青草掷过去。也没撇到,惹得父亲哈哈笑。再比如说,二驴生了儿子,这送线钱的,竟是络绎不绝。二嫂看着满墙的线钱,心里是百种滋味。有点儿甜,有点儿酸,又有点儿苦。说不清,真说不清。透过窗子,我母亲的影子投过来,一伸一缩,正在晾尿片子。二嫂瞥了一眼。怎么说呢,自从二嫂从母亲那儿要九百九十九元的彩礼钱没到位后,二嫂心里就有了结。这个结是个死结,一辈子都没有再打开。其间,她也努力过。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婆婆,能怎样呢。可是,没用。她看着母亲为了他们操劳,她也心疼,母亲是一年一年老了。然而,也还是怨恨。其实,母亲是真心答应给她的,说年底把那头猪卖了,换了钱就给她,可是她等不得了。
母亲疼爱孩子。她把孩子尿尿,一只手端着,一只手拨弄着孩子的小雀子,嘴里嘘着哨子,孩子冷不防尿出来了,尿了她一手,她倒呵呵笑了。也有时候,她把孩子的小脚放在嘴里,含着,孩子怕痒,咯咯地笑。二嫂冷眼看着这一切,不知怎么,心里却是烦得很。还有饭桌上,坦然接过母亲递过来的饭碗,对母亲,竟是连让也不让一下。母亲又给二嫂添了一回饭,那神情,殷勤,近乎谄媚了。二嫂吃着吃着,当的把碗一放,回了西屋。
母亲坐在院子里,看着一朵飘絮慢慢落下来,落在印着红喜字的脸盆里,在水面上悠悠转着。母亲的眼泪淌了一脸。在旧街,母亲是最要脸的人。如今,在儿媳面前,竟是碰了壁。她恼火得很。正应了那句话,媳妇越做越大,婆婆越做越小了,然而,儿媳毕竟是儿媳,虽说是娶进门成了自家人,终究不比儿子,可以当面锣对面鼓直来直去。其实,这只是个安慰,儿子,儿子又能好到哪里呢。儿子也变了。人前倒不怎么样,没人的时候,对她却是淡淡的,有时候搭讪一句,也待理不理的,自己的一张脸倒先自涨红了。还有母亲很多的时候是想到爹,这么些年,为其养儿育女,他的心思不知在哪儿,她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这样一种光景。没有理由,有时候,夜里睡不着,想起这么多年种种艰辛,磨难、不堪、像一场乱梦,她都不愿去想了。早在二嫂娶过来的时候,她就知道,她的时代是过去了。自此,旧街是年轻一代的天下。
五
父亲是矿区掘进队的记工员。我至今还常常记起,父亲把我家吃饭的桌子放在炕上。然后坐在桌前,噼里啪啦拨算盘,黑褐色的算盘珠子闪转腾挪,太阳光从格子窗照过来,一线流光在上面闪烁。偶尔,父亲抬起头来,同旁边的我说上一句,就又埋下头去,继续算账。账本是一种很挺厚的纸张,上面有红的蓝的格线,密密麻麻的,有很长一段时期,我的练习本就是这样的账本订成的。这让我在伙伴们中间很是骄傲。那时候,我家下趟房同我们对窗户的邹婶常来我们家,也总管我父亲要这种本子。现在想来,这样的本并不好,主要是线条太乱,远不及白纸的干净清爽。可是在当时,账本纸代表了一种权力。幼小的我,竟也知道特权带来的虚荣了。算起来,当时邹婶总也有四十出头了。四十多岁在女人一生中,该是最好的年华。像初秋的庄稼、饱满丰饶、汁水充盈,浑身上下洋溢着成熟女性的风韵。仔细想来,邹婶算不得好看,但却是生动的。性格又活泼,人又能干,我不知道,对于邹婶父亲心里有什么想法。可是,看得出来,邹婶是很喜欢同父亲在一起的。往往只要有父亲在,邹婶的笑声就格外清脆,神情也格外娇柔,不经意地就飞红了脸。很妩媚了。
有一回,是个傍晚吧,母亲让二哥去田里采上一堆毛豆,说给父亲当下酒菜,毛豆里放了盐煮熟了,剥开皮,露出里面的青豆,香嫩可口,是不错的美食。二哥正在看二嫂給孩子喂奶,应了一声,却不动弹。于是,我便说,还是我去吧。于是我把门摔在了身后,小人儿惊慌地抬头看了一眼,半天定不下神来。哥在身后骂了一句,这死丫头,看把孩子给吓着。我回望了一下,做个鬼脸,一溜烟跑了出去。
夜色朦胧,空气湿润润的。院子里的东西都渐渐没有了轮廓。菜畦、树木,影影绰绰的,还有玉米地,热烈烘烘的,把人紧紧包围,已模糊成一片。
忽然,我听见一阵脚步声,很轻,在玉米地间停住了。我的心跳得更厉害了。心想,一定是有什么坏人。可是,却迟迟没有动静。许久,一个女人说,走吧,天黑了。是邹婶。这个时候,邹婶子是来掰玉米吧?嗯,你先出去。父亲!竟然是父亲!这个时候,父亲和邹婶在这里,他们做什么呢?我支起耳朵,却再也听不见什么。沉默。沉默之外,只见他们一前一后走出了玉米地。然而,在这黏稠的沉默里,却分明有一种异样的东西,它潮湿,也疯狂。
我回到家的时候,夜色已经把旧街淹没了。屋子里,灯光明亮,一家人坐在桌前,桌上是热腾腾的饭菜。看见我回来,父亲微笑了,说来,吃饭了。母亲骂道,才回来。我坐在灯影里,静静地吃饭。父亲和母亲,偶尔说上两句。不知说到了什么,父亲先自笑起来。我疑惑地看了一眼他的脸,平静,坦然,笑的时候,眼角已经有了细细的鱼尾纹。英俊倒还是英俊的。也不知为什么,我分明感觉到他那些从容后面全是惊慌和掩饰。他微笑得有些艰难、有些吃力——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他慢慢地吃了一口饭,强自镇定。母亲也笑着。我停下来,看着父亲,忽然跑到他的身后,把一根玉秸屑从他的头发上摘下来。父亲惊诧地看着它,也只是一瞬间的事。那一根玉秸屑,衬了乌沉沉的饭桌,变得那么的触目。
我们家的硝烟战火更是不断了。有时候,从外面疯玩回来,看见家门口挤满了人,有的在看,有的在劝,知道是父母又吵了架。母亲的呜咽一阵阵传来,夹杂着父亲粗重的谩骂声。一颗心就立刻缩紧了。那时候,常常半夜里,看母亲不见了。我就去叫醒二哥。
矿区的夜,寂静,深远,二哥打着手电筒,我跟在后面,满街找母亲。电光朦胧着映出我们的影子。母亲,你在哪里?我的一颗小小的心充满了忧惧,竟然不敢哭泣。从一开始,母亲就为大哥操劳,历尽了煎熬。父亲的粗暴,儿媳的轻视,贫困的日子,母亲不知该如何面对。她只有逃离。有时候,我们会在深深的玉米地里找到母亲,她披散着头发,满脸泪痕,露水把她的鞋子打湿了,走起路来,吱吱响。有时候,满矿区里找,也找不着,母亲是去了河北的英嫂家。这个时候,英嫂把我叫过去,让我去找父亲,央他来接母亲。至今,我还记得,黄昏,父亲在喝酒,我立在一旁,低声哀求,我想娘了。父亲的脸一点一点模糊了。半晌,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现在想来,那时候,英嫂家是母亲的一个避风港了。英嫂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嘴巴向来不饶人。我母亲坐在灶边,只是低头垂泪。英嫂立在当地,冲着我说,丫蛋,你回吧。你娘就在这里——不回去了。早晚有一天,她得让你们气死。这话是说给父亲听的。我扭头看看父亲,他闷头吸烟,一张脸在烟雾中阴晴不定。
我不知道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之间是怎样一回事。他们一定互相怨恨过,他们有过抗争,也有过妥协,然而,终究是坚忍。他们一生生养了三个儿女,可是,他们爱过吗?我还记得,有时候,早晨赖在被窝里,听见父亲和母亲在院子里说话。母亲在扫院子,父亲在喂鸡,他们漫不经心地说着闲话。甚至有点儿索然。我在枕上听着,半闭着眼睛,心里却荡起一种温情。我喜欢这样的早晨。也有时候,我歪在母亲身旁睡午觉。父亲走过来,俯下身,看看我,转而逗母亲说话。母亲合着眼,只是不理,父亲把手指在母亲下颌上挑一下,母亲就恼了,佯骂一句,父亲觉出了无趣,便走了。这个时候,我紧闭着眼睛装睡,心里却是充满了喜悦。多么好,我的父亲和母亲,至少在那一刻,他们恩爱着。直到现在,我所理解的爱情,也不过如此。
六
旧街不一样了。仿佛是一夜之间,人心散了。人们都自顾地飞出去了。只留下石头哥,在原地,怔怔的,半晌醒不过来。对于他,对于他的聪明、善良、敦厚、实诚等人们越来越淡了。他后来也不教学了。有人说,是学校里裁人,裁下去了。也有人说,当教师作风要正派,可是我从没认为石头哥有什么不正派的。但石头哥的说法是,没意思。现在想来,可能石头哥的话是真的。没意思。在石头眼里,什么有意思呢?天气晴好的日子,石头会立在院子里,看着头顶树叶缝隙里的天空发呆。院子里寂寂的,微风把树影摇碎,零乱了一地。一朵蒲公英英絮落下来,栽在他的肩上,只一会儿,就又飘下来,飘在水瓮里,悠悠地浮着。石头盯着那朵英絮,失神了很久。当初,他也许再没想到,这样一种命运会降临到他的头上,他这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旧街的娇容,会经历怎样的生活的碾磨,其间,虽有不甘与挣扎,却也渐渐学会了隐忍和屈从。在时代的风潮中,他渐渐被湮没了。
那时候,我已经在很远的城里读书了。寒假回来,看父亲、母亲。同二哥二嫂还有邻里讲起城里的趣事,都笑了。父亲母亲很惊讶地抬起头看着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而很快就释然了。我心里一酸。我们都以母亲的名义聚到家里,可是,我们却把母亲忽略了。我们明知道母亲耳背,她听不见,我们还是不向母亲解释,照常说笑。我们这些儿孙,冷酷、自私,竟舍不得放弃一时口舌之快,走过去坐在母亲身旁,摸一摸她枯枝般的手、她苍老的面容、她的白发,附在她的耳朵边,说一句她能够听清的话。我们把年迈的母亲排除在外了。
多年以后,我从省城回到矿区,回到旧街,母亲是越发苍老了。石头还孑然一身踯躅在旧街的老宅子里。旧街,在儿时的记忆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可是,如今,在周围楼房的映衬下,却显得那么矮小、狭仄。这是当年那个旧街吗?在这里,有我的迷茫的童年岁月,我的哥嫂,英嫂和石头,在旧院走过了他们的苦乐年华。当然,还有我的父亲母亲,他们一生的艰辛、困顿、微茫的喜悦、漫无边际的伤悲,都在这里了。
那棵枣树已不在了。这么多年,走了这么多的路,我却再没有吃到那么好的醉枣。香醇、酸甜,那真是旧院的酸枣。而今,都远去了,再也寻觅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