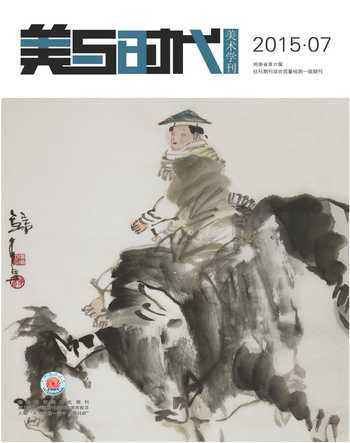摹古与创新
2015-05-30赵锦屏
摘 要:清代绘画,在当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下,呈现出特定的时代风貌。文人画呈现出崇古与创新两种趋势,山水画方面以“四王”为首的“摹古派”为誉为正统,重在继承和总结,代表了传统的笔墨程式。以“四僧”为首的在野遗民画家重在发扬个性,师法自然,代表了笔墨程式新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摹古;师法造化;创新;四王;四僧
我国清初画坛上出现过很多优秀的画家,其中以“四王”“四僧”为“崇古”“创新”的两种不同风格的趋向为主。“四王”是指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四人,他们均擅长山水画,因受到皇帝赏识,被誉为“正统派”。以“四王”为首的清朝正统画家由于社会背景等原因,缺乏去自然中体真实验生活的感受,在绘画上一直无法超越前人。而明末董其昌为了扭转当时画坛所处的现状,提出了著名的“南北宗论”观点和一系列文人画理论,如“‘画以自娱的创作宗旨、‘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的崇古观点、‘偶然兴到的感知方式,追求具生拙味的士气等”[1]。“四王”在绘画风格和艺术思想上,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董其昌的影响,于是放弃了师法自然,开始致力于摹古,尤其崇拜元四家。在“四王”屹立于清初画坛的同时,出现了一批在野的遗民画家,他们在政治上孑然独立,艺术上重视创造,表达自己的个性,喜欢游于山水之中,师法自然,走上与“四王”完全不同的艺术道路,呈现出与“正统派”相左的艺术追求,代表了当时笔墨程式新的发展方向。其中最有名的是朱耷、石涛、髡残、弘仁四人,因他们都出家做过和尚,所以被称为“四僧”。前两人是明朝后裔,后两人是明朝遗民,他们四人都怀着孤臣遗子之心在政治上不与新王朝合作而仍然忠于旧王朝,有的奋起抗争,有的遗世独立。他们的绘画无不带有深挚的情感色彩,并且通过绘画曲折隐晦地反映了各自的遗民意识,加上作品具有强烈的个性化,给当时的画坛带来了一股新风。
“四王”山水画分为两代,第一代是王时敏、王鉴,第二代是王原祁、王翚,他们之间有亲友或师承关系,是董其昌绘画上忠实的追随者,极其注重以笔墨为代表的形式因素,追求绘画章法和笔墨,强调临摹与仿古,对绘画中的现实性因素极少关注,实际上脱离了真山真水真性情。比如王时敏的《南山积翠图》,此画从构图到用笔,从林木到山峦,从皴染的山顶到山间的云层,全都是从传统中来,临仿宋元画家遗法。“王时敏仿古人画,形体基本相似,仿某家,即使不题款识,也可以知道是某家之作。”[2]这无不与他小时候的成长环境有关,王时敏从小就喜爱绘画,阅览历代书画名作,再加上他的祖父与董其昌是良师益友,在他七岁时就得到了董其昌的教导,自幼便走上了摹古道路。他曾在《西庐画跋》中反复强调作画要与古人同鼻孔出气,可见对古人技法临摹的痴迷程度。《夏山飞瀑图》是他的得意之作,此画以全景式构图画峰峦层叠,画法上追踪黄公望,山石多用披麻皴,设色苍翠秀润,生动地表现出夏天被日光照射的山峦草木华滋的特点。和董其昌相比,他去掉了过于生拙之处,加强了笔法的统一感,丰富了干笔皴擦的技法。而“四僧”中的朱耷也曾受董其昌影响,他所作的《临董其昌仿古册》几乎可以乱真,但他与王时敏不同的是,做到了师古意而不师其迹,不为古人之笔法所限制,他学董其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随董的摹古作业,而是通过其临本来研究五代、两宋乃至元时名家的绘画风貌。加上他独特的“八大体”书法与绘画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画风,作品使人一眼就可辨出是经于他手,个人风格极强。朱耷画山水花鸟也是一绝,常以象征、寓意和夸张的手法,塑造奇特的形象,抒发自己愤世嫉俗之情和国亡家破之痛。他所作鱼鸟形象倔强冷艳,眼部描写夸张,眼珠皆向上方,似是以白眼瞪人,流露出一种不满的情绪,可见其中所寄托的一股愤慨沉闷的情感。其中最值得赏味的是他的《孔雀图》,他在画中题诗到:“孔雀名花雨竹屏,竹梢强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他在画中以孔雀象征清朝官员,讽刺他们长有三只耳朵,三根羽毛如同三眼花翎。用牡丹折射统治者,以长在悬岩上暗示它没有土壤,孔雀站在危石暗示根基不牢,寓意他们都一样有垮台的危险,表达了朱耷的愤怒与蔑视。“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在创作高度上达到南宗顿悟境界的,不是四王,而是八大山人;而一味摹古的四王追随者们倒是落入了北宗渐悟的法障之中。”[3]八大能去诸家之长为己有,又保持住了自己鲜明的特征,既不同于前人,又不为时人所及,表现出了明末清初的时代精神。与朱耷相比,王时敏缺乏依靠自己对自然的真实心境去创作绘画,导致脱离了真实丘壑,就算模仿得再真,始终都让人感觉缺乏一种酣畅淋漓的真性情。
王鉴的画主要分两种风格,一种是模仿“董巨”、倪云林、黄子久、王叔明之作,另一种是取赵孟頫、赵令穰、赵伯驹等人之长。他在青绿设色上是非常优秀的,清代在近三百年的山水画家中,很少有人能超越他。他的《仿黄公望山水轴》一画虽然表明仿黄公望,实际上在丘壑位置仍仿吴镇,画法上也引入“董巨”之笔。这说明他和王时敏一样,在艺术追求上并不关心去描绘真山真水,只是以古人概括自然景物的笔墨范式与经验再去创造一个心中的自然,这样的山水缺少生气,很难引起人们心灵上的共鸣。而“四僧”中的弘仁和髡残,虽是从师古道路走起,但他们师古全在通过画作把握古人精神,像弘仁就主张师天地造化,师自然山水,强调抒发个性,常常往来于各个名川大山之间,勤于观察写生。他的《黄山始信峰图》就显示出这一独特魅力,画中山石线直而陡,多空勾而不渲染,只点出几簇树木,便有了疏密变化的效果。仿佛通过他的画笔,所有变幻不定的东西都变得不朽了。还有髡残,黄山之行是他一生中很重要的经历,正是通过黄山之行让他认识到师法造化所能得到的无限生机,从而跳出古人藩篱,生成个人风貌。他注重对景物气氛的描绘,笔墨率性而浑厚,含蓄而引人入胜,反对模仿古人,常常将自己的艺术见解作于书画之上。特别是他的笔法与画中题跋所用的行草书法相贯通,随意挥洒,粗服乱发,体现了他独特的绘画风格。他们二人虽都曾以黄山为师,但表现出来的风格却是完全不同的。这全源于他们不同的自身感受与独到见解,但无论是这其中的哪种画风,凡是游历过黄山的人见之作品,都无不发出感叹,觉得分外亲切。这就是师法自然的力量。而呆在墙瓦之中,无论你如何研究摹习,始终与真实丘壑相差有别,即使画出了形也画不出神。
其实对中国山水画家来说,在攀登艺术高峰的过程中,“师古”是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向前人学习是绘画家的基本要求,但是在这个前提下,一种是师古而不师其心,盲目地拜倒在前人脚下,墨守成规。另一种是“师古而化之”,能把古人的精髓之处与自己的风格结合起来去大胆发展,积极创新,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绘画道路。王翚、王原祁在继承、发展王时敏、王鉴的绘画思想时并没有质疑他们创作的出发点,而是依旧落入了摹古之框。将王原祁的《仿黄公望山水图》和“四僧”中石涛的《山水清音图》相比,更能体现出这一特点。在《仿黄公望山水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不怎么讲究命题,主题直奔“仿”而去,并且把注意力放在了轮廓位置的安排,从他画中开合起伏的措置,通体与段落的有机联系就可看出他想在构图上竭力创新的想法。他的笔法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但对笔墨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真实自然的体察,所以他笔下的景物比起“前二王”更显符号化,与真实丘壑的距离越来越远,完全感受不到真实山水的写生趣味,从画中构图就可以看出,这一切都是经过作者反复琢磨,精心布局之作,绝对不是真实山水该有之态,缺乏了动人之味。而《山水清音图》构图出奇制胜,富有冲击力,用笔劲力沉着,线条较方,山石渲染有力,线条情趣经过个人性格的渲染后,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笔法。特别是那满幅的浓墨苔点配合着以尖笔剔出的丛草,使画面产生了如惊风骤雨般的韵律,呈现出苍茫深邃、豪情奔放的壮美,绝对是中国画“用墨如用色”的绝佳典范。石涛半生游历山水之中,我们甚至可以在通过他的画感受大自然的芬芳,如果没有真正投入到大自然中去深入的观察、体验,绝不会有这样生动优秀的画作。石涛的画论《苦瓜和尚画语录》对绘画中众多问题作出了精辟的分析,提出了著名的“一画论”“我用我法”“搜尽奇峰打草稿”等主张,强调抒发个性,主张师法造化,他的这些对绘画的独到见解对当时被摹古风气笼罩的沉闷画坛,无疑是当头棒喝。
纵观“四王”“四僧”山水,前者笔法造诣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但因在继承董其昌思想的同时,却并没有提倡、鼓舞画家去真山真水中感受自然,也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仿的那些古人画家成就也都是从真实体察中所积累、创作出来的,在思想上无限制地放大了董其昌摹古这一观点,导致他们脱离客观事实,走向了形式主义。另一方面,他们在画风上趋于统治者的爱好,迎合清王朝贵族的口味,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创作,造成了因循守旧,阻碍了他们取得更高的成就。而“四僧” 的作品表现出了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特点,他们不仅有扎实的绘画功底,更懂得以画来寄托自己的情感,不受外界主流干扰,能够到处游历,切身接触自然,抒发自己对美的独特追求。僧侣生涯也使他们少了一层俗世的束缚,多了一层禅思的切身体会,能将自己对自然的感悟无拘无束地表达出来,将一切恶境变为殊胜之境。通过对“四王”“四僧”的比较我们知道,好的艺术作品需要艺术家有真实的体验和感悟,而如今的中国当代艺术恰恰需要这种精神。
注释:
[1]紫都,范涛.董其昌生平与作品鉴赏[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11.
[2]张书珩,傅新阳.四王吴恽绘画艺术[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6:24.
[3]洪再新.中国美术史[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362.
作者简介:
赵锦屏,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