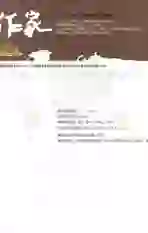以往作为当下
2015-05-30赵叶莹
赵叶莹
摘要: 本文力图通过对《继续生存》和《迸涌的流泉》两部德语自传文学作品的时序与叙事策略进行分析和比较,来证明保罗·利科“包含自传在内的一切叙述最终都是当下叙事”的论断。
关键词:自传文学 时序 当下叙事
露特·克吕格,奥地利裔美国文学家、作家,1931年出生于维也纳富裕犹太家庭。1942年,克吕格随祖母及母亲被运往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后成功逃脱。战后,克吕格进入雷根斯堡哲学与神学院学习,在那里结识了德国当代作家马丁·瓦尔泽。1947年克吕格随母亲移居美国。《继续生存》(以下简称《继》)便是作者回忆自己这段童年和青少年经历的自传作品。
马丁·瓦尔泽,德国作家,是继海因里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之后德国战后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迸涌的流泉》(以下简称《迸》)是瓦尔泽晚期重要作品之一。在这部自传体小说中,瓦尔泽不仅真实再现了纳粹统治时期博登湖畔小镇瓦塞堡的生活状况,同时也通过对人物的精准刻画展现出一幅特殊时期的乡村生活众生相。小说作者力图通过一种“脱离所有先入为主的历史阐释”的不存偏见的讲述,从一个孩童的视角真实再现历史。
克吕格与瓦尔泽曾是相交多年的挚友。1992年,克吕格曾在其作品发表后不久明确表示她的这部自传是写给马丁·瓦尔泽的,而马丁·瓦尔泽在六年之后发表的自传体小说《迸》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对克吕格这一“挑战”的回应。本文将从时序的角度对这两部产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德语自传作品中的“当下叙事”进行分析和比较,力求以此证明“包含自传在内的一切叙述最终都是当下叙事”这一论断。
一
按照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的定义,“时序”指的是“能够按照其发生的先后顺序来对其进行重构的事件的时间顺序(即“故事”,story)和这些事件在文本中被叙述的顺序(即“话语”,discourse)之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回忆性作品大多数都是以倒叙的顺序呈现的,即“时间顺序在前的事件反而要晚一些——作为叙述者或者人物的回忆——被叙述”。因此,在回忆性作品的一个章节或多个章节中甚至在整部作品中都会出现在其框架内进行回忆的“第一叙事”层和描述回忆内容的倒叙层的对峙。传统自传文学中的倒叙一般都是按照时间顺序从童年时代开始一直持续到回忆过程的起始时间点——即热奈特所谓的“完整倒叙”——从而突显作品中人物的一种有意义的成长和发展过程。
对于分析第一叙事层和倒叙层之间的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两个叙事层中谁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如果第一叙事层占主导地位,那么所回忆的事件就会缩减为极其短小的回顾性叙事内容;如果第一叙事层仅仅局限于“框架叙事”,那么读者在阅读时很可能会忘记内叙事层涉及的是一段回忆;如果两个叙事层之间基本不存在谁占主导地位或者说当两个叙事层之间的关系趋于平衡时,“回忆的模仿”尤为突出。也就是说,“回忆的模仿”通过两个叙事层之间的不断变换而得到增强。尽管从表面上看来,《继》中的第一叙事层作为后记被放在了作品的最后部分,但是,作品中大量出现的无时序性和元叙事性的评论确保了叙述的回忆性特征。
具体说来,《继》中的“当下叙事”分为两种:一是明确指向回忆行为的评论,这些评论有的是对回忆的开始及其地点与时间的说明,有的是对回忆行为本身的强调,有的是对回忆事件发表的当下评价;二是对写作行为进行的反思性评论,这些反思性评论或者说明了选择所叙之事的理由,或者是对所叙之事进行评论,或者是进行自我批评,或者是评价写作的难度,将写作过程作为同时性、插入性的内容来叙述,从而将作品的完成过程变得透明。这些叙述者评论使过往被回忆者“我”当下的观点所打断,从而将焦点从“陷入过往”变成了“对回忆的分析”。比如叙述者“我”对惨死于纳粹毒气室的姑婆有这样一段评论:“早已遇害的她代表了与父母一代的距离,我无法带着感动去回忆她和那位舅舅。同时有一件事令我惊奇,那就是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对于这位被毒气毒死的罗莎姨妈——那个当她发现我把早餐热可可倒到水槽里时惩罚我的女人——只剩下愤怒。”(12-13)
因此,《继》中的叙事顺序并非按照事件顺序、而是按照叙述者的思维来安排的。换句话说,事件的选择和安排都受到了回忆者“我”的写作思维的强烈影响。叙述者的评论一再打断叙事层面,或者说,这些评论销蚀了事件之间时间上的因果联系,而是通过题材上或形式上的相似或对立来建立起一种非线性的逻辑关联。这一逻辑关联使时间上彼此分离的事件具有了同时性,构成了“与连续性和因果性相抗衡的均势力量”,从而打破了传统自传文学的时序定势。
二
与克吕格自传中的叙述者不同,《迸》中的叙述者创造了一种将当下与过往——或者说作为第一叙事的注释层与回顾叙事的叙事层——分隔开的个人记忆的叙事策略,并意图将这种分隔明确表达出来:在《迸》中,每一章的第一节都以“以往作为当下”为序言,从记忆理论的角度对“以往”、“当下”和“回忆”等关键词进行诗学阐发和反思,可以说是对“当下集体记忆准则之外的个人回忆的辩护词”。在这三节序言中,叙述者从隐蔽的位置显现出来现身说法,直接面对读者阐发他的回忆策略。在其他章节中,叙述者则完全隐退到主人公背后,以主人公的视角叙事。也就是说,在其他章节中,都是异故事叙述者通过主人公约翰的视角对事件进行内聚焦。
过往的图景应该只代表其自身,不应该为当下的信息所推动或者为事后的知识所覆盖,应该允许这些过往的回忆保持其原状。对于这一问题,马丁·瓦尔泽借小说叙述者之口这样说:“以往会不喜欢这样,要是我打算支配它。我越是直接地接近它,我就越清楚地碰不到以往,遭遇的却是眼下正在召唤我的这个主题,去探访以往。经常缺少让一个人回溯过去的辩解。人们寻找让人能够辩解自己就是自己的理由。”这段引文中最后提到的回忆与辩解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明晰了两部作品中叙述视角的不同。《迸》以生活在纳粹统治下、但未受其迫害的男孩的视角讲述了1933到1945年间发生在一个偏僻德国小镇上的事情,就这一点而言,《迸》与《继》截然不同。克吕格的叙述者将对童年回憶的抵抗作为问题提出来并加以论述,因为其与幸存者后来获得的知识无法调和;同样地,瓦尔泽也认为应该使童年回忆远离事后获得的知识,因为后者将所有1933年之后的童年都马上打上“第三帝国时期的童年”这样一个标签,从而使过往屈从于当下的主流观念而失去真实性和客观性。瓦尔泽的叙述者倡导的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或者说不言自明的回忆。他希望“以往有一个我们无法掌握的在场……理想的目标:对以往的没有兴趣的兴趣。它会似乎是自动地朝我们走来。”
事实上,在名为“以往作为当下”的三节内容中,叙述者“我”并没有做到将当下与过往分开,而是在阐述过往“无法从当下中获取”的同时插入了对过往的讲述,这一点又和《继》有几分相似之处,即并非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而是按照叙述者的思维来安排叙事顺序。当然,为了明确将当下与过往分开这一叙事理念,《迸》中的叙述者在其他章节中很快消失不见,使记忆如一汪“迸涌的流泉”自然呈现,“自己来到纸上”,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来讲述小说主人公约翰的童年,追求热奈特所谓的“完整倒叙”,以突显童年和青少年约翰的成长和发展轨迹。
三
保罗·利科曾断言:“包含自传在内的一切叙述最终都是当下叙事。”不管是当下的心境、评论、知识和信息与过往的回忆交织在一起的《继》,还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回顾叙事层的《迸》,虽然从叙事形式和特点来看各不相同,但都无法抹煞掉其叙事的当下性。在过去的“我”与当下的“我”之间,横亘着一条时间长河。年过花甲的叙述者和旁观者站在长河的此端,回望彼时曾经的那个孩童与少年。“回想中的往事已被抽去了当初的情绪, 只剩下了外壳。此刻蕴含其中的情绪是我现在的情绪。”回忆绝不仅仅是为了单纯再现过往的图景,“记忆或想起并不单纯是过去的再现,它拥有忘却和写入两方面”。这里所说的“忘却”既包括因时间久远而自然从记忆中消失的生理学意义上的“忘却”,也包括为了服务于当下的写作目的而有意“屏蔽”掉的过往,亦即德里达所说的“对现在之所谓先前在场的引证”——一“引”一“证”无疑道出了个人主体记忆对于回忆内容的主观选择性。
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A·科瑟在写给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的导论中,曾明确指出“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的,因此,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哈布瓦赫无疑是第一个强调这一点的社会学家。”可以想见,由个人记忆升华和汇集而成的集体记忆自然也离不开当下的影响和烙印。“过去是一种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他认为,在每个历史时期分别体现出来的对过去的各种看法,都是由现在的信仰、兴趣、愿望形塑的。”因此,无论是个人主体记忆还是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都立足于当下,为当下所掌控。诚如学者徐贲所言:“人们如何构建和叙述过去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回忆是为现刻的需要服务的。”
参考文献:
[1]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 [法]热拉尔·热奈特,王文融译:《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 徐贲:《文化批评的记忆和遗忘》,《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Andrea Krau?茁:Dialog und Worterbaum.Geschichtskonstruktionen in Ruth Klügers,weiter leben.Eine Jugend“und Martin Walsers,Ein springender Brunnen”[J].In: Barbara Be?茁lich/Olaf Hildebrand/Katharina Gr tz(Hg.):Wende des Erinnerns? Geschichtskonstruktionen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nach 1989.Berlin:Schmidt 2006, P.69-85.
[5] Barbara Be?茁lich:Unzuverl ssiges Erz hlen im Dienst der Erinnerung.
Perspektiven auf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bei Maxim Biller,Marcel Beyer und Martin Walser [J].In:Barbara Be lich,Katharina Gr tz,Olaf Hildebrand(Hg.):Wende des Erinnerns?Geschichtskonstruktionen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nach 1989,Erich Schmidt Verlag GmbH,Berlin,2006,P.35-52.
[6] Barbara Sützl:Die literarische Konstruktion von Erinnerung in Ruth Klügers weiter leben und Jorge Semprúns L criture ou la Vie[D].Universit t Wien,2013.
[7] Michael Basseler/Dorothee Birke:Mimesis des Erinnerns [J].In:Erll Astrid/ Ansgar Nünning(Hg.):Ged chtniskonzepte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Berlin:de Gruyter,2005.
(趙叶莹,中国政法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天津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