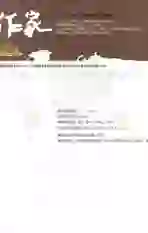失去女人的男人们
2015-05-30村上春树
午夜1点多,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唤醒。午夜里的电话铃声总是很急迫、刺耳,听起来好像有人用无比粗大的金属器械要砸碎这个世界似的。作为人类的一员,我必须予以阻止。于是,起身下床,走进客厅拿起了听筒。
耳旁传来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他告诉我:“一个女人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声音低沉的男人就是她的老公。至少他这样自诩。接着他又说:“妻子在上周三自杀了。其它暂且不说,首先应把这消息通知给你”。“其它暂且不说”,在我听来,他的语气没有夹带一丝感情,像电文一样。词汇与词汇之间几乎没有间隔,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通知、一个没有修饰的客观事实、一个终止符。
我是怎样安慰他的呢?的确是说了什么,但回忆不起来了。总之,接下来彼此沉默了好久。这沉默如同两人相对,窥探着马路当中裂开的深洞时屏息无语一样。后来,对方什么也没说就挂断了电话,像把易碎的美术品轻轻地放在地上一样。我穿着白汗衫和齐腿短裤,握着话筒呆立在那里,一脸茫然。
他是怎么知道我的?我无从知晓。难道是她把我作为自己的“前男友”跟丈夫说了吗。他是什么目的?他是如何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公众电话薄上没有)?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她丈夫特意给我打电话,非要把妻子死亡的消息告知我呢?她根本不会在遗书中做过那样的交代——把自己的死讯通知我——。因为我们交往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分手后也没再见过面,甚至连电话联系都没有过。
唉,算了,随他便吧!但问题是他没给我任何解释。他首先想到把妻子自杀的消息告诉我,于是又设法从什么地方搞到了我的家庭电话号码,但又不想告诉我过多的详情。他似乎有意而为之,把我置于知道和不知道之间。究竟为什么呢?难道是为了让我想起一些什么事情吗?
比如,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情?
我毫无头绪,思考只会增加疑问数量符罢了,像小孩在画本上随意按橡皮图章一样。
在这样状态下,我目前一片茫然。她为什么自杀、用什么方式自绝生命,即使想要了解一下情况,也无法查询。因为不知道她居住何处,其他情况更一无所知,甚至连她结婚的事也不知道。当然也不知道她结婚后随婆家姓啥(男子在电话里没说姓什么)(日本女性出嫁后,一般要改随丈夫家姓氏。——译者注)。结婚多久了?有没有孩子?有几个孩子?
不过,还是相信她丈夫对我说的是真的,我丝毫没有怀疑。她和我分手后,在接下去的人生中,(大概)遇到了如意郎君,并与其结婚。再后来,上周三因为某个理由,用一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它暂且不说”这句话蕴含着他与死者生前关联密切。在深夜的静寂中,我听出了他们生前相处的密切关系,也看到了二人间紧绷着的一条纽带,闪耀着熠熠光辉。从这个意义上讲,——暂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有意——在半夜1点多种打来电话,对他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如果是中午1点钟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了。
我终于放下听筒回到床上,此时妻子也醒了。
“谁的电话?谁死了?”妻子问。
“谁也没死。打错电话了。”我拉长语气,故作困倦状。
但是,她当然不相信我说的话。因为我的语气中夹杂着一种对死者的伤感。从刚刚去世的人那里带来的冲击,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这种冲击会变成微微的震颤,通过电话线传导,改变音频,让世界与震颤同步。然而,妻子没再过多地说什么。我们躺在夜幕下,在静谧中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如此说来,在我交往过的女性中,她是第三个走上自杀道路的人。当然,不用细想也知道这是多么高的致死率啊。真是难以置信!因为我的女性朋友并没有那么多。三个人都那么年轻,为什么要相继结束自己的生命呢,为什么非死不可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常想,不是我的错就好,与我无关就好,或者在她们想象中没把我当做目击者或记录者就好。这种想法发自肺腑。怎么说好呢,她——第三个自杀者(没有名字不方便,所以暂称作M)——无论怎么想,都不是那种会选择自杀的类型。因为在M周围总是不乏世界各地身强力壮的船员们追随着她,宠爱着她。
M是个什么人物,我们何时何地相识,又做过什么,恕我无法加以具体的描述。非常抱歉,如果公开那些事情,现实生活中就会出现很多麻烦,恐怕还会殃及到身边活着的人。所以,就我来说,在这里只能写出来的是,很早以前我们俩有过短暂而甜蜜的一段往事,但后来好合好散了。
说实话,我一直认为M是我十四岁时交往的那个女孩。尽管与实际有所出入,但我还是有这样的希望。十四岁的时候,我们在中学教室里。没错,是生物课。菊石类啦、腔棘鱼啦,大概谈论这类话题。她是我的同桌。我常借口说“不好意思,忘记带橡皮擦了,你有多余的话,能借用一下吗?”,她便把自己的橡皮擦切成两半,把另一半递给了我,还对我莞尔一笑。我于是瞬间就坠入了爱河。当时我认定,她是我迄今为止所遇见的女孩中最美丽的女孩。我希望在心中留住她的美丽,我们就这样在教室里有了第一次约会。菊石类化石啦、腔棘鱼化石啦,这类话题悄悄地成为我们之间的纽带和媒介。想想看,世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十四岁的我,身体健壮,像刚出炉的某铸件一样。每当和煦的西风吹来,我的下体就会自然勃起。总而言之,我正值那个年龄。这不是她的错,她没有撩拨我。她凌驾在所有西风之上。不,不单单是西风,她的美艷几乎使从任何方位吹来的所有风儿都会甘拜下风。在如此美貌的少女面前,怎能不令人心生杂念而自然勃起呢。遇到让我如此怦然心动的女生还是生来第一次。
我觉得这是我和M的初恋。我认为事情就是这样巧合,我十四岁,她也十四岁。尽管实际年龄有些出入,但年龄不是问题,重要的是我们的相逢是命中注定的。
然而,好景不长。M突然从我的眼前消失了,不知去向。好像是我把M看丢了,怎么也找不到。就一转眼的功夫,她就从我眼前走丢了。刚才还在身边,可一转身却发现她不在了。大概被哪个帅气的船员骗到船上,带到马赛或象牙海岸去了吧。我陷入了失望的深渊,失望之深超过他们所有航行过的深海,也超过所有大乌贼鱼、所有海龟潜入的深海。我强烈地对我这个人讨厌起来,变得不敢相信任何事情。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我是那样地喜欢M,那样地深爱着她,那样地需要她,却偏偏……。我怎么不小心把她看丢了呢!
退一步来想,我感到M自从我眼前消失后,她便无处不在、随处可见了。她存在于各种场合、各种时刻、各类人群之中。我深知这一点。我把那半块橡皮擦放入塑料袋里,经常带在身边,像拿着一个护身符,一个测量方向的指南针。只要它在口袋里,总有一天可以在这个世上某个地方找到M。对此深信不疑。她只不过是被深谙世故的船员的那些甜言蜜语所欺骗,坐上一艘巨轮,被带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罢了。她是一个容易相信别人的善良女孩。因为她会毫不犹豫地把一块崭新的橡皮擦切分成两半,然后把另一半送给他人。
我想尽办法在各种场所,从不同人的口中捕获到她的一些蛛丝马迹。但只是一些零碎的蛛丝马迹而已,收集再多也白搭。她的核心信息如同海市蜃楼一样,始终无法触及到。我不停地追逐着,马不停蹄地从一个地方追到另一个地方。这些零星的蛛丝马迹像天边的地平线,亦如两条平行的轨道。我追到印度的孟买、南非的开普敦、冰岛的雷克雅未克,甚至到了巴哈马。我寻遍了有海港的所有城市。但当我追寻到那里时,她就销声匿迹了。凌乱的床上还留有她的微微体温,她的那条印有浪花旋涡图案的围巾还搭在椅子背上,没读完的书就那样扣在桌子上,洗手间里还晾着没有干透的长筒袜。但她已经不在了。一定是全世界机敏的船员们都嗅出了我的气息,在我赶到之前迅速地把她带走,并藏匿起来。当然,此时我不再是十四岁了。我皮肤晒得更加黝黑黑的,身体更加强壮,胡须也浓密起来,可以分辨出暗喻和明喻的不同。不过,我身体的一部分没有变化,还是十四岁。内在的一部分永远处在十四岁的我,耐心地期待着和煦的西风来抚摸我纯洁无垢的下体。
在那和煦的西风吹过的地方,一定有M。
这就是我心中的M。
一个不会在一个地方过安逸生活的女人。
但也不属于自绝生命的那类女人。
我在这里究竟想要说什么呢?这一点自己都不清楚。我大概是要写出非事实的一种本质吧。但是,写出非事实的那种本质,犹如在月亮的背阴面与人幽会一样,周围漆黑一片,看不到目标,而且广袤无边。总之,我是想说,M就是我十四岁时所爱慕不已的那种女人。不过,我和她实际坠入爱河却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的事。那时她(很遗憾)已经不是十四岁了。我们错过了相识相遇的时机,好像弄错了约会的日期一样。时间和地点是对的,只是日期弄错了。
在M的心里依然住守着一个十四岁少女。那个少女作为一个整体——绝不是某一部分——存在于她的心中。如果凝目仔细观察,便可隐约管窥到在M心中活动的那个少女的身姿。我们睡在一起时,她在我的臂弯里时而变得衰老难耐,时而又是羞花闭月的美少女。她如此任性,经常在自己的时空中任意往来穿梭。我很喜欢她的任性。那时,我便尽情地把她紧紧地揽在怀中,甚至弄疼了她。也许是我用力有些大了吧。不过,是我故意那样做的,因为我真的不舍得让那个任性的她离开我。
当然,再次失去她的时刻还是到来了。当时的情况是,整个世界的船员都对她垂涎欲滴,伺机下手,我一个人根本无法守护她。谁都有走神儿或打盹儿的时候嘛。我要睡觉吧,要去洗手间吧,要清洁浴缸吧,有时会切圆葱吧,摘扁豆吧,有时还要检查汽车轮胎的胎压吧。就这样,我们分手了。或许说是她离我而去。在这过程中,始终有船员的影子相随左右。当然,船员的影子是单身,其浓密而自律,宛如顺着公寓墙壁轻盈敏捷爬上来一样。浴缸、圆葱、气压都不过是影子撒下的隐喻碎片而已,像一颗颗散落的图钉。
她走了。那时,我陷入了何等的深渊,又是多么地苦恼,这些肯定无人理解吧。不,根本就不会理解。因为那些苦恼与消沉几乎连我自己都无法回想起来了。我到底有多苦恼,到底有多心痛?在这世上,如果有一台能简单、准确地测量悲伤的仪器就好了,可以转换成数字留存下来。仪器的大小,正好拿在手掌上就太完美了。每次测量胎压时,我总是这样想。
最终,她还是死了。午夜时分的电话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尽管她死去的地点、方式、理由和目的我都无从知晓。总而言之,是M自己决心要结束生命并实施自裁的。她(恐怕)静静地告别了这个现实世界。即使动用全世界的船员,用尽所有的动人的甜言蜜语,把M从深不见底的黄泉下拯救出来——或诱拐回来——都已不再可能。在深夜,如果侧耳仔细倾听,你也一定能在远方听到船员们悼念她的哀歌吧。
我感觉到,随着她的死去,十四岁时的我也将永远随之消失了。就像棒球队的球衣后背号码被确定为永久空号一样,十四岁这一数字将从我的人生中被彻底根除了,然后又被放入某个固若金汤的保险箱中,加上结构复杂的密码锁,沉入海底。那保险箱恐怕十亿年后也不会被打开吧。菊石和腔棘鱼之类的化石静默地守候着它,美妙绝伦的西风也已戛然而止。全世界的船员们都在悼念她的死去,情真意切。世界上船员的情敌们也一样处在悲痛之中。
当我得知M的死讯时,便感到了自己是这个世界上第二孤独的男人。
这个世界上第一孤独的男人肯定是她的丈夫。我把那个席位留给他,尽管我不清楚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年龄有多大?在干什么?这些我都一概不知。关于他,我所知道的仅有一点——声音低沉。这个声音低沉的男人没有告诉我任何有关他的具体事情。他是船员?还是船員的情敌?如果是后者的话,他则成了我的同病相怜者之一。如果是前者的话……,即便如此,我也会同情他。我想最好能为他做些什么……。但我根本就无法靠近她曾经的丈夫。不知道他叫什么,也不知道他的住所。或许他已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总之,他是世界上最孤独的男人。在散步的路上,我坐在独角兽像的前面(在我经常散步的路上有一个公园,里面建有独角兽像),常常一边望着湿冷的喷泉,一边思忖着那个男人。而且,按照我的思维方式,在头脑中想象着世界上最孤独的人是怎样的一种状况。现在,我已十分清楚了世界上第二孤独的人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但还不清楚世界上最孤独的人是怎么回事。在世界上第一孤独和第二孤独之间存在着一条很深的沟壑。大概是这样的,这条沟壑不仅有深度,还有令人生畏的宽度,连鸟儿都无法飞越到对面去。因体力耗尽飞到沟壑的中间就坠落下去的飞鸟的骨骸,在沟壑的底部堆起一座高高的山峰。
有一天,突然你也成了一个失去女人的男人。那一天来得极其突然,没有一丝的提示和预告,也没有心理感应或预感,更没有敲门和在门前故意咳嗽一下。在一个拐角处转过弯来,你便已经转世于另一个世界。尽管你知道是这样,但已经无法后退了。一旦转过拐角,那里便成了对你而言唯一的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你就被称为“失去女人的男人们”,并且,这种刻薄的复数形式始终与你相随相伴。
失去女人的男人们是多么郁闷、多么痛苦呢,只有他们自己清楚:失去了心仪美貌的西风;十四岁被永远地——十亿年大概近似于‘永远这个时间概念吧——夺走了;在远方聆听船员们痛苦忧伤的哀歌;伴随菊石类和腔棘鱼之类的化石一起沉入黑暗的海底;午夜1点后给某家打电话或接到电话;在不确切的地点与素未谋面的人相约;一边测胎压一边在干巴巴的马路上抹眼泪儿。
总之,我在独角兽像前,祈祷他有一天能重新振作起来。也祈祷他能把真正重要的事情要牢记心间,——我们偶尔会把它称为“本质”——,而忘掉其他的一些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我甚至希望他,永远忘却那些已经忘记了事情。这是发自内心的祈祷。我是不是很了不起!在这个世界上第二孤独的男人为世界上最孤独的(未曾谋面过)男人担心,为他祈祷。
不过,他为什么特意打电话给我?在这里绝没有责备他的意思,我只在内心深处抱有这样单纯的疑问而已,一直持续至今。他是怎么知道我的?为什么那么在意我?答案或许很简单,恐怕是M把我或我的事情跟他的丈夫讲了。我只能想到这些。但究竟她向丈夫讲了我的哪些事情,我也无从知晓。究竟在我的身上发生了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的事情,作为曾经的恋人,她需要(面对丈夫,特意)讲述出来呢?这些是否与她的死有重大关联呢?我的存在是否给她的死亡蒙上了某种不祥阴影?或许,M向丈夫说了我的性器长得非常好看。正午刚过,她曾经在床上仔细观赏过我的阴茎,好像在把玩一件雕刻在印度王冠上的玉器一样,爱不释手。“形状太棒了!”她说。实际如何,我并不太清楚……。
大概是源于这个原因,M的丈夫才给我打来电话吧?为了对我阴茎的形状表达敬意,不得不在深夜1点过后打电话。开玩笑,根本不会的。再说,我的阴茎无论怎么看也不是那种出类拔群之物,和他人别无二致。我回想一下,很早以前我就怀疑M的审美眼光,她具有一种与其他人截然不同的奇妙的价值观。
(归根到底,这只是我个人的想象)大概她把自己在中学教室里分给我半块橡皮擦的事情告诉了她丈夫了。虽然这话没有其它特别意思,更没有恶意,只是极其正常的小小的一段往事而已。但很显然,她丈夫听了此话,却心生醋意,妒火中烧。假使M与两辆大巴的强壮的船员交往过,相比之下,她丈夫对于能得到半块橡皮擦的我的妒忌程度要强烈得多。这不是明摆着道理嘛,两辆大巴车的船员又算得了什么!总而言之,当时我和M都是十四岁,就拿我来说,正值青春萌动的年龄,稍有异性接触就会勃起。把新橡皮擦切成两半分给这样的青春少年,那会形成一股巨大的能量,就好像把一排搖摇欲坠的仓房卷入巨型龙卷风之中。
从那以后,每当我路过独角兽像前,都会在那里坐一会儿,思忖着失去女人的男人们。为什么一定是在那里?又为什么是独角兽呢?也许那个独角兽也是失去女人的男人中的一员吧。因为迄今为止我未曾看到过出双入对的独角兽。
他——可以肯定——总是孑然一身,把一只锐角气势如虹地顶向天空。也许失去女人的男人们应该把它作为代表,象征着我们所承载的孤独。也许这些男人在胸前和帽子上都戴上独角兽状的徽章,静悄悄地走在世界各地的马路上,没有进行曲,没有旗帜,没有飞扬的彩花筒。或许……。(我对‘或许这个词汇使用过度了吧。或许)
成为失去女人的男人中的一员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你先深深地爱上一个女人,然后那女人离你而去,消失在一个地方就可行了。绝大多数情况(如您所知)带着那女人离开的人都是情场高手的船员。他们用甜言蜜语诱骗女人,然后迅速地把她带到马赛或象牙海岸之类的地方。对此我们却无可奈何。还有,与船员毫不相干,女人们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对此也束手无策,甚至连船员们也无计可施。
不管怎样,你就这样成了失去女人的男人。这只是瞬间的事儿。一旦成了那样的男人,其孤独的色彩就会深深地渗入到你的体内,犹如红酒洒落在浅色调的地毯上而留下的渍迹一样。即使你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最专业的家政学知识,要清除那些渍迹恐怕也绝非是件易事。那色调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淡,但作为渍迹将永远定格在那里,不会消失,直至你的生命走到尽头。那污渍拥有它应有的存在资格,有时甚至还有公开的发言权。你只能随着污渍颜色的慢慢褪变,伴随着那些多重意义的图案共度余生。
在那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与现实世界不一样。音响不一样,喉咙干渴的感觉不一样,胡须的长相不一样,星巴克服务员的态度不一样,克里夫德·布朗(1)的小号独奏听起来也不一样,地铁车门的开关不一样,就连从表参道步行到青山一丁目的距离也明显不同。即使你后来又遇到了另一位女性,而且她再出色(不,越是出色的女性),你也会从遇到她的那一瞬间就开始思考失去她以后的情形了。船员们的故弄玄虚的身影、他们口中的外语(希腊语?爱沙尼亚语?菲律宾语?)都会使你感到不安。世界上所有的异国情调的海港名称让你闻而却步。原因是你已经知道了成为失去女人的男人们意味着什么。你是浅色的波斯湾地毯,那么孤独就是那块永远清除不掉的、法国波尔多红酒(2)的污渍。就这样,孤独来自法国,伤痛来自中东。对于失去女人的男人们来说,世界是个辽阔并充满悲痛的混合空间,完全就是月亮背面的那片世界。
我和M交往大约两年左右,时间并不算很长。但却是沉重的两年。两年时间,既可以说成短暂的两年,又可以说成度过了漫长的两年之久。当然,由于看法不同,对时间长短的感受自然也就迥然不同。虽说交往两年,但实际上每月才见面二、三次。她有她的事情,我也有我的事情。而且,很遗憾,我们那时已不再是十四岁了。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最终断送了我们的交往,尽管我紧紧地拥抱她,不让她离开。船员的浓密的阴影不停地撒下尖尖的隐喻图钉。
关于M,至今我还记忆犹新的是,她很喜欢“电梯音乐”。常常回荡在电梯里的那种音乐——如,帕西费斯(3)、曼托瓦尼(4)、雷蒙·勒菲夫(5)、法兰克·查克斯菲尔德(6)、弗朗西斯·莱(7)、101管弦乐(8)、保罗·莫里哀(9)、比利.沃恩(10)等类型的音乐。她天生就喜欢这些(用我的话来说)健康有益的音乐。流畅舒展的弦乐合奏,丝丝柔情沁人心扉的木管乐,装有弱音器的金管音乐,使心灵愉悦放松的竖琴的弦声。还有,那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旋律、像甜点一样入口即化的和声、余音袅袅的回声,更让人如醉如痴。
我独自一人开车时候,经常播放摇滚乐或蓝调音乐布鲁斯。比如,迪雷克&德米诺斯(Derek and the Dominos)乐队(11)的专辑、奥蒂斯·雷丁(12)专辑、大门乐队(13)专辑等等。不过,M和我在一起时绝对不让我播放,她经常会在一个纸袋内装入一摞儿类似电梯内播放的音乐磁带带来,一盘接一盘地播放。在我们漫无目的地地驱车兜风的整个过程中,她都伴随着弗朗西斯·莱的《白色的恋人》,轻轻地蠕动着嘴唇,那是一对涂着淡雅口红的水样性感的美唇。她大约有一万盒电梯音乐磁带。而且饱有世上所有无罪音乐方面的广博的知识,几乎可以开一家电梯音乐博物馆。
我们做爱时也是如此,音响里一直播放着电梯音乐。不知道有多少次,我一边搂抱着她,一边聆听着帕西费斯的《夏日之恋》。虽然有些难以启齿,但不得不说,至今我仍然一听到这支曲子,就会感到性亢奋,呼吸有些加快,脸颊发烫。一听到帕西费斯的《夏日之恋》前奏就会感到性亢奋的男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之外恐怕再无二人了吧。不,也许他的丈夫也会这样吧。有关空间话题在此不表,过会儿再说。这样重新更正一下就准确了:听到帕西费斯的《夏日之恋》前奏就会感到性亢奋的男人,在这个世界上大概(算上我)就两个人吧。
空间的话题
“我喜欢这类音乐。”有一次M对我说:“总的来说,就是因为空间的问题”。
“空间的问题?”
“这样说吧,当我陶醉在这类音乐之时,就会觉得自己处在一片什么都没有又格外宽敞的空间里。那个空间太大了,没有任何间隔。没有墙壁,没有天花板。我在那里我可以什么都不想,不用讲话,不用做任何事情,只是身处那里就好。只需闭上眼睛,全身心地沉浸在美妙的弦乐之中就好。这样,没有头痛,没有寒冷症,也没有月经和排卵期。那里的一切都是美轮美奂,放松安逸,气氛和谐。没有人强迫你做任何一件勉强之事。”
“像在天堂上一样?”
“是的。”M说,“我想,天堂里的背景音乐也肯定播放着帕西费斯的音乐吧。亲,你能再抚摸一下我的后背吗?”
“当然啦,乐意效劳。”
“你可真擅长抚摸后背啊,太舒服了!”
我总是背着她与亨利·曼西尼(14)相逢。此刻,我的嘴角上便会浮现出一丝窃喜的微笑。
我不仅失去了M,当然也失去了电梯音乐。每当我独自一人驱车行驶在路上时就那樣想。甚至还梦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等信号那一刻,一个不相识的女孩突然拉开我的车门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一言不发,也不看我一眼,直接把《白色的恋人们》磁带插入车内播放器。可是,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过,因为我的车上没有播放磁带的设备。现在,我开车时,总是用ipod听音乐。当然在我的ipod里没有存储弗朗西斯·莱和101管弦乐团的音乐。但存储了街头霸王乐队(15)啦、黑眼豆豆合唱团(16)啦。
失去一个女人的结果就是这样。此外,失去一个女人,有时也意味着失去所有的女人。于是,我们成了失去了女人的男人。于是,我们失去了帕西费斯、弗朗西斯·莱、101管弦乐乐团,失去了菊石类和腔棘鱼化石,当然失去的还有她那性感迷人的后背。当时我曾一边欣赏着亨利·曼西尼指挥的《月亮河》(17),一边随着那舒缓的三拍儿节奏,用手掌尽情地抚摸着M的后背。我的老朋友,等在小河对面的心上人儿……(此句为《月亮河》的歌词。——译者注)。不过,这一切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留在记忆中的,只有那一小块旧橡皮擦和远方传来的船员们的悲伤歌声。当然,还有那尊在喷泉旁孤独地把尖角顶向天空的独角兽。
我想,此时此刻M要是在天堂——或者类似天堂的地方——聆听着《夏日之恋》就好了;要是她仍然沉浸在那个没有间隔、浩瀚飘渺的音乐空间中就好了;最好不要播放杰费逊飞机乐队(18)的音乐(上帝大概不会那样残忍吧。我如此期许)。我心中还期待着,她能时常一边聆听着小提琴弦上飞扬的《夏日之恋》,一边能想起我来。不过,我不要过多的奢求。即使我被遗忘,我也会在心里祈祷M在我不知道的那个地方,与她永不凋谢的电梯音乐共同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作为失去女人的男人们中的一员,我衷心地祝福祈祷着。除此之外,我似乎没有什么能做的了。在此时此刻。或许。
(选自村上春树《失去女人的男人们》,文艺春秋社2014年4月20日第1版)
注释:
(1)克里夫德·布朗(Clifford·Brown):1930年10月生于美国,爵士乐手,擅长小号演奏。1956年6月死于交通事故。——译者注
(2)波尔多(borudoo)红酒:法国南部著名的葡萄酒产地波尔多生产的葡萄酒。——译者注。
(3)帕西费斯(Percy Faith):1908年4月—1976年2月。出生于加拿大的多伦多。他是美国轻音乐编曲家兼乐队指挥。他的乐队是美国著名的轻音乐队。——译者注
(4)曼托瓦尼(Mantovani)1905年11月—1980年3月。生于意大利威尼斯,音乐自幼就是他执着的梦想与追求。1935年创建以弦乐为主的轻音乐乐团。乐团的成立是轻音乐诞生的标志,他被称为“世界轻音乐教父”。——译者注
(5)雷蒙·勒菲夫(Raymond Lefevre):1929年11月—2008年3月。法国的作曲家、编曲家、指挥家、钢琴家。1956年成立了自己的乐队——雷蒙·勒菲夫皇家乐队,他把古典音乐和现代轻音乐的不同特征巧妙地结合,融为一体,曲风浪漫、优雅,充满了法式浪漫情怀。——译者注
(6)法兰克·查克斯菲尔德(Frank Chacksfield):1914年5月-1995年6月。英国的抒情音乐家、指挥家。1953年,他创建了自己的乐队“流行歌手”(The Tunesmiths)。他们在英国和美国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乐队规模不断扩大,加入了弦乐手,成为一支管弦乐团,即弗兰克·查克斯菲尔德乐团。—译者注
(7)弗朗西斯·莱(FrancisLai):1932年4月生于法国。作曲家。——译者注
(8)101管弦乐(101S trings Orchestra):简称为101Strings。101弦乐乐团创建于1957年初,以演奏通俗电影,流行音乐而出名。——译者注
(9)保罗·莫里哀(Paul Mauriat):1925年3月—2006年11月。法国轻音乐大师,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1944年,19岁的保罗开始了通俗乐队的指挥生涯。1965年他组建了自己的乐团,也就是后来成为世界著名三大轻音乐团之一的保罗·莫里哀轻音乐团。——译者注
(10)比利·沃恩(Billy Vaughn)1919年4月——1991年9月。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美国最有名气的流行管弦乐队指挥和流行音乐编曲家。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干净利落地把摇滚歌曲或R&B歌曲改编成主流乐曲。——译者注
(11)迪雷克&德米诺斯(Derek and the Dominos):乐队名称,美国摇滚乐队。男主角是克莱普顿,他是这首歌的演唱者、吉他手及故事主角。——译者注
(12)奥蒂斯·雷丁(Otis Ray Redding,Jr):1941年9月9日—1967年12月10日。是一位知名的美国灵魂乐歌手,作词、作曲。以唱腔中的热情和单曲《坐在湾边的港口》广为人知。——译者注
(13)大门乐队(The Doors):是1965年于洛杉矶成立的美国摇滚乐队,1973年解散。大门乐队由主唱吉姆·莫里森、鍵盘手雷·曼札克、鼓手约翰·丹斯莫和吉他手罗比·克雷格组成,乐风融合了车库摇滚、蓝调与迷幻摇滚。——译者注
(14)亨利·曼西尼(Henry Mancini):1924年4月—1994年6月。男,是美国著名音乐家、指挥家,曾获奥斯卡奖。—译者注
(15)街头霸王(Gorillaz):英国的乐队组合。颓废派。创始于1997年。——译者注
(16)黑眼豆豆(The Black Eyed Peas):是一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嘻哈(Hip-hop)流行音乐团体,融合了灵魂乐、爵士乐与拉丁节奏与现场演唱等多种风格,该组合于2007年取得格莱梅“最佳流行组合大奖”。——译者注
(17)《月亮河》(Moon River):1961年亨利·曼西尼作曲。是电影《第凡内早餐》主题曲。并在当年获奥斯卡奖。——译者注
(18)美国摇滚乐队。成立于1965年,于1972年解散。——译者注
(周晓杰,上海理工大学日语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