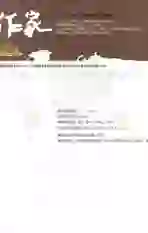从叙事声音角度看《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双重文本性质
2015-05-30曾宪柳
摘要: 1928年2月丁玲女士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环境中,该小说不单被启蒙/权力话语场接纳,还一直被启蒙/男性话语场以固定的话语模式加以解读。《莎菲女士的日记》被不断地误读与其叙事声音的复杂不无关系,本文将从不同的叙事声音角度,来论述小说对男权话语的批判和对女性主体地位的思考,继而阐述《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双重文本的性质。
关键词:叙事声音角度 《莎菲女士的日记》 双重文本性质
《莎菲女士的日记》一经发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茅盾就对该小说定下了基调,在被启蒙话语场接纳的同时,《莎菲女士的日记》还被茅盾以占主流地位的启蒙/男性中心话语的标准进行解读,强调时代、社会的声音,忽視文本真实的女性声音。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后,《莎菲女士的日记》被接受和重视很大程度归结于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时代病征,他们强调该小说的启蒙/男性话语,忽视它作为女性文本的性别意义。只有对《莎菲女士的日记》进行深入的解析后,我们才能发现其蕴含的女性强烈的个人意志、对男权话语的质疑、对性爱的狂热渴望,而这些长期被忽视和任意解读。
一
1927年秋,丁玲写了第一篇小说《梦珂》寄往《小说月报》,得到编者叶圣陶的赏识,发表在当年的12月号。同年冬天她又创作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她以小说《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登上文坛,即引起轰动,报刊上惊呼“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莎菲女士的日记》深刻地表现了五四运动后觉醒的知识青年的痛苦与追求,也使她在文坛崭露头角。《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的成名作,一经发表,便影响很大,它以日记的形式,写了莎菲这样一个患着肺病的知识女性,南北奔波,不是为了事业、为了读书,而只是为了追求“真的爱情”。她不爱虔诚的求爱者苇弟,但却被仪表漂亮的南洋小开凌吉士所迷住。当她看清了凌吉士潇洒的外表下掩盖着的丑恶灵魂的时候,她痛苦已极,那只不过是她禁不住凌吉士外表的诱惑,陷入感情泥潭而不能自拔,最后她踢开了他,但却又绝望地发出“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的哀叹小说以日记的形式,运用心理描写的手法,细腻地反映出那个时代女青年的苦闷、空虚、渺茫的心情和病态的呻吟。由于这种感伤主义情调契合了当时人们的心态,所以这篇小说在当时拥有许多读者。
作为独特的叙事形式,日记体、书信体能很好地揭示作者的叙述声音。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以下简称〈日记〉)采用了日记体的叙事形式,以典型的第一人称进行回顾性叙述。在三十三则日记中,作者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鲜明生动、真切感人地讲述给读者,叙述风格直白连贯,挣脱了传统权威话语对女性声音的禁锢。《日记》的主人翁莎菲迷恋凌吉士,她欣赏凌吉士的美,是她欲望的对象,也表明了女性叙事声音的觉醒。在传统文学作品中,女性一直被表述、被窥视、被欲望,一直处于从属状态,不能或很少发出自身的声音。而《日记》颠覆了这种现状,话语权掌握在女性手里,男性处于从属状态,被窥视、被判断。长久以来,男权的主导地位,导致女性人性和人权的双重失落。不仅自然本能、肉体欲望受到排挤和禁锢,正常权力也被扭曲和压制。“五四”运动使得女性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女性人性和人权渴望同男人一样受到社会的重视。
在最后,由于苇弟、凌吉士不能满足莎菲的需要,莎菲拒绝了他们,借以追求自我身份认同,摆脱“沿着肉体开辟出的道路,走向婚姻或死亡”的女性宿命。男权话语在当时的社会上还处于主导地位,女性声音细小甚至无声,很容易被遮挡被忽略,在话语权上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只能被动地接受。莎菲对苇弟、凌吉士的拒绝,实际上是作者拒绝在话语权上保持沉默、被动的形象,是作者对女性没有话语权现象的呐喊和控诉,以期重写或改写女性自我身份,最终建立起与男性平等的话语权。女人翁莎菲希望在自己死之前做一些值得慰藉的事情,以使自己的人生每天快快乐乐的,尽量避免遗憾。在文中,作者通过莎菲发出的“缺乏果断而犹豫不决”“鸡毛蒜皮,不得要领”“没有实质意义的”“说人闲话,言之无物”重新编码的女性声音,表现了作者在追求“有力度、有权威感、有效率、直率粗狂”的女性声音时胆识和勇气,也表明了作者对女性尊严和话语权的追求。除了人类早期的母系氏族,语言一直是以男性为中心的,长时间以来男性牢牢地把握着话语权,某种程度来看,独有话语权是男权社会的重要特征,女性没有话语权,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女性逐渐进入社会主流发声的文本中,开始撼动甚至试图取代男性的声音。由于《日记》的时代背景,我们知道,关于话语权争夺,女性还处在极不利的地方,而作者借助莎菲的声音来显现现实文化语境中女性躯体和女性声音。莎菲作为文本的女性叙述者,作者尝试冲破权威话语的桎梏,发出自己特有的声音,拒绝依附的礼赞。
二
在男性主导话语权的社会,女性作家很难通过叙事声音把自己作为权威推到前台,人们更愿意听她们讲讲故事。在男性具有权威性、主体性、话语权的社会,叙事声音是女性抗争的最主要的方式,表面上看,《日记》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保障了声音的真实性,文本以记录莎菲发出的声音为主要框架,不断寻求自身声音,在寻找的过程中一步步地增强女性叙述声音的权威性。而《日记》的双重文本体现在莎菲通过叙事声音,不断地在感性的言语上反抗男性话语霸权,却在理智的行动中为男性话语权进行辩解和维护。我们可以从莎菲与苇弟、凌吉士反反复复的交往中受到的折磨和文本中出现的反讽言辞中感受到文本的悖论。这种悖论注定会导致莎菲在思想和行动上左右冲突,最终发出无奈的叹息:“我能告诉人吗,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但我知道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不准许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语言是男性制作的,男性享有语言的操纵权,它强调男性的价值,所以女性作家在使用语言时会不自觉和不可避免地内化男性价值。女性“失语症”的存在是因为男性主导的声音压迫着女性,逐渐丧失叙事的权利。而女权运动的目的就是使广大女性认识到这种状况,强调女性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话语模式应由她们自身制定。而男性象征序列构成的巨大话语场是女权运动道路上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对女性代码的界定已经过社会的认同,女性也早已把这种界定作为自己的思维准则,相对女性身体的解放,思维的解放更加困难,这也是女性叙事声音易产生双重文本的主要原因。自身性意识的觉醒和自身欲望的张扬与莎菲骨子里面的传统行为准则相冲突,无论在行为还是思想上违背传统规约,她马上说自己不是一个正经女人,不配得到苇弟真挚的爱,还希望世人不要像她那样。文本的个性声音无法脱离于总体声音,叙述声音总被淹没于总体的声音中。充斥着大量的冗长的连接词和从句展现的叙事声音,表明了莎菲对传统的反抗并不会付诸行动。尤其是因果从句,比如“虽然”、“但是”,“因为”、“所以”,以及“尽管”等词语运用,表明莎菲一直为自己的行动找客观的理由,揭示出暧昧、犹豫、迷茫、畏缩的心态。莎菲的自我颠覆对文本的起到了根本性的破坏,它阻碍着知识转化为现实的物质,所表达和追求的不过是自我创造的一个影子。文体、语气和价值观是叙事声音的主要内容,而每种声音都有其特有的措辞和语法,但读者所持的态度和叙述者的主题决定了读者对声音的感知。
在所有的美好的幻想破裂后,莎菲流露出最真实的声音:“不准许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莎菲在自己狭小的世界里折磨自己,这也是她的焦虑和狂热造成的。高雅文体和庸常、俗白的口语这两种文本,是莎菲两种状态的写照,前者是对其美好人生的点缀,后者是在幻影破灭后对美好、高雅生活的反讽,突出了莎菲当时的挣扎状态。
三
作为一种个人话语形式,日记受叙者的选择决定着文本的呈现方式。无受叙者的独语形式的呈现方式是私下的,有受叙着的呈现方式是公开的,呈现方式的选择会对叙述者的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产生影响。在最初,莎菲日记的受叙者是蕴姊,蕴姊死后,其日记的文本的呈现方式依然是公开的,这就使《日记》具有了书信体的性质。而书信体小说的修辞框架弱化作者的权威,这既保持了私人话语的幻想,也保持了男性/女性、公开/私下的二元对立。尽管在蕴姊死后,莎菲为了使苇弟理解自己的心,莎菲把日记给“他”看,但却事与愿违,苇弟没能解读莎菲文本的真实意图。《日记》的女性文本与男性读者之间的寓言化遭遇,注定了莎菲梦想不过是一个美好乌托邦,蕴姊的死亡和苇弟的“误读”使得她认识到自己梦想的不可实现。通过《日记》自我呐喊的文本和自我消解的文本,我们知道:作者除了将写作和阅读构成深刻的性别化行为,其作品《日记》的写作方式依然和传统女性一样,属于女性的自我书写,阻碍着女性文本和男权社会的交流,文本落得无人能读无人能知境地,莎菲依然难逃“沉默”的女性宿命。由于局限于私人的圈子,使《日记》叙述声音失去了生命力,某种程度来看,这种文本巩固了男权主义的权威。
《日记》中“镜子“和“肺病”意象的重复出现,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知道不断重复意象其实就是一种隐喻。意象不仅是图像式的重现,也是理智与感情的呈现和不同的观念的联合。例如,文本中关于镜子的描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符号暴力的论述,在莎菲为了寻求自我而逐渐偏离“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和社会规范后,又不得不否定自我的身份,讽刺意味浓厚,隐喻着女性作家不可能在抛弃男性的情况下完成女性欲望的书写,也说明了她们在男性主宰的文学语言寻找自我建构的艰难,甚至将会以失败告终。《日记》对传统制度的批判,并没有瓦解这个制度,而是更加确立了传统制度的权威,甚至与所反对的合谋,最终导致“自我缄默”。拒绝叙事不仅拒绝了公开受叙者,也随即认同了文本的失败。但这还不足以否定《日记》在现当代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上的深远影响,由于其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这一显在话语特征,长期被“五四”收编,被认为是封建礼教的反叛。而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日记》又成了中国现代女性主义叙事的“先声”,说明了《日记》的双重文本具有悖论的性质。
结语
我们能确定的是《日记》不同于“五四”女性作家的文本,它不仅仅是单一的非指向性苦闷的宣泄和女性与自身直接交流的内在激情的宣扬,作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视野也更加的开阔。这种叙事声音,既表现了现实/男权社会意识具有巨大吞噬力的文本,也有关于男权文化语境对女性躯体和声音压制的文本,通过对双重文本的论述,表现了作者在摆脱传统男权话语规范、独立发出自己的声音上做出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申丹:《敘述学与小说文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康正果:《生命的嫁接》,上海三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2年版。
[4]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曾宪柳,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