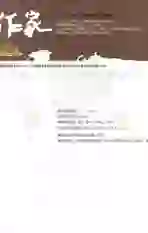地缘伦理: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李约热小说创作研究
2015-05-30李志艳
摘要 李约热是广西壮族作家,目前学术界对其小说创作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在文学地理学视野之下,地理与文学的关系属性贯穿了李约热小说创作的发生学、创作论和价值指向。其小说以最大程度的亲近地理为基本立场并形成地缘本位,以此为基础,在表意结构之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设置、叙事话语和象征结构上,都表征出“接地气”的整体态势。不仅如此,由于李约热将小说控约于冷静的呈现维度,在伦理学之真、善、美在人之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的价值关系中,都显示出丰厚的内涵和形而上学意义,昭示出作为一个地域性、民族性新锐作家的创作能力和旗手本色。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 李约热小说创作
李约热本名吴小刚,系广西壮族作家,自1995年在《三月三》发表第一篇小说《希界》以来,在近二十年的创作时间里,李约热获得了系列荣誉,如第二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最具潜力新人奖、第五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等。张燕玲曾将其定位于“70年代生作家群”,直言“他们富于才情,他们勤于探索,他们以自己的实力再次将广西的作品推到了中国文坛的前沿。”[1]从李约热小说研究现状来看,代表性研究者有贺绍俊、张燕玲、黄伟林、韩颖琦等。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从民族文学谱系、广西文学史、形象学和主题学等方面来进行。这为李约热小说研究打下了基础,也留下了广阔的可发掘空间。是以在文学地理学和伦理学交叉学科视野下,李约热小说创作的本源立场、表意机制、价值意义,都体现出文学创作的可借鉴性和文化上的丰厚意义。
一、地缘本位:李约热小说创作的基本立场与可延展性
文学地理学系基于地理和文学二者关系的文学系列活动研究,曾大兴将其概括为三句话,“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2]。邹建军本位于文本细读,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史及其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地位等方面提出了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文学的地理基础、文学的地理批评、文学的地理性、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意象与人文意象、文学的地理空间、文学的宇宙空间、文学的环境批评、文学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文学地理空间的限定域与扩展域、文学地理批评的人类中心与自然中心。”[3]杨义更是在宏观视野上提出文学地理学研究蕴含着四个重大领域,“一是区域文化类型,二是文化层面剖析,三是族群分布,四是文化空间的转移和流动。”[4]从中不难看出,文学地理学以人文和地理两个板块的运动关系和建构关系为基础,衍生出文学文本内部系统、外部系统、内外系统关系研究,渐次递升为宏观性的相关文化系统研究。而李约热认为自己骨子里还是个农村小孩,与乡土有着无法割裂的天然联系。他试图写出自己看到的真实的乡村[5]。加之以李约热的广西壮族和广西都安作家群身份,这意味着两个基本的事实,一是李约热小说创作的地缘性基本立场,一是运用文学地理学研究李约热小说创作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李约热小说创作的地缘性立场体现在文本故事发生的时空场域和文化语境的清晰性,但并非对现实地缘的简单描摹和复刻,而是具有着自身艺术创作的独特性:第一,以自身经历为基础,在重视审美经验的前提下,形成了单一性地域中心明确突出,却又能涵盖其他地缘场域的文学表现模式。从李约热出版的长篇小说《我是恶人》,中短篇小说集《火里的影子》《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李约热卷》来看,“野马镇”(广西都安)是其小说表现的中心,也包括了江西、广州、湖北一些省份。第二,在李约热小说中,地缘往往构成故事的实在场域、文化背景,以及人物、情节、语言等的影响因素,如《我是恶人》中关于“山洞”中“金坛”的故事,“青果问魂”的故事,都具有明显的广西壮族文化色彩,它形成了李约热小说创作的地域特征和历史厚度。第三,李约热小说创作注重人物与地缘的双重主体性关系,即一方面李约热小说创作深深浸染了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的熏陶与影响,另一方面却又在极力展现人物在现实面前的主体性选择与自我显现。如《青牛》中的“蓝月娇”,《我是恶人》中的“马万良”“黄少烈”不仅能够体现那个具体时代、地缘背景下普遍性的人性需求和文化属性,亦能够折射人物本身的性格心理、行为方式和价值追求。
李约热小说创作对于人与地缘关系的特殊处理,使其小说创作在逻辑上就业已奠定了多维度变化和超越性。第一,紧扣地缘根性,强化现实主义色彩强度和新突变。张燕玲认为李约热等都安作家,“他们的笔下都不同程度地充满了对都安各民族和土地的敬畏、对故土和亲友的温情、对生存困难的疼痛、对城市感觉和乡土经验的把握、对人性复杂性的开掘、对精神灵地的探索。”[6]其中可以看出李约热小说创作是以自身根基于地缘的审美体验为核心,重视文学创作之生命体悟的偶然性与多变性,这在还原作家生命现场的同时,也建构了小说故事发生的实在性与可能性,其小说的现实色彩展现出以地缘为依托的人本中心论。以此为基础,李约热小说创作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政治决定论、经济异化主题和典型化创作原则,而突显出主体感觉性、唯灵论和后现代属性,推动了文学创作现实主义的革新与新变。第二,由于对人本和地缘主体性的强调,李约热小说创作形成了多重对话机制,促生了小说创作的去理性化和多变性。如《火里的影子》中“我姐”内心就交织着“自尊而自卑”的强烈冲突,在长篇小说《我是恶人》中,马万良与黄少烈的无休止缠斗折射出人与人、家庭与家庭、人与社会制度等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使得人与社会的表现都具有高度立体性。而在《戈达尔活在我们中间》却通过“苗红”塑造了一个崇高的艺术理想,在艺术与现实之间建构了话题的敞开性与探索性。是以李约热小说的多重对话机制中充斥着生命本我的狂欢与撕裂、个性与共性的纠葛与嬗变、世俗与崇高的混溶与辩证,奠定了李约热小说创作的纵深感与弹性能力。第三,地缘文化的活动性与超越性。约翰·斯道雷(JohnStorey)认为文化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智慧、精神和美的一个总的发展过程;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表义的实践活动[7]。地理和人之间除了肉体、生理上的直接影响关系外,更多的是来自于以地理为中心的文化板块,但这一切都必须以人为中介、实践途径和意義显现。对此,李约热小说创作所形成的多元地理区域,如《我是恶人》的野马镇,《李壮回家》中的江西鄱阳湖,《戈达尔活在我们中间》的广州市,都意味着地理文化板块的比照与意义互见,昭示了李约热小说创作地缘坚守的另一面是文化属性在文本中的内化与活动范式。在此条件之下,李约热小说创作从单纯的地缘展现中超越出来,走向普泛性与深度性的灵性书写与文化反思。
因此,在文学地理学视野之下,李约热小说创作的地缘本色显而易见,以其为根基,李约热将其延伸为人性探索与文化追问两个基本维度,二者交织一体,互为鉴照,互相推动,形成了地缘—人性—文化抒写的基本模式和延展途径。又加之李约热小说创作对于地缘、人性主体性的推崇与释放,其小说的现实主义色彩便彰显出后现代性的底蕴和先锋作用。
二、接地气:李约热小说的表意结构
李约热的小说创作具有很强的辨识性,谢有顺曾如此评价过李约热的《我是恶人》:“《我是恶人》对现实生活的观察角度独特,对生活的‘变形恰到好处,对复杂人性的挖掘深刻,‘我们可以从广西作家描绘的村镇中看到当代中国南方社会的缩影。”[8]接地气、人本论,再加以独特的视角,构成了李约热小说创作辨识性的主要内涵。不仅如此,李约热强调以自身的生命体悟来感知大千世界,在立足特定地理空间的基础上,探索人性的复杂性与变动性,将文学创作诠释为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发生的过程”[5],显现为“直性言说”的表意方式,它确定了李约热小说创作的基本走向,也表征了其小说意义的生发维度。
首先,接地气:底层人物书写背后的理性显现与意义宽度。人物是小说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虽然在传统、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小说中,对人物塑造的理念所有变化,但都未曾忽视其在小说中的结构性地位与功能。不仅如此,在小说文体学中,故事承载、人物表征的系列描写和行为动作,构建了艺术文本的时空阈限及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而人物的性格心理、价值诉求、行为动作、语言等则提供故事发展的结构要素和动力机制。对于李约热小说创作的此类问题,学术界或称之为“民间的姿态”[9],或称之为“乡村伦理”[10],细细比较起来,都是李约热小说创作“接地气”的不同说法或是论述侧重不同而已。其中更为深刻的是:第一,在艺术发生学原理上,接地气诠释的是艺术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表达了艺术对现实的态度、理解、阐释和探索。李约热的小说创作“不可避免地带着他旧日生活的痕迹”[11],注重对自身在生活履历中所形成的审美经验的直接性传达,艺术是缘于生活的自然发生,是基于生命体悟的直觉性思考。生活提供给艺术发生的可能性、必然性及其变动性的逻辑基石与运动条件。李约热小说创作根植于此,二者在天然亲缘和无限贴近的情形之下,形成了富有无限弹性机制的互文场域与拓展空间。是以,不了解中国、广西乡村,就难以以生命本真的态势走进李约热的小说世界,反过来,理解了李约热的小说,就能触及广西乡村生活的深层底蕴,掌握了中国乡村的滥觞与缩影。第二,接地气显示的是系统的文学活动程序与系统,是地缘对于文学的多维性建构和文学立足于此而昭示的主体性、能动性反应与激变。比如《我是恶人》中的“青果”形象,因为“野马镇”特殊的地理文化和民俗文化状况,又经历了“文革”时期,再加上“青果”自身劳动能力的不足,形成了“青果”既依赖于老婆,又子承父业,视“问魂”为生命至高膜拜的生命观念、经济观念和文化观念。《火里的影子》中“姐姐”出身于单亲家庭和农村家庭,形成了勤劳善良,自强、自尊却又自卑的多重心理,故而在面对同学不遗余力的馈赠与帮助中表现出感激却又抵制的行为状态,最后因为强烈的自尊心与自卑感驱使杀害了自己的同学。在这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塑造中,以地理为中心的系列自然、经济、文化因素控驭着人物性格的形成,但人物性格并不对此决然服从与单方面履行,而是在聆听生命本性的呼喊与指引,在人—地关系中毅然做出属我性抉择,表征出了自然地理、社会文化的多重复合性结构和贴近生活的生命昂扬态势,造成了人性悲剧之后的崇高之美。第三,偏执的生命属性与情节发展动力的主从模式。在李约热小说如《午后苍凉》中,卢秀美爱上了刘竞的表哥,却又在刘竞表哥死去之后立马回归自我,表现出对爱情追求与放弃的毫不犹豫;《这个夜晚野兽出没》中,“我”、韦大光、张放荣、黄云爽等不约而同的跟踪王首功,密查其偷情之事,结果却在其生命性爱的冲击下功败垂成;《涂满油漆的村庄》中加广山为了儿子拍电影迅速的建起了一座涂满油漆的村庄,可是儿子却全然无视亲情和乡村关系,加广山和儿子为此与之决裂而选择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生命的尊严和价值。这些小说故事的起源都可以归之于生活的琐碎现象,但勾连故事的情节序列却是按照生命逻辑来进行,它摈却了生活的世俗伦理道德体系而演绎为偏执性追求与坚守,它与生活世俗逻辑相悖离,形成两条虽有交叉,但却彼此对应、比照的互文体系。故而在此行文中,生命的偏执性越强,则探索生命的本真程度越高,而以此烛照出来的生活现状就越复杂,从而反向的提高了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与探索程度。不仅如此,这些小说往往采用了生命逻辑为主、生活世俗逻辑为辅(为参照)的主从模式,以及人物形象的底层身份,从而形成了底层人物书写就是地缘书写、生活书写、人性书写、文化书写的辩证统一。
其次,在文本直接显现中,接地气还投射于叙事话语之中,从文本的构成来说,包括叙述人话语和故事人话语;从整个社会系统来说,就是文学和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语言学来说,叙事话语就包括语言和叙述,语言是叙述的对象和材料,叙述是语言的呈现方式和制约对象。查尔斯·伯恩斯坦(Charles Bernstein)认为:“语言之于世界,正如身体之于个人;……对语言的存在过于熟悉而忽略了其对世界的价值观和各种事物的建构力。”[12]这意味着李约热小说创作研究不仅要回归一般语言学问题,亦要回归小说叙事学的相关问题。在故事人话语方面,李约热小说紧扣人物身份,实现了人物性格心理、故事情境、地域文化品格、行为倾向展现,以及相应的价值呈现的统一性,如《我是恶人》中黄少烈在儿子黄显达入住马万良家之后的一段话,“那有什么,明天,你把显达的衣服送过去,你要高声地对马万良说,感谢他帮我养一个仔,说得越大声越好。”这段话中在人物命名就显示了当时当地的世俗价值追求,如黄显达;人物与职业身份契合,如黄少烈;小说的反讽意蕴,如黄少烈并不完全以公安身份为当地谋福利,马万良并非传统道德伦理价值的善良之辈。不仅如此,人物话语中“仔”就是当地民族对儿子的特定称谓,是民族文化的体现。深入下去,这段对白还昭示了黄少烈善于攻心的性格心理,并且隐含了其如何对付马万良的行为趋向。在叙述人话语方面,一方面李约热小说创作主要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视角,这种全知模式显示了李约热对于小说的宏观掌控和细节捕捉能力,另一方面,李约热着意于间隔作者与叙述人之间的距离,推进小说由“可读”本文向“可写”文本转化,形成了一种冷漠式,或是白描式的叙述方式,文本的叙述话语显得平实、干净而洗练,更加具有生活质感、叙述人话语和故事人话语的水乳交融。如《马斤的故事》开头如此写道:“一场大雨之后,野马镇就多了一个叫马斤的人。他在野马河边搭了一个棚,打鱼为生。”这段话语中丝毫不露作者痕迹,却在自然行文中皴染出故事发生的地理环境以及生活方式,文笔恬淡却不乏天然之美,同时又赋予了人物一个相对自由的生活场域与生命空间。以上述论证为依据回到语言学一般问题探讨上来,第一,在作者和语言之间,李约热有意抽离语言使用者身份及其限制,努力还原和建构语言原有的生命活性和意义自然显现方式,在价值属性上就标榜了语言的主体属性,在语言工具化的從属性中也就遏制了文学创作单面性的功利目的,实现了文学创作的主体性与自由性。第二,语言的共时性与历史性揭示了其地理缘起、文化体系和社会结构属性与功能,在任何交流语境都要显现其背后的系列关联因素和建构能力。在李约热小说的语言世界里,语言不仅显示了其对小说文体各方面的建构能力,包括叙述方式、人物性格、情节设置和美学风格等的呈现,更揭示出文本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场域活动关系,其相互制约,却又互相促长。
再次,得益于故事、人物形象和叙事话语的接地气,李约热小说创作在平实的行文中,构建了具有相对整体性的象征结构,实现了文本内涵与外延的张力扩大化效果。如《问魂》的结局如此写道:“问魂这种神奇的事情,从此以后在野马镇彻底消失。青果在鸡鸭行摆了个小摊,专门阉鸡。阉割出来的鸡子,他就带回家,炒着吃,炖着吃,吃得红光满面,力气十足。”《欧》的结局是:“第二天梁燕回去了。不久梁燕去找她熟悉的医生韦贸能,她对韦贸能说:‘韦医生,我想把肾摘下来,再换一个新的,行吗?韦医生吃惊地看着她。”《李壮回家》是以李壮的一阵呼喊来结尾:“杨美,我爱你!杨美,我爱你啊!”《永顺牌拖拉机》则在对拖拉机一阵戏谑式的叫骂来收场:“我先骂:拖拉机,我操你妈!兰淑芬说,輪到我了:拖拉机,你这个后娘养的,你上山跌死,下河淹死,走路撞死!随后是刘丽,她说,拖拉机,你不得好死,你不是个男人,你断子绝孙!韦小果放声大笑。”在这些小说描写中,一是它们构成了小说故事和人物行为动作的片段性发生,出现在结尾,系小说写作的完成,起到了小说叙事实践的表征性功能,类似于诗歌意境中的物境层次。二是情感属性,小说以叙述故事来传情达意,显现为事性言说机制,在上述描写中,《问魂》充斥着青果无奈、抑郁和人格转型;《欧》揭示了梁艳对于别人馈赠的难以承受;《李庄回家》则张扬了李壮性之本能在强烈压抑之后狂欢肆意;《永顺牌拖拉机》则昭示了刘丽与陈军婚事不果的情况下,各人的不同心理状态。这些情感表达缘事而发,契合人物身份,符合故事情节发展趋势,入情入理,显现了李约热对小说文本的控制能力和语言魅力。三是对比中的象征结构。李约热小说创作中的象征体系是通过文本中、文本内外的对比性来建构的。在《问魂》中,青果经历了一个问魂师由成功向失败的转化,中间以“文革”为变更中介,结局以“鸡子”(鸡的性器)为意象物,在二重对比关系中,就把小说的内蕴向生命本能和历史的叩问进行了推进。《欧》则传达了生命之轻难以负荷历史之重的哀叹与悲悯。《永顺牌拖拉机》则折射出商业经济所引发的人性裂变与价值观重构的反思。可见李约热善于运用文本中、文本与社会生活的悖立性等为核心来建构极富张力的意义场域,并由此将文本内涵向历史文化、社会生活、人性本真的纵深处拓展。
因此,李约热小说创作在接地气的前提下,寻找地域性、人性和社会历史属性的契合点和关联面,使得故事选取、人物形象塑造和叙事话语包含了地缘色彩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意义。以此为基础,李约热小说创作还善于捕捉人性、故事事件、历史文化语境中隐含的矛盾关系,将此附着于象征结构之中,直接铸造了小说文本表意结构的多义性、纵深度与拓展范域,李约热小说表意结构的接地气就显示出平实而灵动、质朴而深邃、偏执却多元的意义体系。
三、走向形而上:李约热小说创作的伦理价值
关于文学的伦理价值,聂珍钊认为文学本质不仅是审美的艺术,更应该是文学的伦理价值为基础、动机和目的,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13]。文学的伦理问题贯穿于文学的发生学、本体论、创作论、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然而,人们的道德境遇是多元的,人们在面对生活中善与恶、美与丑等各种对立要素时,其价值判断也是多元化的。”[14]伦理道德的判断标准虽是多元化的,但其主要维度是真善美却毋庸置疑。而将其置身于文学地理学视野之下的李约热小说创作之中,伦理价值在“真善美”三个维度上都显示出独特的新锐意义。
首先,真在探索。关于真,首先应该提供三个基本方面的说明:“真之承载者,符合关系和真之制造者——真之承载者所符合的事实或实在。”[15]在文学艺术中,真之承载者是语言的陈述,语言陈述本身是真,真的意义由此而派生,并且指向陈述与陈述对象之间的符合关系。在文学批评中,真就包含语言句式,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大千世界本质规律的描述与探讨。在文学地理学视野下,李约热小说创作之求真意味着在方法论上秉承的是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李约热小说创作对底层书写、接地气的言意结构和都安作家身份就是明证。在求真方式中,作以平面谋求深刻、以片面和琐碎来缀补丰富、以否定来显现肯定等昭示了李约热小说创作的精巧构思与慧眼独具。李约热小说创作的年限还不长,其作品也主要是短、中篇小说,唯有一部长篇小说《我是恶人》,也是由许多短篇、中篇小说组构而成,包括《问魂》《马斤的故事》《欺男》等。也就是说,李约热小说创作并非以宏大视野和宏大叙事来呈现艺术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而是重在于生命断片的发掘、整理与再思考,并与其采用的小说文体一一对应。不仅如此,李约热在小说表现中,让地理、人性和文化深度和丰富内涵浮现于人物、故事常态之中,如《一团金子》《戈达尔生活在我们中间》《郑记刻碑》等就是如此,表现了平面即深刻辩证一体的后现代色彩。就《我是恶人》而言,“恶”是“平庸”[16]的,但却指向人性之否定,它是人性认识的视角和人性发展的动力,也是李约热观察生活、创作艺术的视角和方式,在它附属的不断扬弃的功能中标示出肯定方向,也能对李约热的小说创作生涯提供动力支持和方向引导。在哲学层面上,李约热小说创作整体显现为陈述风格,在其标举地缘本位和接地气言意结构中,语言陈述作为真之承载者和实践者就表现出双重符合属性,并且贯连起李约热小说创作的发生学、动力因素、质料因素、形式因素、目的因素,这在李约热小说文本中不胜枚举。也正是李约热小说这种平静的陈述风格,使真显现于陈述与艺术表象之中,有效的解构了因简单判断与评价所带来的静态可能性,真始终存在,但凸显于动态性的探索之中。
其次,善的敞开性与去定型化。李约热小说的求真态度直接影响了其善恶观,从表现善恶观的视角来说,李约热小说创作具有明显的反常性特征,即李约热直接面对中国当下伦理语境的复杂性,包括中国传统、西方世界,乃至中国当下新生的各种伦理的对话与融合,将作者置身事外,以边缘管窥主流、以细微诉求宏达、以偶然性反思必然性的方式来进入善恶观的探讨。是以,李约热小说创作的着眼点主要是广西农村,甚至野马镇(广西都安),小说人物及其相关故事也是生活中偶然发生系列琐事,而这些小视角、小人物、小故事也无确定的善恶观念,李约热既不盲从中国传统、当代和西方,也不率先自我设定,而是把小说牢牢地控制在呈现这个层面上,尽力凸显小说文本的生命主体性,使其自由地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不断重构自身的艺术生命关联,进而实现善恶观的认知、反思、建构与确认。从表现方式来说,李约热小说具有明显的话题意识和问题限阈,其小说主要以中短篇为主,也更方便其小说形成单篇与具体伦理问题的对应性与探讨的集中性,如《问魂》就是讲生命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生命自我问题;《李庄回家》则是兄弟情感与李壮如何寻找自我的故事,也就是兄弟伦理与自我伦理问题;《戈达尔活在我们中间》则是通过自我、艺术和婚姻生活之间的关系来谈论婚姻伦理与艺术伦理;《永顺牌拖拉机》则主要集中在当代农村婚姻伦理上;《涂满油漆的村庄》则主要阐述血缘伦理;《我是恶人》则相对复杂一些,相当于上述伦理关系的一些集合,但也主要侧重于社会生活的世俗伦理。将这些小说总括起来,亦能发现李约热对于善之伦理问题谈论的全面性,它立足于地缘生活,也就使得这些伦理问题的探讨更具有实体对象性和存在感,促进了善与真的融合与相互促进。从善的探索程度来说,李约热强调小说创作的地缘性和故事的呈现本身,这意味着其小说创作只是冷静的抛出问题话域而无意于下一个绝对性判断,将小说回归于现象本身,在真理与现象的等同中将善之认识、理解和判断留给了读者,作为伦理维度的善也就具有了敞开性与发展程度上的去定型化。
再次,美在重构。在文学艺术中,情感是其本体和生命,而由于艺术形式的赋予,情感在文学艺术中表现为审美与道德两个基本维度并区别于自然情感,“在好的艺术品中,道德情感之所以能够与审美情感融为一体而对立的或隔膜的,是因为它和审美情感一样,都是内在于主体的,出自于直觉的,而非有意的安排。”[17]美产生于审美活动,诉诸于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自由性审美活动,而伦理道德的“同一性”[18]意味着其价值实现也离不开受众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以文学艺术中伦理之美关键在于文本和读者关系的建构。李约热曾说道,现实是不完整的,是以碎片的方式存在的。作家必须小心翼翼地跟在一块现实的碎片后面,小心求证、仔细模仿,并努力去解释它,但结果总是不尽如人意。我把这种求证、模仿堪称一件神秘的、不可言说的事情。他还借用马尔克斯的话,认为小说是用密码写成的现实,希望有一天能编制出自己的密码[19]。李约热的“密码”论其实就是直觉性创作,在作品之美的内涵构造上,体现为将作者的生命感知与觉悟直觉性渗透于作品之中,做到美之感性显现、理性规律和小说陈述的先在性统一;在美的文本呈现上,得益于小说创作立场、小说言意结构的契合,小说之美流溢于文本之间,现象即美;在审美活动上,以前两者为基础,李约热小说文本提供给读者一个个相对完整,且极富主体性的小说场域,它能够较大限度的超越作者限制,以和现实生活相互缠绕但有彼此并置的方式形成与读者的平等对话形态与途径,在文本与读者主体间性发生与形成过程中,读者在感知美、品评美,并在发现自我、建构自我的进程中重构小说美学价值与意义。在这个角度上,李约热小说创作的伦理之美,在于集体性读者连续性的反复建构与重构,它着眼于意义的延宕与将来,不断生发而无止境。
总的来说,在文学地理学视野之下,地缘性贯穿于李约热小说创作的整个活动程序,包括发生学、创作论和价值论等,他将小说创作制约于冷静的呈现维度上,实现了现象即真理,“虚构却很真实”[20]的辩证性,凸显出小说创作以现实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复合色彩,他疏离观念、还原艺术表现的生活现场、建构艺术世界的自由空间,诉诸于小说叙事的主体性与对话性,活化话题论域和对话机制,将接地气的言意结构在伦理价值领域推向了形而上学的高度。是以,李约热小说创作作为“地域文化和族群文化交融的鲜明个案”[21]必定会有更多思考,创生更多期待。
参考文献:
[1]张燕玲:《平实的收获——2004年广西青年文学扫描》,《文史春秋》,2005年第4期。
[2]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意义》,《文学地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版。
[4]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5]李丽、李约热:《单纯快乐的写作者》,《南国早报》,2013年5月25日。
[6]张燕玲:《山里山外〈都安作家群作品选〉杂感》,《广西日报》,2005年12月19日。
[7][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郭发勇、周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秦雯:《区内外评论家谈李约热作品〈我是恶人〉》,http://www.gxwenlian.com/index/wldt/czdt/20140616/113111.asp,2014年6月16日。
[9]周飞伶:《重提启蒙:“重返80年代”——对〈欺男〉的一种读法》,《南方文坛》,2014年第2期。
[10]韩颖琦:《悲情书写背后的些许暖意与慰藉——广西作家李约热小说论》,《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
[11]金莹、李约热:《从广西乡村走来》,《文学报》,2007年9月24日。
[12][美]查爾斯·伯恩斯坦:《语言派诗学》,罗良功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13]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14]张杰、刘增美:《文学论理学批评的多元主义阐释》,《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5期。
[15][德]R.尚兹等:《真与意义理论》,王路编译,《世界哲学》,2007年第6期。
[16]贺绍俊:《野马镇上“平庸的恶”——评李约热的〈我是恶人〉》,《南方文坛》,2014年第2期。
[17]张晶:《审美情感·自然情感·道德情感》,《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
[18]樊浩:《“伦理”—“道德”的历史哲学形态》,《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
[19]《南方文坛》编辑部:《第五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纪要》,《南方文坛》,2007年第1期。
[20]石曼琳:《广西亲年作家群步履坚实》,《文艺报》,2007年11月14日。
[21]刘大先:《广阔大地上的灿烂繁花——2012年少数民族文学综述》,《文艺报》,2013年3月6日。
(李志艳,文学博士,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