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意斋论艺
2015-05-30吴悦石
吴悦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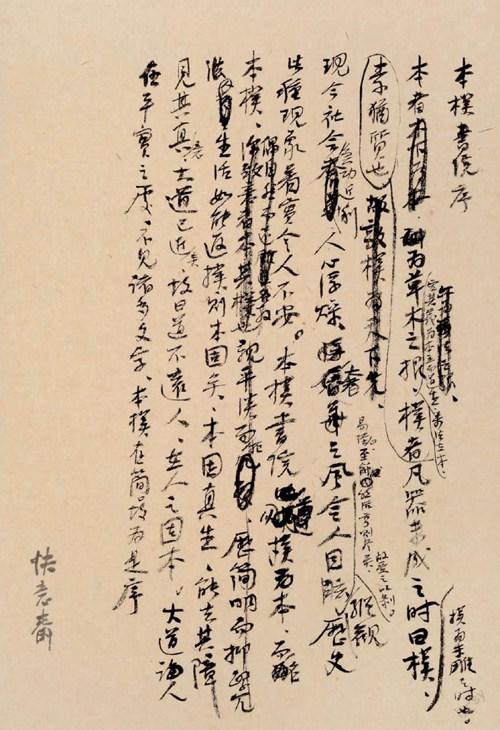
中国书画每以天趣称神妙,所谓鬼神使之非工力者。“天趣也,非得之于人,实受之于天”。所谓“天”者,契机也。融情、景、机、趣于—炉,赖人以发之:“趣”者,必先究其情,穷其性,牵其机,尽其态,八面来风,涉笔成趣,耐人寻味,曲尽其妙者也。情有不容己,趣有不自知,是不期然而然,物我两忘,自然流露。诗云:“松风涧响天然韵,抱得琴来不用弹”。此等境界非拘执于斧斤者可以梦见。陶渊明有句云:“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音。”物我交融,令人神往。
倘若技法纯熟,而终不能成透网之鳞,除障之法无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志行高洁之人为友,脱去胸中尘浊,自然丘壑内营,信手拈来,妙趣自生矣。此是法,亦是理,前人之述备矣。
画禅室论作书之法“在能收纵,又能攒捉”。须知“收纵”和“攒捉”极形象,极富神韵,乃耳提面命之语,一经开窍,终生受用。“收纵”和“攒捉”一语道破天机,执管之时,揣摩其度、其法、其神,可以豁然心胸。
又云忌“泛泛涂抹”。“泛泛”则不经意,无神采,非精神专注,亦非心神往之。病其浮、薄、软、滑、荒率之气也。泛泛日久,成为习气,则终生不得解脱。
东坡云:“天真烂漫是我师。”真书画之精髓也。道法自然,大道之行也。能天真则能以气行,当不乏烂漫。千年来能入此境界者数人而已。
“书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则直率而无化境矣”。思翁此论似过于简略,又不甚道地。无巧不成拙,拙而能巧,巧拙互用,方有奇趣。拙可医甜俗之病,倘若一味用拙,恐入板、结、刻、滞之病,此是思翁不能用拙,故于化境尚欠一步。
思翁云:“古人神气淋漓在翰墨间,妙处在随意所如,自成体势。”此正一句丹髓,乃臻于化境之法。至于努笔而行,夸张态势,存揠苗助长之心,所谓朝学执笔而求暮合辙者,焉有体势可言?有神气则有态势,有淋漓之势则随心所欲,自有妙着。惜天下人不能淋漓,一淋漓便入江湖。神气淋漓与随心所欲可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凡人终老不得其门而入。
“字须奇宕潇洒,时出新致,以奇为正,不主故常。”思翁此论实为搔痒戳痛之语。人有自知,知有先后,知后能身体力行,而“时出新致”,何其难也!“故常”乃自我,一立面目便是新自我,时反“故常”则可时出“新致”。此关钮所在,为万古不移之秘法,学子当知。
“字之巧处在用笔,尤在用墨,然非多见古人真迹,不足与语此窍也。”思翁此语,正可纠正时人弊端。墨汁问世,省时省力,推广书画极为便当,亦有功于时代。然今人不以磨墨为乐,则无旷逸之心,无悠游之态。岂不知墨汁用淡则无活化之灵,用浓则无笔趣之变?笔墨生发在千磨万磨之中,中国书画不磨墨则不知其所以。近人林散之,行笔之中得水墨并行之法,亦得磨墨之趣,曾有话语传世,以教后人。
缶翁笔下酣畅淋漓,气使笔运,如长枪大戟,戛戛有声,胸中块垒齐出笔底,是书卷气,是金石气,是浩然气,是雄健气,是丈夫气。后之学者学养不够,气势不足,有学无创,笔力孱弱,努力而行,则失之枯梗。
墨须久研,浓后方可使用。散之老人所谓“熟”也,不熟不用,不熟无精光,无墨彩,不熟无晕化之妙。生熟之墨用过便知其妙。
书画虽小道,而小能通大。倘能“成教化,助人伦”,名德垂于丹青,固然可喜。若案头挥运,退以自娱。自娱娱人,亦不可作颓唐之笔。风骨照人,宜见正气。吾今日此言,非欲为高论。眼中之物烦杂,不得不开口耳。
包安吴曰:“书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质。性情得于心而难名,形质当于目而有据,故拟与察皆形质中事也。”书画中之神妙不可名状,故日难名。书画中之能事可以历数,故日目遇可以辨析。
王右军作草如真,作真如草,观《兰亭》《十七》二帖可见端倪。包安吴云:“可为百世学书人立极。至若书写时用意飞腾跌宕,筋摇骨转,无一笔板刻,然其用锋洁净,又悉归平正。”此言浅意深,座右常记,当有裨益。
人品不高落墨无法。所谓法者,求之于形,体现于道,形于一画,表象万端。知画者,见一画而知其人,是中国书画魅力所在。
有品则有格所谓格高句响,乃文艺之要义。沁人心脾,荡漾心胸,或日豁然心胸,都在一“心”字,亦都为一“心”字。
品格高下即可定生死,心知其意可以领传承,无源之流必不能人东海,无本之木绝难参青天。生活如此,学问如此,书画亦如此,故日吾道一以贯之。学书学画平常事也,由平常而起,终成不平常之功,水滴石穿,此是理法同源。
梁山舟论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杨守敬以为需增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二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前人此等论述极多,要言不烦,乃命脉所系,余拈出以为座右,与同好此道者共勉。
杨守敬论书云:“若郑板桥之行楷,金寿门之分隶,皆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然后学师法则魔道也。”惺吾老人晚年语重心长,既说与时人,亦警醒后人。可惜后人不自醒,岂不冤哉?
习中国文化者如能养心,则一生受用不尽。平时能燕居静坐,读书品茗,养心调息,以使精光内敛,一旦用时则神采飞扬,精光四射矣。观名家之作,无不神完气足,异彩竞放,或有狂放之处,亦不过平生养心之故耳。
有清一代及民国书家学书者多宗王、赵,以宗王、赵则可楷、可行、可草。问其所以然,日:其转折无不提顿,出笔总在秀洁。王、赵虽相隔千年,然精神承接,亦自高古。非议之人多在少壮,史传傅青主则一例也,及到晚年则有体悟。赵之高迈不在皮相。余少年时学书,长者亦主学赵并授赵帖,十分关爱,不能忘却。
前人有以楷法作草者,所谓收而齐之即为楷,纵而省之即为草。以此授徒,谓不碍楷,亦不碍草,冀楷草并进,所谓善楷者必善草,此民国前之说法。今人以一味作草亦可成书家,要求不同,认识不同,更兼时代不同,或一时也,或一世也。喧闹者总归平静,此要时过境迂、水静河清之时,吾辈或已成土灰,方有分数。
相家有凡人信命、超人不信命,命有不足、修心补相之说。凡人命理,皆有某种不足,能知不足,能补不足,善莫大焉。千余年来,书画之道议论纷繁,第一被人称道者即人品,凡欲成大器者,莫不于此花费毕生之精力,力求进步。斤斤于技法甚夥,然最终鲜有所获。于求道者'乃志存高远,品性高洁,有眼光,有定性,能不为时风所动。虽一时寂寞,亦有益于大成,古来如此,今日亦不能逃此规律。达人知之,勿谓余言之不预也。
《淮南子》云:“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宝也。”心者有形而神者无形。无形之于笔墨,在于形中有神。而神者,望之可得,触之无相。书画一道不在工拙,以得神为主。故名家作画放笔之时如有神助。神由气生,养气得气是为心法。前人之论如汪洋大海,然刘勰之“气以实志,志以定言”是为可学可用,至理名言。至于养气,余前曾著文论及,倘能调整身心,崇尚自然,心神合一,神行之境则油然生于笔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