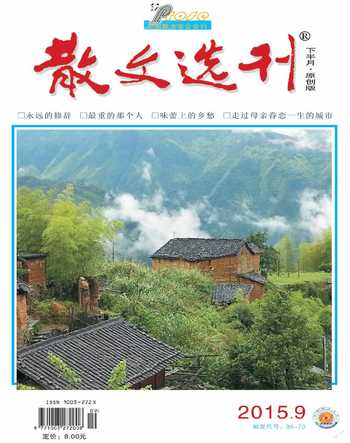二爷
2015-05-30陈寿新
陈寿新
二爷按理应称二伯,老家称叔伯叫爷,因打小这样喊,现在也只得这样叫。
祖父生有五男二女,这位名闻一方的瓦匠挑了无数担大米送三个儿子进私塾,最多的与圣贤打了十多年交道,唯有二爷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但二爷对祖父母很孝顺,心地也很善良。父亲排行老末,祖父在他未成年时就撒手西归,他无人管束,就放下牛鞭参加游击队,一次被潜山县大队抓获。通“匪”是要活埋的,好心人念及祖父一身的好手艺,悄悄地把这消息走漏给祖母。祖母正在烧晚饭,知道消息后拿着火钳求当甲长的长子,大爷眼一瞪:“活该,人牵着不走,鬼指着飞跑,我有么法子呀!”祖母向自己的长子跪下了,大爷却背过身去。他本分,一生节俭,胆又小,钱就是自己的命。求当先生的老三,三爷慢条斯理地答应了,却将借来的银元一夜之间输掉了几块。还是不知世面的二爷张罗着卖掉父亲名下的几亩田,烙了一大包面饼,连夜走了几百里,在县大队门口泡了几天,父亲才被赎回来。他得知原委后,抱着祖母痛哭一场,又是“鬼指着飞跑”,钻遍了金寨、六安、岳西的沟沟洼洼,最后踏上了淮南战场,跨过长江,又风里、雪里滚过“三八”线。他是闹着要回来的,除了一身军装,一床被子,他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却凭空长了许多脾气。不过他对二爷很敬重,当地方基层干部时,常摸黑上他家坐坐,还记得家里每次杀猪,母亲都送二爷点儿肉,有时还炖好。去年底,我添小女,今年初,父亲匆匆来住了两晚就急着赶回去,说是赶二爷“三七”。
二爷很早就丧妻,我对二娘依稀的记忆是滚动着火舌后面的灵位。二娘死了,一个鳏夫,儿子又在马鞍山工作,二爷就和儿媳分开单过。
最喜欢和二爷去放牛,那意味着有东西可以吃。放牛是轻松活,赶出赶进麻烦些,牛上了山,照看它不乱跑就没事了。趁牛吃草,二爷就到荒山开点自留地,种些花生、黄豆、南瓜、芝麻什么的,所以二爷能变戏法般掏出炒花生、南瓜子,或是盐黄豆什么的。没地挖,也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便躺在石板上晒太阳,很是惬意自在。
我小时候,很机灵,和二爷放牛,耳濡目染,掌握了不少与牛打交道的绝活,如骑牛过河、穿牛鼻子等等。
放牛放出了我的胆大包天,这是二爷所没有料到的。一次,将牛赶上山,二爷又回去挑粪浇自留地去了。忽然下了一场暴雨,我赶紧就近跑向一簇枞树,刚一定神,呼吸就停止了。枞树下是裹着稻草的棺材,淡淡的还散发着腐尸的气味。我正准备抬腿挪窝,茂密的枞树里有一双圆溜溜大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我全身毛发倒立,身子一软依瘫在棺材上,紧紧盯着那双大眼睛,发不出声,抬不起腿。雨停了,传来二爷喊我的声音,声音由远及近,由平静到生气,到恐慌。我心里明白,耳朵也听得真切,就是发不出声。看到二爷的身影了,他茫无目的地边跑边喊,还跌了一跤。老天保佑,他朝我这方向跑来。我陡增勇气,跑出枞树林,冲向二爷:“二……二……二爷,有大……大眼睛……”我分明看见二爷铁着脸,巴掌扬起来又放了下去,迅速弯腰将我抱起来:“不怕,不怕,我伢不怕!”事后他说我脸白得像张纸,眼睛发直,抱在手上火一样烫,全身哆嗦着,湿得没有一根干纱。那天牛没有吃饱,就被早早赶回来,夜里母亲还为我招魂。
那年我十岁,吓坏我的是一只猫头鹰。
生与死的距离原来只有这么近。有了那次怕极的体验,我就变得什么也不怕,敢走夜路,敢追叼鸡的狼,敢在无任何麻醉的情况下用老虎钳拔牙,甚至敢踩着无主坟的棺材板在水库里钓虾。
我到外地念书,离开了二爷。听说二爷还是照样放牛,照例变着花样哄其他小孩照看他的牛。在外地工作,偶尔回去,见面点头打招呼并不很热情,对话也极其简练:“家来了?”“家来了。”“来坐坐。”“好。”前年春节携爱人省亲,上二爷家,发现他蜷在墙角晒太阳,半睡半醒的,身子弓得很厉害,极像焙红的火虾,眼睛深陷在皱纹褶里,神态很安详。这就是犁田打靶样样在行的二爷么?那双粗糙得如枯枝的手曾魔术般变出花生、黄豆、南瓜子么?大自然的法则,谁也无法逃脱。
二爷的死讯是父亲带来的,二爷死在农历小年的后一天,无疾而终,享年八十又二,棺材寿衣和闹丧的粮食都是自己准备好的,前一天还请人宰了一头大肥猪。父亲说我堂哥真有福气,用不着操一点心。我心里说,真正享福的是二爷,安享天年,无疾而终,至少在他一个侄儿心中铭刻着一块碑。
下次“家去”,一定在他坟上磕个头。
责任编辑院刘高亮
题图摄影院子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