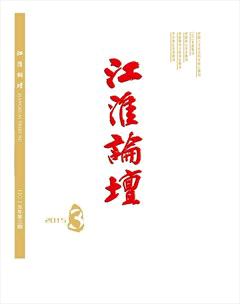都市文学镜像中的都市异化与主体重建
——以朱天文、朱天心作品中的台北书写为例
2015-05-29陆沁诗
陆沁诗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100871)
都市文学镜像中的都市异化与主体重建
——以朱天文、朱天心作品中的台北书写为例
陆沁诗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100871)
现代化都市的诞生催生了都市文学的发展。台湾文坛的都市文学主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不断为人演绎。台北的都市文学形象及其复杂的城市发展进程,为都市文学研究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思考来源。在这被现代文明解构复又重构的都市世界中,台北的异面呈现和主体重建,在台湾著名作家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的笔下,伴随着对现代物质的描写和古旧记忆的探寻,直面历史地理学的当下焦虑与选择。
台北;朱天文;朱天心;都市文学;异化;主体重建
一、都市与都市文学关系述略
“城市是一种话语。实际上,它是一种语言。城市对其居民说话。我们叙说着城市,我们居于其中的这个城市,只因为我们生活其中,漫步其中并注视着它。”[1]城市与文学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的历史同样悠久——城市为文学提供重要的灵感,在其中收纳聚集的故事和辗转于都市乡野之间的人类社会生活,催生了城市文学的诞生。城市所拥有的“特殊的政治空间、庞杂的消费市场、开放的社会风气以及发达的出版印刷业等诸多优势条件”[2],为城市文学的生长提供了最合适的温床。而文学同时也记录了城市中不断变换的生存与价值追求,以及特定的空间场域背后所隐藏的多重异面。相对于笼统的“城市”而言,“都市”这一伴随现代化、市民化潮流而出现的复杂机能区域,更能凸显地理文化视域下的主体异化面。都市兴起所带来的国际化生产模式、发达的金融服务业、爆炸的资讯链和流行消费文化,解构了时空中原本寄托的价值认知,赋予文学重新想象和建构都市记忆的权力。
1991年经济社会学家萨思琪亚·塞森(Saskia Sassen)发表《全球性都市:纽约、伦敦、东京》一书,提出“全球性都市”的概念。塞森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深刻的变化,经济活动的地理与组成产生了“空间上分散,可是全球整合”的双重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大城市的角色发生根本变化,而“城市功能的变化对于国际经济活动和都市样貌(urban form)造成极大冲击:都市集中掌握了庞大资源,而财务和专家服务业重组了都市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于是一种新都市出现了:“全球性都市”[3]。塞森还指出除了纽约、伦敦、东京以外,她的全球性都市名单还包括了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阿姆斯特丹、洛杉矶、悉尼、香港,而且最近这个网脉更加扩大,进一步包括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庞贝、曼谷、台北、墨西哥市。可见台北已经在全球经济整合发展下,晋升至主控全球经济的财务金融都市体系里。
以城市、文化和人为顶点的都市空间三角形,构成的是城市文化生态系统,是一种有机动态结构。这个形似闭合的三角形,实则是个开放系统——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城市能不与外界环境进行大量的能量、物质、资源、信息的交换而生存。全球性都市的合纵连横使得台北与纽约、伦敦等都市共享一种特殊的地方工作文化,彼此接近。虽然就领土而言,它们并不相邻,但这种联系却超越了地域,使得中心都市与其他地域之间发展不再平均,仿佛是异国。因而朱天文笔下《世纪末的华丽》中的米亚,离开台北市区“越往南走,陌生直如异国”,“等不及要回去那个声色犬马的家城,离城独处,她会失根而萎。”[4]23
关于城市的想象与再现主题,台湾文坛自20世纪80年代起已有呈现。彼时台湾社会形态的都市化为都市文学提供了文本场域,这个在历史上充满悲情的美丽岛如今已变成“都市岛”。时至90年代,被称为战后婴儿潮作家的朱天文、朱天心姐妹,在题材上接续了都市主题,以台北为中心,穿行于现实、想象与记忆中,展开一幅多面都市的立体画卷,寻找将自身内洽于空间主体的方法。她们对都市的感觉复杂而暧昧,在这被现代文明解构复又重构的都市中,重拾似乎被消解的记忆,希图将建构在追怀上的历史想象,缝补进新地理形态的都市空间中。
朱氏姐妹的城市话语立场,绝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台北,这个如今的国际化大都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传统的封闭的乡土世界变为现代都市,是殖民文化与传统东方文明的结合体,由外来资本文明滋养、翼覆着记忆或想象中古旧的生活方式。缓慢流逝的时间好似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地理空间的变换却是明显而快速的,从废墟中起高楼,又在炮火里重沦为废墟,现代化都市的高效率、繁华梦和不确定的仓促感在破坏与重建中交替呈现。现代城市的建设在资本文明的覆翼下,似乎掩盖了旧时代的风貌;但事实上,在新旧二者的冲击中,敏感的记忆追怀者却能在矛盾的裂隙间发现变形了的历史遗留物,因而文本中不断呈现着复杂多面的城市映像。
二、文学镜像中的“他者”——异化的都市与边缘的个体
1.物欲升腾的都市
20世纪的机械文明与商业文明的发达,使现代都市被物所包围,并且以物(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为特征。“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它构成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5]这种变化使得物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提升,弗洛姆曾作过这样的描述:“世界是一个供我们消费的庞大的对象,是一个大苹果、大瓶子、大乳房。”[6]对物质永恒的信仰,使得感官功能的重要性大大加强。于是文学像一面镜子,反射出都市弥漫的物欲与主体对于感官的渴求。对于米亚来说,依赖嗅觉与视觉的生活才能为主体带来存在感:“米亚是一个相信嗅觉、依赖嗅觉记忆活着的人。安息香使她回到那场八九年春装秀中,淹没在一片雪纺、乔其纱、绉绸、金葱、纱丽、绑扎缠绕围裹垂坠的印度热里,天衣无缝……米亚也同样依赖颜色的记忆。”[4]27
可以说,是物质的触感、色泽、质地填充了米亚日常都市生活的巨大缝隙。米亚刻意地沉溺于商品社会带来的感官刺激中,通过让人应接不暇的各种艳妆华服的符号铺排,夸张地展现现代都市台北的消费文明特征。文中如汉大赋一般所大量列举堆砌的潮流与品牌,包括川久保玲、迪奥、香奈儿、皮尔卡登、山本耀司、三宅一生、圣罗兰等,多为日本、法国、意大利等日欧名牌。米亚虽然身处于90年代的台北,事实上却身处于无国界的奢华物质世界中。强势资本文化大举入侵,以物质符号打破原生传统乡土城市边界;个体原本的民族意识与国族记忆显得极度虚无缥缈并轻质化,国界与国籍仿佛变得游移流动。这个时空被国外物质偶像所填充,而并非被家族亲人等传统血缘族亲关系相连缀。
服装既是都市生活的外象表征,又是她们构建都市归属感的工具。米亚坚信“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予以重建”。[4]31以大工业和商品经济为表征的新文明,以快速而强烈的节奏,剥夺了前现代文明的存在场域,历史的叙事在空洞的个人都市生活中瓦解,到处充斥着衣食色相的物质细节描写,而这些琐细的才能勾连起米亚的存在本身与这座被商品消费所掌控的现代都市。米亚在浴室里养了花草,风干了玫瑰,并将自己对于物质的渴望和需求寄托在对荷兰玫瑰的所谓患难之情上,这种类似偶像崇拜的行为已然凸显了一种拜物心理。
在朱天心的小说《第凡内早餐》中,都市人这种对物的迷恋凝结于钻石的意象上(文章标题本身取自奥黛丽·赫本的经典电影,而影片中迷恋浮华都市的物质女郎一角,正与文中女主人公形成意味深长的对照)。读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和《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都市职业女性,自明是在商品社会中出租劳动力的“女奴”,产生被商品美学刺激控制所激发的虚假需求,渴望得到一颗钻石重获自由。她洞悉一切钻石工业的内幕,却甘愿受De Beers一样的垄断资本的蛊惑,在购物前一日保养双手,备妥穿着,以一身玛莉珍、Armani、D&G的穿戴去购置有着同样符码意义的“土耳其石色的纸盒”、“普鲁士蓝的丝绒盒”中的一粒“商品拜物异教的法器,资本主义淬炼出的舍利子”[7]41。这样一类女子对物的迷恋,指向的是在浮华后现代都市中的自我迷失——在外部文明的冲击下,都市空间日新月异,个人的主体归属记忆失去了在地的寄托场域,因此需要借用官能与物质唤起身份的确认,召唤影影绰绰的记忆,找寻时间和历史的轨迹。
2.时空边缘的个体
米亚们并非天生就具有对物质的迷恋,她也曾经历过一段毫无虚伪矫饰、物质简单质朴、历史记忆秩序井然的“那年头”:“那年头,米亚目睹过衣服穿在柳树粗桠跟墙头间的竹竿上晒。还不知道用柔软精的那年头,衣服透透晒整天,坚质粝挺,著衣时布是布,肉是肉,爽然提醒她有一条清洁的身体存在。”[4]37回忆中属于这都市过往的“那年头”如昙花一现,很快被米亚18岁时一场玛丹娜的服装模仿秀匆匆打断。这一场现代化的模仿秀仿佛催生了所有都市人和整座都市的时尚意识,带领着台湾米亚开辟了新的模特生涯,令台北大跨步地向前,追赶流行前线欧洲。当物质上的摩登潮流与都市景观上的“赶超流行”同道而行,一夕数变的台北时空被压缩断裂,使得城市中的米亚们在身体上疏离了作为一个居住主体和这座城市之间原本存在的许多关联。然而都市的裂隙里透露出的“老灵魂”记忆感召,又使得米亚不由自主去寻找遗失的历史。
因而米亚常常以一种仰望的姿态去寻找:“这是台湾独有的城市天际线,米亚常常站在她的九楼阳台上观测天象。依照当时的心情,屋里烧一土撮安息香。违建铁皮屋布满楼顶,千万家篷架像森林之海延伸到日出日落处。”[4]37-38地面空间景观的破碎重建,使得时空记忆也被取代,把衣服穿在树杈竹竿上的景象,被高楼大厦和精品店这些新的都市景观所取代。这个城市轰轰烈烈的现代化和商品化进程,直接在物的层面上抹灭了她个性化的回忆。
在都市出生成长的米亚,很容易就被布置时尚、诱导消费的精品商店所吸引,穿街过巷如同“走经一遍世界古文明国”,悠然心安;然而当面对台北以南的小城市、郊区和农村这些更为自然乡土、代表着台北过去历史的外在地景时,却显得震惊无措。她不得不“退”到未来——城市现代化的一步步推进,除了意味着与乡村的区隔,还意味着都市空间本身的重新分配和竞逐。在闹市的金碧辉煌之外,似乎应有更广阔的“看不见的城市”浮现出来,这就是她仰望华丽的天际线的原因。然而此时的天际线是“违建铁皮屋布满楼顶,千万家蓬架像森林之海延伸到日出日落处”,是被“雪纺、乔其纱、绉绸、金葱、纱丽”着色,被各式干燥花草熏染的“虾红、鲑红、亚麻黄、蓍草黄轰轰焚城”的天际线。铁皮屋是现代都市建筑文明的外象,让人反思也许无论今昔样貌的都市都未必能长久持存,而不断的“违建”、破坏拆解才是永恒生命力量的显现。然而铁皮屋也是一个牢笼,就像这座充满消费和欲望的都市困住了米亚,令她无法脱身。而在被囚禁的同时,米亚又渴望将刹那的观感凝固在永恒之中,于是楼顶上除了铁皮屋,又挂满了晒干的各式花草。她希图用这种方式将具有时效性的鲜花的娇粉和香味,留驻在具体的事物上,与稍纵即逝的时间剥离开来。
如同米亚一般被剔除在历史时间线外的个体,只能通过物化的方式去凝结流动的精神世界,将短暂的人生与长久的物质建立联系,在空间化定格中完成亘古的时间体验。在这座都市,有无数像米亚一样的个体,站在楼顶的铁皮屋旁,侍弄着干花干草。他们寄生其中,却无法逃离这座城市赋予他们的悖论:一方面主体世界无根而萎,被迫尝试利用各种琐碎的物质和繁复的方式去抵抗消费主义的侵袭,开拓精神空间;而另一方面,这座都市被资本社会所催生的物质化层面不断滋长延伸,每一个寄居其间的主体都无法走出那个以取消个体特性、将人异化为同质化的消费者为最终目的的时尚怪圈。模特出身的米亚身处风云变幻的时尚浪潮中,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终将“年老色衰”的结局。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势中诞生的“飞地”台北,同样也存在着可能随时被资本抛弃的命运。于是,都市人主体的生存经验某种意义上反射了台北的现状——一个正在忘却乡土记忆、追随着资本运作的边缘化都市形象。
三、移民与遗民——多元都市文化心理下的都市主体重建
1.都市主体的身份与归属焦虑
在全球化时代,超越地域的经济都市网造就了城市“去畛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现象,因此生发出全体文化意识层面的飘萍感觉。所处城市环境的日新月异造就的陌生感,使人们文化寻根的冲动,或对“家”和本乡本土的向往,油然滋生。寻根往往是全球化发展中“时空压缩”和“文化混种”过程所引发(或至少加强)的效果之一。已晋升操作国际经济“全球性都市”行列的台北,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几乎所有与高度都市化相关的文化和地理问题。
朱天心的《古都》即是描绘在台北蜕变后,个人记忆与空间感危机促发的主体追寻之旅。朱天心笔下对台北主体的追溯,自然最先是通过血缘上的关系得到祖国“大中国”的认同。连姐妹朱天文亦说:“单为了张爱玲喜欢上海天光里的电车叮铃铃的开过去,我也要继承国父未完成的革命志愿,打出中国新的江山来。”[8]69在小儿女天真浪漫的岁月里,她的父亲朱西宁、精神领袖胡兰成使之相信“世界史的正统在中国”,因此作者笔下经常既甜腻浪漫,又怀想中国:“那三月如霞,十月如枫似火的,我的古老的中国……我永生的恋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只是向中华民族的江山华年私语。他才是我千古怀想不尽的恋人。”[8]73
但是万里江山入梦遥,流入血肉的国族记忆虽根深蒂固,然这非经验性记忆却是要遭到质疑的。《古都》开篇即点明记忆乃至主体身份的不确定性,“难道,你的记忆都不算数”[7]13,指向“记忆”的崩坏质询,“你”的身份流失。在这里,“记忆”“我”“你”的存在论式表征皆动摇不定。这种对于“记忆”与“主体认同”的挫折经验,以及从其中生发的寻找姿态,与作家“外省人第二代”的身份密切相关。朱天心的父亲来自山东省,但她本人则是在台湾出生、成长的“第二代”。对于从来没有去过大陆“故乡”的她们来说,所谓的“故乡”,是经常摇摆于观念性的虚构场所和实际生长的台湾之间,被撕裂为二者的存在。这刚好与为保持虚构的整合性,而主张台湾的首都始终是在大陆南京,以至让台北陷入所谓“临时首都”的尴尬状态,具有同构性。相对于大陆,她是遗民(adherent);相对于台湾,她亦是移民(immigrator)。她认识到,血缘上的祖国大陆,只是个架空的“故乡”,而她是必须不断寻求个人立足点的“夹缝”世代的文学家。身为眷村子弟的朱天心也目睹了台北——这座见证了荷兰殖民者、明清王朝、日本人半个世纪的占领、国民党统治直至解严后新党政争而饱经沧桑的历史名城,正以建设的名义变得日新月异,面目全非,她忧心如焚,依着记忆开始了对故都的探访寻觅。
2.怀乡式的重建与嫁接
同样作为现代性都市的巴黎,在19世纪由奥斯曼进行剧烈改造后,出现的是一个崭新的空间,意味着同过去的决裂。“巴黎新空间的产生,在重新塑造一种新的共同体的同时,也是对旧共同体的摧毁……一个新的巴黎被打造出来,这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巴黎人被打造出来,一个新的巴黎政治经济关系被打造出来。”[9]奥斯曼的创造性的破坏,是“要向旧的巴黎告别”,通过建造巴黎,证明这是一个全新的与旧时代毫无瓜葛的帝国。类似于此的现代化都市重建工程,似乎使得城市的历史与今天割裂;然而都市文学的叙述者,或者说空间记忆的搜寻者却能够在时空之隙中追本溯源,重构主体。
《古都》的作者来往于往昔所流连忘返的地方,希望能找到曾经的伊甸园,这种找寻的焦虑与失落在朱氏姐妹的作品中无处不在。在作者的眼中,承载记忆的古都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变化,建筑拆迁,面目全非,儿时的嘉年华广场早已不复存在,童年疯野的山丘也被连绵的公寓占据,昔日如绿色城墙一般的百年茄冬也因为理直气壮的开路理由一夕不见,太古巢惨遭日人的拆毁,明知桥深埋于地下,枫香不见了大半,美琪饭店改成了上海商银。“你简直无法告诉女儿你们曾经在这城市生活过的痕迹,你住过的村子,你的埋狗之地,你练舞的舞蹈社,充满了无限记忆的那些一票两片的郊区电影院们,你和她爸爸第一次约会的地方,你和好友最喜欢去的咖啡馆,你学生时常出没的书店,你们刚结婚时租赁的新家,甚至才不久前,女儿先后念过的两家幼儿园都不存在了。”于是“‘你’变得不愿意乱跑,害怕发现类似百年茄冬不见的事,害怕发现一年到头住满了麻雀和绿绣眼的三十尺的老槭树一夕不见。”[7]15
在对记忆中的家园进行事无巨细地考古式谱写后,作者发现在台北已经无法寻找到田园式的桃花源,于是将中国传统文学中这个幸福之地的原型嫁接到京都这座她有切身体会、又带有古中国叠影的城市上,进行理想他境的构造。小说中对京都风貌的描写,不时穿插引自川端康成《古都》的片段,这种有选择性的细节引用,是运用京都这个对比符号时,自觉生发的针对台北现状的在地性表现。文中所呈现的京都,有数不清的大小寺院和神社,花木扶疏,人情淳厚,还有善待各国游客的开阔国际观。最难得的是,古典风俗(祭祀、节庆、花季、庭园、吃食等)融入在现代人的优雅生活中,并未像在台北一样被视为“和进步有势不两立的关系”。而小桥流水、锦鲤杨柳,更是令叙述者不时想起诗词中的江南。作者的这些联想正是基于她“从日本想见中国”的心理:“日本的一器一物日常人家生活礼节也真是美到极致了。日本东西对我们来说真是完全新鲜极的,真是不该的,比起来,我们对西方东西反倒百般熟悉,真是从小出门的浪荡子,此番老大回家,认认手足,也从兄弟脸上忆忆父母的神采。”[10]
对于作者来说,神州既然没办法回去,便只能在兄弟(日本)脸上忆忆父母(中国)的风采。当然,引入京都的永恒性与台北的瞬间性作对比装置,是借用宛如川端所创造的千重子与苗子两姐妹一样的关系,在“双胞胎城市”中追寻不被记忆的历史和无法确定的主体。她所植入的文学京都,被希望承担负载台北历史的重任,但终究只是她心目中在异域范围内选择的理想的空间形态:东方古典成功地蜕变为一种具有历史纵深和地方特色的现代都会生活。她移民身份所赋予的焦虑和执着,使得她对都市主体的追寻仍要回到有血缘关系的记忆文本中去,《台湾通史》的引用就正好缝补了她的在地怀想。叙事者深知,当年连横盛赞的宝岛并非真正的福尔摩沙、人间天堂。然而叙事者以20世纪的现代人回顾过往,却为之悠然神往:“来采硫磺的郁永何在《稗海纪游》形容台北:非人所居。但那早在一六九七年,不能怪它,同时期的嘉南平原乘牛车行经其间,如在地底(多令人神往!)”。[7]18当时的“婆娑之洋,美丽之岛”,就并非是单纯的现在进行时,而是未来时。而作者由今观之,似乎也并未实现,而是在今非昔比的发展中成了过去未完成时,因而叙事者所寻找的城市主体和自我身份也并未完成。全文结束时,作者引用连横自序的结语“婆娑之洋,美丽之岛,我先王先民之景命,实式凭之”[7]21,是主体追寻者在响应《通史》对过去的检讨,对未来的憧憬后,期待台湾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资本浪潮冲击下,成为保有历史记忆、都市主体的美丽之岛。
在全球经济秩序急速转换、消费文化愈加发达的今天,每一座现代都市都永远处于拆与建、变与不变、非常与恒定、记忆与忘却之中。对于今日世界,这也许是一种更完美的历史地理学选择。城市变迁进程中,台北空凭大中国的记忆,又借用京都,甚至巴黎等都市的主体意义来解构自身,构成一种印证自我身份的镜像互看,却也在不经意间形成了独属自身的城市形态而自成特色,庶几成为构筑未来市景的蹊径。如此,时空交错的古旧历史与殖民文化、资本文明相遇时,城市的气质,不是更清晰,而是更暧昧,不是更现实,而是更浪漫,不是更政治化,而是更诗意化。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说:“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也许,我不愿意全部讲述威尼斯,就是怕一下子失去她。或者,在我讲述其他城市的时候,我已经在一点点失去她。”[11]因此,在讲述台北的都市故事时,这样暧昧不尽的叙述话语反而才能在时代破立中为其保留着对希望和记忆的复刻与更新。
[1][法]罗兰·巴尔特.罗兰·巴尔特文集:符号学原理[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7.
[2]高兴.中国现代文人与上海文化场域(1927—1933)[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20.
[3]Saskia Sassen.The Global City:New York,London,Tokyo[M].Princeton:Princeton Uni versity Press,1991:3.
[4]朱天文.炎夏之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5][美]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2.
[6][美]埃·弗洛姆.爱的艺术[M].刘福堂,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73.
[7]朱天心.古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8]朱天文.淡江记[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9][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M].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4.
[10]朱天心.江山入梦[M].台北:台北远流出版社,1992:51.
[11][意]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M].张宓,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79.
(责任编辑黄胜江)
I207.42
A
1001-862X(2015)03-0140-006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陆沁诗(1991—),女,安徽合肥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