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真的反写真情结
2015-05-28陈奇军
陈奇军
“写真”的来历
“写真”二字,人们都以为这是个日本词,其实并非如此。一本介绍日本写真的特辑《知日-写真》一开始就指出:“写真”本来不是个日本词,而是从中国传来的词语。
“写真”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梁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写道:“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不过,刘勰的“写真”在此指的是文学如实描绘事物。后来,北齐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杂艺》中将“写真”引申为惟妙惟肖的人像画:“武烈太子偏能写真,坐上宾客,随宜点染,即成数人……”。此后,文人墨客凡提“写真”,大都指逼真程度高的肖像画。摄影术于19世纪中期传到中国后,最先应用的领域就是人像。这项西洋术由于更加逼真,所以就替代肖像画成为“写真”。不过,“写真”一词也像其他诸多中国文化现象一样—在中国诞生,被日本光大。
保罗?德拉罗什:“达盖尔式摄影法的出现将是绘画的末日!”
在距今约3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有一群人类居住在位于今天法国南部山区的一个洞穴里。有一个人在吃饱喝足后,想把自己亲眼见过的那些大型动物告知缺乏见识的同伴,以显示自己的高明。但光凭手势和简单的言语无法达到目的,于是他就尝试着在岩洞壁上涂画……这幅现在叫做肖韦(Chauvet)洞穴岩画的作品,有可能是人类最早的绘画艺术。
从史前文明开始,人类就用各种方法尝试着“写真”,以便传递视觉体验。在物质技术和人类造型能力受限的情况下,即便是能工巧匠,要想准确还原自己的视觉体验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一旦有所成功,便会赢得尊重。进入文明史以来,随着新技术的发明和人类造型经验的积累,再加上幼童时期就开始的刻苦训练,画者、雕者、塑者模仿“上帝造物”的能力得以大幅提高,其中的一些能者因为可以做到惟妙惟肖而成为当时最受推崇的工匠,载入史册后他们就成为后人顶礼膜拜的所谓“艺术家”。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以及北欧的伦勃朗、东土的吴道子,便是南北西东各方工匠中的圣者。
自人类艺术史开启到19世纪上半叶,视觉艺术的轨道从来没有偏离过“追求逼真”这个方向,古希腊时期形成的“模仿说”一直都是艺术家们的金科玉律。但是,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复制视觉经验的技术有了重大突破,从根本上改变了视觉艺术的方向,这就是1839年法国科学院对全球公开的达盖尔摄影法。
由于自古以来衡量绘画优劣的标准都是能否做到写真,因此当更加写真的摄影术到来之后,许多画师不得不改行做了摄影师,因为他们的确觉得,自己的艺术造诣无法达到照相机的高度。“达盖尔式摄影法的出现将是绘画的末日!”法国画家保罗?德拉罗什(Hippolyte-Paul Delaroche,1797—1856)的这句话,道出了所有画家对该项工业技术的看法。

波德莱尔:“摄影像印刷术和速记法一样都是艺术卑微的仆人,那些懒惰和没有天赋的画家可以成为摄影师。”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画家们想象的那么糟糕。1859年,法国艺术界最具话语权的人物—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出来为画家们撑腰了:“我们必须认识到,摄影只是为了服务科学和艺术而存在,它就像印刷术和速记法一样都是卑微的仆人,既无法创造,也无法提升艺术品位。那些懒惰和没有天赋的画家倒是可以成为摄影师。”波德莱尔对摄影下了如此结论之后,画家们迅速找到恢复自信的理由:一个只会借助机器“作画”的人,怎能与心灵手巧的画家相提并论。而波德莱尔的“懒惰和没有天赋的画家”一说,则让那些本来沾沾自喜的摄影师羞愧难当。
法国画家、摄影师纳达尔(Nadar,Gaspard-Félix Tournachon,1820—1910)并不认可自己是“懒惰和没有天赋的画家”。他认为,如果摄影技术运用得当的话,将可以“使艺术家达到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可另一位画家杜米埃(Honoré Daumier,1808—1879)却对纳达尔的论断不屑一顾。杜米埃画了一幅名为《纳达尔将摄影提升到艺术的高度》的漫画,就是讥讽摄影师对艺术单相思的著名典故。
19世纪中叶,印象派绘画尚没有诞生,那些细节清晰、画面细腻的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拉斐尔前派油画依然是主流。在英国,一些有着艺术情结的摄影师为了让摄影成为艺术,极力在内容和形式上模仿油画。他们采用“叠印法”,将人物、道具、环境、天空合成在一起,从而制作出拉斐尔前派油画效果的摄影作品。摄影师们凭借这种“摄影画”终于获得了艺术殿堂的入场券—尽管照片被安排在油画展厅中最不起眼的角落。为了区别于“那些懒惰和没有天赋的画家”,这些迷恋艺术的摄影师将自己归结为“高艺术摄影派”(High Art Photography)。
迈克尔·兰福德:“当制造商们煞费苦心,急于提高镜头的分辨率和干版记录细节的能力时,画意摄影家们却在力求达到相反的效果。”
到了19世纪后半叶,欧洲人对绘画的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1863年,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专门为那些被法国皇家画院拒之门外的画家举行了“沙龙落选作品展”。在此次“落选展”上,爱德华?马奈(Edouard Manet,1832—1883)的《草地上的午餐》首次得到展出。马奈这些人的作品只是不符合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1780—1867)等法国皇家画院权威所定义的“艺术的可接受范畴”。以“定义艺术的可接受范畴”为使命的学院派,即法国皇家画院和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所掌握的“艺术尺度”,首先用来丈量的都是画面逼真程度。包括大名鼎鼎的安格尔在内,画家们为了提升画作的逼真性,都会借助“艺术卑微的仆人”即摄影术的帮助—即先用相机拍摄,然后比对着照片绘画。在当时,威廉-阿道夫?布格罗(William Adolphe Bouguereau,1825—1905)被学院派奉为典范,因为他许多画作在摄影术的帮助下,逼真程度甚至可以媲美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问世的照相写实主义作品。不过,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布格罗等人只是古典艺术的回光返照。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摄影术已经影响到艺术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画家认为:追求逼真的画面就让照相机这种机器去做好了,画家应该另辟蹊径。
1874年,在第一届“印象派”画展上,莫奈(Claude Monet,1840—1926)的《印象-日出》首次展出。但在坚守传统的学院派看来,莫奈等人就是“那些懒惰和没有天赋的画家”,他们没本事画出更好的画作,只能拿一些类似半成品的玩意儿甚至是草稿来哗众取宠,于是就讥讽莫奈这些人叫做“印象派” (法语Impressionnisme)。然而,这些学院派眼中的“三流画家”在1878年举办第三次画展时,就已经自觉地用“印象派”来称呼自己了。
印象派绘画以及现实主义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的艺术创作开始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即现代主义的兴起。印象派画家们先后举办了8次画展,期间又诞生了“新印象派”,“新印象派”又分离出以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为代表的“后印象派”。到了19世纪末,讲究逼真的古典主义绘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画得越来越不像的印象派艺术开始演唱主角。与此同时,那些有着艺术情结的摄影师们也紧跟绘画的步伐而转向,模仿拉斐尔前派等古典艺术的“高艺术摄影”被模仿印象派画作的“画意摄影”(即绘画主义摄影,Pictorialism)所取代。
在19世纪后期,摄影镜头的分辨率有了大幅度提高,感光材质也有了长足进步,摄影师们要想得到一张清晰的照片已经变得容易多了。但这些技术进步反而让那些追求艺术的摄影师非常纠结,因为与当时最时髦的印象派绘画相比,用照相机拍摄出来的作品过于写真,而不印象。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迈克尔·兰福德(Michael Langfords)在他的《摄影艺术与摄影流派》一书中这样描述画意摄影家的反写真情结:“当制造商们煞费苦心,急于提高镜头的分辨率和干版记录细节的能力时,画意摄影家们却在力求达到相反的效果。”为了实现印象派绘画那种“艺术效果”, 画意摄影师们有的故意选用针孔相机,有的将镜头上涂上油脂或其他脏物,有的干脆在曝光时用脚踢一下三脚架,这一切努力都是让影像模糊不清,以便“印象”。
“美国现代摄影之父”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 1864—1946)以及大名鼎鼎的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1879—1973)、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1886—1958)都曾经是画意摄影领域最活跃的人物,印象派绘画对摄影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当然,上述三位摄影名人的历史地位并不是因为弘扬画意摄影,而是抛弃旧爱而另寻新欢。
爱默生:“摄影应该像自己,而不是去模仿其他艺术形式。”
尽管绘画主义摄影家们想尽千方百计模仿印象派绘画,但是他们在艺术界始终没有达到与绘画平起平坐的地位。摄影界嘲讽他们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而画家们也自然不把这些学徒放在眼里。1910年之后,画意摄影在风行30年后逐渐式微。画意摄影没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印象派绘画风头已过,野兽派、立体派、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等更加抽象和前卫的艺术风生水起。就连画家老师们都对早已过时的印象派不感兴趣了,作为徒子徒孙的画意摄影者们还有什么理由对其毕恭毕敬呢!
其实,英国人彼得·亨利·爱默生(Peter Henry Emerson,1856—1936)在画意摄影风头正劲的时候就对其进行了质疑,他是第一个提出“摄影应该像自己,而不是去模仿其他艺术形式”论调的人。爱默生在1889年发表的《自然主义摄影》一文中写道:“没有一种艺术能比摄影更精确、更细致、更忠实地反映自然。自然是艺术的开始和终结,只有最接近自然、酷似自然的艺术,才是最高的艺术。”不过爱默生后来又对自己的这种表述提出质疑,他在1891年的一本小册子中的观点是:摄影并不是艺术,而是一项科技。
斯蒂格利茨等人为了让摄影摆脱绘画“卑微的仆人”地位,逐渐与欧洲的画意摄影分离,并在北美大陆推动了“直接摄影”概念的形成。作为直接摄影派代表人物的韦斯顿及F64小组,也不再拍摄模糊不清的反写真式照片,转而利用优质镜头和大型相机拍摄细节丰富、未加修饰的石头、树木、人像等。F64小组的重要成员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1902—1984)发明了“区域曝光法”,将直接摄影的魅力发扬光大,亚当斯这个名字也因此尽人皆知。
与保罗·斯特兰德(Paul Strand,1890—1976)、韦斯顿等人倡导的直接摄影相呼应,后来成为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摄影部主任的爱德华·斯泰肯,也发现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社会纪实摄影更有魅力,于是举办了令其名垂青史的“人类一家”和“艰难岁月”大型纪实摄影展览。
美洲的摄影人发扬光大了摄影的写真功能,欧洲的画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08—2004)则不务正业,终生探求摄影的另外一大魅力,即凝固不可预见的有趣瞬间,并提出了“决定性瞬间”理论。
在以绘画为代表的艺术界看来,所谓的“直接摄影”,实际与艺术的方向背道而驰了,重新回到了写真术天经地义的科技轨道。
苏珊?桑塔格:“不完美的技术现在受到青睐,恰恰是因为它打破了大自然与美的静态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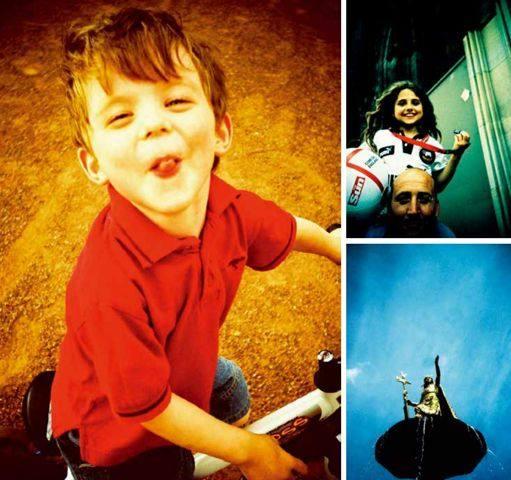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那些使用粗糙、怪异、不和谐的音色和生硬、歪曲的演奏技巧着力营造出一种噪音效果的摇滚、朋克音乐成为流行,这就是“lo-fi”音乐。“lo-fi”(低保真)是“hi-fi”(高保真)的反义词,最早是西方音乐界讥讽音乐作品音质低劣的词汇。lo-fi在音乐领域成为潮流之后又向外扩张,由此诞生了lo-fi美学以及lo-fi生活。大凡是那种追求简单、质朴、反科技的生活方式,通通都被贯以“lo-fi”之名。
人类所有追求的总体方向是高保真,在“发展中”这个阶段—绘画要逼真,音乐求高保真,生活渴望奢华,发展追求速度。不过,事物发展到极端后就会向相反方向转化,“物极必反”这个道家哲学观点无论在东土还是在西方都能得到应验。当学院派画家们在摄影术的帮助下将写真式绘画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之后,印象派应运而生;lo-fi则是音乐的保真技术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的必然产物。摄影,当然也不例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科技的发展让摄影的写真能力明显增强,越来越多的人能轻松得到高保真的照片,而安塞尔?亚当斯的区域曝光法也将银盐摄影的高保真特性推向极致。不过在这个时候,从音乐领域诞生的 lo-fi文化已经潜移默化影响到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追求时髦且标新立异的年轻摄影人由于受到低保真文化影响,自然不欣赏那些高保真摄影。
1991年,两名奥地利维也纳美术学院的学生在捷克布拉格的一家古董商店买到了乐模(Lomo)LC-A相机。由于他们用乐模LC-A拍摄的照片效果非同一般,因此乐模LC-A相机声名大振。奥地利人还根据“Photography”(摄影)生造“Lomography”一词,并以这个名字注册了公司,这才有了后来波及全球的乐模文化。
乐模LC-A是苏联的泽尼特(Zenit)相机工厂模仿日本确善能(Cosina)CX-2生产的一种廉价相机,具有色彩不准、暗角、漏光、边缘像质恶劣等几乎所有摄影缺陷,不过这些缺陷并非厂家所希望看到的。相机品牌命名者当初并没想到“Lomo”名字中的“Lo”恰好与“lo-fi”的“lo”有关联,更不会认同这个“Lo”代表着低劣。
尽管大名鼎鼎的森山大道、荒木经惟等人也跟在那些“懵懂”的年轻人身后加入了乐模大军,但乐模摄影与100年前那些画意摄影的“反写真” 情趣一脉相承,只不过是在“低保真”文化影响下的又一次“印象”运动而已。不过,从“乐模十大原则”来看,乐模摄影与并不是简单重复“画意摄影”,乐模不仅具有简单、原始、反科技的“lo-fi”特色,还打上了后现代艺术的反艺术、反规则、反绝对等烙印。
荒木经惟:“数码摄影很容易流于满足,所以很危险……现在已经不是写真的时代了。”
从高艺术摄影到画意摄影;从直接摄影再到乐模文化,摄影让艺术改变了方向,然后又跟在艺术屁股后面晕头转向地跑了两圈。数码影像时代之后,又一个“写真与反写真”轮回拉开序幕—摄影这一轮的反写真运动更加普及而猛烈。

高分辨率的数码成像设备和经过数码优化的摄影镜头,让摄影的写真性能有了质的变化,即便安塞尔?亚当斯在世,他的8×10技术相机和“区域曝光法”都无法与当今的数码影像设备相媲美。别说顶级的3600万、8000万像素的数码相机和数码后背以及以蔡司“猫头鹰”为代表的高素质镜头,就连普通的数码相机和镜头也能轻松获得与双眼所见一模一样的高清晰度影像。当数码成像系统的写真能力登峰造极之后,“物极必反”又一次得到了应验。
不可否认,对于普通摄影者特别是初学者而言,纤毫毕现的成像效果依然魅力无穷;但对于一些资深摄影玩家来说,这种“眼见即所得”效果因为得来全不费功夫而变得索然无味。2008年,“所得非眼见”的“艺术滤镜”(Art Filter)应运而生。艺术滤镜是奥林巴斯公司在E-30数码单反相机上首次提出的概念,现在除了专业级别的数码单反相机之外,其他所有数码相机和智能手机均有各种效果的艺术滤镜。苹果公司的iPhone之所以深受摄影人欢迎,并非是它的硬件配置多么高超,主要在于其软件效果即艺术滤镜颇为讨巧。
使用艺术滤镜后,一些极为平常的画面立马显得“艺术”起来,这不仅让初学摄影的人尝到“艺术创作”的甜头,就连一些功成名就的摄影家也乐此不疲。可是荒木经惟却说:“数码摄影很容易流于满足,所以很危险……看着相机的液晶屏,你一定认为‘照上了,可在我看来完全没照上—现在已经不是写真的时代了。”
阿瑟·丹托:“当代艺术已经转化为观念,走到这一步时,艺术就终结了。”

从最早模仿印象派的画意摄影,到lo-fi文化之后的乐模摄影,再到各种艺术滤镜以及个性镜头的尝试,摄影人的这些“艺术”追求实质都是“打着写真反写真”,即让拍摄出来的画面尽量与双眼所见有所不同。难道,写真一但反写真就变成艺术了吗?倘若用百年前画意摄影的观点来看不无道理,但时过境迁,当今用来丈量艺术的尺子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重形式轻内容的现代主义艺术在半个世纪之前就走向了没落,随之而来的“观念艺术”就像急性传染病一样,迅速扩散到当代艺术群落的每一个个体,就连纪实摄影也未能“免疫”。1967年,爱德华?斯泰肯的接班人约翰?萨考夫斯基(John Szarkowski,1925—2007)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新纪实摄影” 展览,实际是将再现事实为主“老纪实”变成表达观念为主的“新纪实”。与此同时,那些所谓“懒惰和没有天赋的画家”也正好可以凭借观念摄影了却艺术心愿;即便是一些拥有绘画天赋且勤奋的画家,也觉得摄影是表达观念的最佳方式。
摄影诞生不久就爱上了艺术,经过三个轮回的不懈追求之后,摄影似乎终于赢得了艺术的芳心,但摄影原来的那个梦中情人却死了。当代著名的艺术评论家阿瑟?丹托(Arthur Coleman Danto,1924—2013)在分析了当代艺术的现状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已经死了,因为当代艺术已经化身为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