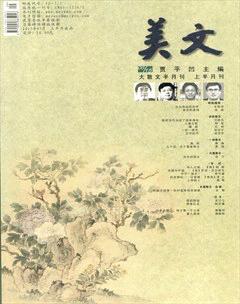想起路遥
2015-05-20吴兰兰
吴兰兰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转眼又到了2014年冬月17日。这是个特殊的日子,二十一年前的今天,一颗文坛巨星陨落了。青年作家路遥裹着严寒,带着他对生命的无尽渴望,对亲人的绵长悠思,对黄土地的深深眷恋离开了我们,年仅42岁。噩耗传出,震惊文坛,让高山锁雾,流水息声,让无数人为之哭泣、动容。
今天,当人们以各种形式又一次缅怀路遥,追思他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巨大贡献时,路遥生前与我们的一段交往、一段故事,让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二十多年了,我一直想将它付诸笔端以告慰亡灵。
那是1991年初春的一天,朵朵白云点缀着依然寒冷的天空,窗外的梧桐树上,几只小鸟在妈妈的声声召唤下,试图离开蜗居了一个冬天的巢穴飞上蓝天。我们突然接到了路遥的电话,说他要专程前来拜访。我和文兰无不惊喜,特别是我,赶紧从书架上取来路遥的《人生》翻阅着。那书页上的斑斑泪痕一下子将我带回到1983年寒冬那个夜晚。那是我第一次读《人生》,也是我第一次读路遥的书,是从晚上11点读起,直到第二天清晨六点。这是只有我读最喜爱的世界名著时才会有的状态。其间我数度哽咽。主人公高加林、刘巧珍缠绵凄婉的爱情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为书中人物的命运而揪心、悲悯、感伤不已。以至此后的几天里我常常会彻夜不眠。那一夜,泪水湿了脸颊、湿了头发、湿了枕巾,也震撼了我的心。很久很久,这本书都压在我的枕头底下,以便我随时翻阅。
其实文兰与路遥相识是在1981年他修改誊写《人生》最后一稿时,为了避免干扰,躲到了咸阳地区创作研究室来的(当时还没地改市)。那时创研室刚刚成立两年,租住在中医学院对面极其简陋的秦阳旅社二层,房子很小,约七平方米。每间房里只有一张老式三屉桌,一把木椅,一张单人木板床和一个脸盆。那时我还在兴平上班,我们属于两地分居,文兰在单位自然算單身汉了。路遥住在文兰隔壁,灶就搭在对面中医学院的学生灶上,因此每到饭时,文兰便夹着碗喊上路遥一块去吃,因为是集体灶,半小时开饭时间一过就关门了。路遥吃的很简单,每天中午一碗面条搞定。文兰急了:“路遥,你黑天白夜地熬,光咥一碗面咋能行?我去打些肉菜来。”被路遥一把拦住了说:“面条就挺好,在西安我也是一碗面条,有时换个花样,荞面凉粉或者凉皮什么的。可每天两包烟绝对少不了,够奢侈的,比起过去,我这已经是天堂了,不知你老兄咋样,我可是贫农出身啊!”说得两人都大笑起来。晚饭是稀饭馒头,一成不变,他一般都会多买一个馒头,以备写太晚了当夜宵用。就这样路遥坚持了十几天,直到《人生》修改誊抄完毕。十几天里,休息时文兰陪着路遥一起谝闲传、谝文学、谝创作,谝国内外风云变幻,也谝家庭。后来文兰经常感念与路遥这短暂相处带给他的愉悦。他说路遥是真诚的,是最值得交的朋友。
我的思绪飞得很远,文兰一把夺过我的书说:“你咋还愣着呢?一会儿路遥来,咱们去哪个酒店吃饭?你快准备一下。”我这才醒过神来。我们俩换好衣服,说等路遥一来就去酒店。可话音刚落,只听三声敲门,路遥已站在门口了。原本魁梧的身材消瘦了,着一身已经泛白的休闲装,手里提着个大塑料袋,由于坐公共汽车来,头发很蓬乱,脸色也有些苍白,屁股还没坐稳,便把手里的袋子往桌上一放说:“文兰兄、嫂子,我是专门谢你们来了。”他操着浓重的陕北口音继续说:“没啥拿,就三瓶酒,不成敬意。”说着又从挎包里掏出三大本《平凡的世界》说:“这书送给你们留个纪念吧,是第一版出的。”看着眼前三大瓶葫芦状的龙参酒,再看着路遥递过来的三大本还散发着墨纸清香的新书,我们真有点不知所措了。文兰赶紧说:“路遥啊,你这叫弄啥呢!我给红玲办事,是看重咱俩交情的份上,是为了给你老弟卸愁帽子呀!书我们收下,你提酒来,别说我不会喝酒,就是会喝也不喝这酒,要喝我舍命陪君子,咱上西安喝去。”我一边帮腔一边接过路遥递过来的书,抱在怀里爱不释手。看着路遥给我们的亲切签名,激动地说:“路遥,你是了解文兰的,他的口头禅就是为朋友办事两肋插刀。这书是多么珍贵的礼物啊!别人哪有这份殊荣呢。这酒你可就见外了,是万万不能收的。”路遥急了,不是一般的急,要生气的样子。他坚持说我们办事要花钱的,摊时间看脸色跑了路不说,让我们破费他心里不好受。就这样推来让去,酒还是留下了。后来那三瓶龙参酒一直放在我家的柜子上面,每当我看见它就想起路遥。这酒也让我困惑:路遥当时已经是中国文坛的星腕人物了:《平凡的世界》获茅盾文学奖;根据《人生》改编的电影大获成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可路遥却依然摆脱不了来自贫困家庭带来的烦恼与无奈。除了写作时是专注的,他用“焦头烂额”来形容自己的日子。不经意的谈话让我记忆犹新,不无惋惜。我想这大概就是路遥倾其毕生心血创作的动力吧。他深知生活在社会底层民众的疾苦与生存境况,他呼唤年青人为改变命运而努力奋斗,自强不息。无论条件多么艰苦都不能放弃,不能忘记自己的本分。“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这是路遥的座右铭。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提起路遥的愁帽子,这还得从路遥的侄女红玲说起。
红玲是路遥养父母家的一个侄女,十七八岁,聪明伶俐。是延川县卫生局首批派往陕西中医学院的定向生。所谓定向生,就是从哪儿来的,毕业后还回到哪儿去,说白了就是县上花钱为本地区培养人才。1991年,红玲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可这孩子说啥也不肯再回到延川的穷山沟里去,整天在路遥跟前哭哭啼啼,闹着要留在咸阳或者西安。这是多么难的事啊!虽说比路遥为弟弟王天乐办事时的大气候稍微好了点,但国家的政策是不容置疑的,红玲唯一的指望就是叔叔路遥了。路遥无奈了。劝也劝不了,眼看都毕业快三个月了,人还在空里飘着,隔三差五红玲就去磨叔叔一回。后来听路遥说,为红玲的事养父母那边非常生他的气,红玲的父母也很生他的气,他们以一个本分而老实的庄稼人的判断和思维方式来表达对这位养子、哥哥的责怪与不满。说他们为供路遥上学费尽了难肠,现在出息了、成名了,就不管娃娃的事了。这时路遥因写《平凡的世界》,身体能量透支殆尽,身心都已经极度虚弱了。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可他还不得不为酝酿《平凡的世界》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而作准备。为红玲的事他八方求助,也找了省上很多部门和领导,但都不了了之。可路遥亲戚却欲罢不能。不相信路遥那么大的名气“办不成这么个事,是你不想办!”万般无奈之下,王观胜提议去找文兰。路遥这才想起文兰,想起了咸阳还有文兰,于是,电话成了热线。路遥将他的难肠一五一十道给我们,以此来说服我们,好让我们有义不容辞之举。说实话这事情在当时是太难办了。我们先要把红玲的农村户口转到咸阳来,然后才能谈工作。第一步得先找到接收单位,前提还必须是延川县那边同意放人。可是那边坚决不放。记得当时我们跑断了腿的地方就是咸阳市人事局。我们天天都在为此事奔忙,能跑到的地方都跑了,能想到的关系一个也没放过,所幸大家都认为一个大作家也会遇到过不去的事,也乐意帮忙。终于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红玲的事总算有了眉目,给她解决了城市户口和干部指标。根据她的要求,进了当时很火的505集团公司,成了这个在国内外响当当的大企业的业务总管。消息传给路遥,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谢谢!谢谢!说我们可帮了他的大忙了,最后还不忘添上一句,改天一定去咸阳当面致谢。
就为兑现这一句承诺,路遥还是风尘仆仆地来了,带着他的喜悦,带着他的真诚,也带着些许无奈与酸楚。我在心里一遍遍为路遥鸣不平。路遥的一生注定是苦难的。因为上天让他无法选择地诞生在陕北高原的破窑洞里。那荒蕪贫瘠的黄土地是他的根。孟子曰: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苦难成就了路遥的辉煌,生命潜能的喷涌与宣泄让他深切体验着感恩、回馈、无私奉献的崇高与快乐。然而路遥悲剧的人生是不可逆转的。无私和奉献终究未能抵挡住苦难的摧残与折磨,尽管他从不漠视生命。他的英年早逝,给成功与辉煌蒙上了悲壮、哀伤的阴影。以路遥的才华与执著,以他对生命的诠释,以他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洞察与思考,他原本应该是无忧无虑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
那天在路遥的执意和坚持下,我们没有去酒店,在家吃的,油泼棍棍面,两盘素菜,是我亲手做的,路遥吃了一大碗。我们一边吃一边聊,他盛赞那是他吃的最好的面条,假如肚子还能盛下,他会再吃一大碗的。直到今天,我还在当时不知路遥不吃肉的情况下,为那天没来得及买肉,没给路遥做盘肉菜而追悔莫及呢。
1992年十月间,听说路遥肝硬化晚期住进了西安医院,我们的心里好一阵刺痛。因病情严重大夫已禁止探视了。文兰两次探望,每次给路遥的弟弟打电话,说明想看望路遥的焦虑。没想到得到的回话都说“可以进去”。
病房里安静极了,除了两张白色的单人床,重症监护室里用于急救的设备一应俱全。氧气瓶靠墙站着,稍息的姿势仿佛有些筋疲力尽。输液管里,白色的液体以钟摆的速度一滴一滴地流淌着。路遥紧闭双眼,脸色蜡黄,显得非常虚弱。弟弟俯下身去轻轻地说了声“哥,文兰来了”。路遥微微地睁开眼睛,目光里含着亲切与向往,含着一个生命垂危者对于生的渴望与期待。双腿在被窝里抽搐了几下试图坐起,弟弟和文兰赶紧上前阻止。这时,路遥用他那微弱的声音一字一句地告诉文兰“要爱惜身体”。文兰默默地点着头,激动的话语哽咽在喉,一句也说不出口。此时此刻,安慰已显得那么软弱无力,微不足道。无声在三个男人的世界里凝固了,慢慢地成为永恒的记忆。
半个月后,文兰还去过医院一次,他说哪怕是在路遥病房门口站会儿,他也要去,他想带去我们的祝福与祈祷。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与路遥的最后一面!仅仅过了二十天,在西安三兆殡仪馆,文兰参加了路遥的追悼会。当文兰绕着路遥的遗体告别时,竟抑制不住,失声痛哭起来。直到低头走出吊唁大厅,眼泪也没止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