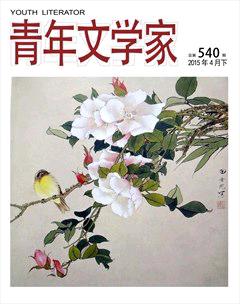论萨达姆的战争修辞
2015-05-09陈玮
摘 要:当代新亚里斯多德主义修辞学对演讲实践有了全新的发展。本文对伊拉克军事领导人萨达姆在海湾战争发表的广播讲话进行分析,分别从论据、组织结构、文体、记忆和现场发挥五个层面展开论述,最后对其演说效果做出深刻分析。
关键词:新亚里斯多德主义;听众;演讲效果
作者简介:陈玮,1978年1月出生,男,福建福州人,讲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语用学,认知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12--02
前言
20世纪以来,当代修辞学批评的发展如火如荼。1925年维切恩斯的《演讲文学批评》一文的发表,正式掀开了当代修辞学批评的序幕。该文提供了修辞学批评的具体原则——新亚里斯多德主义批评原则。作者提到了三种论据:演讲者的人格因素、观众的人性和讨论问题的判断;涉及了西塞罗和昆提连所说的修辞五因素。在1948年出版的《演讲批评》中,作者桑森和白爱德提出了典型的维切恩斯式的批评方法:修辞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则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一场演讲是演讲者、主题、听众在具体的场合下相互作用的结果;评论家的最终目的是弄清者场演讲的影响如何。1954年霍齐姆斯在《修辞学批评》中再度强调了新亚里斯多德的评论准则。她列举了修辞学批评要研究的六个方面,其中有在规劝情境中的演讲者,听众对他有没有好感;有听众,他们的观念、情感、倾向性等;有演讲的内容,如何运用修辞论证,如何表达理念的。最后是“效果说”。1968年,比彻尔发表了《修辞情景》,该文的发表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议。他对“修辞性话语”提出以下观点:修辞性话语的产生依赖于修辞性的情景或环境,即突变的环境往往给修辞性的话语带来契机。比彻尔认为以下三个因素构成了“修辞性话语”:事变状态,积极参与的观众和种种制约因素。
综上所述,新亚里斯多德主义修辞学理论及其批评实践是遵循亚里斯多德关于“在每一件事上运用可以规劝的能力”。批评实践则从演讲者出发,从三个方面入手:理念方面、人格方面和情感方面。除此之外,则从构思、组织、风格和实际演说等方面来考察。
1990年的波斯湾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领导的盟军和伊拉克在两个战线展开战斗。为了对盟军展开反击,萨达姆通过媒体对盟军展开言论攻势,成功地取得了阿拉伯民众的同情和支持。
本文拟用新亚里斯多德批评主义观点,来检验萨达姆的战时讲话对伊拉克本国人民及邻国人民的影响效果,所选用的讲话是萨达姆于1991年2月在无线电广播中发表的。
(一)演讲的语境
了解萨达姆的背景信息有助于受众理解其海湾战争时演说的动机及性质。首先,萨达姆是穆斯林信徒,他演说针对的听众也是穆斯林。在他的演讲中,他极力赞美安拉。其次,作为伊拉克的军政领导人,在广播演讲中萨达姆极力维持自己的权力和威望,表现了他有控制和支配别人的欲望。再次,从无线电讲话发表的场合看,由于当时盟军的空中优势,伊拉克军队的作战情绪不高。为了提振伊拉克民众士气,并寻求阿拉伯国家对伊拉克的支持,萨达姆通过无线电短波不定期地发表讲话,向人民发布一些有战争价值的消息。萨达姆广播讲话所针对的阿拉伯听众和萨达姆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和世界观。对于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阿拉伯听众有相当强烈的反感,因而萨达姆的演讲激发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二)萨达姆广播讲话分析
萨达姆在他的广播讲话是如何运用修辞学的以下五种方法“1)论据适当; 2)组织结构;3)文体; 4)记忆;5)现场发挥”来实现他的演讲目的呢?
首先,《可兰经》是萨达姆演讲的逻辑根据来源。在萨达姆的广播讲话中,他通过《可兰经》和安拉来证明“进攻科威特”是合理的。在阿拉伯社会的阿拉伯文化里,如果一个人能够在没人反对或几乎没人反对的情况下采取行动,那么,在安拉的眼中,这个人就被认为是正确的,这个人的行动就被安拉证明是合理的。因为萨达姆的军队在几天之内就成功占领科威特,几乎没遭到什么反抗,阿拉伯逻辑就认为萨达姆在上帝的眼中一定是正确的。
通过这种逻辑萨达姆证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行动是合理的,萨达姆在他的广播演讲中,表明自己有权占领科威特。例如,在盟军空袭开始后不久,他在广播中做的第一个公开声明中说:“上帝赋予我们力量和权利去除掉科威特又腐败又罪恶的领导人。”因此,萨达姆在演讲中表明“是安拉给他权力去征服科威特,去纠正科威特的错误”。通过宗教的方式,萨达姆努力在伊拉克人民及邻国人民中构建一种阿拉伯民族精神。
萨达姆的第二个论据是“伊拉克人一直都认为科威特是伊拉克的一部分”。这源于部落冲突时期,那时贝都因人因为季节的不同而在中东地区迁徙。伊拉克人普遍认为“现在科威特所处的那片土地属于现在伊拉克人的祖先的”。因此,科威特实际上就是伊拉克的领土。萨达姆利用了这种想法,为他占领科威特的行为提供证据。
最后,萨达姆在他的无线电讲话中始终强调一个论据, 他号召其他阿拉伯国家帮助伊拉克击退干涉阿拉伯事务的“邪恶的”西方社会。他从两方面阐述这个论据:1)他尝试向其他阿拉伯国家灌输或强化一种种族偏见;2)他努力把以色列卷入阿拉伯国家冲突中从而转移公众对科威特问题的关注。
在广播讲话中,萨达姆号召其他“阿拉伯兄弟”帮助伊拉克“击败并羞辱”美国及其盟国。萨达姆用理性、民族精神、感染力来阐述这个论据。他在演讲中强调阿拉伯“兄弟们必须团结起来打退邪恶的布什及其走狗”。萨达姆认为所有阿拉伯兄弟们,不管他们过去发生过什么样的冲突,都应该团结起来:“在安拉的眼里,你们全都是阿拉伯兄弟。我们必须走到一起来,摆脱危害我们土地的险恶形势。”
在广播演讲中萨萨姆成功地构建一种民族精神。他的策略就是不断地强调所有阿拉伯人民都是“兄弟”,都是穆斯林,他们必须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并肩战斗。他表明自己是穆斯林,也是阿拉伯人,这样,他为自己的侵略科威特行为提供了依据。为了同样的理由,他的演讲也带有感染力的种种迹象。由于萨达姆和伊拉克人民既是穆斯林又是阿拉伯人,他期望能激发起其他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同情,使他们能和伊拉克站在同一阵营。
另外,萨达姆还试图把公众关注点从科威特冲突上移至巴勒斯坦问题上,以号召阿拉伯人和“邪恶的”西方社会斗争。他尝试提出阿拉伯文化中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从而把其他阿拉伯国家卷入这场冲突中。也许意识到其他国家对参加他的“圣战”持保守态度,萨达姆提出承诺,拟帮助巴勒斯坦人从以色列手里重新夺回“原本就是他们的”土地。这是萨达姆所采用的一个权谋,用来推动其他阿拉伯国家和伊拉克一同作战。基于这个理由,萨达姆可被视为试图解决巴勒斯坦争端,并从而有助于阿拉伯民族精神的领袖。因为他提出了一个所有阿拉伯人都关注的问题,他可以被看做是为了所有阿拉伯人民的利益而抗争的领袖。
演讲的组织结构
通观萨达姆的广播讲话语篇的组织结构,我们可发现一种恒定的模式:每篇演讲开头都要从《可兰经》中引一段话或转述一段话。然后是赞颂伊拉克人民有力量有勇气,能经受住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的空袭。他还请求伊拉克民众放心,许诺伊拉克最终会占上风,会取得胜利。萨达姆在讲话快结束时总要抨击西方盟国。他使用的独具感情色彩的词语有“邪恶腐败的社会”或“邪恶的总统布什”等,以激发阿拉伯民众对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的仇恨。最后,他再次号召其他阿拉伯人们加入到伊拉克发动的这场战争中,从而帮助巴勒斯坦人民。
演讲所使用的文体
萨达姆在讲话中所用的文体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使用的是古典阿拉伯语,而不是其他阿拉伯方言,这种文体使他具有威信。作为伊拉克的外交语言也是它的宗教语言,使用古典阿拉伯语就能树立一种威严而高贵的形象。为了说明这种阿拉伯语文体的效度,让我们假设这种文体用在西方社会演讲中。美国总统向全国发表讲话时会有意使用一种较正式的文体,因为这种文体适合其领袖身份。使用古典阿拉伯语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在阿拉伯人心目中,一个领导人使用这种文体既有说服力又合乎身份。
为了确保阿拉伯人们都能听懂他的讲话,萨达姆向他的受众阿拉伯人使用古典阿拉伯语。阿拉伯语有许多特点鲜明的方言。因为古典阿拉伯语是阿拉伯国家的学校普遍教授的语言,因此,所有阿拉伯人,都能听懂萨达姆的讲话。
因为古典阿拉伯语文体就是《可兰经》所用的书面语言,萨达姆使用这种文体使他作为宗教权威有一定可信度。萨达姆宣布这场战争为圣战,他使用神圣的语言更加深了这一印象。从本质上看,萨达姆使用古典阿拉伯语是想树立自己受安拉保佑的宗教领袖形象。
萨达姆的现场发挥
在广播演讲时萨达姆给听众一种权威感。他的现场挥生动又活泼,尤其是他朗读《可兰经》时,更是如此。事实上,他的现场发挥给人一种印象,即他十分热衷于这项事业。
笔者认为萨达姆早在实际发表讲话之前就开始精心筹备演讲。他的讲稿用词谨慎,唯恐得罪任何伊拉克潜在的盟友。另外,他使用格外生动的语言来谴责美国(例如“他们如此冥顽不化,必将淹没在自己的鲜血中”,或者“安拉必将降尘土于邪恶的机器【盟军的战争机器】,从而保护穆罕默德真正的追随者”),这一切表明在讲话发表之前,他已做了精心准备。
记忆
记忆是笔者用来分析萨达姆无线电讲话是否有效的最后一个标准。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笔者认为这些讲话在发表之前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偶尔,萨达姆在某些地方结巴一下,然后很快恢复正常。
(三)萨达姆演说效果之评价
创造让听众过目不忘的讲话只是萨达姆演讲术的一个目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他的讲演术是否有效地达到预期目标。尽管伊拉克的军事战争没有获胜,但笔者认为在论战中萨达姆的讲演术略胜一筹。虽然阿拉伯国家没有帮助伊拉克,但萨达姆已经成功地赢得了穆斯林国家甚至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同情。最令人难忘的一个例子是美国轰炸了伊拉克一个“居民区”后,萨达姆严厉指责美国故意杀害无辜平民,许多阿拉伯国家都宣布自己站在他的立场一边,表达对美国这次行动的不满。萨达姆试图处理巴勒斯坦问题,还试图同俄罗斯签署一项和平和约,这些都对他的对话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伊拉克试图处理阿拉伯社会都关心的政治问题,并试图提出和平的解决方法,这些都引起了人们对伊拉克的同情。
萨达姆的讲话的确激起了阿拉伯人的自豪感。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和其他新闻单位的报道表明,许多阿拉伯人认为伊拉克领袖萨达姆试图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并为“阿拉伯人民”的利益同盟军战斗,是一种英勇的行为。他们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再次成为公众关心的热点,使得阿拉伯人树立团结和“兄弟情谊”的观念。
萨达姆通过他的演讲打动了他所针对的听众,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许多其他国家的阿拉伯人愿意参加伊拉克军队,为萨达姆而战。再一次,阿拉伯“兄弟情谊”被萨达姆利用,成为有利于他的政治话题。
参考文献:
[1]Aristotle, Rhetoric, in Rhetoric and Poetics of Aristotle, tran. W. Rhys Robert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4)
[2]Lester Thonssen and Craig Baird, Speech Critic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8)
[3]Marie Hochmuth, “The Criticism of Rhetoric” in History and Criticism of American Public Address. Vol. 3, ed. Maria Hochmuth (New York: Longman, Green, 1955)
[4]Donald Bryant, “Rhetoric: Its Scope and its Func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39 (1953):404
[5]Lloyd Bitzer, “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1 (1968): 2.
[6]姚喜明,《西方修辞学简史》,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
[7]袁影,修辞新模式构建;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5月1日
[8]胡春阳,传播的话语理论;复旦大学博士伦文,2005年4月20日
[9]滕慧群;霍君;“现代汉语话语超常衔接的形式与功能“,《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1月25日
[10]余芬芬;张萌,“从修辞情景角度看列宁的党报思想”, 《新闻世界》,2012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