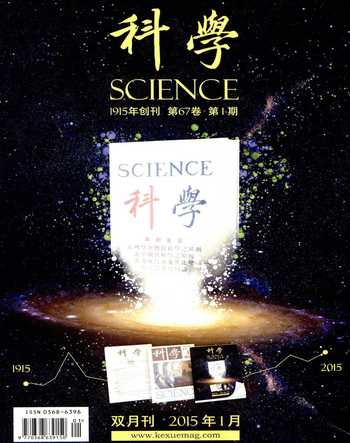突破光学衍射极限:实现远场纳米级分辨的光学显微镜
2015-04-29倪洁蕾程亚
倪洁蕾 程亚
由于光学衍射极限,远场光学显微镜的分辨率仅能达到光波长的一半左右。在可见光波段,这一极限大约为200纳米。而对于生命科学研究,往往需要数十纳米甚至更高的分辨率,以获取组织或活细胞内部精细结构的信息。2014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解决了这一世纪难题。
2014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在超分辨光学显微镜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的三位科学家:贝齐格(E.Betzig)、黑尔(S.W.Hell)和莫纳(W.E.Moerner)。对于很多同行而言,这件事既在意料之中,却也颇显意外。
西方人有一句谚语:“Seeing is believing(眼见为实)。”因此,成像与观测领域的重大突破一直为诺贝尔奖所青睐。300余年前,当荷兰科学家列文虎克(A.van Leeuwenhoek)利用自己搭建的显微镜观察水珠时,他意外地发现了悬浮在水滴中的细小浮游微生物,从此向世人打开了进入微观世界的大门。从几何光学角度看,通过合理设计光学成像系统,光学显微镜具备实现任意放大倍率的能力。然而,人们身处的世界在本质上是量子世界,最终一切物质都必须用“波”的概念来描述,对光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当人们利用光波来进行显微观测时,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为光学显微镜的分辨率设置了一道屏障,即光学衍射极限。
自从1873年德国科学家阿贝(E.Abbe)首次提出光学衍射极限的概念开始,直到20世纪末,人们一直认为光学显微镜所能够看清的物体的最小尺寸大约为光波长的一半左右(对于可见光而言,这一极限尺寸大约在200纳米)。这意味着科学家们可以辨别完整细胞,以及其中一些被称为细胞器的组成部分。然而,他们却无法分辨一个正常大小的病毒或者单个蛋白质。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对于很多一流的光学科学家,他们也已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认为突破光学衍射极限在理论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正是得益于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奖者提出的开创性成像新概念,这一状况才得以被奇迹般地终结。
值得注意的是,阿贝的光学衍射极限概念是基于光波自身的波动本性所得到的,而当代很多的先进光学显微技术往往借助于光与物质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各种奇特效应来实现,这为突破光学衍射极限打开了缺口。迄今为止,成功实现超分辨的途径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对激发光进行整形,再结合材料对光的非线性响应来减小光斑,例如受激发射损耗方法(stimulated-emission-depletion,STED)和结构光照明显微镜(structured illumination microscopy,SIM);另一类就是借助单分子成像技术,光激活定位显微镜(photoactivated localization microscopy,PALM)和随机光学重建显微技术(stochastic optical reconstruction microscopy,STORM)是其中的代表。
受激发射损耗
黑尔自1990年在海德堡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就一直在寻找突破衍射极限难题的方法。1994年,黑尔发表了一篇论文阐述了利用受激发射来操控荧光分子的想法。在他设想的技术方案中,显微镜(也称STED显微镜)利用荧光分子作为成像对象的标记物。荧光分子的特性是可以被一束波长较短(即光子能量较高)的光束激发,然后发射出波长较长的荧光。正如人们感觉黑夜中穿着荧光衣的人特别显眼,荧光标记使得感兴趣的观测对象在复杂的生物结构中脱颖而出。
黑尔的方法是通过扫描一束激光聚焦焦斑来对样品进行逐点成像,成像的分辨率取决于焦斑内所能够激发的荧光分子占据的体积。因此,为了缩小荧光激发体积,他采用了两束组合激光,即一束光被聚焦成正常的衍射极限焦斑,将焦斑内的荧光分子抽运到激发态;而第二束光则选取在荧光分子的发射波长范围,并被聚焦成一个中心与第一束光的焦斑中心完全重合但却是中空的环状焦斑。第二束光可以将被第一束激发光抽运到激发态上去的荧光分子从激发态淬灭到基态,因此也被称作淬灭光束。由于淬灭光束的光强分布仅在几何焦点处为零,因此从原理上讲,只要淬灭光足够强,由第一束光激发的荧光分子所占据的体积几乎可以被无限制地压缩到几何焦点附近极小范围内。目前,利用该方法可将光学显微成像的分辨率推进到数十纳米的尺度,远远突破了光学衍射极限的限制。相比传统的共聚焦显微成像,STED成像技术提供了高得多的光学分辨率,将神经元的细节清晰地显示出来。
相对于其他光学超分辨成像技术,STED技术最大优点是可以较快速地观察活细胞内实时变化过程,这对于生命科学中很多实际问题的研究十分关键。2008年,黑尔等人在美国《科学》上发表文章,报道了以视频速度(28帧/秒)来采集记录神经细胞内突触小泡的高分辨率图像(62纳米)。2012年,他们又利用STED显微成像法记录了活体老鼠脑细胞内神经细胞间的突触运动,该项工作有助于理解突触的运动机制,并可能促进针对突触内的精神治疗药物研究获得突破。
黑尔是首位不仅从理论上,而且用实验证明了使用光学显微镜能达到纳米级分辨率的科学家。但黑尔早期的文章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轰动,即使是非常著名的显微领域科学家仍然对此抱怀疑态度。如德国科学家施特尔策(E.H.K.Stelzer)于2002年在英国《自然》上发表文章,对黑尔发明的STED技术是否从本质上突破了衍射极限表示怀疑。并用坚定的口气写道:“眼下有一件事仍然是对的:海森伯(的不确定性原理)是正确的,阿贝极限肯定不会突破。”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由于100多年光学衍射极限理论的统治地位,人们在思想上已经形成了很深的思维定式。
单分子技术与光激活定位显微镜
莫纳在1989年任职于美国IBM研究中心时,首次在凝聚态相中实现了单个分子的光吸收测量,这项工作吸引了大量化学家将注意力转向单分子研究。两年之后,他与另外一个博士后安布罗斯(W.P.Ambrose)利用荧光实现了单分子成像。1997年,他与因绿色荧光蛋白的发现而获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的钱永健合作,发现了绿色荧光蛋白的光转化效应。这一发现使得控制荧光探针的发光成为可能。以光激活荧光蛋白分子为例,当受到波长488纳米的光激发时,该荧光蛋白开始发出波长更长的绿色荧光,直至被淬灭(淬灭的荧光分子将不再有发射荧光的能力)。如果此时利用一束405纳米的激光照射该荧光蛋白分子,可以将该分子再次激活。激活之后的荧光蛋白如果被488纳米的激光照射,又能恢复发射荧光能力。简言之,利用488纳米和405纳米两种波长的激光,可以交替实现这些荧光蛋白分子的“开”和“关”状态。
这一发现对贝齐格至关重要。贝齐格注意到光学衍射原理虽然不允许人们同时分辨间距小于大约激发光波长的两个荧光分子,但一旦两个分子的间隔增大,从光学上讲,它们都分别可以无限高的空间精度被定位。早在1995年,贝齐格就发表文章提出用不同颜色荧光分子来绕开衍射极限。但由于分子合成与标记等方面的实际操作困难,无法从实验上加以验证和实现。2006年,他意识到,其实不需要不同颜色的光,只需借助莫纳的单分子技术,让荧光分子在不同的时间发光,就可以实现超分辨成像。于是当时赋闲在家的贝齐格和赫斯(H.F.Hess)利用一部在自家客厅组装的光学显微镜搭建出这样一套显微系统,称之为光激活定位显微镜(PALM)。他们使用微弱的光脉冲激发荧光分子,使其中极小部分的荧光分子能够发出荧光。因为这些荧光分子很稀疏,相距较远,所以它们的位置能够被精确定位。等到这些分子光致褪色后,再继续用微弱的光脉冲激活另外一小部分荧光分子,让它们发出荧光。通过分别记录多幅图像,使不同图像中的荧光分子所成点像不再相互干扰,从而能够对每个荧光分子逐个进行定位。在全部荧光标记分子的定位完成后,一幅超越衍射极限的图像即已形成。随后他们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及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科学家合作,利用该新技术对生物样品进行成像,在每平方微米塞满高达十万个分子的细胞样品中,成功分辨出相距仅2~25纳米的分子,在细胞片足(lamellipodium)内的肌动蛋白(actin)、黏着斑蛋白(vinculin)、细胞膜上的反转录病毒(retroviral)蛋白Gag等方面取得高清晰成像。
2008年,贝齐格等人将PALM显微技术应用于活细胞成像来记录细胞黏附蛋白的动力学过程。2010年,赫斯小组将PALM技术与光的干涉原理结合起来,发展成干涉测量光激活定位显微技术(iPALM),将三维的分辨率提高到20纳米以内,在纳米尺度上观测到了黏着斑(focal adhesion)的蛋白组织方式,为分析蛋白功能提供了新的信息。
随机光学重建显微技术
作为第一位获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的华人女科学家,庄小威在生物物理显微成像领域做出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几乎与贝齐格提出PALM概念同时,庄小威也提出了原理相似的随机光学重建显微技术(STORM)。STORM与PALM不仅是同年提出,原理也极其相似,都是通过反复激活一猝灭荧光分子,使显微镜每次只记录相距远的几个荧光分子,从而对它们进行精确定位,通过光一化学手段,以时间换空间方式获取了超分辨。与PALM不同的是,庄小威使用的是有机荧光分子对,而非光激活蛋白。他们发现,不同的波长可以控制化学荧光分子Cy5在荧光激发态和暗态之间切换,例如红色的633纳米激光可以激活Cy5发射荧光,同时长时间照射可以将Cy5分子转换成暗态不发光。之后,用绿色的532纳米激光照射Cy5分子时,可以将其从暗态转换成荧光态,而此过程的长短依赖于第二个荧光分子Cy3与Cy5之间的距离。因此,当Cy3和Cy5交联成分子对时,具备了特定的激发光转换荧光分子发射波长的特性。
2007年,庄小威研究团队进一步发展了多色随机光学重建显微方法,并以20~30纳米级别的分辨率演示了DNA模式样品和哺乳动物细胞的多色成像,研究结果公布在《科学》周刊上。2008年,他们在《科学》周刊上展示了用3D STORM成像技术拍摄的肾细胞内微管结构图和其他的分子结构图。2011年,庄小威与另一位华人科学家谢晓亮,利用超分辨率荧光显微镜对活体大肠杆菌细胞内的拟核相关蛋白(NAPs)进行了跟踪观察,并由此揭示了细菌遗传物质组织机制。2012年,庄小威小组对STORM进行了改进,通过双物镜STORM,在生物成像中获得了小于10纳米的横向分辨率,以及小于20纳米的纵向分辨率。采用这种方法,他们对细胞中的微丝进行了成像,揭示了这种重要细胞骨架的超微结构(微丝是由肌动蛋白组成的直径约为8纳米的纤维结构)。2013年,他们又利用STORM的技术优势,分析了神经细胞中肌动蛋白、血影蛋白(spectrin)等相关蛋白的组织结构,提出了关于细胞骨架结构的新假说。
庄小威研究组利用STORM等技术获得了不少关键分子的结构,为超分辨的发展和推广应用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次她未获诺贝尔奖,其中的是非曲直,科学界人士各有说法。
结构光照明显微镜
2000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物理学家古斯塔夫森(M.Gustafsson)领导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了结构光照明显微镜(SIM),并得到了海拉细胞中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的图像,相比传统显微镜的图像来说,在横向上的分辨率提高了2倍。结构光照明显微镜利用调制光源照明样品。将原本不可分辨的高分辨率信息编码入荧光图像中,结合计算解码获取高分辨率信息,其过程可以通过光学莫尔条纹来理解。莫尔条纹是指由两种具有精细结构的图形叠加之后出现的比较粗的干涉条纹。在结构光照明成像中,具有精细结构的样品和调制照明光场都有很高的空间频率,难以直接分辨,但是其叠加产生的粗条纹(莫尔条纹)却具有很低的空间频率,可以直接被分辨。由于调制光场是已知的,通过测量莫尔条纹就可以反推出样品的精细结构。SIM技术同样也生成了许多美丽的高清晰细胞图像。
2005年,古斯塔夫森又利用荧光分子的饱和吸收特性,发展出饱和结构光照明显微技术(SSIM),将整体分辨率提高了4倍。
结构光学显微镜在宽场成像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简单、具有快速获取图像能力的超分辨成像技术,为生物组织纳米结构的活体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遗憾的是,古斯塔夫森于2011年因癌症去世,享年51岁,无缘此次的诺贝尔奖。
展望
由于上述光学先驱的贡献解决了光学显微成像领域中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难题,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其科学意义显而易见。早在十年前,不少同行学者已认为光学超分辨成像领域的几位先驱将有望获诺贝尔奖。事实上,当时人们甚至比现在更为乐观,认为这些技术能很快达到小分子级的成像精度,从而给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带来根本性变革。然而,随后的研究发现,虽然理论上具备了潜力,但在技术上彻底实现这一目标仍存在诸多挑战。因此,超分辨光学成像领域的后续发展空间仍十分巨大,孕育着新理论、新技术,并有着在生命科学、纳米科学等相关领域获得进一步广泛应用的诸多机会。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在实现这些美好愿景尚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将2014年度的化学奖颁给该领域的科学家,略显意外。简言之,即使该领域在短期内很难被再次授予诺贝尔奖,仍有望产生诺贝尔奖级的研究成果。
长期以来,诺贝尔奖评奖的大致标准还是比较明确的。首先是关注研究成果的原创性,一般都是奖励给一个研究领域中最早的概念提出者或是核心现象的发现者。那些针对后续问题开展跟踪性研究的同行。即使也曾做出卓越的贡献,但往往丧失了获奖机会。其次是关注这些原创成果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产生的影响力。影响力的产生主要来自于两方面:或者是通过重要科学发现来加深人们对宇宙或自然规律的理解,或者是通过重大技术发明推动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相比于在那些已获认可的热门领域开展跟踪性研究。从事原创性研究面临着更高的风险,并且即使能够成功,短期内其价值也未必能迅速获得认可并产生充分影响。扭转这一状况,促进开展那些可能产生显著影响力的原创研究,可能需要更加包容的氛围。以促进思想和理念的多样化;需要更加宽松的环境,以降低功利的影响并鼓励独立的科学判断;还需要撇弃浮躁的心态,容许科学家长久地专注于那些有挑战性的科学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