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与畸零人同行
2015-04-29朱又可
朱又可
张炜的《你在高原》中的主人公宁伽,无聊时喜欢让街头的人算命,有一次被人用“揣骨法”算过:摸按头部和其他部位,以判断命运。当算命先生按过他的脚时,马上叹息一声:“你长了双流离失所的脚哇!”
“其实这样的经历我也有过,当时听了那声长叹真是害怕,看看四周围观的人,赶紧走开了。”张炜说。“我后来故意不出远门,以便躲开那句危险的预言。可是我这人从小走惯了,真的闲不住。”
他回想这几十年来,小时候生在海边林子里,大多数时间在荒野林中奔跑;十几岁时又离家去了山东南部山区,从那时起就常常是一个人了,许多时间都是奔走在旅途上的。特别是近二十多年在东部半岛上来回行走,一方面是为《你在高原》做些实勘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停不下来。
“这些年来我遇到多少有意思的、难忘的人与事,它们都算我一路的酬劳。”
张炜在二十多年间游走半岛,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比如他在小说中有个人物,是一位知识分子,父亲是一个高官,但他抛弃了如花似玉的妻子,跟着一群乞丐去流浪,不知所终。就像意大利亚西西的圣人方济各一样,赤身裸体地离开富商的家庭去当一名贫僧。
张炜在游走中,颇为羡慕那些背井离乡的流浪汉,他有时跟他们籍天席地而卧,当然,游走时,他是带着帐篷和一副地质队员的野外装备的,里面工具齐全,能应付一切不虞之需。他赞赏和怀念那些社会难以理解、极其顽强和乐观的人。他往往在后来条件相当好、有小车接送的情况下,走到半路上,弃车而行,拐进山里,一个人翻山越岭重新体验孤独穿越的况味。张炜说他有这么个癖好。
他爱跟脱离正常生活轨道的流浪汉、畸零人为伍,跟逃离社会的隐士同行。他觉得这些人才属于真正的民间。张炜考察他们大约是这么几个原因形成的:一是逃避计划生育,再就是身上有什么案子;还有的是跟整个家族闹纠纷,因为械斗打散了才跑出来的……反正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与世隔绝了。这一类人聚在一起就形成了特殊的部落,中间有一个男人或女人像酋长一样管理大家的生活。
他曾经认识一个人,这个人离家几十年,当年是因为一个政治事件,一直跑到了深山老林里。后来社会发生巨变,当年的案件都不成立了,他却一点都不知道。当他胆战心惊摸回老家去,一看家里人全都不在了,就跪在地上哭了。他在外面的几十年多不容易,简直就像鲁滨逊。
为了完成《你在高原》这个艰巨的写作任务,朋友给他找了一个“三线”建设时期的房子——筑在大山深处的一处废弃不用的变电所管理房,它建在山岭的一小块平坦地方,又沿山势修成了一个大大的院落,里面有救火池,有几棵巨树。一溜宽敞的大房子都空了,里面有几张陈旧的办公桌,几件破损的大皮沙发。
这里安静得就像另一个星球。无数的野物一天到晚光顾这个院子,竟然不怕突然住进来的这个客人。兔子和獾,一群群的喜雀,有时会互不相扰地在窗外转悠。一些鸽子飞到窗台上往里看,想知道客人的一些秘密。张炜只有一些书、一叠纸和一支笔,它们歪着头瞅来瞅去,一时不得要领。他向它们打着手势,它们并不害怕。
到了夜里,这里的天空清湛得没法形容,星星又亮又大,仿佛从未有过地逼近了地面。张炜心里充满了感激,不光是感激朋友,还有另一些说不出的东西——它们也许是遥远的神灵之类,是无限远处的什么。他说:“我多年来被纠缠着的一些东西,这会儿都在心中化掉了。我可以安静下来了。”
张炜说,他要避免自己成为腐殖质,而提醒自己从腐殖质中努力长成一棵大树。“占领山河,何如推敲山河。”占领会被占领物腐蚀掉,而在山野间跋涉、推敲,甚至与畸零人为伍,才会不忘一个人的初衷。张炜说,《你在高原》里这方面的内容有60万字删掉了,他打算再版时补上:
“事实上这种痛苦是很沉很沉的一根弦,任何杰出的书里都应该埋一根老弦。中国的弹拨乐有中弦、子弦、老弦——子弦就是最细的弦,老弦就是最粗的那根弦。光有细弦的尖音,拨响了很刺激人,很多人听了以后会振作,很提神很惊讶。但是老弦弹拨一下,会把心底振动,会轰击心灵。所谓的1950年代生人的悲凉、痛苦、绝望、沉沦,让我们站在边上的第三者看起来,都会有一种大痛。删去60万字,影响了这根老弦的鸣响。不过这根老弦仍然在弹拨,它仍然引起那种震耳欲聋的和声。老弦自己会鸣响起来,低低的,有人会在午夜里听到,并且坐起来望着窗外的夜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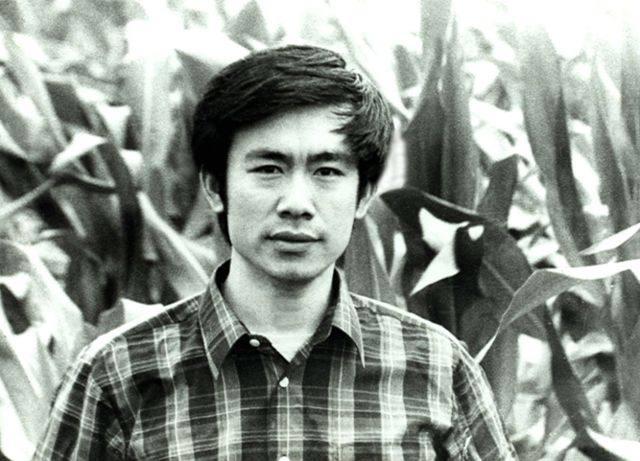
我经历了几十年的写作之后,很想让作品“回生”
《青年作家》:1980年代初,当时你为写《古船》去跑,和后来写《你在高原》的“跑”,两者有什么不同?
张炜:那时候的跑,着眼社会层面比较多,比如要了解四十年代那些变革的过程,其失误和动荡,惨烈程度等等,要搜集很多资料。再到后来就不完全这么简单和直接,这与个人的文学演变及发展有关。四处游走,到各地去,打捞的不再是单纯的层面,而是全面了,比如说民间文学,天籁自然。这就跟少年和童年的很多感觉接起来了。这跟《古船》时期是不一样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差别也在这里。1980年代是依附和依赖当时的社会气氛,后来经过了跌宕、经过了漫长的所谓“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文化界经历了反思、松弛和进一步的视野开拓,想得就多了。个别人有可能将少年生活、青年奋斗,还有写作和阅读,整个一摊子文学现象和历史源头一下子衔接起来。
写《古船》的时候,去半岛地区搜集材料,直接到胶东的粉丝厂,了解它的收入如何、领导结构如何、一个镇子的政治和经济情形、它的历史。比如具体到土改,死了多少人、重要的事件有哪些、冲在前边的人是哪一部分、这部分人现在到哪里去了。目标明确,而且社会性很强。
今天走到海边或山里,对海浪的声音,迷茫的山雾更加留心。晚上在帐篷里看天空亮着星星,它们像燃烧一样,一颗一颗,这在城里是看不到的,因为灯光污染,不会有这种感受。在旷野里,一下子唤起了少年的记忆。这一切作为文学的因素,显然无比重要。尽管与社会层面的东西拉开了距离,却更有意义了。
《青年作家》:1980年代跑的时候,也看到山林、自然,但对这个留意多吗?
张炜:当年出发的目的过于明确,再加上没有那样的觉悟和情怀,会忽略掉重要的东西。人的情怀决定了许多,过去有一句话:看山则情满青山,说的是人的感情把大山包容了弥漫了。当一个人情怀不够、觉悟不高的时候,同样到一个地方,收获就不会太多。当然后来的走和1980年代的走,也有一个延续性,是更加走向了深入,有了大量重新探索和注意的角落,对于民俗部分、海洋动力学、植物学、考古学,包括造酒,都感兴趣。我把各个门类的学问功课和实地勘察结合起来。而以前行走的趣味性不如后来,包容性不够,大量与当时的写作似乎没有关系的东西,不太注意。
《青年作家》:怎么去想到要写这么一个大的东西?有什么文本参照?
张炜:文本参照没有。尽管阅读中也有像《追忆似水年华》、《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这些作品,但都不是作为范本对待的。当年写完了《古船》,《九月寓言》也基本完成了,暂时不太想去写一般的单行本。心里各种各样的情绪,包括几十年来的行走所积累的,需要有一次大的释放。
我需要极其浓烈的奔放的、更为吸引我的什么——它除非是巨型的创作而不能够完成。人生经验、激情,全部的文学手段的使用,是它们的一次集合。1988年之前就有这种想法。我1975年发表作品,从写诗,那么凝练的形式,最后到散文,再到短篇小说,再到中长篇小说,从篇幅上看是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再往前走就是这样庞大的计划了。一开始我以为十年就可以完成。
《青年作家》:当时设计十卷?
张炜:我知道大约有几百万字,结构起来才知道有多少卷,觉得这个工作可能要干十年——那时候年轻,敢想敢干,同时会把困难想得比较少。但是巨大的劳动量放在那里,具体做起来会发现许多地方需要投入相应的劳动,那是减省不得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两方面在改变,一是个人劳动的速度在减慢,再就是对于各种事情会想得更细更周到。这两个方面的改变就使这个书拖了很长时间,再加上疾病,身体更加不如过去,结果最后写了二十二年。
《青年作家》:那时候有了想法之后,开始动笔写了,还是要跑?
张炜:我从1986年写《古船》、《九月寓言》的时候就在做这部长卷的准备,当时还写过一些片断,一些笔记本积了一大摞,行走的间隙里要写,回到书房里也要写。那都是比较激动人心的片断、一些突如其来的思绪。直到写了很多本笔记以后,就到了1988年下半年,可以正式工作了。第一本是写《家族》,这中间也写了别的东西——因为这个长卷太大了,处理的问题很多,不可能在长达二十二年里其他什么工作都不做。如果有一个新的构思,在故事、气韵和审美方向与正在进行的写作差异很大,那就需要写下来。当然主要精力是写这十部。
《青年作家》:像《柏慧》是单独的长篇小说。
张炜:《柏慧》单纯从故事上看,似乎与《你在高原》有连接,但那种气质、叙述方式二者差得还是比较远,我还是让它独立成书了。还有《刺猬歌》,无论如何不能归到这十部之中。每本书像人一样,有自己的气质。作为单行本来说,《外省书》、《刺猬歌》就我个人来说,可能是技法、思想等各个方面综合分数较高的。
《青年作家》:包括它一开始就吸引住人了,比如像主人公说话用的那种独特的语言。
张炜:当然,那些单行本无论怎样,还是替代不了《你在高原》的容纳——尝试了很多表达方式、多种元素、多种的可能性。要看局部的技艺、精妙和凝练,可能是《外省书》、《刺猬歌》等。但是《你在高原》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就像一位评论家说的,它全部的缺点也就是全部的优点。它在更开阔更巨大的物质层面,展现自己的精神。
《青年作家》:行走主要接触农民?
张炜:各种人都有,山里看山的老人,海边上打鱼的人,还有逃避计划生育跑到河汊子里住的人……书里写了很多。如果仅仅为了写作去搜集材料,过分注重社会层面的东西,目的性太强,思路就会封闭,就会过滤掉很多重要的东西。这需要完全放开,不要管自己的书用上用不上,只是自然地行走和生活即可。这个过程将接受很多启发,使人想得更多,使心情变得饱满,原来没有预料的,会全部涌进来。
有一次走到了一条大河汊中,那里全是芦苇——书中写到了这个场景。那里遇到的人可能是逃避计划生育的,开始是两个身上涂满了泥巴的小孩,他们走我就跟上,直走到一个隐蔽的住处:利用发大水漩出来的一个小沙洲,顶上搭一个棚子。走进去,见到里面有锅碗瓢盆,一男一女两个人……
一切故事都需要发现,它们并不在城市的窝里,不在网络中。城里的窝既有电脑又有电视,现代化的装修,仿佛很精致——这种现代家居生活是狭窄的,和许多虚拟的东西结合在一起,阻隔了更丰富的存在。而大山里的独居者,就那么住了一辈子,没有电视更没有网络,却是直接连通了大地天籁。那种连接是更大的真实。
我经历了几十年的写作之后,很想让作品“回生”。长期不再做案头工作,在外面跑久了,有一些字和词都忘记了,也就是有了职业上的生疏感。但是一旦投入工作,会很有冲劲,很有力量。《你在高原》这十本书,从结构到文字表述,跟我过去的作品已经有很大的距离了。
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够进入推敲山河的状态
《青年作家》:你小时候全家搬到林子里住,是从另外一个地方迁徙到那里的,这个牵扯到你们家族的事情了吗?
张炜:《你在高原·家族》里集中写了一些事情。作家一般会尽可能地绕开真实的个人——无论怎么绕,还是借助现实去想象。很早的时候我们全家不在那片海边林子里,是从外地迁到那里去的,因为各种原因……在动荡的社会生活里,几十年周折了好几次,最后就来到一片没有人烟的地方居住了。小时候看到的人很少,无非是打猎的、采蘑菇的,再后来接触园艺场和林场的人、一些地质工作者,他们都是到处游荡的人。离我们林子最近的一个小村叫“西岚子”,要穿过长长的林中路才能找到。这个小村我在《九月寓言》里写过了,它是从很遥远的地方搬迁过来的,是逃荒人组成的一个村落,让人感到分外亲切。我小时候跟那个小村的人发生了很密切的接触。后来那一带发现了煤矿,还发现了浅海油田,于是矿区建起来,各种外地人越来越多了,我的视野开始扩大。
我原来接触最多的是动物和植物,那是一种孤独的童年和少年生活。
大约十六岁左右一个人到山东南部山区去生活,后来返回了一次,最终又回到山区。这样一直到1978年,考入半岛地区唯一的一所大专学校中文系。
《青年作家》:你家住在林子里,是单独的住吗?是不是和你《家族》里面写的有点像?
张炜:是单独,在林子深处——四十年代末搬入的。反正是经历了动荡的生活,最后既不能在城里,也不能在乡村生活,是这样一种可怕的状态。父亲一直在一个水利工地,在南部山里。但与小说还是不一样,小说总是一种虚构。真实的情形或许比虚构的生活还要复杂一些,它一旦被对号入座,对生活和艺术都是尴尬无趣的。
《青年作家》:这么讳莫如深?
张炜:有些作家是不愿意书写自己的——无论是苦难的家族还是幸运的家族——我就属于这样一类写作者。我并不是担心一些人思想僵化,将作家的表达和他的经历之类一一联系,将文学表达简单化和表面化,于是对作品和作者造成双重的伤害——我不是出于这样的担心。我只是不愿意谈论自己。
《青年作家》:作家对自己的出生和来历,不想多谈吗?
张炜:许多人是不谈的。因为阅读者很容易跟作家具体的创作道路、思想倾向等各个方面发生联系,产生特殊的反应——这也属于“化学反应”,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作品了。这对艺术和思想的理解都没有好处。当然倒不仅仅是因为这些顾虑,是现实生活和艺术想象的关系,作者担心被扭曲和误解。
《青年作家》:你为了写这个,《你在高原·家族》,会重新找一些资料吗?
张炜:尽可能多地了解一点,这太重要了。因为从小就知道这一类故事,耳濡目染,很具体,这就避免了故事的概念化。类似的故事很多,在貌似一样的故事里面,找出这个故事的个性到底在哪里,这才是重点要做的事情。我小时候跟在外祖母身边,跑到林子里去玩,有点像童话和小说里经常写到的那种场景。《你在高原》里我反复提到的离我们家最近的那棵大李子树,全都是童年的真实记忆。那棵大李子树真是够大,我到现在都没有发现有比它更大的——浓旺的大树冠好像一直笼罩了我的身心。
《青年作家》:那是一片原始森林中的?
张炜:原始林与后来的人工林连在了一起,成为无边无际的一片,不知有多少万亩。那棵大李子树就在我们房子旁边,出奇的大,记得比我们的房子高多了。我回忆起小时候的环境,马上就会想起它,它代表了全部童年的烂漫、向往、迷茫和未知,总之一切都在那棵树里包容了。回忆中很难解脱它的形象的笼罩。一到了春天它就开满了繁花,整个世界都是它的香味,无数的蜂子蝴蝶都飞过来了。
《青年作家》:在你们家院子旁边吗?
张炜:就在我们房子后面,偏右一点,下面是一口甘甜的、永不枯竭的水井。大树分开几个巨杈,树桩直径需要数人才能合抱过来。它在我心里是十分神奇的——不是象征的意义,而是深刻的印象和记忆让我吃惊。
《青年作家》:小说最重要的原型是“宁伽”?
张炜:读宁伽也可以。实际上应该读伽(qie)。小说里有一个地方,是在“小白笔记”这个缀章里吧,谈到这个问题。有人叫他“宁伽(jia)”,他也不反对,但是准确的叫法应该是宁伽(qie)。
《青年作家》:你能多说说这个原型的故事吗?
张炜:因为是第一人称,阅读中才会与作家本人靠近。但这只是叙述的方便,肯定不是作家自己——但是会不自觉地在叙述中融入自己的生活。这里面写了大量远行的朋友,这在现实中倒几乎都是真的。1980年代济南很有一拨人,辞职后要到西部去,心气很高。有的眼看要大学毕业了——考大学多难,他们却在冲动中不想读下去了,可见那时的心情是很激烈的。当时我们都投入了,也很激动,参与一起,准备行李之类上路的东西。那一拨人有的今天已经不在了,有的就活在当下的潮流里。当年那么大的雄心,多么严酷的环境都不能改变他们,但是商业主义的水流一冲,这支队伍就散掉了,各个不同的人生道路就分开了。我是一个参与者,也是一个旁观者目击者,最后成为一个稍稍冷静的观察者和总结者。我跟这拨人的距离,跟小说里写的宁伽与吕擎这拨人的距离差不多,参与的深度和程度跟他们也差不多。
《青年作家》:你写那个庄周这个人物,他变成流浪者了?
张炜:是的。不止一个朋友没有了,消失了,消失在民间,在谁也不知道的什么地方。书中还有一个跳楼的画家,故事中他没有死——实际上是我不忍,现实中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已经死去了。
《青年作家》:林蕖和这个人是好朋友?
张炜:庄周和他是好朋友。我写的是他的胯关节摔坏了,残废卧床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天才画家,是我心中的凡高。他在二十多岁一点曾给我做过一幅素描,那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幅作品了。我以前还为他写过一部中篇小说……
《青年作家》:以他为原型的?
张炜:就是《请挽救艺术家》。其中引用的一些信件就是他的原件——我写不出这样的信,只好用他的原文。这个人对生活绝望了,像许多天才人物一样,他们当中有人是脆弱的。我到现在认识这么多艺术家朋友,但固执地认为他是最有才华的人。他从省城回到了半岛,后来跳楼了,一共两次,终于……
《青年作家》:什么原因?
张炜:绝望,单纯而又执拗,对这个社会不能接受,对生活不能接受。他是特别敏感和纯洁的那种人,是悲剧人物。他给我的刺激太大了。和另一些人不同,有的人出走的时候那么壮怀激烈,想不到回来后一头扎入了欲望之海,变成了非同一般的坏人。
《青年作家》:林蕖等于坏人了。
张炜:有的犯罪了,有的堕落了,有的没心没肺了。有的那么有才华,却又自杀了。这都是1950年代生人的故事。我平时不太敢想那个画家,因为他跟我不是一般的密切——两个省城里的单身汉,几年来一起弄吃的,一起讨论艺术,一起幻想。我们在一个机关工作。
我写作中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把这拨人的经历写下来。没有比我们这拨人更惨的了——话又讲回来,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是最惨的,经历的事情最残酷、领受的苦难最多——但是每一代人实在是可以比较可以量化的。1950年代生人这一拨真的够不幸了,他们生下来就没有东西吃,比如说1960年是长身体的时候,却遇到了大饥饿。整个走过了那样的年代,充分领受了那个时期的严厉。在学校教育这方面真是大不幸,不能学英语,不能读国学,如果家庭有问题,连高中都不能上。他们经历了文革,那是多么残酷和荒诞的年代。可是到了所谓的思想解放时期,从政治严酷的时代突然来到了物质主义的声色犬马,等于是人生最突然最巨大的跌宕。这一代人无法承受,他们没有做好准备。他们是特殊的一代,他们具有足够的悲剧环境。
《青年作家》:宁伽确有其人了?
张炜:无一不是实有其人,也无一不是虚构。文学与报道是极为不同的——现实人物关系对书的虚构产生了关键的帮助,但任何一个书里的人物都不能说是生活中实有的。这就是小说的艺术。将生活材料彻底发酵是重要的,这样才能把它变成酒——这是所有艺术生成的通理。但是粮食肯定全都存在的——作家的想象力是那么贫乏,很少能够离开真实去虚构任何事物;另一方面我们又惊叹其虚构能力之强,可以把所有的现实变形、组合、再造,让当事人也恍惚起来。一切都服从了艺术的和谐。
《青年作家》:这个人物是一个贯穿性的人物。有的地方报道说这是为一个地质队员写的小说。
张炜:因为主人公学过地质,有过这样的从业经历。这是重要的。我们小时候那个地方发现了石油、煤炭和金矿,这部分地质人戴着太阳帽和黑眼镜,看上去很是浪漫。他们到了哪个地方就搭起帐篷,木板一铺帆布一扯就是很神秘的窝了。他们从来不住到老乡家里。我们小时候没什么好玩的,除了玩林子、玩海、玩动物和植物,再就是分拨打架。外来地质队员就像天外来客一样,他们的服饰和口音都和当地人不一样,让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他们也喜欢我们,跟我们玩,讲许多故事。我们在他们帐篷里有时候要待到下半夜。白天看他们的机器、看他们的操作,一切都忘记了。那时候觉得这个职业特别神奇,很浪漫,对他们跋涉千山万水的辛苦考虑不多,只往有趣的方面想。这些人到处走,知道的事情特别多。我们缠着他们讲故事,也吃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们好吃的东西也多。我们作为交换,就带水果给他们。他们买来许多海产品,大口喝酒抽烟,我们也跟着学。这对于林子里的孤独少年来讲,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所以我曾经铆着劲儿要做这样的工作,后来还写了很多诗和散文小说,都写了地质队员的生活。现在的主人公是地质工作者,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够进入推敲山河的状态。
所有杰出的作家都只跟“个人:对话
《青年作家》:你究竟为谁写作?读者,市场,今天,未来?
张炜:在我看来,一个好的读者和一个好的作家是同等量级。有人说阅读相对简单,只要识字就可以读。创作很难,中国民间有一个说法:看花容易做花难。但实际上真正能看懂花的,也同样难。接触过大量的读者,跟他们交谈就会发现,有的人虽然表述能力很差,但的确是懂的,他能感受作品中的一切,这说明他是很高级的读者。阅读的能力和写作的能力是不同的,这两种能力虽然不可以换算和等同,但要达到较高的量级都是很难的。对于作品的全部感悟,许多读者不能表述,但是心里都有。他可以用另外一些概念来表述,许多时候跟作家的感受是一致的,知道文字内部蕴藏了什么、是怎么一回事,懂得文字背后的东西,懂得形成文字的代价在哪里,盲角在哪里,无限的可能性在哪里——他阅读的时候留下了这些空间,所以能够掌握这部书。
作者为什么不能为读者写作?因为不可靠,因为危险。只为读者写作,很可能就要假设这样的读者存在——既然有一大批或一小部分这样的读者,那就要自觉不自觉地去迁就他们,为其服务。其实这是以折杀自己为代价的。我以前谈过个人的临场感受,说我在为一个“遥远的我”在写——那个“我”在更高处,他在注视我,我为他去写作。
《青年作家》:你什么时候有这种意识?因为过去有个说法是创作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
张炜:1980年代中期,我就开始解决一个问题,即设问并回答为谁而写?因为我们这个传统里面,特别是这几十年较短的传统里,核心问题就是强调文学为谁的问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让老百姓喜欢,其余都无所谓了,甚至还问“你算老几”——这个“你”就是指创作主体,指作家,创作者都不算什么了,作品怎么会有价值存在?当然也不必期待这个民族会产生什么了不起的杰作了,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将“民众”视为一个理想的理性的概念,那就只能是等同于时间的概念——在时间里留下来,肯定是获得读者人数最多的,这也就是“民众”了。真正的杰作往往并没有一哄而上的阅读效果,起哄的“民众”大致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乌合之众”了。
谈到更为可靠的“时间”这个概念,我好像仍然也不能接受。因为即便如此,写作的功利性也还是太强了。作家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时间也不能过分地干涉,这才是理想的境界。
后来我用了一个很“虚”但又很“实”的一种说法,来作了稍稍准确的表达。我努力回忆自己的写作状态:凡是写得好的时候,倾注其中沉浸其中的时候,总是觉得有一双很高的眼睛在注视,它在我不能察觉的时候随时出现。就为了让它满足和高兴,获得一个呼应和理解,我才努力而兴奋地工作着。那个高处的人既是我,又不是我,因为他比我高,比我远,他是放得更遥远、更全面、更完整的一个生命。我和它达成了默契和呼吸的关系,那是一个“遥远的我”——这样的表达,才比较接近写作的实情。
这样的写作是自由的,个人的,是其他人所不能取代的。
现在我们大家很容易写出一些区别不大的、似曾相识的作品,所以它们最后不得不被淘汰。非常个人的,不被重复的——跟未来、现在、过去都不重复的,或者说是很大程度上不重复的,才会被保留下来。
比如说托尔斯泰,同样是代表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大师,他跟法国的雨果差异多大,跟本国的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差异多大?他们各自独立——当时,过去以及未来——直到今天的俄罗斯,也没有出现和托尔斯泰重复的作家,那是绝对没有的。以往俄罗斯历史上没有产生过托尔斯泰式的作家,不仅是规模,而是个性的特异。所有这些杰出的作家,都只跟个人进行着对话,当然这种“个人”打一个引号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