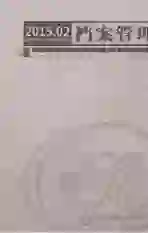礼法之间:清水江文书的定性问题
2015-04-23刘崧
刘崧

摘 要:清水江文书是黔东南清水江流域特定经济基础和地域文化的历史产物,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质。深入考察其约束力之来源和作用方式,可知它不同于纯粹法律意义的契约,而是介于礼法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存在,它在法的外形中包含着传统礼文化的精神。准确而深入地定性清水江文书,对开展相关研究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
关键词:清水江文书;契约;礼法之间;定性
Abstract:The folk document of Qingshui River is a historical product with specific economic base and regional culture in Southeast of Guizhou, which has a unique nat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If we dig into the source and effect way of its binding force, we would discover that it is different from contract of legal meaning, but is a kind of special culture between etiquette and law. In order to carry out relevant research deeply, it is of vital significance to determine the character of the folk document accurately.
Key words:Folk document of Qingshui River; Contract; Between etiquette and law;Determine the character
留存于黔东南清水江流域的民间文书近年来日益引起世人关注,其富含的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化学、人类学、文献学、档案学等方面的学术价值日益凸显,围绕清水江文书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可谓路数纷纭,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一个前提性的关键问题还有待思索,那就是:我们究竟该如何来定性这一大批民间文书资料?可否无区别地一概视之为契约文书?毋庸置疑,从形式上看,这些文书确实具备契约的形式特征,但是,是否应该追问一下:这一批具备契约之形式的文书是否具备契约的真正精神内涵?即便我们可以笼统视之为契约文书,也可以再问一下:这种黔东南“土生土长”的契约与原本意义的契约能否相提并论?这些问题恐怕并非无谓,而涉及该如何定性一个事物的问题。定性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性质不定,则物象不明;物象不明,则意义不清;意义不清,则难免盲人摸象。
1 清水江文书只具有法的外形
清水江文书普遍存在于黔东南清水江流域的民间,在清朝到民国时期几乎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事务,涉及田产、菜园、屋基、山林等的买卖,同时还包括典当、租佃、借贷、抵押、对换、借讨、赋税、婚姻、继承、丧葬、族谱、纠纷处理等各种各样的经济社会关系和人伦秩序,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对这样一种内容多样、普及日常生活的文书,我们可否视之为一种契约?如果视之为契约,则等于承认它是一种法律文书。一种法律文书在民间如此普及,渗入百姓生活如此深广,几乎达到一种人伦日用的状态,这不禁让人发问:既然一种法律文书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难道当时黔东南的清水江流域已经是一个法治程度很高的社会了?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深加考察,可以发现,清水江文书虽然具备契约的形式,但并不具备原本意义之契约的内在精神——即西方意义的契约所包含的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精神要件,也不具备现代市场社会所强调的私人契约和公共契约的理念。严格说来,清水江文书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现,是中国传统礼俗文化发展到近代产生较大规模商品流通而出现的一种文化民俗现象,它不具备充分的法律意义,也不是纯粹的礼俗。准确地说,清水江文书是介于礼与法之间的一种特殊存在,它具有法的外形,而贯穿着礼的精神。
之所以说清水江文书只具有法律(契约)的外形而不是纯粹的法律文书,理由如下:
1.1 从文书签订程序看。大多数文书都是在无官方参与、不关注国家律法具体规定的情境下,由当事人双方共同约定中人来签订。而且,大多数文书的内容仅限于陈述事实,表明态度,末尾只是签字,很少画押或盖章。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文书所约定的内容完全是双方协调而来,其协调过程是由中人作证或主持的相互说情讲理,这一过程是完全独立而自洽的,与官方或其他公共组织无关。不难看出,由这样一种程序而产生的文书,其礼节意义浓于法律意义,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1.2 从文书通行面看。大多数文书是在熟人社会中签订的,其通行面也限于熟人社会。这些文书之所以出现在黔东南清水江流域,与当时木材贸易的兴起密切相关,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这种地域性可以概括为熟人社会,不管是签订文书的双方,还是双方共同约定的中人,均可以定位为熟人,至少可以定位为熟人社会(乡民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我们虽无法断定这种文书能否通行于生人社会(市民社会),但从历史的事实来看,当时文书通行的社会就是熟人社会(乡民社会)。在熟人社会中签订的文书,其礼节意义大于法律意义,其礼义约束大于法律约束。
1.3 从文书约束力看。从大多数清水江文书来看,其功能主要有二:一是记忆功能,二是约束功能,而且第一项功能决定(指向)第二项功能。清水江文书的末尾一般都有“恐口无凭,立此为据”“今欲有凭,立此存照”“恐后无凭,立此据为实”等语,这说明立文书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无法改易的凭据,即文字凭据。因为口说无凭,而且容易忘记,立为文字之后,就获得了固定的凭据,从而获得一种约束力。“固定”是约束力的保证。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文书有没有约束力(没有约束力的东西不可能广泛通行几百年),而在于其约束力的来源和约束力发挥作用的方式。
从清水江文书施行的客观效用来看,可以说是普遍有约束力的,违反文书而诉诸法律的案例非常少(不是绝对没有)。这就很值得探究,这些文书的约束力究竟来自何处?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如何?
2 清水江文书约束力的内在根据是礼义精神
事实上,清水江文书的约束力与其说是法律的约束,不如说是礼义的约束,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不是一种外在的制约,而是一种内在的自觉。这种礼义奠基于乡土熟人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机理,与熟人社会的礼义、荣辱、廉耻等观念密切相关。法律不能不讲理,礼义不能不讲情,综合而言,这些文书的约束力正是来自一种情理交融的价值向度和生存模式。《管子·心术上》有云:“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既然礼之创立与情、义密切相关,则礼之本义就包含着个体之自觉性、主动性。礼本是经过教化而养成的内在情感之自然要求,无假外求。《隋书·刑法志》云:“礼义以为纲纪,养化以为本,明刑以为助。”与礼对应,法的精神则有不同。礼法之殊异可由下表之对比而见:[1]
从大多数清水江文书的内容来看,其性质正是介于礼法之间,可以说具有法的形式而内含着礼的精神,故其约束力主要是来自礼而非法。
2.1 文书的签订过程具有礼仪色彩。虽然我们无法复原当时签订文书的具体情景,但是从文书留下的字句来看,大体可以界定为一种比较正式的礼俗活动。参与人一般有三方:双方当事人和中人(执笔人),没有特殊情况必须都在场,并且有一套约定俗成的仪式规程,比如杀鸡宰羊、起誓等。如果是鸣神文书,则礼仪色彩更为浓重,须焚香烧纸,祷告天地,有的甚至请求菩萨帮忙,“祝告南狱庙大神大道”。[2]
2.2 文书的内容既讲道理,又诉诸感情,甚至主要诉诸感情。从大多数文书内容来看,一般都要摆明事实——这是讲理,也是主要成分;但是,在摆明事实之后,文书中常常出现一些诉诸情感的字眼,诸如“二比心平意愿”“二比不得翻悔异言”“务须实心赶办”“各自安听天命……此系两厢情愿”“恐有人心不古,今欲有凭”“祖父母得心安而瞑目也”“俱已同心合意……立此同心字为据”,[3]等等,这些字眼有意无意透露了文书的情感取向。相反,文书中很少出现如果违反约定会采取什么法律措施的约定。这说明,文书讲究情理交融,既合情又合理,讲理(摆事实)是必不可少的,但真正发挥约束力的还是感情——这正是礼之精神的体现。
2.3 文书的精神指向是无讼。文书的签订当然是有目的的,就是为了平息事端或避免事端,其基本精神是调解,其终极目的是无讼。这本是儒家的精神传统。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儒家一贯重和睦,反诉讼;重预防,轻惩治;强调教育为主,刑罚为辅。孔子还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种以无讼为指向的礼治最终诉诸人的良心和情感,强调礼法交融、援礼入律、法由礼断,其基本方式是把法化入情感之中。在礼治格局下,法并不具备原本应该具有的普遍化的理性意义,而是从属于情感导向的伦理秩序。“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身内的良心。”[4]清水江文书常常可以看到“不得欺心异言”这句话,屡见不鲜,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谁要是违反文书的约定,那不单纯是违反约定的事情,更是昧良心的大问题——这是两种意义完全不同的性质。
3 清水江文书的伦理意象具有超越精神
清水江文书如此通行而又具有效力,而且主要不是一种法律的效力,而是一种道德(伦理)的效力,正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礼治社会,人们主要过着一种情感的、心灵的生活,而不是过着一种理性的、逻辑的生活。清水江文书发挥效用的具体方式是一种自觉主动的内在的自律,而不是一种来自外在的附加的制约。它不是在服从一种规定,而是在履行一种情义。人们之所以自觉自愿履行这种情义,是因为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的人们原本就有情义,原本就不想“欺心”。而人们之所以不想“欺心”,是因为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模式决定了人们内心洋溢着一种共同的价值向度和伦理意象。这种伦理意象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确确实实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
有这样一份鸣神文书,可以说明当时当地的人们心中的伦理意象是多么确实。这是一份单方面的鸣神文书,大意是说立约人与一个名为姜建猷的人为一块山场起了争执,请中人来理论,对方不予理睬,于是立书人只得求告神灵,希望神灵降下报应。文书内容如下:“大清国贵州镇远府天柱县属文斗下寨,居住某某村,为冤沉海底,无处可伸。恳祈诉神鉴察事。缘蚁村于道光年间祖用价得买姜老贵山一块,地名培拜,界址:上凭屋地基,下凭河,左凭岭,右凭冲,四抵朗明,不料于前月姜建猷就某某串通某某霸砍吾弟兄之山。伊等起不良之心,已将木放下。现请中人理论,不由中人,今已此山伊无字据可凭,伊只行口说有味,不那天良(缺一字)心,亦不以道理服人,大坏心术。蚁等已得告神,强霸吾弟之山,若不灭没断根,强暴得惯横行,良善之辈难(缺一字)矣。为此,诚心祈于天地菩萨,连彰报应,虚买(缺一字)分,是以吾弟兄人等诚心(缺一字)具香纸,同祝告南狱庙大神大道,虚空过往一切执印使者、掌簿仙官大显威灵,如果真(缺一字)业,乞赐吉祥,满门福寿,倘若……”[5]
这则文书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社会已趋向复杂,利益格局及利益纠纷解决方式已趋向多样化。从对方不理会立约人的诉求来看,可见当时的纠纷解决方式已不限于文书一途;但这则文书同时又说明,人们对文书的精神依赖依然存在,人们心中善恶相报的伦理意象并未消失,也就是说,“良心”依然是人们心中的最后皈依,只不过良心在现实中难以发挥实际的效用罢了。也正因此,这一份文书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它可以否定用契约来界说清水江文书这一做法,因为它不具备契约的基本要件——它是单方面的;其次,它可以启示我们,这一份文书的象征意义、符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它不是作为法律的凭据在申诉一个人,而是作为一种伦理意象和精神符码在抒发立约人的主观情感和意愿。在这个意义上,它更像是一首不平则鸣的控诉诗。
法的确立和施行基于理性,讲求普遍的形式化原则;而礼的教化诉诸情感,强调“根据情况活用原则”。中国自古就是礼治传统,清水江文书正是这种传统的独特体现。但清水江文书的复杂性和学术价值就在于,它可以反映出一个处于不断变迁中的社会。在此变迁过程中,法的理性原则越来越显得重要,而传统的礼的精神日显式微,受到了时代问题的挑战。“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6]随着商品交换日益扩大和加深,熟人社会与生人社会的界限渐趋模糊,乡民社会不断趋向市民社会,在维系社会正常运转上,法的理性原则显得越来越紧迫了。
但是,社会和人心常常不会同步发展,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具有顽强的传承性,以孝悌为精神导向的中华民族尤其如此,这就会出现美国学者奥格本所说的culture lag(文化滞差)。直至今日,虽然中国的法律制度已经比较健全,但不能说中国人的法治精神已经完全确立了。乡土熟人社会遗传下来的文化精神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搏动:“迄至今日,中国人不重个人及其权利,而重相互关系及其感情;不习惯(甚至以为羞耻)兴诉讼、上法院,去寻求公正裁决,而宁喜调解互让,自行私了,以‘不伤和气。凡此等等的习俗、观念、行为方式、价值标准、情感态度、思想定势,构成了中国人的‘人情味特征。”[7]从哲学意义说,这种人情味对于中国人而言本身就是一种“理”,不是与“理”相对立的纯粹的感情,而是情中有理,理中有情,情理融一。
参考文献:
[1]李泽厚.己卯五说[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75.
[2]潘志成,吴大华.土地关系及其他事务文书[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233.
[3]潘志成,吴大华.土地关系及其他事务文书[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60,62,68,92,93,100,106.
[4]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2.
[5]潘志成,吴大华.土地关系及其他事务文书[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233.
[6]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0.
[7]李泽厚.己卯五说[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96~97.
(作者单位:中共黔东南州委党校马列教研室 来稿日期:2014-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