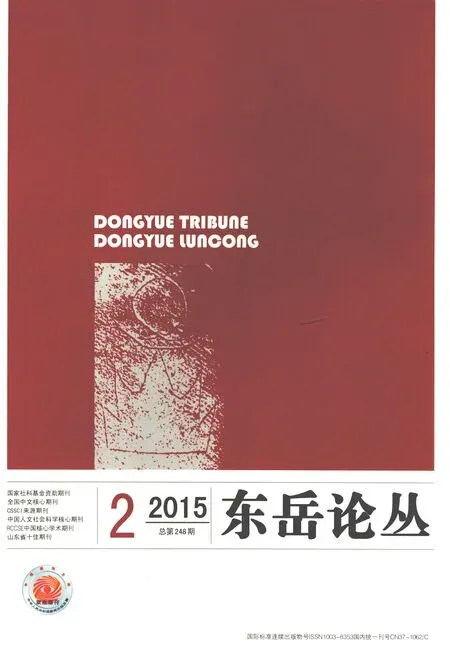从国家法团主义到社会法团主义
——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行业协会关系的演变*
2015-04-21张长东
张长东,顾 昕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从国家法团主义到社会法团主义
——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行业协会关系的演变*
张长东,顾 昕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行业协会是中国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相对于多元主义和国家法团主义,我国的行业协会和国家的关系更接近于一个社会法团主义模式——虽然尚有一些出入,这不仅体现在监管体系本身的性质上,而且还体现在这些社团组建和运作过程中国家涉入的程度。一方面,社团监管体系正变得更为开放,自发成立的行业协会在近十年有大量的增长;国家为行业协会提供的财务支持非常有限,而且业务主管单位通过领导人选择来控制行业协会的方法也越来越少,领导人民主产生的比重上升。同时,业务主管单位更多地采取了财务审计、年度报告审查等事后监督模式。在这样一种大的制度框架中,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得到初步发展,中国的社团空间已经接近社会法团主义模式。
行业协会;公民社会;法团主义;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
市场转型给中国带来的最深刻变化之一,就是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时社会自组织的空间也得到拓展。在改革之前和改革初期,民营企业处于非法或地下生存状态,行业协会更是少而又少。在当时,由于很多行业存在着相应的行业管理政府机构(如轻工局、一轻局、二轻局等等),民间行业协会缺乏存在空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开放,一方面,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自身的机构改革和国家放弃了以穿透社会各个角落为特征的全能主义式社会控制①,国家对许多行业的管理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退出了对企业的微观管理。因此,行业协会纷纷兴起,并开始在行业治理上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这种趋势在一些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如温州)尤其明显②。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行业协会的兴起,最饶有兴趣的问题之一就是国家与行业协会关系的变迁。当全能主义一去不复返之后,市场经济急速发展,国家与行业协会的关系究竟发生了何种演变?很显然,作为一种制度变革,国家与行业协会关系的改变无疑会受到原有制度遗产的制约,同时也会呈现路径依赖的特征。改革前的全能主义无疑留下了国家强控制的遗产,这一遗产为当前国家与行业协会的关系打下了厚重的国家法团主义烙印。那么,就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而言,国家法团主义的现状如何?进一步转型的演变走向如何?国家在推动这一演变方面可能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重新定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探索中国国家治理改革的方向。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首先简要概括一下有关国家与社会法团主义关系的理论框架,并借此简要评述一下已有文献对中国行业协会的研究成果。接下来,本文将利用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中国社会团体调查”数据库中的数据,对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政府在行业协会法人治理结构中的作用,进行研究。最后,本文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
一、国家与行业协会的关系:一个比较分析的框架
就国家与行业协会的关系而言,存在两个理想类型:一端是以自主的、民间性的行业协会进行行业自治,又称协会治理(associational governance),行业协会在美国经济生活中的运行状况比较接近这一模式③;另一端则是由政府对行业直接进行行政管理,而无需行业协会等中介性组织,转型前或尚未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属于这一模式④。处于中间位置的模式则是政府积极参与民办行业协会的治理和活动,西欧国家大体都属于这一模式⑤。这三种关系种类实际上正是如下三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多元主义、国家主义和法团主义。
依照法团主义理论的权威学者菲利普·C·史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的解释,法团主义和多元主义都是“以社团形式组织起来的民间社会的利益同国家的决策结构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⑥。与多元主义下社团组织及其与国家关系的情形有别,法团主义具有如下6大特征:
1. 在某一社会类别中社团组织的数量有限;
2. 社团组织形成非竞争性的格局;
3. 社团一般以等级方式组织起来;
4. 社团机构具有功能分化的特征;
5. 社团要么由国家直接组建,要么获得国家认可而具有代表地位的垄断性;
6. 国家在利益表达、领袖选择、组织支持等方面对这些社团组织行使一定的控制。⑦
就国家卷入与社团自主之关系的问题而言,史密特还进一步区分了“国家法团主义”和“社会法团主义”两个亚类型。在国家法团主义模式中,上述种种特征是经过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力干预而形成的,即通过种种行政化或者直接明文规定的方式,国家赋予某些社团以特殊的地位,而对其他竞争性社团则根本不给予合法地位。相反,在社会法团主义模式中,某些社团享有的特殊地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竞争性淘汰过程形成而非国家指定的,同时竞争性社团的出现在国家的法律监管体系中并没有得到禁止,只不过由于国家的力量毕竟强大,已经获得国家支持或承认的社团拥有丰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本,新兴的社团无法通过竞争撼动其垄断性或主宰性地位而已。社会法团主义与国家法团主义的区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两种利益聚集和表达模式所嵌合于其中的政治体制的特征。产生社会法团主义的政治体制具有多元化自由主义的特征;与之相对,孕育国家法团主义的政治体制则具有集中化威权主义的特征⑧。
由此,就涉及国家与行业协会关系的三个重要方面,即行业协会的发起者、融资来源和监管体系,我们给出多元主义、社会法团主义、国家法团主义和国家主义4个理想类型(参见表1),构成本文的分析框架。有了这一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在下文详细讨论中国行业协会发展的制度空间及其特征。
二、中国行业协会与国家的法团主义关系
在中国的社会行政管理体系中,行业协会是所谓“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的一个子类,由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负责管辖。因此总体来说,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的格局。
国务院曾在1989年10月制定并于1998年修订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内外很多学者认定,基于这一条例对于各类社会组织的管制规则具有“强”国家法团主义特征,如强有力的政府(通过业务主管单位所实施的)行政控制(即俗称的“挂靠制”)、单一垄断的功能区分、等级化层级结构和社团数量单一性等。早在1994年,美国学者裴松梅(Margaret Pearson)依据政治体制的特征提出“社会主义法团主义”(socialist corporatism)的概念,以外资商会为例说明中国社会组织的层级性和垄断性等特征,以及兼具国家控制与自主性的两面⑨。国内学者顾昕和王旭认为,“中国社会团体的监管框架具有强烈的国家法团主义色彩,体现了国家对公民社会高度防范的取向,维持国家对社团空间的有效控制是有关行政法规出台的主要目的”⑩。美国学者马秋莎提出,行业协会等经济型社会组织既是政府下放了的经济管理权力的承接机构,又代表了政府对经济实体干预权的继续延伸,具有法团主义的典型特征。英国学者希尔德布莱特(Timothy Hildebradt)持相似观点,认为社团登记管理条例有许多条款限制社团自主性(尤其是“挂靠制”)、规定社团的活动范围、限制社团的能力提升、限制社团异地办分支机构、限制社团的横向联合等等,使得很多社会组织无法正式登记而成为不受法律保障的草根组织。国内学者张钟汝等人通过经验研究试图将国家法团主义的框架进一步细化,区分了“庇护性国家法团主义”(指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利益联盟关系,非政府组织仰赖政府提供权力与资源)和“层级性国家法团主义”(指通过半官方中介机构的沟通,非政府组织实际上成为政府非正式的下层序列)。当然,有别于法团主义主导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小国,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不同层级的社团在不同层级(政府)从事利益表达的活动,呈现鲜明的地区性、行业性的色彩。也有学者专注于非政府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提出了“地方国家法团主义”的观点。此外,一些商会开始尝试异地建商会的模式,而地方政府出于招商引资的考虑,也愿意接受这种做法,但这种情形尚不普遍。

表1 国家与行业协会关系的四种理想类型
法律法规文本和现实运作往往存在出入,这在转型社会中尤其明显。因此,就中国行业协会与国家的实际关系而言,不少学者认为的确具有国家法团主义的特征,但也持一定保留态度。他们发现,在中国很多地方,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仅有国家法团主义的形式却无其内涵。美国学者福斯特(Kenneth Foster)在二十世纪末对山东烟台社团的调查发现,那里的行业协会其实是一些“嵌入在”官僚体系上的“空壳子”,或是各个利益相关部门所利用的工具,反映的是国家的意志与权力,因此它们与国家的关系表面具有法团主义的形式,但缺乏法团主义的核心实质内涵,即未能代表行业利益与政府展开协商。澳洲学者安戈(Jonathan Unger)在世纪之交开展的个案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个体户组成的协会实际是政府部门的外延,这类协会与政府的关系徒有法团主义的形式而无实质;而面向大企业或商人的工商联合会,其运作却主要受其主要成员操控;这两种类型都偏离了国家法团主义结构的原初意义。国内学者吴建平认为,“尽管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空间得到了较大发展,社会群体日渐活跃,并且在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日益呈现出与法团主义高度相似的制度特征,但这并不足以表明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是或正在走向( 国家) 法团主义,因为缺乏相应的社会组织基础,这种制度相似性呈现出来的不过是一种‘形似神不是’的法团主义表象”。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行业协会和国家的关系,乃至更大的社会组织与国家的关系,开始超越国家法团主义,有走向更具有多元性的公民社会之迹象。如康晓光和韩恒基于个案研究,认为行业协会和商会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因为其对政治权力的挑战不强而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较强,因此从政府处获得的自主性要比一般的社会组织强很多。张建君发现,在私营企业发达的地区(如温州),行业协会自主性强于集体经济发达的地区(如无锡)。郁建兴和周俊对温州行业协会的研究发现,虽然国家力图它们加强控制,但是行业协会还是积极寻求参与行业治理,并不断获得政府的赋权而获得发展,从而使这种国家与社会相互赋权的发展模式远比社团一味寻求增加独立性的发展模式更为可行。美国学者毛学峰(Andrew Mertha)认为中国的社会正在变得日益多元化,使得碎片化威权主义1.0版演化为了碎片化威权主义2.0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关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研究者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业主委员会、环保组织、劳工组织以及志愿团体等非正式登记的草根组织,而非不是行业协会这类和官方有正式关系的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
同时,中国政府对社会组织(包括社团以及本文关注的行业协会)的管治制度也在进行改革,而改革的核心在于渐进地取消“挂靠制”和允许某些社会经济领域中出现多个社团。早在2012年,辽宁、广西、深圳、青岛、宁波、郑州等地相继出台相关政策,开展省、市两级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试点工作,无需寻找“挂靠单位”。2013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方案》第二十三条提出“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制度,依法加强登记审查和监督管理。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推动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方案》第十八条提出“逐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强化行业自律,使行业协会商会真正成为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主体”。国家民政部部长李立国也在多个场合发表讲话,阐释“行业协会去行政化”这一改革方向。2014年4月1日,深圳市政府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行业协会条例》,展开了“一业多会”的试点。由此,随着挂靠制的逐步取消以及行业内社团数量管制的放松,既有国家法团主义型社会组织管治制度在国家强控制和数量单一性这两点上有所改革。尽管改革后的社会组织管治制度依然停留在国家法团主义的制度框架之中,但是这一制度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的转型,已经显露出某些初步的、但却具有重要意义的迹象。

表2 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中国社会团体调查”问卷回收情况
注:此表显示的是调查中所有社会组织的回收率情况,因为政府部门提交的社团名录里没有具体的分类,所以我们很难单独统计行业协会的回收情况。对两个县的抽样检查发现四类社团的回收率接近。
那么,在实际运行中,中国行业协会同国家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前文提到的许多个案研究和比较个案研究都很有启示性,但缺乏代表性——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的情况可能很不同,因而无法给我们一个宏观的图像。本文基于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中国社会团体调查”数据库中的资料尝试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量化的研究,从而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个中观的层级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该项调查于2010-2011年间在北京、浙江和黑龙江三省市进行,采用分层、概率与规模成比例的方式抽取样本。首先,调查以每个地级市登记的社会团体的总数量为规模度量(MOS),采用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方法抽取3个地级市,再按同样的方法在每个抽到的地级市下面抽取两个县;然后对抽取省、市、县三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按照系统抽样的方式抽取样本。样本量按照不等比的方式分配。这样的一个样本不足以让我们推断全国正式登记的社会组织的状况,但可以推断选中的三省市的状况。另外,因为浙江省的民营经济比较发达,黑龙江则不太发达,所以在全国意义上,这一样本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本文将从行业协会组建的发起者、业务主管单位在行业协会运作中的作用、行业协会领导人的提名过程和行政级别、行业协会获得政府拨款等方面,具体考察政府涉入社团生活的情况。本文的初步发现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相对于多元主义和国家法团主义,我国的行业协会和国家的关系更接近于一个社会法团主义模式——虽然尚有一些出入,这不仅体现在监管体系本身的性质上,而且还体现在这些社团组建和运作过程中国家涉入的程度。
三、行业协会组建和运作过程中的国家涉入
首先,我们考察行业协会组建过程中政府涉入的情况。图1显示,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兴起,自发成立的行业协会数量和比重都有显著上升,而自上而下的“组织决定”成立的却逐渐下降。在1990年以前,以自上而下方式建立的行业协会占45%上下, 但2000年后下降到22%上下。图2 显示,除了北京的区县之外,其它各地在各个层级上由组织出面组建行业协会的比重更低一些。这里所谓“组织”,主要是指“业务主管机构”。很显然,自下而上组建方式在行业协会领域的强势增长并开始占据主导性这一现象,反映出国家法团主义色彩逐渐衰弱,社会法团主义色彩开始增强。

图1 行业协会组建的发起者,以时间划分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第二轮“中国社会团体调查”数据库(下文除特别注明,资料来源都相同) 注:N=476
第二,既然越来越多的行业协会要么是自发成立,要么是组织和社会双方商议决定而组建的,那么业务主管单位究竟在社团的运作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图3显示,业务主管机构在审查社团的年度工作报告和出席社团的会议方面比较积极;审查社团的财务情况也是业务主管机构的主要工作,但一半以上的业务主管单位出于各种原因并不这样做。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业务主管机构对于行业协会活动的监管和控制的局限性,这意味着国家法团主义的式微。业务主管机构任命社团领导人的比重近三分之一,这也显示了行业协会自治性的增强。同时,业务主管机构也为行业协会提供一定的支持,其中提供住房是主要手段,而提供经费或派遣专职人员则是次要手段。 由此可见,这几个部分我们需要和下面更具体的数据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图2 行业协会组建的发起者,以注册级别划分 注:N=495
无论从控制还是支持的角度来看,业务主管机构在行业协会的运作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当被问及同业务主管单位的关系时,32.3% 的行业协会选择以“非常密切”来形容, 50.5%认为是“比较密切”, 14.3%选择了 “关系一般”,仅有1.9%认为“联系不多”,没有任何协会选择“没有联系”,另外有 0.4%认为这一关系“说不清楚”。
第三,我们考察行业协会领导人的提名过程,以了解国家在社团领导人遴选过程的涉入情况。在中国社团的运作过程中,社团的一把手掌握众多实际权力且/或主持社团运作的日常工作。图4显示,以会员自由竞选的方式提名一把手的社团比重都非常低;业务主管机构(挂靠单位)直接推荐的比重占1/5强,也不算高。相反,由理事会推荐提名的比重相对较高,这符合社团法人治理结构的一般运作常规。我们虽然缺乏直接的数据显示业务主管机构在理事会中的代表性,但根据常识判断,业务主管机构对理事会成员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理事会协调”作为一把手提名的方式,占有高达55%的比重。相对于业务主管机构直接推荐,理事会协调更少行政色彩,更多民主色彩——当然,民主程度可能在各个行业协会有所不同。
可以说,数据显示,业务主管单位在中国行业协会领导人的遴选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这一点正是国家法团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然而,业务主管单位的人事影响开始变得更为民主化,简单的直接推荐的比例并不高,也意味着国家法团主义中行政协调机制的式微和社会法团主义中社群协调机制的孕育。

图3 业务主管机构在行业协会运作中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考察社团领导人的行政级别。图6显示,接近60%的行业协会的一把手曾担任过科级以上行政职务。值得注意的是,拥有行政级别的人士并不一定是政府官员,在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中工作的、隶属于干部系列的所有雇员都有行政级别。 但在实际的社团生活中,退休官员出任社团名誉会长、会长的情况非常常见。这一情况,一方面体现了国家控制行业协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行业协会依赖或者动员其政治社会资本以维持垄断性的需要。

图4 行业协会一把手的提名情况 注:N=403
最后,我们考察行业协会获得国家财政拨款的情况。图6的数据显示,在2009年,67%的行业协会没有获得国家的财政拨款。国家拨款占其运行经费比重不足1/3的行业协会有7%,超过1/3不足2/3者有7%,超过2/3的行业协会比重为19%。可以说,绝大多数行业协会在运行经费上不依赖于国家,这一点同行业协会制度空间的法团主义性质并不相悖。实际上,作为会员制组织,行业协会的主要职能是为会员企业服务,而且由于很多企业加入行业协会具有强制性,因此大多数行业协会完全可以依赖会费实现财务自主。同时,各级政府都面临着预算紧缩的艰巨工作,而减少社团(包括行业协会)的财政拨款无疑是预算紧缩的一大手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行业协会也不得不努力实现财务自主。行业协会具有较高的财务自主性意味着它们正在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型。

图5 行业协会一把手曾任最高级别 注:N=463,部级以上2个
上文的经验研究表明,至少在行业协会的空间,中国已经完成了从国家主义向国家法团主义的转型,并已经显示出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型的明确特征。国家对行业协会空间无所不在的穿透和无所不能的控制已经不复存在,企业自发组建行业协会的常规性合法渠道已经存在,并且能够正常运行。然而,在国家主义遗产依然强大的社会背景中,中国行业协会对国家依然具有严重的依赖性,进一步转型的障碍还是不小。如有近三分之二的行业协会认为应该挂靠业务主管单位。
四、结论性思考: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型?
在一个和本文相关的研究中,基于对2000年前后的北京、浙江、黑龙江三省市社会团体调查问卷数据,顾昕和王旭发现当时专业性社团与政府的关系处于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状态,并提出一个问题:国家法团主义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在中国究竟是一种常态,还是一种过渡形态?如果是过渡形态,那么它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型的重要关节何在?经过十年的发展与改革,无论从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还是就其具体的实践层面而言,我们发现国家法团主义确实是一种过渡形态。随着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朝着社会法团主义的方向转变。这种转变背后的动力又是什么呢?
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的路径大体有三:第一种是公民社会反对国家的路径,其中社会团体不遗余力寻求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这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的推动力;第二种是国家中心论的路径,亦即国家根据自主的理性选择在推动自主性社团空间的成长中发挥各种积极和消极作用;第三种是国家与社会相互赋权的路径,亦即国家与社会双方主动寻求建立公私伙伴关系以治理公共事务。

图6 政府拨款在不同行业协会总收入中的比较,2010注:N=199,数据缺失的社团占总样本(517)的61.5%。如果将它们视为政府拨款比例为零的话(因为回答问卷时,回答者倾向于跳过答案为“没有”的问题),那么政府拨款比例为零的行业协会比重将达到总样本(517)的87.4%。
实际上,法团主义在西方演变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三种思路的适用性。基于维阿达对大量研究文献的综合,我们可以构画出法团主义变革的脉络。在法团主义的初期阶段是所谓“传统性法团主义”,其中各种源于身份的社群(例如贵族团体)同国家建立各种特殊关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各种行业协会逐渐形成,向国家争取对其代表性的承认。国家在应付这些“新社会问题”时,一开始往往会采取压制性政策;之后国家基于各种理性考量,开始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国家在承认新兴社会团体的合法性的同时,也把它们纳入到既有的体制之中。随着整个政治体制走向自由化和民主化,国家与社会的伙伴关系也就变成社会法团主义的常规形态。
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与行业协会关系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型涉及到更广范围内的制度性变革。在中国社团空间的成长过程中,至少在行业协会领域,公民社会对抗国家的路径实际上极不可能存在,因此同本文所关注的社团空间的转型问题不大相干。实际上很多行业协会是从国家体制中分离出来的,国家在行业协会空间的发展中,不仅维持了控制,而且还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因此,当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从全能性政府向服务性政府转变的过程中,把更多的服务递送工作转移给民间非营利性组织,包括行业协会。随着政府职能改革的深入,一个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或者说公民社会与国家协同发展的局面还是可以期待的。
本文的经验研究发现,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和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相对于多元主义和国家法团主义,我国的行业协会和国家的关系正在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模式的转型过程之中。虽然这一转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多快的速度在进行,这还有很多尚待仔细考察之处,这不仅体现在政府监管体系本身的变化上,而且还体现在这些行业协会组建和运作过程中政府涉入的程度。根据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三省市社会组织问卷调查数据,我们发现:随着政府对社团监管体系正变得更为开放,自发成立的行业协会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的第一个十年内有大量的增长;国家为行业协会提供的财务支持非常有限,大多数行业协会都依赖于社会和市场资源获取资金;业务主管单位通过领导人选择来控制行业协会的方法也越来越少,行业协会领导人经过民主产生的比重在上升;与此同时,业务主管单位更多地采取了财务审计、年度报告审查等事后监督模式而非事前控制,从而减少了对行业协会日常运行的干预。虽然现在行业协会还存在着行业代表性不足等问题,社会组织与政府所拥有的权利还不对等,使得社会法团主义模式在中国的存在还缺乏充分的制度化条件。然而,本文发现,尽管在一些关键性因素(尤其是行业代表性和自主性)上面尚有阙失,但是国家和行业协会关系,不仅仅从正式的法律法规,而且还从实际操作层面的国家和行业协会关系角度来分析,大体上是向社会法团主义发展的,当然这一发展过程或许将会是漫长的。
[注释]
① Tang Ts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②陈剩勇等,《组织化、自主治理与民主——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 John L. Campbell, J. Rogers Hollingsworth, and Leon N. Lindberg (eds.), Governanc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④ Wyn Grant,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Vol. 9, Issue 2 (1993), pp. 86-100.
⑤ Rainer Eis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ate-Business Relations in Europe: Interest Mediation, Capitalism and EU Policy Making. London: Routledge, 2009.
⑥ Philippe C.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36, No.1 (1974), p. 86, pp. 93-94.
⑦ Philippe C.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36, No.1 (1974), pp.103-104.
⑧ Philippe C.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36, No.1 (1974), pp. 85-131.
⑨ Margaret Pearson, “The Janus Face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 Socialist Corporatism in Foreign Enterprises, ”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1(1994), pp. 25-26.
⑩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155-175页。
[责任编辑:韩小凤]
张长东(1979-),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博士;顾昕(1963-),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荷兰莱顿大学政治学和历史学博士。
* 本文的理论框架借鉴了本文作者顾昕与王旭在2005年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一篇关于专业性组织和国家关系的论文,该文基于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2000年三省市社会组织问卷调查数据库,而本文则基于2010年三省市社会团体调查数据库,并改以行业协会为对象进行研究。王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在与顾昕合作发表论文之后不久,就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转赴山东任职。2013年1月9日,王旭不幸逝世,年仅43岁,时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政府新闻发言人。谨以此文纪念不幸英年早逝的王旭博士。本文的写作得到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袁瑞军教授的大力支持,深致谢意。
C912.2
A
1003-8353(2015)02-00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