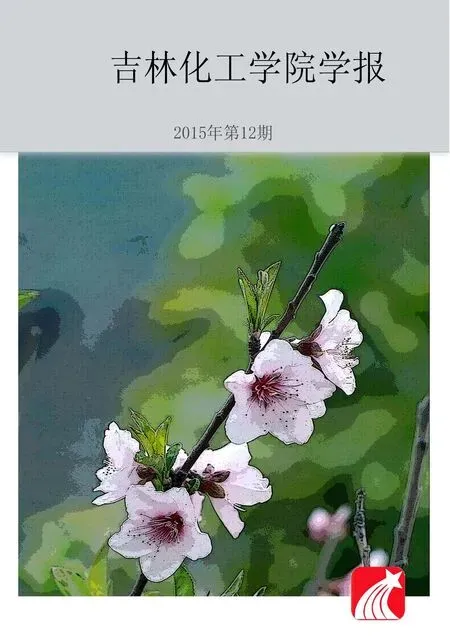美国中国学研究论略
2015-04-18张丽丽
张丽丽
(吉林化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吉林 吉林 132022)
美国中国学研究论略
张丽丽
(吉林化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吉林 吉林 132022)
摘要:我们如何用分析的方法逐个梳理美国中国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在美国中国学的学术谱系下进行研究,是一个既具有学术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的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的选题。
关键词:美国中国学;研究;述介
作为全球意义的大国不断发展、日益崛起的中国,不管是它的现代图景还是历史记忆,一直都吸引着海外中国学界,这种吸引已经从单纯的兴趣爱好——汉学衍伸为带有强迫意味的现实需要——中国学。虽然这种分类方法不够精确与科学,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概括的维度。随着中国逐渐走向国际舞台的核心位置,对世界范围内人们“中国观感”的认知与探讨就成为我国学术界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了,相较而言,对海外精英群体中国观的认知则尤为重要[1-5]。
一、研究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的日益开放,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程度日益加深,国内学术界对海外中国学的重视程度也日益提高,出现了一系列专门研究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机构及学术团队。
1975年,在著名学者孙越生的倡议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了“国外中国学研究室”,设在现信息情报研究院的前身情报研究所之下,这是国内学术界最早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术机构,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国外中国学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1985年,北京大学组建了“国际中国学研究室”;1991年,四川外国语学院成立了“国外中国学研究所”;1992年,清华大学成立了“国际汉学研究所”;1996年,华东师范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分别组建了“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汉学研究所”和“海外汉学研究中心”;2003年,陕西师范大学成立了“国际汉学研究所”;2005年,苏州大学成立了“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6];
从上述研究机构的设立情况我们大体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态势非常迅猛,可以说,海外中国学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的“显学”之一。虽然上述学术机构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与侧重,但总体上都属于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范畴,其研究对象的属性都可以纳入中国研究的范畴。其中,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对海外中国学尤其是美国中国学的学术史梳理与研究是比较有特色的。
目前,国内研究海外中国学的学术期刊或集刊有《国际汉学》《世界汉学》《汉学研究》《海外中国学评论》等几种,刊登国内外学术界中国研究与中国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上述研究机构与学术期刊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内学术界研究海外中国学的最高水准,海外中国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历程昭示着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的世界性意义的认知逐渐趋于成熟,对海外中国学的理解逐渐趋于深刻,更为难得的是,国内学术界开始在自觉意义上建构海外中国学视野下的中国观感。国内学术界对海外中国学的学术史总结与反思工作正在逐步展开,其中包括对海外中国学演进历程的梳理,对其演进阶段、规律、特征的探讨,以及对海外中国学著名学者、主要著作、理论形态、思维方式、观察视角及方法论的引介与研究。总体上,上述国内学术界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多集中于学术史研究层面,对傅高义的中国研究及其中国观的涉猎也主要是在这一范畴内进行的,但在研究深度上明显不足。
就美国汉学-中国学学术史意义上的谱系问题,国内学术界大体能够达成共识,即美国汉学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一战结束后美国汉学开始偏离欧洲传统汉学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范式,成为一支独立力量。1925年,太平洋学会的建立标志着美国汉学开始转向现实问题与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领域,哈佛大学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与左翼记者也推动了这一转型,美国中国学的雏形开始形成。二战后,美国中国学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重镇、代表及发展趋势。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之所以支持学术界进行中国研究,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决策中迫切需要掌握东亚地区的相关资料,需要深刻理解东亚地区的历史与现实状况,这种现实诉求催生了美国中国学。回应这种需求的最典型例子就是费正清的区域研究范式,这一特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主导着美国中国学的学术实践。二战结束后,战时的现实诉求减弱了,但随之而来的冷战局面又使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的需要变得越发迫切,美国现代中国学从此得以迅猛发展。
衡量某一学科的研究进展情况,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展开该学科的学术史研究,对该学科领域各项学术成果的个案分析则是最终综合概览该学科研究进展情况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准备工作。
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学的借鉴尚处于初级阶段,“在学术交流开放后的三十年里,中国学界对于海外中国学太多翻译、模仿和跟风。”并没有深入思考海外中国学的理论内涵,对其研究视角、方法、问题的提出及解决也较为缺乏深入探讨,很多时候只是简单地将海外中国学界构建的阐释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理论模式照搬过来,这种情形的存在影响到中国学术界学习与借鉴海外中国学的效果。
尤其是在对明清以来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研究上,研究者的分布密度与影响力尤其显著。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明清以来的中国历史较其前期具有了更多本质意义上的内涵变化,即具有了更多的近代意义。海外中国学尤其是二战以来的美国中国学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意味,出于为现实需要服务的出发点,他们对中国的解构就倾向于更多地集中在近代中国。
近代以来,中西方之间交流沟通的频繁程度要较以往各个历史时期剧烈得多,其内涵也丰富、深刻得多。中国以其庞大的体量、精致的古代政治设计、悠远神秘的历史文化以及温顺复杂的国民性格长期吸引着传统汉学家的目光,而现代中国学家则把研究维度放在传统中国在各个社会层面的近代转型上,但在总体上,这两种维度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只不过其关注重点有所区别,在这种意义上,汉学-中国学可以被认为是海外学术界中一个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科门类,或者说是一个由各学科组成的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综合研究领域。
从词源上讲,Sino与China具有共同的来源与意义。China最初可能来自中国历史上著名朝代秦(Cina-s)的音转,拉丁文表示作“Sina”,最早由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采用,用以指代中国;Sino与之相类似,也可能来自秦(Ch’in)的音转,最早出现于1879年,后几经演变,由“Sino”,到“Sinai”,再到“Sin”,其意义在“中国的”“中国人的”(the Chinese)与“中国”(China)之间不断转换,最终确定表述为“Sino”,指与中国或中国人相关的事情(Chinese and something else;relating to China)。所以说,从词源的角度上讲,汉学(Sinology)与中国学(China Studies)之间的差异并不是那么显著[7-8]。
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讲,汉学(Sinology)与中国学(Chinese Studies)则具有迥然不同的分野。朗文词典对汉学家(Sinologist)的定义是研究中国文化、语言与历史等领域的人(someone who studies Chinese culture,language,history etc)。朗文词典所列举的文化、语言、历史领域正是传统汉学关注的焦点领域,也就是更偏向于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这是符合汉学实践意义上的学术倾向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正是汉学产生时期欧洲人理解上的中国。
二、对中国学者的启迪
海外中国学在本质上是国外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是来自“他者”的注视,所谓“中国学”首先是“外国学”。因其问题意识、研究思路乃至方法常常跟它本国的、当时的学术脉络、政治背景、观察立场密切相关。所以我们第一步就应该把“中国学”还原到它自己的语境里去,把它看成该国的学术史、政治史、思想史的一个部分,不要以为他们和我们研究的是一回事。也就是说,海外中国学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它的优点在于把海外当下思考的问题、流行的新理论和使用的新方法,融会在具体的中国历史、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中,他们的一系列做法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思路,让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还可以这样去分析、去研究。但他们毕竟是外国人,他们有自己的语境、自己的立场和自己的角度。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就去盲目地接受、跟风就会使自己的认识变得缺乏根基。
总体上说,中国学界的自我意识建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由理性主导的过程,“在世界文化的范围内确立对中国文化的自觉。在中国重新返回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刻,文化自觉成为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实现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在这样的考察中,我们会有一种新的历史感,会重新树起文化的自信。”首先我们要在自身的历史语境中认识自己的文化起点、文化内涵,再从外界中国研究中获取我们所缺乏的独特视角,最后将二者结合起来,放到现代语境中进行综合考察,建构出中国学界的自我意识,实现民族文化的自信、自觉。
三、对美国政府与民众中国观感的影响
在中美关系中,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著书立说,不时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和传统上以文史哲等传统文化为研究领域、远离对华决策层的汉学家是有所区别的。中国学家的观点经常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这些专家学者被称为美国政府的“智库”,智库通常由学者、专家或经验丰富的实践者组成,作为一种沟通知识与权力的桥梁而存在,他们的存在可以完善政府的科学决策过程,仅在哈佛大学就有十多个与中国研究有关的机构,这些机构的研究成果或多或少地都会作为美国政府的决策参考。
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决策。他们经常应邀到国会作证,就涉华问题提出建议。一些重量级的中国问题专家通常还是一些著名智囊团的成员,可以通过参与撰写提交政府的政策报告来影响对华决策。这些智囊团还适时举行研讨会,邀请政界人士参加,进行学术界与政界的沟通。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还得以进入政府部门,直接参与政府决策。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不可能没有利益冲突,但同时也不可能在全球化成为既定事实的情况下拒绝相互合作,中美两国需要在广阔领域内进行频繁的沟通与合作。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中历来重视对智库的咨询,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了解美国学者中国学的研究现状与水准,以及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和判断,他们持有的中国观感,对于我们理解美国政府对华策略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价值。也不失为返观内照的一种方式。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对现实问题的主观理解会有偏差,这样呈现出来的只是“美国眼中的中国”,与“真实的中国”很有一些距离。但是,美国中国学研究总体上向着更符合客观事实、更严密细致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美]施坚雅.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美]塔尔科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刘进等译:经济与社会:对经济与社会的理论统一的研究[M].刘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美]王国斌.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面[M].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4][英]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M].陈才,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
[5][美]魏斐德.王小荷译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M]王小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6]程中原.与哈佛学者对话:当代中国史若干问题[J].党史文汇,2009(7).
[7]褚艳红.美国中国学的奠基时期:“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学”学术研讨会综述[J].探索与争鸣,2006(7).
[8]崔存明.美国的中国观——新乐观主义和一些历史性的考察[J].国外理论动态,2007(9).

A Brief Review on China Studies
ZHANG Li-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Jilin Institute of Chemical Technology,Jilin City 132022,China)
Abstract:How to comb the achievement of China studie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analysis is a significant topic of academia and reality which deserves the further research.Meanwhile,we discuss it in the academic genealogy of China studies.
Key words:China studies in America;study;introduction
中图分类号:G 642
文献标志码:A DOI:10.16039/j.cnki.cn22-1249.2015.12.031
文章编号:1007-2853(2015)12-0109-04
作者简介:张丽丽(1979-),女,吉林德惠人,吉林化工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跨文化比较方面的研究。
收稿日期:2015-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