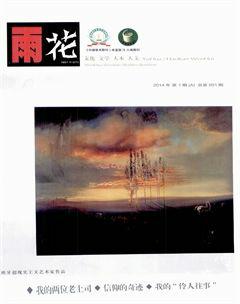我的“伶人往事”
2015-04-17孙曼
孙曼
在那个年代,离婚还是件大事,一时间全楼人议论纷纷,所以连我们小孩子都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大多数人都谴责男方不道德,是不负责任的“陈世美”,但也有个别人觉得他是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勇气可嘉。不过议论归议论,大家对他们一家的态度还是很友善的。
近日重读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卷首那句“我听得耳热,他唱得悲凉。粉墨人生,风流云散,由伶人身世,看尽世情悲欢”,深深地打动了我,也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由于父母工作的关系,我从小在省戏剧学校的大院里长大,虽不认识多少名伶,但也有很多难忘的人和事。
戏剧学校,顾名思义,就是培养戏剧演员的地方。那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各行各业百废待兴,戏剧学校也不例外,京剧班、越剧班、话剧班,都是新招的一批批少男少女学员,很是热闹。校内还有一剧场,有正规的舞台,却没有观众席,有演出的时候会摆上一排排折叠椅给观众坐,没有演出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排练场,我对京剧班学员的排练场景印象尤为深刻:他们一律穿着那种深蓝色的运动衫,手臂外侧有两道白杠,每天都三五成群地练功。有吊嗓子的,有踢腿劈叉的,还有很多人排成一行,双臂向外伸开,无数次地围绕着排练场疾步走,听说这个动作叫做“跑圆场”。我那时大约5岁多吧,刚开始记事,梳着两个羊角辫,是一个文静可爱的小姑娘,我最爱看的是——女生们练习“甩水袖”,那水袖一般都由白色或天蓝色的丝绸制成,当本身就很漂亮的女孩们双手舞动着长长的水袖时,顿时有一种“仙女下凡”之感,令童年的我深受震撼。老师一般都很严厉,嘴里念叨着“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手持一把竹尺,不停地巡视着,偶尔遇见不认真练的人,就对着其屁股来上一下子,当然,下手并不重。所以,多年后,当我看到电影《霸王别姬》中孩子们练功时的情景,觉得是那么的亲切,一切都似曾相识。
有一个夏天,小剧场里每天都在排练《红色娘子军》,不记得是什么剧种了,反正光是彩排我就看了好多遍,也不厌倦。有一幕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恐惧——吴清华逃跑,黑沉沉的椰林从天而降,吴清华在林中独舞、旋转、跳跃,倒踢紫金冠,但还是不幸被南霸天的家丁抓到了,这时,南霸天在令人心生恐怖的音乐声中出场,身后跟着四个丫鬟,为他撑着一把巨大的阳伞,他穿着黑色的对襟绸褂子,满脸横肉,面相狰狞。总之,他是孩提时代我心目中最可怕的人!其实演南霸天的演员也是我们一个家属楼上的邻居,但看多了戏之后,路上遇见他我只想远远地躲开,父母再怎么敦促我“叫伯伯好”,我也忸忸怩怩地看着地面半天不愿意开口。虽说那个演员生活中倒是个笑眯眯的老好人,不过,孩子哪能分得清戏里戏外呢?
成天出入排练场的我,很快也有了一个登台的机会。话剧班在排演一场话剧,需要一个5、6岁的小姑娘,其实只是一个没有台词的龙套角色,但我也每天跟在后面排练得不亦乐乎。依稀记得我上台后先是在房间一角独自玩一个洋娃娃,大人们在热烈地讨论着粉碎“四人帮”的新闻,后来我突然发烧了,还晕倒了,然后一个大叔匆匆抱起我,奔赴医院,这幕戏就算是结束了。为了让我在正确的位置晕倒,细心的导演还用粉笔帮我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害得我几天排练下来,心爱的粉红毛衣都被粉笔灰弄得脏兮兮的。这次参加演出的经历,使我获得了人生第一笔收入——5元钱的排练补助,并体会到了当演员的辛苦与无趣。说元趣,也许是因为当时我太小了,还无法体会到表演的乐趣吧。
那个年代的戏剧学校大院里,除了几栋简陋的教学楼、宿舍楼和一个小操场之外,竟然还有一处茂密的小树林,也可以说是尚未开发的荒地吧,那里很快便成为我们一群孩子的乐园,我们经常在里面流连忘返,躲猫猫、摘狗尾巴草编草帽、用一种蓝色的小野花编成花环戴在脖子上,总之,对于那个年代的我们来说,哪怕是一朵沾着露水的喇叭花,也是绝好的玩具。在夏日微凉的清晨,看见攀附在大树上怒放着的喇叭花,有淡紫色的、淡蓝色的,还有粉红色的,那种感觉,真是无比的惊艳!我对花草的热爱之心,就起源于童年时的那个小树林。至今,在我心中,“树林”,都是个潮湿、碧绿、凉爽、飒飒作响的字眼,提到这个词,我就会想到儿时在那里见到的布满长毛绒似的苔藓,会听到啾啾的鸟鸣和昆虫翅膀的摩擦声,会想象那密集的树冠形成的许多摇动的阳伞,以及喇叭花花瓣那绒布般的质感。对于我来说,小树林散发着梧桐树和青草的气息,它发出风声、流动的水声、鸟的歌声和啁啾声,还有昆虫的唧唧声和小青蛙的呱呱声;它使我联想到阳光投射到地上的圆圈、又大又甜的野杨梅、驮着嫩树叶的蚂蚁大队以及凉爽而昏暗的绿色光线。那两棵高高的野杨梅树,每到夏天,叶大如伞,一颗颗红艳艳的果子躲藏在茂密的树叶中间,让人看着都垂涎三尺。可是因为树太高了,一开始,我们几个小女孩只能通过摇动树枝,才能勉强吃到几颗落下的果子,它们甜津津、水灵灵的,还带着一层柔软的刺,美味无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有一年暑假,我们的家属楼新搬来了一对兄弟俩,哥哥的个子已经很高了,而且身手特别敏捷,只见他“嗤”地一下就爬到了树上,然后就不停地摘下野杨梅果丢给我们,有时甚至把一整根枝条都掰断了丢下来,我们在树下简直应接不暇呢。那个小男孩,那副豪侠仗义的形象,至今想起来我都觉得他好酷好帅!
家属楼其实就是由一栋三层的学生宿舍楼改造的,一共住了近30户人家,房间倒是很宽敞,但是没有厨房,做饭只能在走廊上,就像80年代有部电影《邻居》里描述的那样,这样一来,家家户户每天吃的什么饭菜,只要在走廊里嗅一嗅那飘在空气中的香味,立即就能知道了。哪家的主妇心灵手巧,哪家的主妇又懒又脏,大家都一目了然。那个年代的人们,生活中的确没有什么隐私概念。甚至有一次,二楼有一对小夫妻吵起来了,据说起因是因为丈夫嫌弃妻子生的是女孩(那时候已经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了),两个人吵得还很凶,后来左右隔壁的两家人都去劝架,有个厉害的大姐还指着男方的鼻子训斥了一句:“不要怪别人,生男生女,责任全在你自己!”就这一句话,那个丈夫不再吭声了。多数时候大家非常和睦,邻里之间做了什么好吃的,还会互相赠送一点,有一次隔壁的北方奶奶甚至送来一碗洋葱馅的饺子,令我们全家感到十分稀奇,没想到洋葱还能包饺子!还有一次二楼的李阿姨去上海京剧院观摩,回来时竟然带了8双皮鞋!全是为左邻右舍带的。只见她上楼时每只手里各提溜着4个大鞋盒子,活像一个跑单帮的小贩。她一到家,全楼爱美的女人们立即停下手中的家务,都涌进了她家里,叽叽喳喳地试穿,热闹非凡。虽住同一栋家属楼,但由于大家原本是不同剧种的演员,所以说起话来也是南腔北调。那操一口洪亮京片子的,基本都是京剧班的老师,他们一开口,是那么的字正腔圆,当他们注视着你的时候,眼睛都是会闪闪发光的,有在舞台上“亮相”时的风采。要是越剧、昆剧等南方剧种的老师,则都是轻轻柔柔的吴侬软语,就连吵架也像是唱歌一样,让人百听不厌。那个年代的戏曲教学,基本都还是靠“口口相传”,经常能看到有年轻人到老师家里来学戏,老师唱一句,他们学一句,甚至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是手把手教的。临走的时候,老师还会叮嘱一句:“冬连三九,夏练三伏。回去得继续练哪。”估计这些上门来学的都算得上是老师们的得意门生吧。有一位衣着普通的中年阿姨,看上去十分的和蔼可亲,后来才知道,她还是我们这个省里最权威的程派传人呢,这些都是在夏天纳凉时听大人们议论的。endprint
说起纳凉,则是另外一个吸引我们小孩子的时刻。那个年代没有空调,连电扇也很稀罕。所以每当太阳西沉后,吃过晚饭的人们,就三三两两地走出家门,把家属楼前的一块水泥地打扫干净,再洒上水,然后就带着各自的竹床和躺椅,出来乘凉了。夜色下和小伙伴们一起吃着西瓜看星星,还有,偷听大人们的谈话,是最有乐趣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内容都能听懂。有一个晚上突然停电了,眼见着家属楼变成了漆黑一团。有位伯伯是京胡师,喜欢在纳凉时也拉上几曲,他停下手中的胡琴,对旁边人笑着说:“住我隔壁的我那徒弟,上个月人家帮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刚刚他对象才来屋里找他,这下停电了,可真是太巧了!太好了!”尚未上小学的我,怎么苦思冥想,也没弄懂为什么“停电反而是太巧了,太好了”,于是傻乎乎地问他:“为什么呀?”惹得大人们一阵哄笑,但也没人告诉我答案,答案还是我长大以后自己琢磨出来的。还有一位年纪较大的京剧班元老,别人都喊他“大师”,他却最喜欢谈吃。我听到他用纯正的京腔在痛斥他太太包的春卷,说:“里面全是碎碎的韭菜和肉末,我刚咬一口就呸地一声吐出来了。您说这春卷能吃吗?春卷里面一定得放肉丝和韭黄,咬一口,拖得长长的,那才配叫春卷!”这位伯伯看来是个美食家,我至今还记得他那副义愤填膺的样子。有的老师以前是小有名气的演员,曾经走南闯北地演出,所以喜欢给我们讲祖国各地的各种奇闻异事,直听得我们、包括很多大人,都如痴如醉,忘了一天的辛苦和疲劳。渐渐地夜深了,空气变凉了,人语声也稀落了,人们这时才慢慢地撤回到屋里,整座楼也进入了睡眠状态。
有人认为四季中唯有夏天最苦,所以俗称苦夏,作家冯骥才在《苦夏》一文中说过:“在快乐的童年里,根本不会感到蒸笼夏天的难耐与难熬。唯有在此后艰难的人生里,才体会到苦夏的滋味,快乐把时间缩短,苦难把岁月拉长,一如这长长的、仿佛没有尽头的苦夏。”这段话完全说中了我童年时对夏天的感觉。
转眼间我上小学了,这一年,家属楼搬来了一些年轻的单身演员,据说是新一届京剧班的学员毕业了,都分配到了省京剧院,但是那里没有足够的宿舍,所以就住进了我们这栋家属楼,于是楼里一下子变得更热闹了。本身他们都是经过层层选拔才当上省级剧团演员的俊男美女,有时晚上演出回来,还没来得及卸妆,更是美得像画中人一般。脱下戏服后,他们又极为时髦,所有最流行的服饰装扮,像什么尖头皮鞋、喇叭裤、大波浪发型和指甲油,都会很及时地出现在他们身上,连我们几个楼里的小学生都喜欢带着崇敬的心情,口中喊着哥哥姐姐,跟屁虫般跟在他们身后。有一天我还闹了个大笑话——那时我们家只有一间朝南的大房间,父母和妹妹住着,还有一间朝北的房间,用木板隔成了两半,我们家只拥有其中不靠窗的半间,晚上我一个人住在里面。因为没有窗户,白天也需要开灯,我们称其为“黑房间”。当时家里只有一个闹钟,放在父母床边,每天清晨都是他们准时来叫我起床上学。有一天夜里我在睡梦中,突然被外面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谈笑声惊醒,走廊里似乎还有人在点煤气炉煮面条,其实是他们深夜演出回来在做夜宵吃,但住在“黑房间”里的我却误以为已经是新的一天开始了,于是连忙起床,穿戴得整整齐齐的,连红领巾都系好了,可是父母却迟迟没有来为我开门。当时我心里那个急呀,因为一进小学我就有幸被选为了班长,每天负责检查同学们的迟到情况,班长怎么能够带头迟到呢?于是,我开始拼命敲门,把两个小拳头都敲得通红通红的,也没人听见。然后我灵机一动,改为敲房间里的那个木板隔断,还带着哭腔喊道:“开门!开门!我要上学,我要迟到了……”这下惊动了隔壁的男演员,他赶紧去通知了我父母,帮我打开了房门,其实这时才是晚上11点多钟,都是让那间“黑房间”给闹的!这次事件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父母帮我也买了一只小闹钟放在床头,二是左邻右舍的家长都拿我“半夜急着上学”的事例教育自己的孩子,一不小心我成了全楼小孩子的学习榜样。
进入8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到了我们戏剧学校的大院,那时有一部很受欢迎的日本电影《追捕》,不过大家喜欢归喜欢,总觉得那是发生在异国的故事,离我们的世界是那么的遥远。没想到有一天,日本电影代表团到学校来交流访问,里面竟然还有扮演“真由美”的中野良子和扮演“横路敬二”的田中邦卫等著名演员!那一天校园里到处彩旗飘飘,挂着很多醒目的横幅,学员们也穿上了华美的戏服,化了妆,与日本演员们交流得十分热烈、开心。当然,白天我去上学了,没能亲眼目睹那盛况,但是学校派专人拍摄了很多照片,贴满了校园内的几个大橱窗。我每天放学的路上都要把那些照片看上一遍,到最后就连每张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都背得滚瓜烂熟,可见当时它们对一个孩子的冲击力有多大。还有一次,学校布告栏中通知说,周末会有一位著名的美国女高音歌唱家来校演出,希望大家踊跃观看,我们整座家属楼的人几乎都去了。果然,演出当天,来了一位金发碧眼的女高音,穿着一袭很典雅的深蓝色晚礼服,在钢琴的伴奏下,一个人一口气唱了将近两个小时。现在想来她唱的应该都是些世界著名歌剧的选段吧,但对于当时我们这些观众来说,有点过于阳春白雪了,语言又不通,渐渐地大家就没了耐心,想回家看电视了。那一阵有些电视连续剧,如《霍元甲》等等,放得特别火,人们晚上一般都不太愿意出门。主办方也许是怕观众都走光了,对千里迢迢来演出的美国艺术家不礼貌,竟然将剧场从外面锁了起来。于是我们这些观众只好无奈地聚集在剧场门厅里,男人们抽烟,女人们拉家常,孩子们追跑打闹,而观众席上却门可罗雀,只有我那专业从事作曲的父亲,从头听到了尾。这可以算是一次不太成功的中外文化交流吧。
父亲毕业于音乐院校作曲专业,一开始对于“分配到剧团,为乐队配器写谱”有点失望,但他是一个性格温和、脸上时常挂着微笑的好人,再加上我那活泼开朗、热爱生活的母亲,一家人的日子虽然朴素简单,但却过得十分快乐。母亲是戏剧学校的文化课教师,她爱读书,爱养花,闲来经常把几个花盆楼上楼下地搬来搬去,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名贵的花卉,无非就是一些茉莉、月季以及风仙等,但那些日日盛开的小花,却开启了一个小女孩对花的热爱之心,渐渐地我也学会了去欣赏各种花的芬芳气味和美丽形状。有一次,母亲采下绽放的凤仙花,找一块光滑的石头用力磨碎,然后把那红色的汁液涂在了我和妹妹的指甲上,我们的指甲就一直是红艳艳的了。幼小的我,那天一直很惊喜地看着自己的双手,好像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幸福的感觉。记忆中另外一个幸福时刻是——在我还没有上小学、没有住到“黑房间”之前,经常早晨一睁眼,父亲拉开窗帘,金灿灿的阳光会一下子洒满整个房间,然后他会立即打开收音机,当时我们家有一台长方形的、还带着四个脚的“红灯”牌收音机,收音机里会传来一个很好听的男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乐曲”。好像那时有专门的古典音乐频道,父亲每天都会伴着收音机里的音乐给我们讲解,这是谁的作品,那是谁的作品,还讲过舒伯特穷困潦倒时拿《摇篮曲》手稿换土豆吃的故事。在金色的朝阳中听着美妙的《四小天鹅舞曲》,或是斯特劳斯的圆舞曲旋律,5岁的我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幸福。endprint
不过等到我上了小学之后,收音机的地位渐渐就被录音机取代了,家属楼里那些年轻人,几乎人手一台,有双喇叭的,还有四喇叭的,成天播放着邓丽君的歌曲,什么《你是一朵向日葵》、《千言万语》等等,那甜美缠绵的歌声,恨不得把人的心魂都勾走。但是老派一点的艺术家邻居们都很不爱听,我曾经听到好几位爷爷奶奶辈的人摇头叹息道:“靡靡之音啊,靡靡之音!”可是没有用,年轻人依旧照听不误,还谈起了恋爱,那些年轻的单身演员中一下子出现了好几对金童玉女,他们出入都成双成对的,这很快又成为了大家的谈资。有一个被称为“一号大美人”的姐姐,好像是唱花旦的,洁白的肌肤,水灵灵的大眼睛,苗条的身段,的确是美若天仙,就连市中心照相馆的橱窗里也长年累月地挂着她的大照片。她当时和一个演武生的小伙子形影不离,我曾经亲眼看到过他们在宿舍里含情脉脉地相互喂饭,你先吃一口,我再吃一口,那个甜腻呀,旁边还用收录机放着《月亮代表我的心》!但是过了一些日子,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去上学的路上,却看到他们俩在排练场外的走廊上激烈争论,小伙子的脸因为愤怒都变得扭曲了,后来“一号大美人”姐姐捂着脸哭了起来,伤心欲绝的样子。那天下午的数学课我几乎都没能听得进去,眼前总是浮现出她那哗哗流淌的眼泪。他们到底为了什么事吵成那样?这令年幼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我懂得了“谈恋爱的人,有欢乐也有悲伤”这个道理,这就是我童年时最初受到的、关于爱情的启蒙教育。
其实远不止这些,家属楼里还发生过更加激烈的“作风事件”。有一位已婚的男演员,长得十分英俊潇洒,在演一部爱情戏的时候,与年轻美丽的女主角假戏真做,堕入了爱河。尽管男方在家乡还有妻儿,但最终他还是抛妻别子,与女主角重新结婚了。再婚后他们又生了一个漂亮女儿,一家人看上去很幸福。但是有一天,前妻找上门来,据说是突然从口袋里抽出一把水果刀,在女主角的脸上划了一刀。好在划得不重,还不至于毁容,不过也在额头处留下了一条伤疤。在那个年代,离婚还是件大事,一时间全楼人议论纷纷,所以连我们小孩子都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大多数人都谴责男方不道德,是不负责任的“陈世美”,但也有个别人觉得他是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勇气可嘉。不过议论归议论,大家对他们一家的态度还是很友善的。有天傍晚这个男演员买了一瓶芝麻油回来,用网兜拎着,一不小心在楼梯上磕掉了瓶底,油顿时流得楼梯上到处都是,听到他的惊呼声,楼上楼下的邻居们纷纷跑出来,有的拿着抹布,有的拿着拖把,手忙脚乱地帮他收拾得干干净净。美食家京剧大师一边搓着抹布,一边用浓重的京腔调侃道:“嗬,今天连我们的楼梯都喝饱芝麻油了!只是可惜了这一大瓶好油!”还有个一贯热心肠的大妈,满怀忧虑地戳着男演员的额头,对他说道:“你看看你!可得把今后的日子过好了……”好像这次油瓶碎了,也和他的婚恋风波有关似的。听着的人,也只有连连点头的份……
后来,到我小学毕业时,各个文艺团体、包括戏剧学校的条件都越来越好,盖了很多厨卫齐全的、真正的家属楼,我们都搬离了那座简易的学生宿舍楼,但是依然能够经常听到当年邻居们的消息。戏剧越来越不景气,听说那些神采奕奕的年轻演员们,很多都改了行,有人做了晚报的娱乐版编辑,有人苦心钻研,成了篆刻大师,还有一位唱老旦的漂亮姐姐嫁给了台湾富商。我们家隔壁的一位性格认真的姐姐,当时就因为忍受不了剧团的无所事事,每天晚上都背着一个大算盘去上财会夜校,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一年后,当她顺利地跳槽到一家工厂当会计的那天,还请我和妹妹一人吃了两块花脸雪糕!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奢侈的,可见成功换工作,对她来说是一件多么大的喜事。搬家前,她还收拾了一包再也用不上的舞台饰品给我们当玩具,里面有色彩鲜艳的绒花,有有机玻璃制成的亮晶晶的簪子等,我们两个小姑娘欣喜若狂,她却伤感地叹息道:“学了那么多年戏,吃了那么多苦,流了那么多汗,也没有登过几次舞台。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这位姐姐的感慨我十分理解,听说她出身于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当年以出众的外形和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省城的戏剧学校,全村人还敲锣打鼓欢送她的呢。可是现实就是这样残酷,随着电视的普及,后来又流行起跳舞、唱卡拉OK等娱乐方式,看戏的人的确越来越少了。当然,也有少数人一直坚守着艺术之路,有一天,我突然在报纸上看到,当年的“一号大美人”姐姐摘取了“梅花奖”桂冠,并荣升了京剧院院长!我眼前顿时又浮现出儿时那个阴雨绵绵的下午,她与男友吵架后痛哭时的情景……心中有一点小小的好奇,不知后来她与那个小伙子,到底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呢,还是劳燕分飞了呢?已无从知晓。
但是前两年有确凿的消息传来说,那对历尽波折离婚再婚的神仙眷属,后来也分开了。他们的女儿长大之后,出落得比刘亦菲还要美,在大学里曾是当仁不让的校花,现在已成长为一名在其专业领域小有名气的青年学者。不过,在经历过一段短暂的不幸婚姻之后,现在她也离婚了,和她妈妈住在一起,两个人相依为命,过着极为低调的生活,母女俩都不再貌美如花。偶尔有老邻居见到我父母时,会谈起那些往事和这些年大家的变化,唏嘘不已,还有人会摇头叹息道:“一切都是命。”
不过我倒不这么认为。已经成人的我,在经历了一些人生的酸甜苦辣、明白了与异性的相处之艰难之后,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理解。我相信当年他们都是真挚地爱着对方的,只是彩云易散琉璃易碎,要怪只怪岁月太长,日子太久,而人与人之间的心灵隔膜又太容易形成、且难消除!不是吗?
80年代初的某个国庆节前,那些年轻演员们在练合唱,好像是当年的一首流行歌曲,叫做《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词中唱道:“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我每天放学回来时,都津津有味地趴在排练室窗外看他们唱,还记得当时他们脸上绽放着的那种青春的光芒。
一晃真的好多年过去了,像张爱玲说的那样,“时代的列车,轰隆隆地飞驰而过”,我们身边的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戏剧学校大院里那栋宿舍楼还在,夏日的酷暑也依旧,但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是,当年那种闲适安宁的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那股关怀与温情……不知那些年轻演员们若再相聚时,会不会聊起从前的点点滴滴?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不知为什么,我记忆中的“伶人往事”,却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清晰了。初秋的阳光下,一闭上眼睛,就仿佛还能听到儿时隔壁的京剧大师、就是那个美食家伯伯,在唱《锁麟囊》:
“一刹时把前情俱已昧尽,
参透了酸辛处泪湿衣襟。
他教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
改性情,休恋逝水,苦海回身,早悟兰因……”
当年美食家伯伯唱着的时候,外面走廊上,他在小煤炉上炖着的萝卜仔排汤,正咕嘟咕嘟地冒着香喷喷的热气。而转眼间,他也已经去世好多年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