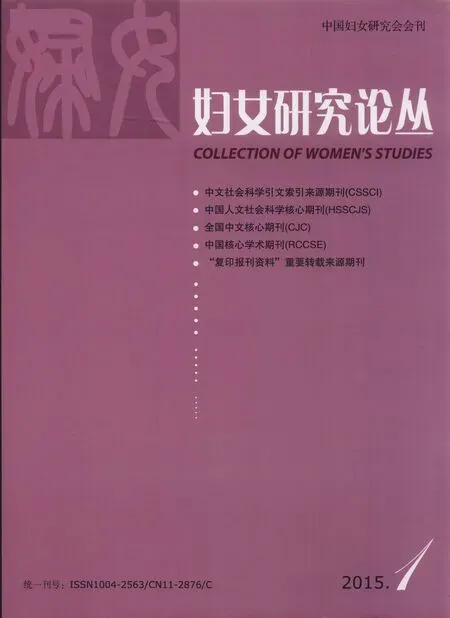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建构的中国妇女
——以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为例
2015-04-17龙丹
龙丹
(四川外国语大学出国培训部,重庆 400031)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建构的中国妇女
——以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为例
龙丹
(四川外国语大学出国培训部,重庆400031)
中国妇女;西方女性主义;东方主义
文章以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中国妇女》以及美国当代著名学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骆里山、周蕾对克里斯蒂娃的批评为例,从国际女性主义、东方主义批评和离散批评的视角出发探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建构中国女性时的几个重要特征:他者化、女性化、东方化,究其本质,对他者的书写是为西方女性自我树立一面镜子,折射了她们的自我身份建构。
白人女性主义者如何再现她们的东方姐妹?印裔美国学者钱德拉·莫汉蒂(Chandra Mohanty)在《西方注视之下:女性主义学者和殖民话语》(“Under Western Eyes: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一文中对此作了全面的总结,第三世界妇女往往被建构成一个简约、同质的群体,性别和种族是她们身份的主要标志:她们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是愚昧、贫困、无知、受传统和宗教束缚的受害者。相反,西方女性则自我建构为受教育的、现代的女性,掌控自己的身体和性并享受作决定的自由。在这个二元对立中,西方女性被建构为全球女性的典范。[1](P69)
西方女性建构的中国妇女形象又是什么样的呢?中国妇女曾一度被西方作家再现为全世界受父权制压迫最深的妇女,早在19世纪就有西方作家如此书写中国妇女:“中国妇女只是男人最中意的奴隶而已。”[2](P384)20世纪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麦克纳布(R.L.Mcnabb)在《中国的妇女》(The Women of the Middle Kingdom,1907)中写道:“中国妇女,无论她家住草顶土坯房还是金碧辉煌的皇宫,不知她的西方姐妹所享受的自由和安逸为何物,因为她是一个女奴、一个苦工,或是她主人家中的一个精美的玩物。她的家就是监狱,而她的丈夫是监狱长。”[3](P70)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陋习如溺婴、裹足、纳妾等几乎是每部谈到中国妇女的作品必不可少的话题,由此论证她们所遭受的深重苦难,同时反映中国社会的野蛮和落后。
事实上,西方所建构的中国妇女形象呈现出两个极端:女奴似的中国妇女、女王似的中国妇女。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以及从国家层面提出的妇女解放运动引起了西方女性主义者的兴趣,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以后,不少西方女性主义者欲一游中国,亲眼目睹中国妇女的解放,试图从中发掘一些对西方妇女问题有启发的东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方关于中国妇女的想象一反受害者模式,而把她们建构成拥有权力和自由的女权主义者,连她们的西方姐妹都无法企及。1974年5月,作为法国知识分子论坛《原样》(Tel Quel)的一员,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菲利普·索列尔(Philippe Sollers)以及《原样》杂志主编马尔塞林·普雷奈(Marcelin Pleynet)等人对中国作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参观访问。克里斯蒂娃应法国妇女出版社邀请,当年就发表了这本纪实游记《中国妇女》,此书是西方女性主义者对中国妇女进行乌托邦式想象的主要代表作之一。该书的英文版于1977年在纽约出版,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一般读者较为熟悉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对克里斯蒂娃的批判,事实上,美国当代著名学者骆里山(Lisa Lowe)、周蕾(ReyChow)等也对其作出了尖锐的批评。三位西方当代著名女性学者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去阐释、批评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妇女的书写,这场理论的对话持续了将近20年,反映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论及非白人女性时的典型问题,即如何再现这些他者,如何避免陷入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误区,如何构建他者的主体性等问题。
一、《中国妇女》对东方他者的乌托邦想象
《中国妇女》虽然是在克里斯蒂娃访问中国后写成的,然而它重点探讨的不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妇女的生存状态和思想状况,而是想象了一个母系社会中的中国妇女形象,她统治家庭乃至整个社会,享受她的西方姐妹无法企及的权力和自由。克里斯蒂娃把中国妇女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史前的母系社会、束缚妇女的儒教时期以及妇女重获自由的新中国,她对第一个时期尤为偏爱。她根据西方人类学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推演而想象建构了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中国母系社会,女性享有绝对权力,而男性则处于从属地位。女人主导家庭,而男人从母亲的家族中挑选妻子。克里斯蒂娃认为,这种母系传统在中国文化中保留下来,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她认为,中文作为一种音调语言保留了母亲在儿童身份认同中的重要性:“中国儿童比其他语种的儿童更早参与社会交流的编码过程,这是由于他们能较早辨认汉语的基本轮廓——音调,儿童借助他们感知和清晰发出那些音位以进入编码过程。而且这一阶段对母亲身体的依赖是如此巨大,因此作为成熟语言的潜在活跃层,是母亲的心理-身体印记,持续了音调表达和交流。”[4](P53)因此,借助音调,汉语保留了前恋母情结的、前句法的和前象征的记录。她进一步论道:“中国文字在想象、姿态和声音的组织中保留了史前母权制的记忆,它也能够被整合进逻辑象征的编码体系中。”[4](P55)另一方面,在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原始家族的想象重构中,女人是性爱艺术的主要传授者,更重要的是,“女人毋庸置疑地有权享受性愉悦”,[4](P62)她认为这种以女性愉悦为中心的逻辑确保了中国两性的和谐。
克里斯蒂娃认为,中国的母系传统在儒教时代遭遇断裂,父亲的秩序取代了母亲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女人要么被排除在外,要么被无声地忽略。与母系社会不同的是,男性享有性愉悦。然而,中国文化的母系传统却并未消失殆尽。在父权制的家庭中,作为大太太的中国妇女通常享有管理家政的大权。即使是裹着小脚的中国女人,也能通过儿子、孙子而享有某种权威。随着历史的车轮进入五四时期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社会主义革命牢不可摧地联系在一起,她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儒教对妇女的束缚,重新延续了母系文化断裂的传统。克里斯蒂娃对母系社会中国妇女形象、母系传统的乌托邦想象,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西方白人女性正在面临的性别危机问题和西方女性主义者的理论难题。
当时,克里斯蒂娃以及她代表的西方白人女性,在一神教的资本主义社会寻求性别平等和妇女解放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阻力,因此把目光转向东方,希望从中国寻求灵感。克里斯蒂娃提出是谁在说话的问题,然后自答道:“是受够了这些角色的女性——圣母,基督处女,或因消失而美丽的贝特丽采(Beatrice)。她们的声音脱离了肉身,肉身暗哑;她们的词语节奏和语调被痛苦怪异地堵塞着,色彩富于想象却没有语言、没有声音也没有形象;她们身处在时间/知识之外,皮肤和内脏上被永远地刻画上多彩的韵律;无论‘社会化’的还是‘革命性的’斗争,都以她们的身体作为代价;她们的身体癫狂地叫喊着,连时光和岁月也变成了牺牲品;她们的身体被切断和吞并了:一方面,在分娩时享受着失语的快乐,把自己想象成宇宙循环的参与者;另一方面,她们又身处一种法律的(父权的、家族的、社会的、神的)象征性压力下,成为牺牲品,其身体被否认,但只要没被谋杀都发出喜悦的荣光。”[4](P15)这里克里斯蒂娃用诗性的语言勾勒出西方女性的现状——身心均受父权法律的压迫,自己却还充当着帮凶;被剥夺了主体却为父权社会歌唱。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无奈地问道:“处在转变中的中国,是否会成为我们的希腊?”[4](P65)对西方当代现实失望的克里斯蒂娃把目光投向中国这个古典文明,希望能找到根治西方女性问题的良药。
克里斯蒂娃进入中国时已经带着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即中国与西方是处于时空两端的完全不同的文化。然而这种差异却因为中国革命的成功让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对中国充满浪漫主义幻想,克里斯蒂娃更是对中国的妇女解放产生了美好的遐想,希望建构一个自由的东方妇女的形象来体现内心关于女性自由的遐想。此外,她试图通过建构一个中国母系社会来推翻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为首的西方理论家在理论建构中对妇女的边缘化。骆里山在批评克里斯蒂娃的《中国妇女》时指出,她通过想象一个前俄狄浦斯的中国母系社会,体现了几种欲望:“理论的欲望——寻找一个法国结构主义和心理分析以外的位置来从外面进行批评;女性欲望——去发现并赞赏绝对女性,去定位一个实现这种权力的母系社会。”[5](P139)
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妇女的书写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她遵从西方话语传统,想象了一个不符合现实的中国妇女形象,使之服务于她的理论建构;第二,她强调中国的阴性传统/母系传统,乃至把西方看成男性的自我,把中国看成女性的他者,复制了殖民主义话语的东西方二元对立逻辑。斯皮瓦克、骆里山和周蕾从不同的层面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了批评。
二、斯皮瓦克:《中国妇女》让中国妇女失声
斯皮瓦克1981年发表于《耶鲁法国研究》(Yale French Studies)的文章《全球语境下的法国女权主义》(“French Feminismin an International Frame”),以克里斯蒂娃的《中国妇女》为例探讨所谓“国际女性主义”的问题,指出克里斯蒂娃从一个享有特权的白人女性主义者的视角出发替中国妇女说话,事实上却令她们失声。她指出该书对中国妇女的再现充满认知暴力:“意识或主体的设想和建构最终与帝国主义的主体建构保持一致,让认知暴力伴随学问和文明的进步。而属下阶级的妇女将和以往一样不能发声。”[6](P90)
斯皮瓦克犀利地指出该书在再现中国妇女时的两大缺陷:第一,克里斯蒂娃把理论话语的建构置于中国的现实之上,因此误现了中国妇女;第二,克里斯蒂娃的跨文化书写仍然是种族中心主义的。
在详述克里斯蒂娃的理论缺陷前,斯皮瓦克讲述了童年的自己在1949年印度独立后见证的一段小插曲,显示出学院派女性主义者与第三世界妇女之间存在的误解和鸿沟。一个印度洗衣工指责另一个洗衣工侵占了她的河水时,后者辩解道:“你这个笨蛋!这是你的河吗?这是东印度公司的!”[7](P156)斯皮瓦克以此为例说明殖民主义统治虽然结束了,但是殖民主义的思想余孽仍然束缚着印度人,尤其是印度妇女。
西方女权主义者应该学会如何与印度洗衣工这样的第三世界妇女沟通,从理论思辨的象牙塔转回现实。但克里斯蒂娃在《中国妇女》中用西方理论去解读中国现实,必然导致误读。她套用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尤其是前俄狄浦斯阶段婴儿对母亲的依赖以及母亲对婴儿产生重大的影响,用前俄狄浦斯阶段去定义中国古代的母系社会,认为母系社会是该心理学理论的社会体现,以此来解释她心中的理想,即建构一个先于父权社会、先于男女不平等现象的女权社会。针对这一问题,斯皮瓦克认为不能把理论的思考凌驾于对现实的观察之上:“学院式的女性主义者必须学会向她们(第三世界妇女)学习,跟她们说话,质疑她们进入政治领域的途径,而不是仅仅借助于我们的高级理论和启蒙热情去纠正这些弱势妇人的历史经验。”[7](P158)
由于缺乏现实的观察,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妇女的书写以西方作家的文本为基础,因此她再现的是西方话语,而非东方现实。克里斯蒂娃关于中国古代母系社会的推断,基于葛兰言关于中国的舞蹈和民间传说的著作,以及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关于亲缘关系的人类学初期读本。斯皮瓦克指出,在克里斯提瓦短短两百页的著作里,“有七十页是没有任何档案史料证据的情况下,(她把)自己的猜测写成了史实”。[7](P157)
斯皮瓦克指出,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妇女的误读反映了广泛存在于西方女性主义思想中的种族中心主义:“无论‘基督教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是否追求性自由,对于中国的预言肯定是一种慈善行为。我以为,它起源于殖民主义安抚主义的症状。”[7](P161)斯皮瓦克通过对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妇女的再现,揭露了国际女权主义戴着“姐妹同盟”的面具,关注的仍然是西方女性自我的身份问题,而再次把第三世界女性的问题搁置。换言之,克里斯蒂娃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用西方中心话语来认识和阐释非西方妇女的体验和身份认同,究其本质是一种帝国主义的话语修辞。
克里斯蒂娃的目的并非要再现真实的中国和中国女性,而是为西方塑造一个史前的东方他者,作为一面镜子来反观自我:“尽管他们(克里斯蒂娃一行参观中国的法国知识分子)偶尔有兴趣触及形而上的、资本主义的、西方的他者,他们的问题始终是自我中心的:如果西方历史和哲学无法定义我们,那非-我是什么?”[7](P159)也就是说,他们试图通过认识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东方他者,从而从反面来定义西方自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克里斯蒂娃在讲述中国妇女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了史前的东方,而非当代的中国:“克里斯蒂娃更中意中国神秘的过去。关于当代中国的叙事多是时间、法律、重要的人物和地点。对‘典型’的东方充满了原始的敬畏,而对当代的东方则是现实政治的轻视。”[7](P156)
斯皮瓦克以《中国妇女》为例,指出把西方女权理论应用到政治地理语境不同的第三世界是危险的,因为掌握这些理论的白人女权主义者在广大的第三世界他者面前仍然享有某种特权:“第一世界的女权主义者必须学会放下作为一个女人的特权。”[7](P157)这里的“一个女人”指的是掌握话语权的西方白人女性,特权即她们替第三世界妇女言说的特权,她们的再现与殖民主义话语和男权话语一样可能导致第三世界妇女失声。
三、骆里山:《中国妇女》是新东方主义话语
华裔美国学者骆里山是美国当代学界研究、批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她关于多样化、移民等理论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代表作《批评的疆域——英法东方主义》(Critical Terrains:British and French Orientalisms,1991)一书以克里斯蒂娃和《中国妇女》为例,阐释了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的多样性。萨义德认为,西方关于东方的指涉都是服务于白人男性殖民主义目的,对此,骆里山提出质疑,她认为东方主义是一个包含多种子话语的母话语,而每种子话语再现东方的目的不尽相同,《中国妇女》则是服务于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女性东方主义话语。骆里山从东方主义批评的视角出发,指出《中国妇女》对中国妇女的东方化、理想化建构。
骆里山把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等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想象定义为东方主义话语体系中较为年轻的成员,称之为“后殖民主义东方话语”,它既批评传统东方主义话语中的霸权主义,也继承了其话语特征:“他们书写东方时采用的术语、姿态和修辞与以前的文本如出一辙。”[5](P138)克里斯蒂娃等人对中国的再现以20世纪70年代法国的社会境况为参照物,目的是解决法国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其中,克里斯蒂娃把中国建构成前俄狄浦斯的母系文化,她对中国他者的想象是为了“树立一个西方父权体制以外的女性的、母性的王国以颠覆西方的意识形态”。[5](P137)这种他者化建构表面上看来与传统的东方主义话语形成了断裂,实际上重复了其话语模式。
在克里斯蒂娃书写《中国妇女》的20世纪70年代,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受到攻击,自我与他者、男性与女性、文化与自然等之间的截然区分受到来自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等领域的质疑。骆里山认为,克里斯蒂娃想要超越西方二元对立思维范式,因此她建构了一个位于西方话语体系之外的绝对他者,以摆脱她在女性主义理论和心理分析理论中所陷入的僵局,她所建构的中国成为其欲望投射的客体,而她关于自我与他者的想象仍然重复了东西方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中国妇女》中言说的主体白人女权主义者克里斯蒂娃与言说的客体中国妇女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好像他们(中国人)看到的是奇异的动物,无害却不理智。没有敌意,但与他们隔着时空的深渊。”[4](P13)中国人在这里似乎是注视的主体,克里斯蒂娃是被观看的客体,而事实上中国人只是回应了她的注视:“户县农民那令人费解的注视只是回应了我的目光而已。”[4](P139)尽管克里斯蒂娃把中国妇女建构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原型,但她在现代中国的在场却仍然被视为中心,来自西方的白人女性从这个中心凝视边缘的他者。
《中国妇女》把中国社会建构为阴性的,而把法国社会想象为父权的,这同样重复了东方主义的话语修辞,即东方与西方分别代表阴与阳。克里斯蒂娃把中国传说中的母系社会称为前俄狄浦斯社会,西方则是俄狄浦斯社会。在前俄狄浦斯社会,母亲与孩子的天然联系从来没有被打断,而女性享有一切特权,在这里男性没有权威,更不存在男性压迫女性的现象,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母亲与孩子分离后的俄狄浦斯社会通过语言或其他社会化体制建立起来的。骆里山认为这种建构表达了作者克里斯蒂娃的三重愿望,除了理论和女性主义的欲望外,还是一种东方主义欲望,即从东方的历史中找到西方的反面,找到西方缺场的东西。[4](P141)
骆里山认为,克里斯蒂娃书写《中国妇女》的最终目的是解决西方社会的理论问题,是关于自我而非他者的东方主义话语。通过想象一个与当代西方女性截然不同的中国妇女形象,克里斯蒂娃批评法国和北美妇女运动缺乏心理学的深度,同时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质疑弗洛伊德和拉康所提出的性别差异范式。[4](P147)她塑造了一个强势的中国“女王”形象,用来颠覆西方男权话语和心理分析理论中关于妇女是第二性的论断,而新中国被想象成异于同时代法国的理想国。因此,“中国和中国妇女仅仅是西方争论中的一个论据,是解决西方的政治和理论问题的一个想象物”。[4](P147)克里斯蒂娃对中国母系社会的想象源于葛兰言的两部作品:《中国文明》(1929年)和《古代中国的婚姻制度和亲属关系》(1939年)。这两部作品对中国母系社会的推论源自民间传说和舞蹈,通过想象构建了一个中国古代以女性为中心的部落文化,女性享有充分的权力。可见《中国妇女》与其他东方主义话语一样,它所呈现的东方是西方作家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所想象的他者,并非对真实社会的观察和书写,是西方中心的。
《中国妇女》把传说中的中国母系社会与20世纪的新中国混为一谈,忽略了历史的变化,这也重复了东方主义话语的特征,即把东方建构为无历史的、亘古不变的他者。骆里山认为,克里斯蒂娃把母系社会当成新中国的前身,跨越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全然不顾历史的变化,各种力量的矛盾冲突、此消彼长,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中国有母系社会传统,因此当代中国能给法国的女性主义僵局提供解决方案。[4](P151)
克里斯蒂娃试图在短短几十页中重构中国妇女的历史,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母系社会、儒教社会和新中国,其中,妇女在儒教社会受尽压迫,就如西方妇女受基督教的性别约束一样。她认为,正因为中国有母系社会的传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反父权的革命,给父权制家庭和中国妇女的地位带来根本性的转变。骆里山总结道:“克里斯蒂娃的基本论题是在中国妇女的历史中,‘她’的体验与父权社会中的西方妇女完全不同”,文本的隐含意义是女性写作应该尊敬、赞美、书写中国妇女,因为认同一个西方意识形态之外的位置形成了反对这个体制的革命性的政治策略。[4](P151)但是,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妇女的想象忽略了她们的现实情况,没有意识到她们真正的自由与约束、顺从与反抗。究其本质,《中国妇女》是把中国妇女建构成西方心理分析和女性主义理论的他者,重复了东方主义话语。
四、周蕾:《中国妇女》对中国的女性化再现
周蕾出生于香港,接受西方教育。她是当代离散批评理论最重要的贡献者之一,也是最著名的华裔美国学者,主要研究中国性、华裔美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电影批评等。斯皮瓦克在《全球语境下的法国女权主义》中提到,如果是一个中国人来言说中国,又会是什么样的?他们享有什么特权又存在什么样的局限?周蕾在《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1991)中回应了这个问题。周蕾是一个既熟悉中国现实又熟悉西方批评理论的华裔美国人,她从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的族裔视角对克里斯蒂娃的《中国妇女》进行解读,批评它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女性化建构。
周蕾认为,《中国妇女》把中国建构为阴性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是阳性的:“中国被置于西方的对立面,不仅因为它不同,还因为它是女性化的。”[8](P5)尽管克里斯蒂娃的出发点是关注西方社会被男权压抑的女性,但当她注视中国时,她的目光顿时变成了白人男性的,而关注的对象中国替换了她原来所处的位置,成为女性的他者。周蕾提出,克里斯蒂娃-西方-中国的关系就如同男人-上帝-女人的关系,中国,同女性一样,被排除在外,成为绝对他者。[8](P8)克里斯蒂娃把中国他者化、女性化,实际上重复了她试图颠覆的西方形而上学的男性中心主义。周蕾从三个方面反驳克里斯蒂娃的论点,认为这种他者化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关于汉语的声调问题。克里斯蒂娃提出汉语声调保留了前恋母情结的、前句法的和前象征的记录,因此是母系的。然而她忽略了使用这种语言的现代中国人,他们是不能简单地被形容为前句法的、前象征的。事实上,克里斯蒂娃过度赞赏她在中国文化中看到的这种前心理分析特征和它的原始性,这样便于把它置于西方现代性之外。
其次,关于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妇女缠足的解读。她把中国女性缠足比作西方男性的割礼,认为都是一种象征性的阉割。在西方,割礼是禁忌的标志,让男性的身体成为象征,而西方女性被认为是肤浅的、不算数的。相似地,在中国缠足成为女性进入象征秩序的标志。周蕾认为,按照克里斯蒂娃的逻辑解读,缠足本是男性权力对女性身体的残害,却变成中国社会认同女性参与社会权力的象征了。[8](P6)基于这样的误读,克里斯蒂娃得出中国仍然保留其古代的母系传统,因此是父系西方社会的绝对他者,是不攻自破的。
第三,关于中国的道教文化。克里斯蒂娃认为道教文化给中国妇女提供了颠覆和解放的精神源泉。然而周蕾认为,克里斯蒂娃对道教的推崇,实则反映了西方人向神秘的东方寻求精神的指引,[8](P9)也是他者化的一种表现。最后,周蕾得出结论:克里斯蒂娃只是重复了西方18世纪以来的传统,即把中国看作是永恒静止的。
周蕾从中国文化内部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的视角反观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妇女的书写,扮演了她所提出的“族裔观者”(ethnic spectator)的批评角色。如果斯皮瓦克对克里斯蒂娃的质疑主要是从言说的白人女性和被言说的第三世界女性的主体性进行的,那么周蕾则为这场对话增加了一个新的参与者,即谁是观众/听众。受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观点的影响,周蕾提出“族裔观者”的概念。穆尔维提出,在视觉方面,电影赋予男性和女性的角色是完全不同的。镜头的目光是男性的,而荧幕上的意象,因被注视,是女性的。[8](P16)更重要的是,荧幕上的形象绝非是某种纯粹的观看对象,它本身就包含了某种隐形的注视。[8](P18)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认同了镜头的视角,就如同接受了阿尔都塞意义上的“询唤”一样,采用男性化的眼光。因此,周蕾认为,《末代皇帝》的溥仪是女性化的角色,而这部电影的观众的视角则会跟从那种隐形的白人男性目光。这也从另一个方面道出了克里斯蒂娃书写中国女性的不足,她认同了西方白人男性的视角来观看中国,从而把中国女性化。
一边是被女性化的中国形象,另一边是叙事者的西方男性注视,当一个中国观众观看/阅读这一叙事时,会有什么样的阅读策略?周蕾引用她母亲的评价来引出“族裔观者”这一概念,她母亲说:“一个洋鬼子拍中国电影达到这样水平是很卓越的。我得说,他干得不错。”[8](P24)周蕾认为她母亲的反应是很有意义的。《末代皇帝》的叙述者是“洋鬼子”贝托鲁奇,叙述内容是中国人溥仪以及那一段中国历史,而观众是中国人周蕾的母亲。周妈妈的反应暗示着:“那仍然是我,是我们,是我们的历史,尽管影片出自‘洋鬼子’之手。”[8](P24)这是一个中国族裔观者对中国文化、中国性的认同。另一方面,意识到导演是“洋鬼子”也彰显了中国观众对此持有的保留态度,下意识地质疑这个外国版的中国历史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认同和质疑的背后是一种渴望,渴望“在场、在电影里”,[8](P25)渴望认同中国这个“想象的社区”,渴望中国及中国性变得可见。周蕾从她母亲的例子进行总结:“中国人为之着迷的客体——‘中国’或‘中国性’——不能被当作是情感简单化,而是征兆了一种迟到的意识或再现,这种心理活动并非克里斯蒂娃所说的‘前心理分析的’。我们可以说这样的反应——‘是的,那就是我,那就是中国’是对中国的物神崇拜似的想象,但这种反应背后是一种愿望,反抗本质是帝国主义暴力的西方化对中国文化的解体。”[8](P27)周蕾承认中国读者在阅读西方关于中国的叙事时,很有可能会接受其西方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的“询唤”,但关键的问题并不是中国或中国性是否得到了准确的再现,而是在这个再现和认同的过程中,中国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和集体认同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
事实上,周蕾作为一个美国当代学术圈的中国女性研究者,尤其是在美国的汉学研究领域中,自身也是一个“族裔观者”,既是研究对象,同样也是研究主体。让北美的汉学研究者苦恼的是,中国的“特性”或“中国性”在逐渐消失,因此,他们跟克里斯蒂娃一样,对所谓“古典”的中国着迷,轻视现代中国,认为那只是西方化的结果。费边指出:“传统和现代并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冲突的……事实上,相互对立的不是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同一社会,而是在同一时期遭遇的不同社会。”[8](PP31-32)周蕾借用费边的理论提出,“族裔观者”的位置正是不同社会、不同文化在同一时期接触互动的位置,是一个同时性的位置(position ofcoevalness)。所以“族裔观者”这一群体的存在本身就攻破了西方与东方的对立是现代与传统的对立这一论题。
斯皮瓦克、骆里山和周蕾分别从国际女性主义、东方主义批评和离散理论的视角解读克里斯蒂娃及其《中国妇女》,指出其对中国和中国妇女的再现重复了东方主义话语,把中国想象成西方男性文化对立的阴性文化,处于较西方国家更为原始的历史阶段,而中国妇女则是与西方妇女完全不同的他者。《中国妇女》与贬抑化的中国叙事不同,对中国和中国妇女进行乌托邦式的建构,延续了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对中国的奇异想象,但与贬抑叙事一样,是把中国置于西方的对立面,其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通过这个差异的他者想象一个西方中心的自我。斯皮瓦克曾说:“在父权与帝国主义之间,在主体的组成和客体的形成之间,女性消失了,不是变成了原始的虚无,而是反复穿梭于传统与现代的暴力中,这就是第三世界女性。”[9](P165)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再次让中国女性消失,失声于女性主义话语暴力中。归根结底,对东方女性的关注反映了西方女性对自我主体的建构。印度裔女性主义批评家格雷沃(Inderpal Grewal)提出,“国际框架下的当代文化对性别、阶级和种族的生产是与早期的殖民历史相关联的”。[10](P27)当代美国女性主义对第三世界女性的范畴性建构,实际上也难逃殖民主义模式的认知暴力。正如斯皮瓦克论及对第三世界的世界化一样,西方话语通过对其他文化进行话语建构,以形成西方主体:“把第三世界当成偏远的文化,有丰富、完整的文学史,等待发现、阐释、翻译引用、变成为课本,这让‘第三世界’变成了一种能指,让我们忘记‘世界化’,而事实上它扩展了英语文学这一文化帝国。”[11](P269)同理,西方批评理论把中国女性当成一个新的能指,仍然是一种对第三世界的世界化。
[1]Chandra Mohanty.Under Western Eyes: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A].in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C].ed.Chandra Mohanty,Ann Russo,and Lourdes Torre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
[2]Mary Gaunt.A Woman in China[M].London:T.Werner Laurie,1914.
[3]R.L.McNabb.The Women of the Middle Kingdom[M].New York:Young People's Missionary Movement,1907.
[4][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著,赵靓译.中国妇女[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
[5]Lisa Lowe.Critical Terrains:French and British Orientalisms[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6]Gayatri Spivak.Can the Subaltern Speak?[A].in Patrick Williams&Laura Chrisman ed..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A Reader[C].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
[7]Gayatri Spivak.French Feminism in an International Frame[A].Feminist Readings:French Texts/American Contexts[C].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
[8]Rey Chow.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M].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1.
[9]Gayatri Spivak.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0]Inderpal Grewal.Transnational America:Feminism,Diaspora and Neoliberalism[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5.
[11]Gayatri Spivak.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C].Ashcroft etc.ed..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5.
责任编辑:含章
Chinese Women in Western Feminism:Julia Kristeva
LONG Dan
(Department for Training Candidates Going Abroad at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1,China)
Chinese women;western feminism;orientalism
This paper compares Julia Kristeva's Chinese Women with the criticism of it by contemporary Ameican feminists Gayatri Spivak,Lisa Lowe and Rey Cho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feminism,orientalism and diaspora respectively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women in western feminism.It recognizes the following distinct features of such a construction:othering,feminizing,orientalizing of the Chinese women;in other words,this construction serves as a mirror to reflect western feminin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estern feminine identity.
B089
A
1004-2563(2015)01-0084-08
龙丹(1981-),女,四川外国语大学出国培训部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女性主义小说、西方批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