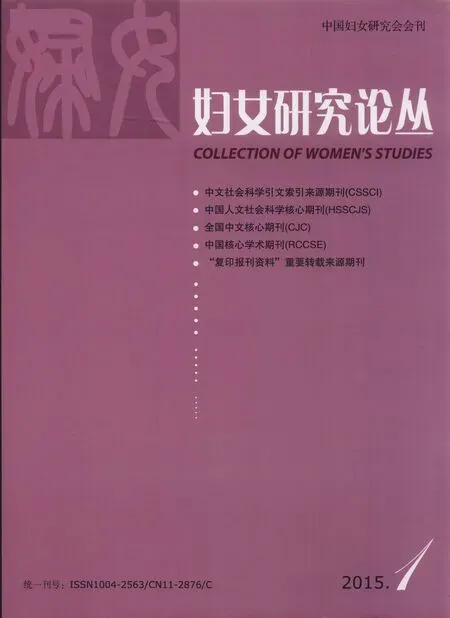性别传播研究的本体之辨
2015-04-17张敬婕
张敬婕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北京 100024)
性别传播研究的本体之辨
张敬婕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北京100024)
性别传播研究;本体;女权主义认识论
无论中外学术界,都存在着将“性别传播研究”、“女权主义媒介研究”、“性别与传播研究”混为一体的现象。而事实上,这三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文章通过论证“性别传播研究”的本体及研究范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可以明确这三个研究领域在认识论层面的根本差别。
性别传播研究(gender communication studies)是以女权主义认识论为主体研究框架的跨学科研究范畴。自20世纪70年代发展至今,其已经成为一种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对传播学研究进行“理论增殖”的研究范式的代表。值得关注的是,当今学界对性别传播研究的本体及研究范式还存在着含混与歧义。例如,国内有学者撰写的一篇性别传播研究文章,在中文摘要里使用了“性别传播研究”这个术语,在正文中使用的却是“性别与传播研究”(gender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在英文摘要中使用的则是“女权主义媒介研究”(feminist media studies)。[1](P60)在一篇文章中出现了三个学术概念相互指代的状况,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这一现象是否意味着三个学术概念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本研究试图回应这些问题。
在国外传播学或社会学的研究文献中,亦鲜见gender communication studies与feminist media studies以及gender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这三个学术概念之间异同比较的文章。对那些没有社会性别学术背景的研究者来说,这三个学术概念也许只是称谓上的差别,它们具体指代的研究内容与研究范式应该是相同的或相似的。即使那些具有社会性别研究背景的学者,对“社会性别”这个学术概念并不陌生,但对这个概念在交叉学科中发挥的认识论作用并不敏感,因此也会存在将三个学术概念混用的情况。毕竟,大部分传播学研究的学者们无意于运用女权主义学术立场以及认识论结构,来对传统的传播学认知体系展开一场颠覆性的革命。很大程度上,许多人对“女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否具有“科学性”甚至还抱有怀疑的态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性别传播研究的本体进行辨析,实质上是厘清三个学术概念所代表的不同的研究范式及其所基于的认识论。唯有明确性别传播研究的基本内涵和研究范式,才能够凸显“社会性别”概念对性别传播研究这一交叉研究所作出的理论推进。历史地看,性别传播研究的本体在知识论的不断发展与更新中,逐渐衍生出两种不同的研究立场与研究范式。
一、从“性别传播研究”到“性别与传播研究”:“性别化”的传播研究
社会性别理论视角在介入其他学科和整个知识系统时,为了描述和说明某个事物的社会性别状况,衍生出了“性别化”(gendered)这个操作框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性别化”被作为一个动词来使用,用来说明某事物如何呈现、如何实践社会性别。
当社会性别视角以及女权主义理论刚开始被引入传播学研究时,前者还没有真正地融会贯通到传播学的研究体系之中,因此只是形成了一股对传播学进行“性别化”研究的潮流。这类研究在研究范畴的命名上,通常采用的是“性别传播研究”这一术语,实际上指的是“性别化的传播研究”。它并没有运用女权主义理论来阐释传播学研究中的性别议题,而是通过分析男女两性在传播语言、传播关系、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等方面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全面地梳理传统的传播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性别差异与性别歧视,强化了在传播学研究中加入社会性别视角的重要性。
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这样一种以“性别传播研究”命名的研究,实际上遵循的是以传统的传播学研究体系为主、以社会性别为辅助性研究视角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的特点是,对传播学不同研究对象的男女差异状况进行描述,对不同性别的受众如何在传播过程中产生各种差异进行研究。这类研究在针对传播语言、传播组织与媒体、媒介内容等议题而展开的“性别化”研究中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例如,美国传播学者小约翰(Little John,S.W.)在其编著的《人类传播理论》(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一书中,思考了传播学研究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关系、二者如何相互融合、融合之后将产生怎样的思想成果等一系列问题。尽管小约翰没有提出更多系统性的新观点,不过,他赞同社会性别研究的本质是“探寻社会中性别意义的研究”,其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这个性别化分割的世界的力量与局限性”。[2](PP424-425)在该书中收录了“无声群体理论”和“男权的全域”,展现了性别化的传播研究在语言学方面的新发现。“无声群体理论”和“男权的全域”都旨在揭示传播关系中男女两性在语言表达方式和话语权力上存在着等级差异的事实,并且提出这种人为的、压迫性的差异是由父权制所决定的观点。
美国学者朱丽亚·T.伍德(Julia T.Wood)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人类学以及传播研究的教授,致力于人际关系、媒介模仿与暴力、女权主义理论以及性别、传播与文化的交叉研究。在其《性别化的人生》(Gendered Lives)中,伍德用两个章节专门论述了“性别化的组织传播”和“性别化的媒体”。在“性别化的组织传播”[3](P166)中,伍德提出媒体的职业生活中贯彻的是男权标准,因此会导致人们在认知上存在普遍的偏差,包括想当然地认为主管都是男性;男性与女性的传播风格有着根本的差异,并且不会发生改变;①一般而言,女性主张通过交流去创建和维持人际关系并对他人作出反应,而男性则强调通过交流去表达独立和地位。但实际上,男女的传播习惯和传播方式都是后天习得的,也是可以改变的。男性与女性合作上存在障碍等。[3](PP171-173)在“性别化的媒体”中,伍德首先指出媒介形象的塑造有两个要点:第一,当今的媒体为我们同时提供了传统和非传统的性别描写。第二,在“新”的女性和男性形象下面隐藏着许多“旧”的性别观念。[3](P185)然后归纳了媒体会通过以下三种方式隐蔽地影响受众对自己作为男性或女性的理解:第一,媒体无限延长对非现实的“理想男女”的表现。第二,媒体使人尤其是女性的身体病理化,迫使人们把正常的身体素质和功能视为不正常,并不断地寻求医治办法。第三,媒体产品中存在着大量将对女性施暴视为正常的内容,使得男性渐渐相信他们被赋予了虐待女性或强迫女性从事性活动的权力,并使女性认为这些侵害可以被接受。[3](P202)总之,伍德的研究强化了在传播组织结构研究和媒介研究中加入社会性别的评价指标和研究视角的价值。
20世纪80年代,这一类研究的热点转向媒体与女性生活的建构关系研究,如《女性版面编辑:性别是否造成差异?》、[4](PP508-514)《女性与大众传媒》、[5]《家庭主妇与大众传媒》[6]等。20世纪90年代起,伴随着女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学术界引起的热烈讨论与广大反响,对传播现象进行“性别化”研究的这一类研究范式,被明确为“性别与传播研究”——将社会性别的视角引入传播学“5W”之中,对传播者、受众、媒介、传播内容、传播效果展开“性别化”的研究,描绘并阐释这些研究范畴内存在的性别差异及其原因。
总体来看,采用这一研究范式的“性别与传播研究”,其研究宗旨始终都是发现差异并分析原因,最多涉及对传播学中所缺失的性别视角和性别敏感的批判,但归根结底,这种研究范式立足于对传播学研究进行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改良”式批判,并不是用女权主义理论或社会性别的研究框架来“改革”传播学研究。此外,这种研究范式有着无法回避的缺陷,并未深究以下这些问题:男性和女性在传播中的差异是“根本性的”还是“建构性的”?这些差异只是因为男女在社交中使用不同的沟通策略吗?哪一种风格或策略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更有效?发现并阐释传播中存在着性别差异能引发什么有意义的改变?若要改变女性在传播中遭遇的不平等状况,应该向男性的标准去“看齐”吗?再者,在传播研究中,造成差异的不仅仅在于性别,还与其他很多复杂的因素(比如阶层、受教育程度、人际网络、社会资源占有情况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单一分析男性与女性在传播中的差异,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存在明显的盲点,显然,这一类“性别与传播研究”无法解决传播中性别不平等的实质问题。
二、从“女权主义媒介研究”到“性别传播研究”:新的研究框架与立场
当“性别传播研究”中对传播学进行“性别化”分析的研究范式逐渐固定为“性别与传播研究”之时,另外一种“性别传播研究”的本体及研究范式也同步发展起来,这就是从社会性别研究框架与批判立场出发,重新审视传播学研究传统中存在的性别盲点和性别偏见的“女权主义媒介研究”。
(一)女权主义学术与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结合
受女权主义运动以及女权主义学术的影响,如何在媒介呈现中更好地贯彻性别平等理念,成为20世纪中后期女权主义学术介入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议题。这类研究不满于只分析媒介呈现了什么样的社会性别现实以及为何存在着这样的媒介产品,而是意欲探索媒介怎样呈现甚至是如何制造、复现了不平等的社会性别现实的深层原因;不再满足于在现有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提供“改善性”的建议,而是试图超越现有媒介生态,并对整个传播机制提出“改革性”的批判与建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传播学批判学派与女权主义学术相互对话与结合,推动了“女权主义媒介研究”的产生与发展。
从传播学研究史来看,由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uchramm)所确立和发展起来的主流传播学研究,是一种不触动现行传播体制的实用主义的研究,这种被称为“传统学派”或“行政学派”的研究,是注重研究传播的内容、传播效果的“体制内”的研究。而由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派等推动的传播学流派,被称为“批判学派”,这一学派往往将传播置于社会政治经济的背景之下,注重研究传播与社会、传播与多元文化的互动及制约的规律,对传播体制提出更为宏观的批判。与传统学派相比,批判学派遵循的是一种“体制外”的研究范式。1941年,为了回应马克斯·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的《传统的和批判的理论》(此文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主旨、方向以及学术名称的基础),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写下了《评行政的和批判的传播研究》一文,提议在“美国传播研究”的名下,不仅应该包括他自己的“行政的传播研究”,而且应该有批判的理论。[7](P297)实际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批判学派就与经验主义纠缠在一起,施拉姆在60年代评价说,美国批判学派“人数虽少”,“却很有权威”。[8](P195)
除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流派比较倾向于进行“体制内改良研究”之外,其他流派的女权主义学术基本上认同“体制外改革性研究”,因此与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立场与研究路径不谋而合。批判性的女权主义学术与传播学的批判学派相互结合,形成了批判性的性别传播研究范式,这类研究范式最初主要是在媒介研究领域展开性别批判研究,因此也称为“女权主义媒介研究”。这类研究注重在社会性别的视角之下,阐释媒介与整体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效果的运作机制与规律。研究的对象不限于男女两性,而是延伸到对不同权力阶层之间社会关系的结构与属性的深入批判。
(二)女权主义媒介研究注重定性研究方法的使用
与传播学传统学派相对,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定量研究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女权主义研究者们注意到,定量研究方法自身存在很大的性别盲点。例如应用最为广泛的内容分析法,往往忽视对媒介文本的深层意义进行阐释,而满足于在统计中得出一个平面式的结论,从而可能会使这个结论在媒介商业的操作中被加以利用和篡改。例如“权利”、“选择”、“自由”等这些女权主义所倡导的概念往往会被运用在一些广告中,这些概念原本的涵义会隐蔽地被置换为鼓励女性保持消费的习惯,如此一来,原本具有政治意义的概念在广告中就被篡改和利用了。如果只运用内容分析法,则无法阐述这一置换是如何发生的。[9]因此,女权主义媒介研究注重发现定性研究的价值与适用性。尽管与定量研究一样,定性研究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都是用来收集和加工整理事实的方法。但是,定性研究的目的是了解人们在何种情境下建构了何种事实,也就是说,与单纯的量化事实相比,定性研究更注重对事实背后深层涵义的描述与阐释。
此外,与定量研究相比,定性的研究观点更强调“当事人的视角”。所谓当事人的视角,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定性研究提出的问题不仅对研究者也必须对被研究者有实际的意义,或为他/她们关心的问题,即强调研究者要理解“当事人”的“文化本位”意义。第二,研究者要进入并长期在研究现场中体验生活,试图从被研究者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第三,研究所建构的概念框架并非如定量研究一样,是事先所确定的,而是作为一种研究指导,真正的概念框架要在与研究对象访谈、参与性观察或实物分析中产生。研究者本身也被纳入研究过程,与被研究者形成一种互动关系。但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通常是研究现场的局外人,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距离,以求达到“客观”或价值中立。[10](P50)定性研究“重视当事人视角”的这种特性,与女权主义“打破性别隔离”、“建立女性成为主体的机制”、“重构中心与边缘的价值观”的立场不谋而合。
除了调查法和内容分析法这样的定量研究方法之外,符号分析、文本分析、话语分析等定性研究方法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媒介呈现、媒介意识形态编码与受众解码关系的研究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权主义媒介研究”代表了“性别传播研究”新的研究范式:“女权主义媒介批评鲜明地表现出它对大众传媒中展现出的性别成规惯例的批判态度。”[9](P257)它强调以女权主义认识论和研究框架为主,重新阐释传播学的不同研究层面,从而形成了女权主义的媒介研究、女权主义的传播者研究、女权主义的受众研究、女权主义的媒介内容研究、女权主义的传播效果研究等不同的研究范畴。
(三)女权主义媒介研究注重女性主体经验立场与结构性批判
女权主义媒介研究呈现出媒介的功能不仅仅在于反映现实。如果用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的框架来分析,媒介实际上也参与了对现实的建构。媒介的“议程设置”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性别因素以及对性别的呈现,因而,媒介呈现的性别形象、性别角色、性别关系,与其说是“真实的事实”,不如说是媒介主动参与“制造的性别”。塞雷萨·德·劳雷提斯(Theresade Lauretis)指出,电影、电视和杂志这样的媒介,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性别制造的工具”(当然媒介也同时是制造民族、阶级和其他不同身份要素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媒介对性别的呈现,就是对性别的建构。[11]因此,女权主义媒介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目标,不仅在于研究媒介呈现了什么样的社会性别现实,更在于探讨如何改变媒介呈现中的性别不平等的策略。因而,对媒介呈现的女权主义研究,更倾向于对“媒介制造”背后的主导意识形态展开批判,对媒介维护、复制、强化压迫性的意识形态的媒介制播机制展开批判。
与那些止步于“发现与描述式”的“媒介中的性别歧视研究”(sexism in the media)不同,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等人编著的《壁炉与家庭:大众媒体中的女性形象》(Hearth and Home:Images of Women in the Mass Media)[12]对于性别传播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占统治及主流地位的性别传播研究范式一直是有限度地将社会性别视角引入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性别化的传播研究”,也就是后来为传播学研究与实践所广泛接受的“性别与传播研究”。从这本编著开始,出现了从女权主义研究立场出发,深入阐释与批判媒介呈现性别形象的研究。性别传播研究的重点不再仅仅着眼于媒介呈现中存在的性别问题,而更在于挑战并揭露隐蔽在媒介呈现背后的、建构性的意识形态与媒介机制。
1989年,出现了运用女权主义立场理论全面检讨社会性别研究如何挑战传统传播学的研究价值观的研究,即帕梅拉·格里顿(Pamela J.Creedon)编著的《传播中的女性——挑战性别价值观》(Women in Mass Communication:Challenging Gender Values)。该书的理论意义在于,一方面明确了除“性别化的传播研究”模式之外,需要发展新的研究模式以扩展性别与传播的交叉研究的深度,另一方面论证了以女权主义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为基础的“社会性别”是分析传统传播学中的性别议题的一个有效的分析范畴。该书在1993年第二版中,增加了从女权主义研究框架出发重新认识大众传播教育中的性别偏差与歧视的内容。该书提出,应该彻底质疑现有的、男权意识形态下所谓的“价值中立”、“公/私二分”、“主/客观二分”、“男/女二分”的新闻实践与价值评判标准,改用女权主义观点重新建构新闻实践与价值评判的指标,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改变女性在传播中所面对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性别歧视与压迫。[13]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传播学的受众研究中逐渐出现了一种变化,即从以传播者的意图为中心转向以受众如何利用媒介信息、如何从中获得满足为中心,并根据后者来确定大众媒介的效果。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和立场被归纳为“使用和满足”理论,它在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受众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后来崛起的批判学派的关注对象,它本身不仅富有理论意义,而且蕴含着形成有关现代社会的某种理论的方向。[14](P58)
在传播学的受众研究中,对女性受众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受到额外的关注。对传播学五大核心期刊——《传播学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广播电视与电子媒介学刊》(Journal of Broadcast and Electronic media)、《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欧洲传播学学刊》(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的定量统计发现,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女性受众为考察对象的研究仅占4.5%。[15](P151)
1944年,赫佐格对广播听众进行调查,探讨电台白天的连续节目为什么会吸引那么多的女性听众。赫佐格对100名女性听众做了长期采访,对2500名女性听众做了短期采访。研究结果发现,女性之所以喜欢这些连续剧,或是因为将其当作发泄情感的办法,或是因为将其当作满足个人“痴心妄想”的机会,或是因为想从中获得处世的指导。[14](P59)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对于女性收视习惯与偏好的研究大多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大部分女性没有走入公共领域,所以在家庭这个私领域中,她们的生活重点是家务劳动和维护家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女性收看电视的时间是断断续续的、喜欢收看的媒介内容是“没什么价值的浪漫小说或肥皂剧”。[16]
从“建立女性成为主体的机制”这一社会性别议题出发,女权主义媒介研究提出了“媒介快感”(media pleasure)/“受众快感”(audience pleasure)的概念,用以说明女性收看电视节目并不完全是“为了打发时间”或者“麻醉神经以逃避现实”,相反,女性的收视活动为她们提供了很多欢乐和满足的“快感”。[16](PP100-104)“媒介快感”/“受众快感”完全是从女性受众的主体角度提出的,因为以往那些认为女性收看电视节目是无关紧要的活动的观点,以及认为女性收看的浪漫小说或者肥皂剧都是不切实际的媒介内容的态度,反映的是男权至上的、贬低女性对事物的价值进行判断的能力以及无视女性主体性的观念与文化。因此,如果不改变评价男女收视差异的指标,如果不能够从女权主义立场来分析男女受众收视的差异,即使掌握了媒介收视的性别化的具体差异,在赋予不同的收视习惯以价值的时候,也可能得出偏差性的、歧视性的结论。
塔妮亚·莫德尔斯基(Tania Modleski)在《复仇之爱》(Loving with a Vengeance:Mass-Produced Fantasies for Women)中,对浪漫小说和肥皂剧进行了大量女权主义式的研究,其中很多经验不是来自普遍受众的体验,而是基于她个人的经验。这本著作在女权主义媒介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开启了女权主义媒介研究新的方法论——这种研究与一般的“性别化的媒介研究”不同,它更注重挖掘个体差异以及个体的主观经验,不会先入为主地将这种个体性的、主观性的经验理解视为“无价值”的或者“低价值”的内容。[17]
此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于英国的文化研究也开始影响到美国学术界对包括浪漫小说和肥皂剧在内的“大众文化”的理解。文化研究学派的观点与女权主义立场结合起来,为分析、评判女性受众的主体体验及相应的媒介产品的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
总之,一些女权主义研究者为了强调与“性别与传播研究”的方法论与研究范式之不同,提出用“性别传播研究”来反对将“社会性别”作为“传播学”修饰词的研究立场,来命名那些将“社会性别”作为跨学科研究中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核心的研究成果。因此,在2000年以后,一批延续了“女权主义媒介研究”立场与研究模式的成果,以“性别传播研究”或“女权主义传播研究”为名陆续出版,如《性别传播理论与分析:从沉默到表现》、[18]《女权主义传播理论》[19]等。
三、结论
“性别传播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具有“双重本体”。最初,那些对传播学进行的性别差异研究被称为“性别传播研究”。从研究范式上看,这一类研究一般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本质上进行的是“性别化的传播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类“性别传播研究”实质上已经明确为“性别与传播研究”,即在不改变既有的传播学研究立场与框架的前提下,将社会性别的批判视角有限度地引入传播学不同层面的研究范畴之中。
自20世纪中后期开始,逐渐发展出了“女权主义媒介研究”的研究立场与研究范式,它强调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和社会性别理论框架来重新审视媒介研究,即摆脱原有的传播学研究的规范模式,运用女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传播学展开一种革命性的价值重建。逐渐地,这种研究范式从针对媒介研究扩展为针对更为广义的传播学研究,并被命名为“女权主义传播研究”或者“性别传播研究”。
因此,“性别传播研究”与“性别与传播研究”、“女权主义媒介研究”之间,虽然都属于性别与传播的交叉研究范畴,但是“性别传播研究”与“女权主义媒介研究”都是以女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基础的批判性研究,它们与“性别与传播研究”所坚持的以传统的传播学研究规范为主、以社会性别为一种辅助性的研究视角的研究立场截然不同。
[1]陈阳.性别与传播[J].国际新闻界,2001,(1).
[2][美]小约翰,陈德民等译.人类传播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美]朱丽亚·T.伍德,徐俊、尚文鹏译.性别化的人生(第六版)[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
[4]Merrit,S.and Gross,H..Women’s Page/Life Style Editors:Does SexMake a Difference?[J].Journalism Quarterly,1978,55(3).[5]Butler,M.and Paisley,W..Women and Mass Media:Resourcebook for Research and Action[M].NewYork:HastingHourse,1980;Gallagher,M..Unequal Opportunities:The Case of Women and the Media[M].Paris:Unesco,1980.
[6]Hobson,D..Housewives and the Mass Media[A].in S.Hall,D.Hobson,A.Lowe and P.Willis(eds).Culture,Media,Language[C]. London:Hutchinson,1980.
[7][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8][美]威尔伯·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9]潘知常,林玮主编.传媒批判理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10]卜卫.方法论的选择:定性还是定量[J].国际新闻界,1997,(5).
[11]Theresa de Lauretis.Technologies of Gender:Essays on Theory,Film,and Fiction[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Press,1987.
[12]Gaye Tuchman,Arlene Kaplan Daniels,James Walker Benet.Hearth and Home:Image of Women in the Mass Media[M].Oxford UniversityPress,1978.
[13]Pamela J.Creedon.Women in Mass Communication:Challenging Gender Values[M].Sage,1993.
[14]殷晓蓉.美国传播学受众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关于“使用与满足说”的深层探讨[J].中州学刊,1999,(5).
[15]廖圣清.20世纪90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16]刘利群,张敬婕.中美女性电视节目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
[17]Tania Modleski.Loving with a Vengeance:Mass-Produced Fantasies for Women[M].NewYork:Routledge,1990.
[18]Charlotte Krolokke,Anne Scott Sorensen.Gender Communication Theories and Analyses:From Silence to Performance[M].Sage Publications,Inc.,2005.
[19]Lana F.Rakow,Laura A.Wackwitz.Feminist Communication Theory:Selections in Contest[M].Sage,2004.
责任编辑:含章
The Debate on the Ontology of Gender Communication Studies
ZHANG Jing-jie
(Centre for Media and Women's Studies,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t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24,China)
gender communication studies;ontology;feminist epistemology
Whether it is at home or abroad,there is a tendency among academia to regard"Gender Communication Studies","Feminist Media Studies",and"Gender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as one.In fact,there are differences as well as linkages among them.This paper identifies fundamental epistemological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specialized fields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ontology and the paradigm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Gender Communication Studies".
G206
A
1004-2563(2015)01-0078-07
张敬婕(1979-),女,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性别与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