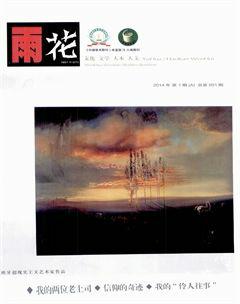我的两位老上司
2015-04-17汤卫文
汤卫文
王部长给周主任搛了一筷他最爱吃的猪尾巴:“我像下象棋的?我看你周爱好像掏蜂窝煤的铁扦子,十二个煤孔你东掏掏西掏掏,哪天全掏通凑足了一打首长就要找你老小子算总帐,到时我可救不了你!”王部长真是太幽默了,我终究是没有忍住笑,一口酒呛进气管,喷得满桌子都是。
一
王促苁是当时我们市委组织部长,一个博学多才儒儒雅雅的老前辈。弄出这么一个下流绰号全赖他的老战友,计委物资办公室的周爱好(读hao)主任。绰号是他俩相互创作的,当着面也只有他俩敢相互发表。
我只是一个刚刚从部队转业在周主任手下写写划划的小巴拉子,平时在我们周主任跟前连个响屁也不敢放。记得刚来报到的那天,我双手捧着介绍信毕恭毕敬地给他老人家递上,他重重往桌上一拍,瞪我一眼便自言自语:好个王促苁的,小瞧我这临时机构杂凑班子,什么鸟都敢往我这儿放,还小战友,这么个当兵三年没放过两枪的小兵蛋子也算战友!刚刚在组织部王部长给周主任打电话介绍我时对我的称呼是“小战友”,当时我心里还美滋滋的,这下凉到了脚后跟。
最近我犯了个大罪(周主任定的调),要在三十多年前就拉出去毙了,这也是周主任的原话。
周主任战争年代留下了老寒胃,下午有吃革炉芝麻烧饼的习惯。这种烧饼本市仅蒋家桥的九如分座有得卖,于是每日购买草炉烧饼的光荣任务就归到了我的工作范畴。路程虽稍远了点,但跑这个二腿子我很乐意。因为一来上班时间可出门散散心,二来呢,也是最主要的这种烧饼二两粮票五分钱两只,倘若买一只的话就得付三分钱,浪费半分钱周主任尽管工资蛮高每月有九十多元也是断断舍不得的。周主任的胃下午只能承受一只烧饼的量,另一只他老人家一边看报一边挥挥手就赏我了。那时我的粮食月定量是二十八市斤,年轻消耗大又是刚从部队那种由着肚皮海撑的地方来,这每日的一只烧饼不啻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周主任就是大慈大悲的天,骂两声也是幸福的。正好昨日周主任让我写一个办公室的工作打算,草稿先前已给他审阅过,下午四点就要在计委各部门大会上向领导汇报。我给周主任桌上的搪瓷大茶缸续上水,奉上草炉芝麻烧饼和报告的誊清件,周主任优哉游哉边吃边最后再看一遍。
周主任平时生活节俭,但同事之间尤其是对下属在钱财上向来慷慨,他自己并不抽烟却经常买一盒大前门的好烟放在桌子上由着贪小便宜的部下们摸。可吃烧饼小气呢,烧饼吃完了连洒在报纸上的芝麻屑子也不紧不慢地戴上那副铜质圆框夹鼻式老花镜,中指往舌头尖沾上口水,仔仔细细,有时一次沾一粒有时一次沾几粒,口中啧啧吐声,津津有味享用,有点小鸡鹪菜叶的意思。
报告上有“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八个字。不知是那天周主任的口水太浓稠抑或是报告的稿纸碰上了什么黏性的东西,反正有一粒别有用心的芝麻粒就潜伏在报告纸上跟着周主任大摇大摆上了礼堂的主席台,还什么部位不好沾,偏偏巧巧就沾在了“狠抓革命”狠字的“艮”头顶上。周主任作报告发音吐字的特色向来是一字一停顿字字皆为逻辑重音且如古刹撞钟振聋发聩。一时间,“狼抓革命”四字从周主任的口中蹦出,后面的“猛促生产”刹那被台下的爆笑声湮没。计委领导原是我们周主任的老部下,也坐在主席台上,连忙敲桌子打圆场解嘲。他歪过脑袋往周主任的报告上瞄了一眼,顺手就弹开了那粒闯祸的芝麻。周主任还犟嘴说他们家乡山岫里的狼劲大呢,狼抓比狠抓力度更大。台下就又是一阵爆笑,计委领导忍不住站起身大喊肃静肃静。一面和颜悦色与周主任耳语,这八个字是中央文件上抄来的一个字也改不得;一面又往台下眨眨眼讪讪地解释,都是一粒芝麻惹的祸,周老看走了眼又不是认不识这个字。
没过两三天,周主任的“狼抓革命”不胫而走沸沸扬扬传遍了整个机关大院。
大罪铸成,这下有我的好果子吃了。“写的什么潦草字害老子出这么大的洋相!你小子我用不起,退给王促履,明天就滚!”退给王促苁翻译出来就是物资办公室不要我了,退回组织部重新分配工作。
周主任的屁都是香的,我第二天早早就去了组织部,昨晚伤心了二夜,眼眶肿成桃子一样。王部长一句话未说,起身给我打了一个热毛巾把子,抽出组织部的红头便笺龙飞凤舞十分钟便写满一纸。递到我手上拍拍我的肩将我一直送到大门口。王部长没有套信封,便笺纸连叠都没有叠,我在路上就看了。
“爱好大主任:毛主席语录,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没有文化的人……,还是毛主席语录,犯了错误不怕,改了就是好同志。小战友的文章书法都在你我之上(王部长鼓励我呢)。再言之,就算小战友一时疏忽大意写成了‘狼抓革命你也不能读出来呀,天天看报看到鼻孔里去了?这样的好同志我收回了怕是你这个老浑球打了灯笼也没处弄。你若再胡闹我就到老首长那儿告你‘凑足了一打。王。”最末一句我只知道一打是十二个数,至于什么含义那是他们老战友之间的哑谜我看不明白。不过这句话加毛主席语录素来是王部长慑服周主任的两个法宝,一出口周主任立马就缴械投降了。
二
老姐徐燕芳龄已四十有三,只是她不许我们年轻一辈叫她阿姨非要发嗲叫姐,她是打字室的打字员。徐燕是周主任的“老搭子”,晓得周主任不少事呢,平时她嘴上又没有把门的,得意起来逮着人便乱说,周主任一点办法也没有。“凑成一打”之谜就是徐老姐给我们解的。那时机关大院里男男女女这类苟且之事不时兴像现如今称情人啊几奶的,一般说成某某与某某有一腿或干脆就明说“搞腐化”。更不像现在竟然成了光荣的事炫耀的资本。那时尤其是对当官的处理起来很重,不然像周主任这种三八式南下时就已经副团职五五年的上校军衔老资格,到七十年代末怎么才弄了个正科级临时机构的小主任?进城后三十年他因为“下面没有配警卫员”(王部长的话)被降职两次,薪水从行政十三级的高干降为十六级的中层。
老姐徐燕是机关出了名的逢人配公共汽车,自荐枕席这方面的爱好每每比我们周主任有过之无不及。有回我去打字室送稿件猝不及防就被她搂进怀里亲了个嘴(我的初吻)。只是这种事古今中外都是罚男不罚女,真是一个哥德巴赫猜想!不过,要说这位老姐勾人的资本确已是到了登峰造极:皮肤奶嫩面若桃花凹凸有致随风摆柳在次,最撩人的是臀部,体积之肥硕,形状之圆翘,每每把周主任馋得是手忙脚乱黏涎四溅。我们周主任的肖像呢,按我以上的叙述,看家一定以为是张飞李逵那种的,其实不然,周主任白白净净瘦瘦条条眉清目秀很有女人缘。坊间传闻据不完全统计从解放后人城开始算前前后后已有“相好的”十一个整。
几年前徐老姐周主任正如胶似漆,有一回忍不住竟然上班时间溜到招待所房间真刀真枪举办星球大战。不知怎么搞的,消息传到了上文提到的老首长市委第一书记陈兴那儿。当即找来王部长训话,王部长避重就轻给周主任打掩护说:他这人平时不烟不酒不赌不毒,优点一大堆,战争年代又是军功赫赫,就这点子小业余爱好,再说也不是他单方面的责任。陈兴书记的脸开始严肃,声调也高起来:“部长同志,不需你给我上课,你刚才说什么,这是爱好?”王部长还在开玩笑,说,我平时都叫他周爱好。陈兴书记怒不可遏:“乱弹琴,沆瀣一气,给这老小子传达我的命令,如果他再乱搞男女关系腐化,凑足了一打,两条路由他选,一是拿把刀自己解决了去喂狗,二是你立即发调令让他平调建筑公司当书记去,两千号人清一色带把的,没有了‘地狱,看他那个无法无天的‘魔鬼往哪儿放!你如再帮他放烟幕弹,我就找监委书记执行纪律!”陈兴书记是沪上的大学教授地下党出身,满腹经纶学贯中西读的书多着呢,他的话王部长这个大才子当然听得懂。老首长真气极了,进城后难得发这么大火。
老首长大动肝火,王部长当然是不敢怠慢,过后如数如实给周主任传达了,周主任赧颜,憨厚地双手从嘴巴一直往后脑勺搓,来来回回好几遍,嘴里一个劲重复,不弄了不弄了还不行么。
凭良心说周主任当兵前是个文盲,文化是差一些,现在到勉强能看书读报的水平全是部队扫盲的功劳。平时他不怎么正儿巴经读书,但报纸是天天必看,半天看一版连寻人启事也不落下,从头一字到末一字认真着呢。再论到谦虚的问题,他虽然爱滥用词语还强词夺理嘴巴不饶人,但王部长的话他其实是听的,给他纠出错,当面不服气顶几句,过后就全改了。比如吹毛求疵(屁)浑浑噩噩(疆)不伦(疼)不类,他现在就念准确了;机关中午下班大门洞中的自行车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他过去说的是“家喻户晓多如牛毛”。最典型的是有一回市委一位领导的老母亲过世,这位领导也是他俩的老战友叫许大炮。王部长周主任带了花圈绸被面领我们去吊唁。临结束时周主任摩搓着许大炮老婆的手,脸对着许大炮,嘴里一个劲地安慰:息怒息怒,息怒息怒息怒!出了门王部长大步流星独自走在前面,我们一帮忍俊不禁捂了肚子笑,周主任则莫名其妙浑然不觉。王部长一本正经地郑重宣告,下次永远不和你周爱好一块出门,你也不要再叫我老战友,我的脸让你丢尽了。应该叫节哀顺变,还息怒息怒,亏你想得出来!周主任又犟嘴说,我是想劝他俩注意休息,许大炮不要发火吓着刚刚续上弦细皮嫩肉的小老婆。注意休息不要发怒连在一块不就是息怒么。刚刚我急中生智好不容易想出一个既精炼,别人又没有用过的好词,一大厅的人都没有异议,许大炮还佩服得朝我直点头呢,难道天底下就你王促苁文化最高?真是扫人的兴。我们一伙已经笑得前仰后翻,相互搂抱,推推搡搡就差岔了气。“放你的×”王部长说话是从来不带脏字的,骑上自行车飞奔而去。
三
周主任要给我介绍对象。我那时已二十四、五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女方就是徐燕的女儿,在发电厂工会工作。我暗自寻思,既是徐燕的女儿想必也是个眉清目秀骨肉匀婷的美人胚子,心里蛮开心一口就答应见面。临行前还往头上匀匀地抹上金刚钻牌的发蜡。那知事与愿违大相径庭。徐老姐这块地是美丽丰腴的好地,可能是种子差了些肯定不是周主任估计是猪悟能娄阿鼠之辈偷偷摸摸下的。身段平平且不说,盘子更是丑不堪言,就是塌鼻扁脸下巴颌还伸多远的那种。周主任的美意我当然不敢为忤,背后我找到王部长一五一十地汇报求救。过了两三天王部长特地捧着茶杯来我们办公室,笑嘻嘻地说要送我们周主任一本书,周主任一看是新《婚姻法》的单行本,便往我这边剜了一眼说:“丑点怕什么,在一块过日子多看看就习惯顺眼了,情人眼里出西施么。”王部长就给他开玩笑:“水平不低嘛,连西施都晓得,不愧是这方面的行家,两个字写出来我看看。”周主任听王部长夸他,心中蛮得意的,便果真从上衣袋口上拔出朝鲜战场上打美国佬缴来的纯铜壳派克金笔,用他那自创的“火柴棒拼接体”(语出王部长)在报纸边自上写出“喜事”二字,王部长迅捷夺过笔在上面划了圈,给他订正成“西施”,并就着周主任的话往下说:“本来是一桩喜事,但要人家小战友乐意才行,你周爱好硬拉郎配强人所难就不对了。”这番话不是毛主席语录周主任不买账。周主任站起身将王部长往门口推:这事不归你组织部王促苁管,就这么定了,今年恋恋爱明年就把喜事办了。
下午临下班时王部长打来电话给我支了新招:到计生委找大姐去。“大姐”就是周主任的老婆,计生委的副主任官比周主任还大一级,也是三八式的老革命,而且不是“抬抬担架唱唱歌没见过鬼子面”的那种(周主任也偶有语录)。听王部长说大姐曾双枪上阵驰骋沙场当过女兵营的营长。机关里的同志包括陈兴书记都尊称她叫大姐。徐燕与他们家老周的花花事她早有所闻,只是碍着陈兴书记王部长的劝,逮不着机会发作而已。
大姐在办公室给周主任打电话:“这事归我计生委管,你强迫婚姻是违法行为我们管定了!再说徐燕那破鞋的、r头能好到哪儿去!这么好一小伙子被你瞎糟蹋,你不要他我找老王开介绍信到我计生委上班,我这儿正缺男同志呢。”
结果呢,这事不了了之。我和周主任又结一梁子。只是没有被调出计委物资办还是继续每天给周主任买馒头每天挨骂。顺便说一句,“狼抓革命”以后,周主任知错就改,芝麻草炉烧饼换成了馒头。用他的话说,白面馒头没有芝麻又没有颜色犯不了大错。只是馒头一两粮票一分钱一只,我每天的腿就白跑了。等到第四年的时候,物资办公室撤销并到了计委的综合科,周主任变成周科长,我被提拔为副科长。许多年以后,有一次陪王部长喝酒,王部长告诉我那次提拔是周主任两次力荐,你才从三个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四五年了,周主任从未在任何场合提过这事。
四
王部长与周主任常常晚上下班后留在办公室喝酒,地点有时在组织部有时在我们综合科的办公室。酒王部长的橱子顶上有得是,菜很简单就是招呼伙房炒两个猪肝熘一盘肥肠之类的,再从外面的摊子上买点卤猪头耳朵尾巴花生蚕豆。王部长下午就给老伴打过电话,周主任则不须向大姐请假,因为周主任夜不归宿是常有的事,大姐这么多年下来已习以为常睁只眼闭只眼弄习惯了。我是当然的陪客,跑腿伺候是我的强项,离了我他俩的酒喝不舒坦。周主任其实对酒一点兴趣也没有,用他的话说:白的辣嗓子红的甜不拉叽啤的像马尿,每每他只是酽酽泡一大搪瓷缸绿茶陪我和王部长喝。王部长呢也只是喜欢抿两杯而已,铁定的两杯二两左右。菜他俩也不怎么动筷子,就是趁机在一块聊聊大天。聊的又大都是我出世之前的事我根本插不上嘴,即使“文革”中的话题我也只能听个懵懂(文革开始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我这人天生善饮,五十六度的老白干一斤下肚漱漱口上班,办公室没人看得出来。所以每次喝酒桌上的酒菜大都被我包圆扫荡得毛干爪净。不用掏腰包又能打牙祭何乐而不为?买单的规定了就是王部长,他是十三级高干每月薪水一百三十多,他不买单难道让我这二十三级每月才支四十五元五角的小科员放血?我偶尔也假模假样客气两句,周主任则大手一挥:留两个钱娶马马吧(马马就是老婆)。有这么大的便宜可得我就常常撩他俩的酒瘾,逢年过节还能去他们的府上蹭饭。弄不明白,过去在钱财上都是群众沾领导下级沾上级的光,现如今倒了过来,这也是一个哥德巴赫猜想。
他俩喝酒聊大天我除了闷头胡吃海喝跑二腿之外,还有给他俩“垫话”的功能。“垫话”就是接话起新话头的意思,相当于写文章另起一行。有一回酒至半酣周主任突然问我,他与王部长哪个好?在他俩面前不敢模棱两可耍滑头,酒壮怂人胆,我想都未想即回说,当然是王部长好,他文化高不骂人,温文尔雅,工作中知人善任……周主任让我“垫话”的本意指望我在王部长面前夸他两句,一听味道不对,立刻就急了眼猛地打断我指着王部长的鼻子嚷:“他文化高,他参军前就是高小生,四二年又上过延安的抗大,解放后又是两年省干校,还走马灯似地去党校学习,党不培养他他能高?”周主任的指头又转向指着我:“还温文尔雅,你知道他怎么参的军?他在老家偷地主的西瓜,被打了一扁担,第二天就伙了人将地主捆了吊在房梁上,脖子结一活扣脚下垫张方凳,继续偷瓜吃。哪知老地主吓尿了裤子腿一哆嗦将凳子碰翻真吊死了。官府满世界捉他回去杀头,他才溜出来当兵。他从小就促点子多,十足的王促苁!”
我噤若寒蝉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偷偷窥了王部长一眼,他正轻斟慢酌有滋有味嚼花生米,脸上笑嘻嘻的仿佛在听一个重复多遍的别人的故事,连颔颔首的兴趣也没有。周主任讲了半天的故事宛如拳头砸在棉花上,更是火上浇油:“他还知人善任?他是满脑袋的促主意,他每天就像下象棋的大师,全机关大院的干部被他整天棋子一样搬东搬西当猴子耍,大家当面恭维他怕穿小鞋背地里别提多恨他呢!”周主任脸涨得通红,仰着脖子灌一大口茶,我连忙巴结地起身为他续水。他将我的手挡开:“滚一边去,你个‘味心小子,良‘秀不分的!'气急生错,这两个字周主任去年就念正确了,我可以作证。
“周爱好,你这么评价我们组织部的工作,出圈了有点出圈了,别的场合可不许乱说。”王部长给周主任搛了一筷他最爱吃的猪尾巴:“我像下象棋的?我看你周爱好像掏蜂窝煤的铁扦子,十二个煤孔你东掏掏西掏掏,哪天全掏通凑足了一打首长就要找你老小子算总帐,到时我可救不了你!”王部长真是太幽默了,我终究是没有忍住笑,一口酒呛进气管,喷得满桌子都是。
五
那时全机关就五辆小车。一辆苏联的伏尔加,一辆上海轿,三辆北京212吉普。伏尔加上海轿均已有了不小的年龄,经常坏在库里“趴窝”罢工,每每是刚刚才开出门十分钟就打电话回来报修,又要派出去两辆施救,一辆将坏车拖回头另一辆载着首长们继续前行。行政处招司机时王部长的条件苛刻:会开会修认路嘴紧四样一点不能“搭浆”。那时市面上会开汽车的人很少,不像现如今小区的保安都有开桑塔纳上下班的。
王部长与周主任在部队时就会开车,伏尔加上海轿是领导的专车很金贵他们不敢动,至多是偶尔将北京212吉普弄出来玩两天过过车瘾。王部长“司机四条件”条条符合,周主任也不孬仅缺最后一条,而且是上下都不紧(王部长语)。
这一日正值春暖花开的午后,周主任弄出一辆吉普载着徐燕老姐去兜风,直逗得老姐花枝乱颤咯咯咯咯笑成母鸡一般。回来泊车后没一刻钟工夫发现底盘漏机油,周主任捋了袖口掀开引擎盖三下五去二就搞定了。重新注满油箱将修好的车另泊个位置,周主任让我在原来漏油的部位垫上一张旧报纸再用碎砖头压住四角便得意地去水龙头洗手下班。
回家的路上我与王部长骑自行车并行,没什么事我就顺嘴将下午的事情告诉了他。王部长揿了两响车铃铛:“给你布置一个小任务,明天上班别睡懒觉起个大早,用机油枪往今天你垫的报纸上喷点机油,要将油枪竖起来垂直往下喷,油渍的形状也要与原来那块漏出的油渍基本相似,最后再重新添满油箱(老式北京212吉普车不用钥匙引擎盖也能打开),周围不能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王部长歪过脑袋往我狡狯地笑笑,又松开右手把往自己食指尖吹了一口气嘱我:“事情办完后,你去伙房吃早饭。吃慢些,一直吃到你平时去办公室的时间。这小任务的,内容不经我批准,就是上了老虎凳也不能说出去!”
第二天,王部长照常提前半小时在篮球场边上慢条斯理打杨氏太极拳。周主任正点上班,未去办公室报到先去验看车子的漏油情况,他弯腰撅臀抽出报纸便一脸沮丧:奶奶的怎么还漏?又准备捋袖口掀引擎盖。巧得很,王部长不早不晚正好就悠悠踱了过来:“慢,不用再修,我有大气功,只要往引擎盖上送一股仙气,油就一滴不会漏了。”周主任笑骂了一句:“老促苁,你说胡话呢,又要使什么促计。”王部长装出很认真的样子对周主任说:“咱俩打个赌,我若输了请你喝一顿酒,并且从此不再叫周爱好这个绰号;你若输了只需将我的绰号中‘苁字改成‘刮字。你也精神文明了,怎么样,还算公平吧?”周主任挠挠头皮憨憨地回说:“行,就依你个王促苁闹封建迷信一回。”于是,王部长对着汽车头,蹲一个两角垂直的标准马步,双臂平伸掌心向前,一口大气深吸进丹田并遽然吐出,双手同时往前猛一推:“齐了,漏油堵住了,你就是在车底下垫一床棉花胎,我也不许一星点油渍洇上去。”
周主任果真又将车开出去兜了一圈——引擎加热机油膨胀后最易溢出——并重新泊到自己办公室的门窗口,又垫上一张大白纸。班也上不安生,连上茅厕出恭都要让我换班看着,眼睛不眨盯住车,以防王部长伺机抢修,那老促苁在部队时就是出了名的风口上抓屁—快手,给他十分钟就能作案弄妥。
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周主任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王部长“气功堵漏油”他是绝对不信的,铁定了是王促苁这老小子装神弄鬼。回想起几十年来自己与王促苁的每次较量大都铩羽而归心中恓惶不已。自己参军比他早先认识老首长,现在他成了香饽饽自己在老首长眼里连臭狗屎都不如。这次如真的就这么稀里糊涂输给他,一顿酒喝不成事小,最不能容忍的如今几乎是自己唯一的战斗成果,即王促苁这个查了字典才琢磨成的绰号也要被他篡改成“王促刮”那真是惨到底了!周主任暗下决心一定要彻彻底底有理有据地将王促苁的阴谋促计大白于全机关大院,让这老小子有寻衅之心无了事之力(这句是王部长常常对付周主任的)。
雷厉风行立即成立侦破小组,周主任不惜血本斥重金二十元——那时婚宴才三十元——当晚在本市最上档次的饭馆富春酒店召开小组成立酒会,上了花瓶洋河大曲红牡丹烟。打硬仗要谋定而后动,组长他老人家自封,我这个作案分子成了副组长,组员就一位,市府办的张秘书,他当过部队的侦察连长,在工作安排上对王部长小有微词。酒会上,增强破案信心的豪言壮语掷地有声。三人分工到位,步骤细节有条不紊,外松内紧,缄口保密限七十二小时破案。
查油箱辨脚印,仔细研究分析报纸上的油渍形状……可惜那时录像探头等等科学机器还没有发明到中国来。七十二小时很快就到了期限,功亏一篑瞎子点灯白费蜡是可想而知的。
那几天周主任整日茶饭不思,搓脸挠头像个祥林嫂逢人便唠叨这事,连下午的馒头也只能咽下去半只了。我开始心疼他,做一回王连举(京剧红灯记中的叛徒)的念头开始萌芽。找了一个周主任较为轻松的时间我给他捶捶背劝慰他:“说不定王部长真的有气功,他天天打太极拳,有一回我亲眼所见他对着办公室院子里的老榆树猛击一掌,榆树钱落了一地呢,老榆树有这么粗。”我给周主任比划出小铁锅的直径。“要不你老亲自去问一问王部长不就全清楚了。”
要问你小子去问。周主任的声音恹恹的有气无力已没有了前几日的铿锵,有点濒临崩溃的意思。已给了我叛变的台阶,心领神会我拔腿便往组织部跑。
竹筒倒豆子,我将这几天的事详细给王部长作了汇报,最后还加重了语气:估计再过两天我们周主任能上五台山(本市精神病院所在地)。
死不了,死不了,打四平的时候这老小子失踪了一天,我把他从死人堆里弄出来他还笑笑说:这个梦做得真他妈香!你回去告诉他,就说我认输了,晚上请他喝酒。
那晚的酒一直喝到夤夜,他俩居然只字未提“气功堵漏油”的事,“王促苁周爱好”六字也只字未提。输赢本兵家常事,这就是胸怀,他们那辈老革命们大都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