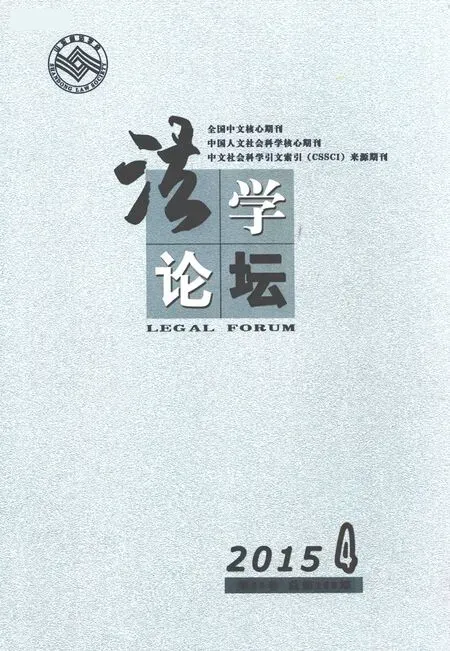论构建法律逻辑新体系的观念前提
——对“天然逻辑”理念的一个发挥
2015-04-16武宏志
李 杨 武宏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延安大学21世纪新逻辑研究院,陕西延安 716000)
论构建法律逻辑新体系的观念前提
——对“天然逻辑”理念的一个发挥
李 杨 武宏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延安大学21世纪新逻辑研究院,陕西延安 716000)
新兴的非形式逻辑或论证逻辑改动了逻辑的版图,特别对许多应用逻辑或专业逻辑分支比如科学逻辑和法律逻辑产生了有力的冲击,结果产生了科学修辞学(科学的非形式逻辑)和法律论证逻辑。然而,变革才刚刚开始。法律逻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难以通过对原有系统的修修补补就可解决,而是需要在一系列重大观念上的根本变革作为指引。“天然逻辑”理念勾勒出了法律逻辑新体系的先决条件:以天然思维之形式为对象,运用适合逻辑理论目标的抽象方法,发掘大量形态各异的论证形式。
天然逻辑;法律逻辑;论证形式;非形式逻辑
我国的法律逻辑正步入变革关键期。如何超越传统逻辑和数理逻辑框架下的法律逻辑体系,怎样勘定法律方法系统的版图,都呼唤观念前提的更新。只有在法律思维的特定环境中去重新梳理我们的一些逻辑观念,领悟了逻辑真谛之后,我们才能够清晰地看到一片法律方法研究的广阔天地。*参见孙培福、黄春燕:《法律方法中的逻辑真谛》,载《齐鲁学刊》2012年第1期。我们认为,法律逻辑学家孙培福教授等最近提出的“天然逻辑”的概念与逻辑学家伍兹教授所倡导的“天然化逻辑”(naturalizing logic)不谋而合,顺应了逻辑领域“实践转向”的大趋势,值得研究与发挥,以便为构建新型法律逻辑和法律方法系统创造先决条件。
一、自然逻辑与天然逻辑
天然逻辑与英语中的natural logic(汉译一般为自然逻辑)相对应。当今中外学者所倡导的天然逻辑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不满意现代经典逻辑(一阶逻辑)作为一般逻辑理论,特别是作为各种应用逻辑的原型逻辑或普遍逻辑;第二,关注真实世界的人的推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与人的实际推理状况更匹配的逻辑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天然逻辑代表逻辑发展的最新趋向。当然,天然逻辑也非今日才萌发的突兀之物,它是40多年来试图改进逻辑的各种努力的自然结果。而且,简要的考察会发现,天然逻辑或自然逻辑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形式。
天然逻辑可能是一种自然语言的自然逻辑。格里茨(Jean-Blaise Grize)及其同事自上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一直致力于发展作为分析论辩工具的自然逻辑(natural logic)。与形式逻辑相比,自然逻辑有三大特征。第一,自然逻辑是对话的而非独白的。它把每一论辩话语都看作是言说者在某一特殊交流情景中向听者做出的提议。为了让听者接受他们的提议,言说者必须提出他们的前提(事实),或者在这些前提尚未被当作事实接受的情况下,提供论证来支持它们。第二,在论辩话语的语义学方面,与形式逻辑中的记号不同,自然逻辑中的话语实体(discourse entity)被当作代表语言中的一个认知
表征(cognitive representation)的语言记号,话语中所引入的实体总是有某个含义,这个含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未决定的。与每一个话语实体相联系的是一组特性,与其他实体、行动(可能用相关实体执行)的关系。当然,并非一个话语实体的所有特性都被预先决定。随着文本的进行,一步一步给出实体更精确的含义,与其他实体的新连接得以建立。另外,实体也被充实和扩展。第三,论辩的目的不像在形式证明中那样将论证的前提之真转移到结论,而是要获得听者对结论的赞成或接受。话语所争议的不是真,而是似真性。因此,应该使用适合听者所表征的世界这样一种方式提出论证。这三个特征表明,自然逻辑采取了一种介于逻辑和修辞学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立场。论辩中使用的逻辑显然不只是形式演绎的逻辑,而形式逻辑的论证评估所要求的重构往往背离自然语言表述的论证。在格里茨看来,把论证仅仅归约为演绎推理既没有先验证明,也没有后验证明,而自然逻辑学家想要用非规范的、“自然主义者的”方式描述日常论辩性话语的“逻辑”。*参见Frans H. van Eemeren,et al.(eds.),Handbook of Argumentation Theory,Dordrecht:Springer,2014,pp. 481-484.范本特姆的“自然逻辑”是一种没有任何人工创造的“逻辑形式”层次的、直接基于语言(语法)形式的逻辑推论的系统。建立这种不是基于“逻辑人工制品”系统的逻辑学家,不用建立生产“逻辑形式”的店铺,而是在其对推论的说明中借用语言学家的语法分析。*参见Johan van Benthem,Essays in Logical Semantics,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6,pp.ix,109.
天然逻辑也可能是强调逻辑之经验基础意义上的自然逻辑。麦蒂(Penelope Maddy)的自然主义逻辑观有时也被当作一种自然逻辑。麦蒂认为,正如世界客观地存在于时空之中,在因果上是有序的一样,从经验上讲,它在普通科学探究来看也是逻辑上结构化的——比如它由具有属性的对象构成,立足于因果关系基础,这就是为什么逻辑规律是真的的缘故。另一方面,从先验上讲,世界的逻辑结构,很像时空的和因果的结构,是理想的,由我们的推论性认知的必然性所生成。形而上学的探究应该是这样开始的:观察、实验、理论形成和检验、随着前行而修正和精炼,但并不依靠构成“科学”的任何正式概念,未经考验的任何证明手段都算不得好方法。但是这种探究做了够多的工作并有相应的一切必要工具。*参见Penelope Maddy,Second Philosophy: A Naturalistic Metho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223-224,411.对话逻辑学者巴斯号召发展一种基于以科学上适当的方式系统地与一种经验逻辑的结果相联系的理论逻辑。*参见E.M.Barth,A New Field:Empirical Logic,Bioprograms,Logemes and Logics as Institution,Synthese,Vol.63,No.3(1985),pp.375-388.研究科学推理的科学哲学家芬诺恰罗也认为,推理研究需要一种更大的经验取向,即面向世界中真实发生的推理;这种经验的重点不可能被心理学的经验方法所满足,而是由广泛构想的历史方法所满足。*参见Maurice A. Finocchiaro,Galileo and the Art of Reasoning: Rhetorical Foundations of 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Dordrecht: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0,pp.437-439.芬诺恰罗最近指出,最好把论辩的理论化当作关于论辩的论证来构想和实践。这样的元论辩也应该努力成为语用的、比较的、经验的、历史的和自然主义者的(就如图尔敏建议的)。他以两类关于论证的论证为标本来研究元论证:逻辑学家和论辩理论家所提出的用来证明自己理论和理论主张的那些论证——理论的元论证;思想史上因各种理由获得了经典地位的那种论证——著名的元论证。*参见Maurice A. Finocchiaro,Meta-argumentation:An Approach to Logic and Argumentation Theory,London:College Publications,2013,pp.16-17.
从根本上说,天然逻辑是基于自然形态思维的。逻辑学家伍兹从推理主体的特性(不高的认知目标、不足的资源等)入手,提出天然化逻辑。这种逻辑考虑的基本问题是:谁在推理?在什么条件下推理?为了什么目标推理?用什么推理形式?应该满足什么理性标准?他指出,只有汲取来自相关经验科学的教益,才能搞好真实生活环境中发生的人类推理的逻辑。只有调整其规准以适应真实生活中的推理主体的认知本性,才能获得我们所寻求的逻辑学。前者意味着新逻辑要对经验保持敏感,后者要求新逻辑要有认识论意识。自然化逻辑是经验敏感的逻辑。自然化并不是一个新理念,它是杜威经验逻辑的奠基原则,也是一些当代哲学家的共同理念。*参见John Woods,Errors of Reasoning:Naturalizing the Logic of Inference,London:College Publications,2013,pp. 2,10-11.非形式逻辑创始人约翰逊认为,逻辑的传统本来是天然的,但在形式演绎逻辑那里,这个传统丧失了,因为其中的“逻辑”和“论证”概念变味了。对逻辑、推论和论证概念的“激进转变”才能恢复逻辑传统。“逻辑必须被天然化”,这意味着:首先,应该将自然语言中的论辩作为逻辑的焦点;其次,逻辑应该在其方法和目标上都是天然的,即应该尽可能多地使用自然语言而不是人工语言,应该有助于人们天然期望的目标——增强推理者更好推理的能力。*参见Ralph H.Johnson,Logic Naturalized:Recovering A Tradition,Frans H.van Eemeren,et al.(eds.),Argumentation: Across the Lines of Discipline,Dordrecht:Foris,1987,pp.47-56.逻辑哲学的中心问题是关于逻辑系统内有效的形式论证与系统外的非形式原型的恰当相符问题,其他问题皆由此派生而来。*参见任晓明、桂起权:《非经典逻辑系统发生学研究:兼论逻辑哲学的中心问题》,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此外,天然逻辑还有一些别的用法。有学者把与形式逻辑相对照的天然逻辑理解为一种心理逻辑或以快速而节俭为特征的启发法。例如赫伯特(2011)指出,大多数人的决策总是基于一种天然逻辑,尽管这种逻辑的规则无疑是易错的,不太严格,但有利于进化。评论者认为,我们应该追求形式逻辑和天然逻辑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我们的决策变成在理性和非理性、情感和认知之间的自觉协调的结果,以一种前者给后者提供增援或反过来的结合方式。*参见Mauro Maldonato,Between Formal Logic and Natural Logic: Prolegomena for a Middle Way,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Vol.125,No.3(2012),pp.387-389.自然逻辑还可能指使用自然演绎方法的逻辑。比如坦南特(Neil Tennant)的《自然逻辑》(1978)其实是介绍自然演绎形式系统的教科书。有人还在更宽松的意义上使用“天然逻辑”,比如管理政策的天然逻辑。*参见Roger I. Hall,The Natural Logic of Management Policy Making: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Survival of an Organization,Management Science,Vol.30, No.8(1984),pp.905-927.
二、“天然逻辑”以天然思维之形式为对象
是否真正研究自然形态的思维是区分天然与人造的唯一标准。自然形态的思维反映客观事物固有的特定关系和规律,天然逻辑只须去发现和总结便可形成自己的理论,因而这种理论成为认识论意义上的学问;但人造逻辑的对象不具有客观基础,需要通过设计和创造来形成自己的理论,因而流于方法论意义上的学问。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只是仿造与被仿造的关系,只有形似而绝无神似,二者从本质上既没有传承关系,也没有发展关系。现代逻辑确实长成了人造逻辑的模样儿。*参见孙培福:《逻辑现代化: 从天然渐变为人造》,载《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仔细考察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弗雷格和图灵在追求完全不同的目标。然而,逻辑教科书作者和许多用这些教科书进行教学的老师常常并不理解这一点。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告诉学生逻辑是论证或演绎推理的理论(部分适用于亚里士多德,但根本不适用于弗雷格和图灵),然后把弗雷格的版本或者(更糟糕)图灵的版本当作这种逻辑本身。非形式逻辑家的埋怨应该是针对那些犯了这种混淆过错的人,而不是针对现代逻辑的创立者。因此,那些被这种混淆所激怒的某些评论家的暴躁是可理解的。*参见John Woods,How Philosophical is Informal Logic? Informal Logic,Vol.20,No.2(2000),pp.139-167.如今已有一种极为一致的看法,即由于经典逻辑并不是设计为一种实践推理的逻辑,所以它并不是实践推理的恰当的一般理论。演绎和归纳的标准逻辑作为真实生活论证和推理的理论做得并不好,逻辑需要重返其历史目标,考察现实的人们如何处理自己的推理和论辩的鲜活议程。*参见Dov M. Gabbay,R.H.Johnson,H.J.Ohlbach,J.Woods(eds.),Handbook of the Logic of Argument and Inference: The turn towards the practical,Amsterdam:Elsevier,2002,pp.v,1-2.
作为天然逻辑之本原的真实生活的实践推理的典型样式是如何的呢?波洛克的回答是:当我们小心考察各种推理,一个认知者必定能够做的推理时,就注意到“好推理必须是演绎有效的”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可废止推理是常态,而演绎推理只是例外。”*参见John Pollock,Defeasible Reasoning,Jonathan E. Adler and Lance J. Rips (eds.),Reasoning: Studies of Human Inference and its Found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451-470.哲学中有一个悠久传统,认为好推理必须是演绎有效的。但是,这个传统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受到质疑,而现在则彻底不足信了。引起这一传统垮台的是这样的认识:许多耳熟能详的推理类型并不是演绎有效的,但显然赋予接受其结论的正当合理性,比如知觉、概率推理、归纳、时间投射等推理。在哲学中,可废止推理的研究始于哈特(1948),他将“可废止的”一语引入法律哲学,而后该术语被认识论学家齐硕姆(1957)所采用。之后,图尔敏(1958)、波洛克(1967)和雷歇尔(1977)等都是追随者。遗憾的是,缺乏哲学训练的人工智能研究者对可废止推理的说明在数学上是成熟的,但在认识论上却是幼稚的。由于他们未能容纳人们实际使用的各种各样的可废止推理,因而他们的理论不可能成为对人的认知的正确说明。虽然人工智能对非单调逻辑的研究迅速发展,但这个缺点今天依然存在。*参见John Pollock,Defeasible Reasoning,Jonathan E. Adler and Lance J. Rips (eds.),Reasoning: Studies of Human Inference and its Found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451-470.
可以从规范立场(我们该如何推理)或描述立场(我们实际如何推理)来分别独立研究推理,但是这两个方面也是关联的。“应该蕴涵能够”。任何人类个体都不能满足确证信念集的规范要件,因为这个标准太高了。*参见Juho Ritola,Book Reviews:Jonathan E. Adler and Lance J. Rips (Eds),Reasoning:Studies of Human Inference and Its Foundations,Argumentation,Vol.28,No.4(2014),pp.493-500.心理学的经验研究表明,当人们看似应用逻辑的时候,并不完全合乎逻辑地推理,他们实际上所做的事更受约束或具有情景化特性。基于一种信息加工视角的论证也认为,某些逻辑推理的要求是不合情理的,因为无法达到——超越了人们的能力。科亨(L.Jonathan Cohen)根据经验文献概括出,对人类合理性的误判可能是恰当规范理论的误用,即人们被误用的标准加以测量;也可能是不恰当规范理论的应用,即人们被错误的标准加以测量。*参见David N.Perkins,Standard Logic as A Model of Reasoning:The empirical critique,Dov M. Gabbay,R.H.Johnson,H.J.Ohlbach and John Woods(eds.),Handbook of the Logic of Argument and Inference: The turn towards the practical,Amsterdam:Elsevier,2002,pp.187-223.逻辑观念的一个核心元素是规范性(normativity)——人们认为逻辑为推理提供规范而不是描述人们如何推理。但是,在规范性方面,人们对现代数理逻辑的一个标准批评是:它的模型并不是心理上真实的。该模型并不是实际的人类推理者能使自己的推理行为遵循的模型,这一点得到大多数理论家的承认。不过,一些现代逻辑的辩护者争辩说,即使如此,它的合法性在合适的理想化之下得以保存。然而在这方面留给理论家一个好而难的问题。按照一种广为接受的观点,仅当一种推理理论的主张在一种合适的理性模型中是真的,该推理理论才是一种权威性的规范解释。比如,假如一个推论规则在该模型中被执行,这就表明该规则是实际的推理者应该遵守的规则,即使他们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但是,另一方面,只有一种推理理论的主张被实际的人类推理者的行为所验证,它才是一种权威性的描述理论。使用者友好的逻辑的理念可以有弱的和强的解释。弱的解释是,使用者友好的逻辑可能少有或没有形式指令被用于真实生活论证的分析和评估。实践推理的良好理论具有避免不必要的技术性和可有可无的复杂性的优点。强意义的使用者友好性是指,在未给不明就里的普通能力推理者形式指令的情况下,一种理论的权威性主张(比如它的定理)也是可识别的。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时,具有高度反直觉数学结构的理论能成为正确的理论,因而可能伴随一种使它们成为极具使用者友好性(基于弱解释的)的应用程序。比如,英语语法就是这样一种理论。现在,有一种看法被广为接受:形式演绎逻辑或标准演绎逻辑并不是实践推理或论证的恰当理论;它其实是一种后承关系的理论。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它作为一种推论或论证的理论并不成功。无人怀疑,与操作后承关系相比,进行推理和论证包含更多的东西。一种实践逻辑是原型逻辑(protologic)的任何合适的延伸,原型逻辑是实际时间中的行动的逻辑,其主体的更深层的特性由相关主体的类型来指明。可以说,一种纯粹的实践原型逻辑承认,资源限制策略是主体层级的基础。主体逻辑是实践逻辑的天然家乡,给一种合理的理论逻辑的概念提供适宜的居所。*参见John Woods,R.H.Johnson,Dov M.Gabbay and H.J.Ohlbach,Logic and The Practical Turn,Dov M.Gabbay, R.H.Johnson,H.J.Ohlbach and John Woods (eds.),Handbook of the Logic of Argument and Inference:?the turn towards the practical,Amsterdam: Elsevier,2002,pp.1-40.
一种逻辑理论中的枢纽概念是“逻辑形式”,逻辑形式的核心是逻辑常项或联结词(关系词)。天然逻辑的关系词基于客观事物的固有关系,其种类之多实在难以穷尽,人们有限度的审美感受只能有限度地认识和挖掘关系词的逻辑性规律。对关系词内部的逻辑性规律,有些被认识到了,有些尚未认识到;有些认识得深刻些,有些认识得浮浅些。真值联结词与普通关系词之间只有形似而绝无神似, 模仿出来的真值联结词只有演算功能,而不能体现普通思维中的天然关系。*参见孙培福:《逻辑现代化: 从天然渐变为人造》,载《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在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考虑逻辑形式的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逻辑形式的核心——逻辑常项是否反映自然语言联结词的标准或普通意义,二者能否等同?真值联结词的确与自然语言中的“相应”连接词在语义上相去甚远。比如,蕴涵、析取和合取并不是条件句、选择句和并列句的准确抽象。通过对┐、∨、∧、→和≡这些基本真值联结词与英语自然语言连接词在语义和所隐含的逻辑规律方面之异同的细致分析,斯特劳森指出,认为(虽然带有某些保留)┐、∨、∧、→和≡分别相当于“非”、“且”、“或”、“若—则”和“当且仅当”这一通常的看法是可疑的。在他看来,┐和∨等同于“非”和“或”最少误导,其余不仅误导而且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所发现的按照其标准或基本用法的普通连词,都不符合适用于真值函项之常项的逻辑规则;反过来,我们发现的真值函项之常项并不符合适用于按其标准或基本用法的日常连词的逻辑规则。*参见Peter Strawson,Introduction to Logical Theory,London:Methuen & Co Ltd.,1952,pp.78-90.真值函项算子完全用真值表和隐含的规律来定义和说明。从认识视角看,人们不会根据P∨┐Q中的支命题进而相信该复合命题,事实上人们相信P∨┐Q是因某个别的独立理由。论证评价试验也表明,许多被试显然不能应用析取引入(P,所以P∨Q)这样的推论规则(应用比例为0.197),这很可能是因为它的结论包括了似乎与所依据的前提不相干的信息,因而违反了会话常规。*参见Lance J.Rips,Logical Approaches to Human Deductive Reasoning,Jonathan E. Adler and Lance J. Rips (eds.),Reasoning: Studies of Human Inference and its Found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187-205.话语表征理论发现,认知主体陈述一个自然语言条件句时,并不断定其前件和后件是真是假,而关注它们之间是否具有某种关联。因而关键是要刻画条件关联的概念。条件关联能在适当的时候导致前后件获得确定的真值,而前后件的真值却不能说明条件的关联。对于反映条件句本性而言,经典逻辑的蕴涵概念——以前后件的真假组合确定整个条件句的真值,其实是本末倒置,因而作为一种对条件句的抽象“不太贴切,漏掉了条件句的关键特征”。这种与自然语言条件句的实际情况相距甚远的蕴涵概念正是蕴涵怪论的根源。*参见邹崇理:《从DRT动态语义学视角看自然语言条件句和蕴涵概念》,载《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01期。
第二,为什么别的连接词不在基本联结词之中,或者没有被当作逻辑联结词研究?(说明:逻辑中用“联结词”,自然语言中用“连接词”)经典逻辑的合取联结词常常被认为是对自然语言中并列、递进、转折、让步等复句连接词——“而且”、“不仅……而且”、“但是”、“即使……也”的抽象。其实不然。逻辑学家在为其规则选择某一言语模式的过程中,强迫出现于该模式中的表达式具有一种它们通常并不具有的逻辑严格性,在其系统中,逻辑学家的公式中出现的语词仅仅具有其规则所描述的逻辑用法。因此,在我们考察那些规则之前,我们不可能对出现于逻辑学家公式中的表达式的意思是什么有把握。人们会注意到,逻辑学家有某种日常言说来源的选择范围,甚至是一种选择的窘境。容易看出,至少为什么“如果”(if)被注意而“倘若”(provided that)“在……条件下”(under the condition that)或“只要是”(given that)被忽略,为什么逻辑学家不需要用“也”和“另外”的规则补充公式“P且Q” 的部分原因。不过,避免重复的欲望并不是逻辑学家之选择性的唯一理由。比如,“但是”(but)、“虽然”(although)和“不过”(nevertheless)并非仅仅是“且”(and)的风格变异,它们的用法至少意味着,在并列陈述之间存在某种对比的因素。尽管这种含义在讨论语词意义时不可以忽略,但它在一个蕴涵或不一致规则里不是容易表达的。逻辑学家对这些连词的忽略是可以理解的。逻辑学家的选择性也表现在量词方面。为什么在逻辑学家的公式中,“所有”和“至少一个”获得了优先于“许多”、“一些”、“数个”或“大多数”的地位?“大多数f是g,大多数f是h,所以至少有一个f既是g又是h”这样的推论模式是一般性的有效模式,但并没有出现在逻辑教科书中。也许是逻辑学家没有注意到从这个方向扩展他们的规则的可能性,但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系统的逻辑理念:逻辑学家喜欢提出一种相互连通的规则的整洁系统。如果包括了太多的常项,系统的整洁性可能受到损害。可见,什么表达式算作逻辑常项在一定程度上是个选择问题。在挑选某个表达式作为一个逻辑常项的过程中,逻辑学家赋予那个表达式某种标准逻辑用法,并不一定限于日常言说中的用法。这一事实能使我们通过参考一种给定的规则系统来说明逻辑形式。*参见Peter Strawson,Introduction to Logical Theory,London:Methuen & Co Ltd.,1952,pp.43,48-49.的确,自然语言连接词有更丰富的意义没有为真值联结词所反映。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杜克罗(Ducrot)和安思科姆里(Anscombre)发现,诸如“但是”、“甚至”、“仍旧”、“因为”和“因此”这些语词具有论辩“运算符”(operators)或“连接器”(connectors)的作用,而且赋予话语某种论辩力量和论辩方向。像“但是”这样的语词,只决定语句所暗示的结论的方向,无关乎该结论的内容。这个内容也依赖语境和说出语句的情景。无论从一个具体语境可能得出什么结论,在所有情形出现的语词“但是”,都引起这样的结论:比起必定从“但是”之前的语句部分得出的结论来,它是相反的,也是更强的。*参见Frans H. van Eemeren,et al.(eds.),Handbook of Argumentation Theory,Dordrecht:Springer,2014,pp.37,491.
第三,定义逻辑常项的其他可能性。其实,即使假定真值联结词是满足某种系统目标的约定意义的情况下,这种抽象或定义也不是唯一的可能,把自然语言连接词抽象为逻辑常项并加以定义的方式存在多种可能性。在洛伦岑(Paul Lorenzen)的对话逻辑里,逻辑常项的对话式定义是逻辑学的语用方法肇始的标志。对联结词的定义是通过描述它们在一场争论(就某事意见不一的人们之间的一种讨论)中被使用的方式来完成的。巴斯(1980)认为,以这种方式所获得的逻辑常项的对话式定义的重大意义是,洛伦岑证明现代逻辑“本质上”是语用的。“首先,他非常明确地把人(语言的使用者)引入逻辑理论,所以逻辑(现代逻辑)穿着一种新的、语用的装束出现。其次,他也表明,在那种逻辑里,人因而早已存在,虽然不显而易见……”*参见Frans H. van Eemeren,et al.(eds.),Handbook of Argumentation Theory,Dordrecht:Springer,2014,pp. 309-310.对话方法基于这一事实:人的言说主要指向听者。如果听者做出反应,那么对话就启动了。陈述并不被设想为真的或假的,而是在对谈者(充当陈述的反对者或支持者)面前被断定或争论的东西。因此,逻辑常项(联结词和量词)的对话式定义是要给证明或反驳以这些介词为手段而构建的陈述的对话所必定采取的路线提供一种指示。例如,合取的定义是:令A和B是陈述。假设一个言说者充任论点A∧B的支持者,即他断定合取A∧B。充当这个论点反对者的另一个言说者那么就有权选择对两个子陈述中任意一个的真实性提出怀疑。如果支持者无法辩护这个陈述,反对者就赢了,这个结果是终极的。不过,假如支持者以对受攻击的子陈述的成功辩护挡住了该攻击,那他就赢了,但不是终极性的胜利,因为反对者仍旧有权发起第二波攻击。假如反对者在第一回合没有成功地攻击(比如说)A,他现在就可以攻击B。如果第二回合攻击成功了,反对者就终极性地赢了;假如支持者又通过成功地辩护受攻击的陈述B成功地挡住了这轮攻击,那他就赢了,这次是终极性胜利。析取与条件句也用类似方法定义。*参见Frans H. van Eemeren,et al.(eds.),Handbook of Argumentation Theory,Dordrecht:Springer,2014,pp. 315-316.
三、“天然逻辑”运用适合逻辑理论目标的抽象方法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逻辑要研究思维形式(结构)。从思维中剥离出一般形式问题,并对其合理性加以专门研究便是逻辑。在法律思维环境中进行这样的研究就形成法律逻辑。非形式逻辑之“非”并不是放弃了对形式的研究,而是不满意现代逻辑仅仅局限于“纯形式化”——真值形式,并以形式有效性为判定推理形式合理性的唯一标准。非形式逻辑依然固守着人类逻辑天然具有的思维形式之形式。非形式逻辑不是不讲“形式”的,也不是没有“形式”的,只是这种“形式”和形式逻辑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形式是抽象的结果,但抽象有不同的层次。顶级抽象与非顶级抽象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总是企图让不同专业思维的形式规律一致起来,而后者总是希望让不同专业思维的形式规律相互区分开来。这种“分层抽象法”能够帮助我们发现法律思维中的独特逻辑规律,从而法律方法研究也能够循着逻辑的脉络去发现更多的新方法。*参见孙培福、黄春燕:《法律方法中的逻辑真谛》,载《齐鲁学刊》2012年第1期。
断言所有推论规则是形式逻辑学家的规则是错误的。“X是小儿子”蕴涵“X有兄长”这一规则并不是一条逻辑学家的规则。逻辑学家规则的存在并未使词典编纂家的规则变得多余。说“所有推论都是形式的”是有价值的,仅仅是在鼓励我们寻找尚未注意到的形式相似性的范围内;而在鼓励我们忽视讨论描述性语言的隐含逻辑特性与一般逻辑函项的明显表现之间的差别的范围内,这一说法却是危险的和误导的。*参见Peter Strawson,Introduction to Logical Theory,London:Methuen & Co Ltd.,1952,pp.54-55.日常言说中有不同逻辑用法的语词被指派一个逻辑学家规则中的单一标准的逻辑用法。这样一来,出现在逻辑学家规则中的表达式与日常言说的表达式之间的裂缝就被扩大了,这是因为要实现系统的逻辑理想。逻辑学家试图提出一个互联的系统,而不是一种不连通的原则的清单。从一开始,在形式逻辑中就提出了系统的这一理想。早先的逻辑学家已经看到,在少量逻辑原则的帮助下,把为数不多的有效推论模式作为基础模式,他们就能证明其他大量模式的有效性,即能在逻辑学中应用逻辑,使逻辑本身系统化。证实这一系统化的理想对现代逻辑的发展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结果,只是编纂我们在做出逻辑评价时所诉求的最一般原则的这个最初设想几乎被丢掉了。日常言说中的连接词的常项地位倾向于被捏造的表达式所取代,它们恰恰被指派了满足系统要求的那种意义。这些捏造的表达式的逻辑用法以部分舍弃、部分背离的方式对应于日常言说里某些表达式的某些用法。换言之,形式逻辑学家现在瞄准一种精确的、高度系统化的逻辑,在这些方面堪比数学。但是,他无法给出日常言说表达式的精确而系统的逻辑。他能做的就是发明满足自己要求的规则集,然而并没有充分利用日常用法的复杂性,反而以多种方式与它背道而驰。逻辑学家制造不像日常语言的一种语言的元素,它们属于严格的、系统的和连贯的规则,制造了某些符号,显示日常言说类似表达式的逻辑相似物。对逻辑学家最具吸引力的是看来最能满足系统之理想的演绎方法,它与数学的相似最为明显。*参见Peter Strawson,Introduction to Logical Theory,London:Methuen & Co Ltd.,1952,pp.56-58.要满足演绎系统之理想,看来对推理的适度抽象就不可避免。
当然,抽象要达到何种程度或水平的一般性,各人可有不同选择。即使是要达到演绎系统判定有效性所要求的逻辑形式的抽象水平,也可能有不同选择。比如,对于一个三段论论证,如果我们用命题逻辑的方法进行抽象,我们得到的结构是p,q,所以r。这是无效形式。而根据另一种抽象(分析至词项成分),我们就可能得到三段论的有效式。如果再扩展逻辑常项(如考虑到模态算子、时态算子、认知算子、道义算子等)的话,显示推理有效性的抽象层次更可能不同。按照通行的做法,用包括被替换的表达式在内的特殊范围的一个变项,替换一个或更多的“内容表达式”(content expressions),就可以从任何论证得到其形式。例如,“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终有一死”可以抽象为以下不同的形式:
p,所以q。
个体对象x是人,所以x终有一死。
苏格拉底是K类,所以苏格拉底终有一死。
个体对象x是K类,所以所有x有属性F。
个体对象x是F,所以x是G。
第一个形式处于最高抽象水平,p和q的变项范围是语句。在较低抽象水平上(比如最后一个),变项x的范围不仅包括个体的名称,也包括个体对象类的名称,个体对象的特性等等。变项F和G的范围是各类谓词,包括归类的、描述的、评估的和规范的谓词。这个形式的便利之处在于,允许推论规则有单一的形式,且能包容范围非常广泛的论证:从某物是F的信息,有权得出它是G的结论。但是,这个形式的规则可能表现为许多类型,例如:
从一个类到一个描述性属性——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终有一死。
从绝对可靠的迹象到一个描述的属性——她有奶水,所以她生了小孩。
从并非绝对可靠的迹象到一个描述的属性——他打喷嚏,所以他有过敏症。
从目前的原因因素到预见的未来后果——他是傲慢的,所以他会失去朋友。
从描述的属性到一个评估——此小说有不合情理的情节,所以不是最佳小说。
从一个后果到一个规范——给某医疗机构捐赠有助于解除大量病痛,所以你应该认真考虑。
要确定这些类型的推论规则的合法性,人们需要确定既是F也是G的对象的某一具体类的成员,它们普遍地、大多数或在缺乏颠覆性或削弱性环境的情况下,是F者也是G。虽然对这些类型的评估目标都是一样的,但是,如何建立该概括的方式在推论类型之间却是不同的。要确定某类的每一成员都有某属性,人们诉求什么属于此类的一个定义,或者在经验上基于已建立的关于该类成员的非偶然概括;要建立一个属性F是另一个属性G的迹象,人们需要在经验上基于良好信息:有属性G典型地引起属于具体类的成员个体x,x在属于有属性F的论据中被提到;等等。不仅在抽象的一般性上,而且在为了概括目的而对特殊论证进行归类方面,人们都可能有不同选择。“x是F,所以x是G”这种形式的迹象论证,可以与其他并无这种明显形式的迹象论证归为一类。比如,“西面天空有黑云,所以快要下雨了。”可以通过把话语中的时间和空间处理为x的指称,重新把这个论证表述为“x是F,所以x是G”的形式:“现在这里西面天空有黑云,所以这里不久之后会下雨。”这种重铸需要理论家的机灵性。*参见David Hitchcock,The Generation of Argumentation Schemes,Chris Reed and Christopher W.Tindale(eds.),Dialectics,Dialogue and Argumentation: An Examination of Douglas Walton's Theories of Reasoning and Argument,London:College Publications,2010,pp.157-166.
人工智能学者维尔希基比较了严格的形式和可废止的形式。一般而言,论证形式是发生于日常论辩中的合理的推理模式。肯定前件、直言三段论等是标准逻辑熟知的严格的形式。但是,在论辩中有许多其他模式,它们常常是可废止的(即可能存在推理形式的结论不能从前提得出的例外环境)和偶然的(即可能存在使用该形式的条件)。比如,
(1) 某人E说P,E是关于P事实的专家,因此P。
(2) 做出行为A有助于实现目标G,某人P有目标G,因此,P应该做A.
(3)如果P则Q是一个规则;情况是P,不存在如果P则Q的例外,因此情况是Q。
(1)表达了根据专家意见的论证,(2)是手段-目标推理,(3)是肯定前件的变体,即“排除例外的肯定前件”(modus non excipiens),它考虑到规则例外的可能性。维尔希基认为,这些可废止的形式和严格形式一样,都是论证的合理模式,而且在现实生活的论辩中,它们比严格形式可能更为常见。严格的推论规则似乎是纯正地可形式化的、必然有效的、严格的和独立于语境的,而非严格的形式是语用有效的,甚至是偶然的、可废止的和依赖语境的。看来必然性、严格性和脱离语境的经典逻辑方法,并不适合于处理这样的语用论证形式。但是,在严格形式与语用的形式之间也明显存在结构上的类同之处:二者都由一个或更多前提与一个结论构成,形式中的语句必须一律被变项代入。这个类同的结果是,严格形式和语用形式都被处理为“前提-结论”的形式:前提1,前提2 ……前提n,因此,结论。维尔希基区别了中等抽象水平的推论规则与非常具体的属于某一领域的规则,同时承认二者之间的边界是流动的。像沃尔顿等所辨识的论证形式是一种较高水平的抽象,但尚未达到纯粹形式的那种抽象程度(如肯定前件),因而属于中等水平的抽象。维尔希基进一步指出,推理模式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体:从抽象推理模式(推论的逻辑规则,如肯定前件),经由语境推理模式(语用推理形式,如根据专家意见),到领域规则(如法律中的判决模式,在法律语境之外是不相干的)。这样看来,人们在哪里画出论证形式和其他规则(内容)之间的分界线几乎不重要。*参见Bart Verheij,Dialectical Argumentation with Argumentation Schemes:An approach to legal logi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Vol.11,No.2-3(2003),pp.167-195.在这种中等抽象水平上,适合某一论证形式的具体论证是否构成从前提到结论的好推论,取决于是否某些条件被满足,这些条件可以用批判性问题来指示。布莱尔也指出,对一个特殊推理片段包含的形式,常常有一系列可能的表述。但不管怎样,应把一个论证性话语意欲的推理类型准确加以表征。因而有两个最低要件是一个推理实例的描述性形式需满足的:第一,形式应该准确表征推理者或论证者意欲的推理类型;第二,形式应该显明地展示该推理之力量的突出特性。*参见J.Anthony Blair,Groundwork in The Theory of Argumentation:Selected Papers of J.Anthony Blair,New York:Springer,2012,pp.166,168.
法律论证语境中所使用的大部分论证形式是可废止论证形式,一般属于中等抽象水平。哪些自然语言语词被选中作为逻辑常项,哪些推论形式成为合理的推论规则,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在论证中反复出现的反映权威-断言、证人证言-断言、因与果、手段与目的、语义与话语意图等关系的语词,都有可能在抽象逻辑形式时被当作某种常项。而那种仅仅把类似于基本真值联结词(以及全称和存在量词)的词项当作常项的抽象方法,会使大量法律论证形式成为漏网之鱼,从而不能解释实际上大量使用的法律论证形式的合理性。
四、“天然逻辑”发掘大量形态各异的论证形式
除了使用形式逻辑所发现的人类思维共同适用的普通推理形式,还应从法律思维的现实出发,开掘本领域独特的推理形式。非形式逻辑正是重新把目光聚焦于客观的、频繁使用的推理形式上,以挖掘、总结更多的天然逻辑形式为己任。它更关注前人未曾涉及的形形色色的逻辑关系,致力于发现其中的逻辑形式及其规律。这些规律未必都具有严谨细密的演绎功能,但只要能对事物之间“相关和不相关”、“强相关和弱相关”等问题给出某些“启发性的”提示,那就很有意义。*参见孙培福、黄春燕:《法律方法中的逻辑真谛》,载《齐鲁学刊》2012年第1期。
的确,逻辑中新近出现的“实践转向”的核心议题之一便是关注所发现的大量非演绎推理。甚至可以说,一部广义的逻辑史也是不断拓宽推理形式研究视域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数理逻辑也是对推理形式的扩展,但局限于演绎推理。作为一种蕴涵的逻辑,它虽然研究了蕴涵的各种形式,但也没有穷尽所有蕴涵,比如格赖斯的语义蕴涵、语用含义等。同样,一部广义修辞学史,也是在不断探索各种可能的说服手段的过程,其中一些说服手段表现为不严格的推理形式。因而我们看到一种历史现象:从逻辑的萌芽阶段开始,在三段论之外还有辩证推理;在逻辑之外还有修辞术里的修辞式推理——“根据可能和迹象”的推理;中世纪逻辑除了词项推理和命题推理而外,还有跨越逻辑和修辞学的“论式”(loci)学说;即使遭到逻辑的放逐,“论式”依然能找到修辞学或写作学这样栖身之地。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则以非演证的、论辩的论证形式作为演绎推理的重要补充,由此开启了当代发现和总结“未经屠宰的”论证的鲜活形式的浪潮。标准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充其量把握的是哲学、数学或某些科学的成功的论证形式。当一个法律论证未能遵循这些形式时,并不见得就必然有瑕疵,也许恰恰表明了法律论辩不同于其他领域的论证。非形式逻辑所分析的某些“非形式谬误”,即使违反了某种逻辑系统所接受的逻辑原则,但它们确实是某种条件下可接受的法律论证的具体形式(比如诉诸权威、证人证言和针对人身等)。这表明,演绎逻辑所提供的推理手段不足敷用,人们总是觉得丰富而独特的推理形式多多益善。事实上,数学哲学中出现的一个最新趋向表明,即使是数学论证也与论辩理论脱不了干系,“数学实践的哲学”、“数学哲学的论辩转向”这些用语把真实论辩的外延扩展到包含数学论证。这一变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修改了图尔敏和佩雷尔曼将数学证明与论辩相对立的基本立场。阿伯丁发现,数学推理由两个平行的结构组成,一个是推论的,另一个是论辩的。推理的唯一数学特性由推论结构的严格性而来,但大量的数学实践发生在论辩结构中。*参见Andrew Aberdein and Ian J. Dove(eds.),The Argument of Mathematics,Dordrecht:Springer,2013,p.6.
如何从我们实际上怎样推理过渡到我们应该怎样推理?有学者把认识论上的“无罪推定原则”(innocence principle)推广到逻辑上,以此来说明一个实际使用的推理形式如何成为规范的推理形式。认识论上的“无罪推定原则”是,除非我们有怀疑的理由,否则我们有理由保持自己的信念。同样,我们的推理是无辜的,除非被证明有过错。或者更准确地说,除非有怀疑它们的某种理由。除非我们找到认为这些推理方式不好的某种理由,否则我们所做的推理是正当合理的。假若如此,我们就能说明为什么可以解决从“是”过渡到“应该”的问题。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的那些实际运用的推论正是我们有理由使用的那些推论形式。这意味着,在诉求某种推论实践时,即使是在对另一个推理实践产生怀疑的过程中,我们在诉求一种有正当理由使用的推论模式,这使我们直接跨过了所假定的“是”与“应该”之间的鸿沟:如果这实际上是我们推理的方式,而且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个推理,那么,这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推理的方式。任何逻辑原则可以从理论上进行批评,我们不必首先建立这种批评背后的逻辑原则的正确性,尽管这些原则本身可能在适当时候是批评的靶子。“无罪推定原则”是一个正确的原则:我们的实际做法是正当合理的,如果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们的话。*参见R.M.Sainsbury,What Logic Should We Think With?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Vol.51(2002),pp.1-17.这与根据另一个经验规律性——“理由规则”(reason rule)做出的进一步推理是一致的。只有在人们知道、认为他们知道或怀疑事情出了差错,或者当对他们而言不抵抗涉及某种不寻常的代价时,他们才会拒斥或反对。一般情况下,对于到目前为止尚未遭到挑战的他人的论据,人们倾向于接受。理由原则在时间和信息方面提供了实质性便利,一般来说,它似乎既没有造成主体犯大量错误,实际上又刻画了一种作为不足资源的守护者的可废止缺省。*参见约翰·伍兹:《实用逻辑的新领域》,刘叶涛译,陈波校,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由此可见,要得到适合我们使用的规范性推理形式,我们就得首先考察实际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推理形式,对其进行批判性审查,然后获得具有规范力量的推理形式,并进一步确定它们的适用条件。自佩雷尔曼开始到今天对“论辩技术”或论证形式的研究走的正是这一条道路。在探寻论证形式之宝藏的过程中,业已出现三种方法。*武宏志:《论证型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445页。
对于法律逻辑的建构而言,最核心的任务是发掘法律论证中独有的论证形式以及在法律论证领域有独特表现的一般论证形式。就论证形式的评估而言,一般论证形式在法律领域的运用有何特点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比如,在法律论辩中运用“后果论证”时,所谓的“后果”很可能显示法律领域的特殊性。后果可能是两类:法律的后果和法律之外的后果。前者指一个裁决在法律系统内部的效应,或者一个裁决内在的可能法律意涵。此时,后果论证实际是“根据法律后果”的论证,使用它是要寻求用宪法和法律系统的其他规范进行治理的一致性和融贯性,同时设法避免法律漏洞和反常。*参见Flavia Carbonell,Reasoning by Consequences: Applying Different Argumentation Structures to the Analysis of Consequentialist Reasoning in Judicial Decisions,Christian Dahlman and Eveline Feteris(eds.),Legal Argumentation Theory: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Dordrecht:Springer,2013,pp.1-20.法律解释中所使用的“归谬论证”也并不是严格的逻辑论证,而是一种语用论证,是关于某一给定结果合意或不合意的论证。此时必定涉及何为法律意义上的“荒谬”,它包括对法条意义的解释导致降低法律体系的权威;把不能忍受的不公正带入法律体系;导致立法者明显或隐含地否认正义的理念;导致与一个法律体系中其意义和有效性无可争辩的某个规范相冲突,等等。*参见Thomas Bustamante,On the Argumentum ad Absurdum i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Its Uses and Normative Significance,Christian Dahlman and Eveline Feteris(eds.),Legal Argumentation Theory: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Dordrecht:Springer,2013,pp.21-44.
如果我们持有一种天然逻辑的观念,就会自然理解,逻辑不是只存在于法律适用的终了阶段,而是在适用过程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存在。就是说,在明确或寻找法律规范的阶段有逻辑,在查清或确定案件事实的阶段也有逻辑,并非只有求得结果的阶段才有逻辑。因为各种论证形式到处现身,无所不在。这就要求我们应当把训练对变项间关系的敏锐性,作为一种能力来培养。如果说存在什么独立法律方法的话,能够让从事法律适用的人具备这种能力,是最基本的法律方法。*参见孙培福、黄春燕:《法律方法中的逻辑真谛》,载《齐鲁学刊》2012年第1期。
[责任编辑:魏治勋]
Subject:On Idea Prerequisite for Constructing the New System of Legal Logic——Based on the concept of “natural logic”
Author & unit:LI Yang (Law School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Hubei 430074,China);WU Hongzhi(21st Century New Logic Research Institute at Yan’an University,Yan’an Shaanxi 716000,China)
The rising informal logic or argument logic has altered the domain of logic, and has had specific impacts on many applied logic or specialized branch of logic such as scientific logic and legal logic. As a result, rhetoric of science (informal logic of science) and legal argument logic have come into being. However, the change has just begun. Which route legal logic should take, this problem can hardly be settled by repairing the original system, but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fundamental change of a series of ideas. The concept “Natural logic ” has drawn the outline of the prerequisite of the new system of legal logic: taking the natural forms of thinking as its objects, using abstract approaches available for the objectives of logic theory, exploring many other argument schemes of various shape.
natural logic; legal logic; argument schemes; informal logic
2015-05-20
本文系陕西省高水平大学学科建设项目之特色项目《批判性思维与非形式逻辑》(2012SXTS09)的中期成果。
李杨(1978-),男,陕西定边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延安大学21世纪新逻辑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法律论证;武宏志(1957-),男,陕西榆林人,延安大学21世纪新逻辑研究院院长,延安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批判性思维与非形式逻辑。
D90-051
A
1009-8003(2015)04-005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