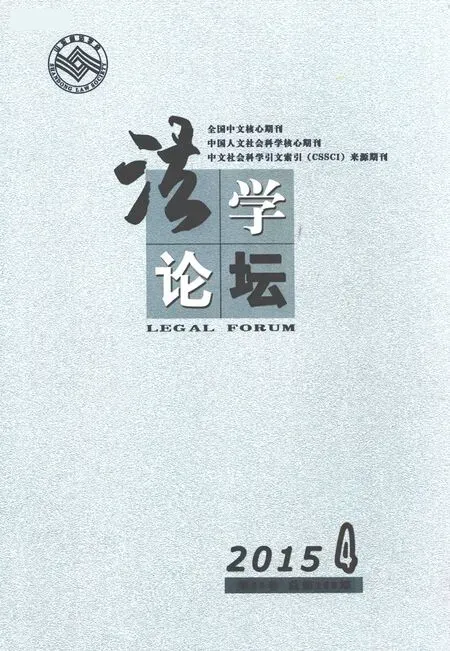美国处理期货法与证券法之间关系的实践及其启示
2015-04-16楼建波
楼建波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1)
一、为什么关注期货法与证券法之间的关系
在当下修改《证券法》的热议中,如何处理证券法与期货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较少为人关注的技术性问题。传统上,期货法与证券法属于金融法体系中两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分别适用于衍生交易与证券(现货)交易。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金融衍生交易出现后,这一判断不再可靠。近年来,域外期货市场交易从商品期货向金融期货的重心转移、证券交易所与衍生品交易所合并、全球性的金融监管一体化潮流等,催生了金融立法体系内部的结构调整。域外很多国家都将期货监管规则纳入到大证券法或者金融商品立法中,如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韩国《资本市场法》、德国《证券交易法》、英国《金融服务与服务法案》等。
受其影响,如何处理期货法与证券法的关系也成为我国金融立法过程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否还有必要制订独立的期货法,还是直接在《证券法》中纳入期货交易的监管原则?后者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既符合国际潮流、又节省立法成本的便捷选择。因为现行《证券法》第2条已经规定了“证券衍生品”;上海证券交易所也曾上市过国债期货、认股权证等衍生品种,最近又推出了股票期权和ETF期权交易;我国的证券监管机关——中国证监会——也同时行使着对期货市场的监管权。可以说,这个问题涉及到以下四个层次的制度安排:(1)我国金融立法体系的内部协调;(2)与衍生交易相关的监管机构的设置;(3)交易所的业务范围与分工;(4)特定交易品种的上市地点。
然而,细究域外的期货立法例会发现,所谓的“大证券法模式”不过是一种含混的归类,各国期货立法的具体形态各不相同,作为立法基础的国内期货市场的结构与形态更是相去甚远。①参见楼建波、刘燕:《我国期货法的定位及其与《证券法》之关系——一种立法论的进路》,载《财经法学》2015年第2期。例如,日本长期以来实行期货法与证券法的分立,2006年虽然以《金融商品交易法》囊括了证券、基金、金融衍生品等各类“金融商品”,但同时还保留了《商品期货交易法》适用于大米等传统商品期货交易。在期货交易历史悠久的英国,2000年出台综合性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之前从未制订过期货法,也没有证券法,而是依靠交易所的自律管理与普通法长期以来积累的判例来保障期货交易的基本秩序。与其说英国属于“大证券法”模式,毋宁说是英国是一个以自律监管为主的模式。①参见季向宇编著:《期货期权市场》,中国友谊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326页。再如,将期货监管规范纳入《证券交易法》的德国,长期以来一直禁止有赌博嫌疑的期货交易,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开禁,目前也仅有金融衍生交易。②上海期货交易所《境外期货法制研究》课题组编著:《德国期货市场法律规范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因此,与其追随所谓的流行立法趋势,不如观察现实中一种期货立法形态如何与期货市场结构进行呼应、互动更有意义,毕竟,期货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在此,美国是一个比前述国家更理想的观察样本。由于美国特殊的地理条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路径,在所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美国的期货交易与期货市场发展得最充分,从大宗商品的现货交易、远期交易到商品期货交易,直至现代金融衍生交易的兴起,整个演进过程非常清晰;同时美国与期货有关的立法、司法与监管实践也最为丰富。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期货立法的形态可谓期货立法与期货市场之间自然演进关系的一个缩影。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它如何处理期货法与证券法的关系对我国当前的期货立法可能有更直接的启示。
二、美国期货市场与期货立法的演进
美国期货市场以及期货立法历史悠久。1848年,美国最早的期货交易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开业。起初CBOT只是一家经营谷物、牛肉、盐、皮革、木材等各类主要商品的市场,但它在短短20年内实现了期货合约的标准化,建立了现代期货交易的结算方式,从而完成了从现货批发市场向期货市场的转型。随着同城其他商品交易所陆续开业,芝加哥也发展为美国中西部农作物产区的转运站和定价中心。至19世纪末,美国各地的商品交易所达上千家,参与者众多,且充斥着逼仓、操纵、内幕交易、欺诈等行为,导致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令美国农业生产者遭受很大损失。这也引发了各方面的立法与监管动议。
1874年,芝加哥所在的伊利诺伊州议会率先通过了《反逼仓条例》,其他一些州也通过了禁止在期货市场进行赌博式交易的法令,但收效甚微。在联邦层面,1880-1920年间美国国会收到了200多项议案试图规范期货与期权交易。1916年,国会颁布了《棉花期货法》试图改善市场环境,但该法仅就棉花等级加以规范,对期货交易行为未作规定。1921年出台了《期货交易法》,但该法有因以课税方式对期货交易所进行监管而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为违宪而无效。随后美国国会通过了《谷物交易法》并于1923年10月1日生效施行。该法要求所有期货交易应在规范的交易所内进行,交易所应公开更多的信息及限制市场垄断的数量。1936年,为适应大萧条后期货市场发展与监管的需要,国会对《谷物交易法》进行了修订,并更名为《商品交易法》(Commodity Exchange Act)。这些商品期货立法给美国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今美国芝加哥成为全球大宗农产品商品定价中心,纽约则成为原油定价中心之一。③对美国期货市场发展以及立法与监管演进历史的介绍,参见【美】杰瑞·W·马卡姆著,《商品期货交易及其监管历史》,大连商品交易所本书翻译组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6页。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各国间汇率开始出现宽幅波动,国际贸易陡然陷入汇率风险中。加之70年代两次中东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货膨胀,西方国家的大宗商品、汇率、利率、股指等价格指数频繁波动,给企业经营以及金融市场投资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由此催生了传统的期货交易所开始提供金融期货合约交易,覆盖外汇、利率、股指等不同品种。1972年5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的国际货币市场开业并推出外汇期货交易,标志着现代金融期货的开端。①对股票的远期与期权交易在17世纪的英国和阿姆斯特丹就已经出现,因此金融学家认为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金融衍生交易并非完全的创新。参见【美】斯科特·梅森、罗伯特·默顿、安德鲁·佩德罗、彼得·图法诺:《金融工程学案例——金融创新的应用研究》,胡维熊主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其后,CBOT在1975年设计出利率期货合约——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GNMA)的抵押凭证期货交易;1982年2月,堪萨斯期货交易所开始价值线综合指数期货交易。短短10年间,国际金融期货的三大产品——外汇期货、利率期货、股指期货——全部出台。②参见[英]阿尔弗雷德·施泰因赫尔:《金融野兽——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与监管》,陈晗、张晓刚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181页。此外,伴随着公司财务理论的突破,特别是1972年B-S期权定价公式的问世,各种金融商品的选择权或者期权交易也开始流行起来,证券交易所与期货交易所都争相上市股票甚至股指的期权工具。③参见[美]罗伯特·默顿:《期权定价理论的应用:最近25年的回顾》,载《诺贝尔奖讲演全集》(经济学卷II),《诺贝尔奖讲演全集》编译委员会编译,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1-446页。
在传统的期货交易所或证券交易所之外,银行间交易的外汇远期、掉期产品以及面向消费者个人的贵金属期权、货币期权或外汇杠杆性交易等也在快速发展,规模迅速超过场内衍生品交易。④参见陈晗:《金融衍生品:演进路径与监管措施》,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第95-102页。在美国,伴随着70年代后黄金走俏,银、铂金等商品期权交易以杠杆保证金交易的面目重新泛滥,交易平台主办方携款“跑路”等传统诈骗行为沉渣泛起。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原来以农产品为中心的期货监管模式已经过时。为了顺应金融衍生交易爆炸式发展的挑战,1974年美国国会修改《商品交易法》,设立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作为新的期货监管机构,同时将金融期货、外汇杠杆性交易等明确纳入《商品交易法》的管辖范围。由此也形成了传统期货立法模式的基本格局:一部有别于证券法的期货法,统一调整商品期货与金融期货交易。
三、证券衍生品的监管归属——期货法与证券法的边界
金融衍生交易的兴起不可避免地引发期货法与证券法的冲突,它尤其集中地体现在证券衍生品交易的管辖权问题上。当美国国会1974年将“金融期货”纳入《商品交易法》的管辖范围时,似乎并未意识到,此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已经开始批准证券交易所以及专门的期权交易所(如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上市针对单个股票的期权合约,从而事实上行使了对特定证券衍生品的管辖权。⑤Joel Seligman,“The Structure of the Options Market”,10 J.Corp.L.141(1984 -1985).当利率期货诞生后,其标的资产为政府支持证券GNMA,这种债券究竟属于SEC监管还是CTFC监管不乏争议。1980年,当CBOE申请SEC批准上市GNMA过手证券的期权合约时,CFTC甚至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自己的专属管辖权。更进一步,随着CBOE在1982年4月推出标准普尔500种股指期货并大获成功,CFTC与SEC之间围绕证券衍生品的管辖权之争也达到顶峰。⑥Jerry W.Markham,David J.Gilberg,“Stock and Commodity Options– Two Regulatory Approach and their Conflict”,47 Alb.L.Rev.741(1982-1983).
在经过了多次博弈后,CFTC与SEC最终达成的监管分工大体为:前者管辖证券的期货交易,后者管辖证券的期权交易。它建立在1982年两家监管机构的主席达成的《沙德-约翰逊协议》基础之上。其中,CFTC管辖的证券期货主要是股指期货以及类似股指的宽基证券指数⑦宽基证券指数泛指“窄基证券指数”(narrow-based securities index)之外的证券指数。美国《商品交易法》对“窄基证券指数”有明确的界定,该指数下包含的证券构成不得多于9只证券,且其中一个证券在指数中的权重不低于30%,5个最高权重的证券相加不低于总权重的60%。因此,窄基指数与其中最主要的成分股属性相近,可以视为是主要成分股的变形。参见《美国商品交易法》(中英文对照本),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组织编译,法律出版社,第28-29页。的期货交易以及期货期权交易,它们通常为现金结算,不涉及具体证券的交割。相反,针对单只股票的期货交易因涉及标的证券的交割而与证券交易极为类似,长期难以确定管辖权归属,故一直被美国国会禁止交易。直到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才对个股期货解禁,并赋予CFTC、SEC共同的管辖权。①Zachary T.Knepper,“Examining the Merits of Dual Regulation for Single - Stock Futures:How the Divergent Insider Trading Regimes for Federal Futures and Securities Markets Demonstrate the Necessity for(and Virtual Inevitability of)Dual CFT/CSEC Regulation for Single-Stock Futures”,3 Pierce L.Rev.33(2004 -2005).另一方面,SEC所管辖的证券期权交易不仅包括单只证券的期权或权证交易,还包含与成分股属性相近的窄基证券指数的期权交易。与这种监管分工格局相呼应,美国《证券法》与《证券交易法》也进行了修改,将“证券”范围进行了大幅度扩展,既包括股票、债券、基金、投资合同、合伙权益份额、中长期票据、存单等公认的投资性工具,也包括衍生自上述证券品种的期权或优先权(如看涨期权、看跌期权、多空套作权、选择期权或优先权),以及任何在全国性证券交易所达成的有关外汇的卖出权、买入权、多空套作权、选择期权或优先权等。
期货监管与证券监管在证券衍生品的这种分界,除了美国特殊的历史与政治因素的影响外,也与不同证券衍生品在交易方式上的差异所暴露的风险形态对监管的不同诉求相关。证券衍生品尽管种类繁多,但交易方式大体可分为现货交易方式与期货的保证金交易方式两种,不同交易方式对应着不同的交易系统与风险控制安排。例如,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衍生品,不论是认股权证、认沽权证还是ETFs,其交易方式与股票并无多大差别,都是先有发行人,然后经交易所核准上市。投资者买卖证券衍生品也与买卖股票一样,全额交易、先买后卖,本质上仍是现货交易。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种现货交易模式并不因融资融券的引入而改变。例如,在融券卖空的情形下,交易者必须先借入证券才能出售,卖出后或结算时必须交付证券。因此,所谓“卖空”只是针对融券者个人而言;对整个交易系统来说,都是实券买卖,不存在卖空机制。相反,在期货交易所上市的股指期货或期货期权等证券衍生品是一种由交易所制定的供交易者交易的标准合约,没有发行人,最初的卖方由交易者来担当,天然存在做空机制,采用保证金方式而不是全额交易方式。③参见杜惟毅、普丽芬:《证券衍生品法律适用分析》,载郭峰、周友苏主编,《国际化视野下的金融创新、金融监管与西部金融中心建设》,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61-74页。因此,证券衍生品的期货交易方式与现货交易方式对于风险控制及投资者保护等方面的监管需求并不完全相同,从而使得监管与市场层面的分工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在场外衍生交易市场,期货监管与证券监管的边界之争持续时间更长。美国《商品交易法》中并不存在“期货交易”(future)的概念,而是有一个非常宽泛的“商品”(commodity)的概念,④美国《商品交易法》第1a条。后者不仅指各种农产品(洋葱除外),还包括现有和将来可能出现的未来交割合约中规定的所有服务、权利和利益。在美国期货监管及司法实践中,对“商品”的界定成为划分受CFTC监管的“期货交易”(场内交易)与不受监管的“远期交易”(场外交易)的标准,它也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导致场外衍生交易的合法性一度陷入极大的不确定状态。⑤对此问题的生动描述,参见马克·D·杨:《衍生工具的法律地位》,载[美]克里夫德·E.凯尔什主编:《金融服务业的革命——解读银行、共同基金以及保险公司的角色变换》,刘怡、陶恒等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157页;Jayashree B.Gokhale,“Hedge-to-Arrive Contracts:Futures or Forwards”,53.Drake L.Rev.55(2004).2000年《商品期货交易现代化法案》宣布豁免对场外衍生交易的监管,也暂时中止了CFTC与SEC在这个领域中的管辖权冲突。⑥Frank Partnoy,“The Shifting Contour of Global Derivatives Regulation”,22 U.Pa.J.Int'l Econ.L.421.但是,这种去监管状态又埋下了场外金融衍生交易野蛮生长的隐患,CDS、CDO等金融工具泛滥,加剧了2008年金融海啸对华尔街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危机过后美国出台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金融改革与投资者保护法案》,恢复对场外衍生交易的监管,将场外衍生交易的管辖权在CFTC、SEC之间进行了分配。其中,CFTC监管一般性的互换交易(swap),SEC监管以证券为基础的互换交易(securities-based swap)。此外,美国财政部以及美联储分别在外汇互换产品以及资本金、保证金等问题上与CFTC、SEC进行合作监管。在某些能源衍生产品的监管方面,CFTC与美国能源管理委员会也存在着监管的配合。⑦参见郭锋、刘燕、杨东、杜晶:《金融危机后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与法律的改革》,载《金融服务法研究咨询报告》2011年第4期。
四、交易所层面的分工——监管与市场竞争的共同影响
传统上,美国的期货交易所与证券交易所分设,前者的主业是商品期货以及期货期权(future op-tion)交易,后者则以证券交易为支柱。金融衍生交易兴起后,二者在证券衍生品上形成的分工是:期货交易所上市宽基证券指数期货合约以及期货期权合约;证券交易所则上市个股证券的权证产品、ETFs等。此外,一些边界模糊的产品通常由专门性的交易所进行经营,以避免与传统的交易所定位发生混淆。如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主营股票期权交易,第一芝加哥交易所(OneChicago)专营单只股票期货交易,等等。
这种市场分工格局除了监管层面划界——即期货归CFTC、期权归SEC——的影响外,更主要是交易所之间自由竞争的结果。不同证券衍生品在交易方式上的差异刺激着不同的交易所根据自身所长选择最适宜的衍生品合约上市交易,使得本所交易系统与风险控制安排最有效率,从而提升自己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也更好地保护市场参与者与投资人的利益。由此逐渐形成交易所之间的品种差异化以及群聚效应。对于那些边界模糊、可能干扰现有交易所的传统优势的新品种,则通常采取设立一家新的、法律上独立的交易所来承办相关合约的交易。
例如,专司股票期权交易的CBOE就是CBOT在上世纪70年代初设立的。①参见[美]罗伯特·索贝尔著:《华尔街内幕》,周友皋译,周希敏校,中国对外法益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11-121页。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对单只股票期货交易解禁后,CME集团设立了OneChicago,专营单只股票期货交易。通过制度设计,单一股票期货可以作为融券交易的替代产品,从而将传统上作为场外交易的融券业务转移到期货市场中进行。②参见 David G Downey,Single Stock Futures:An Alternative to Securities Lending,OneChicago LLC,Aug.24,2010.CBOT与CME都是受CFTC监管的传统期货交易所(现两家已合并),而CBOE与OneChicago两家证券衍生品交易所则主要受SEC监管。
当然,随着衍生交易机制逐渐为公众所熟悉,证券交易所与期货交易所之间可能无须再刻意保持边界的清晰。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电子盘或另类交易设施对传统交易所的冲击、非互助化后各国交易所之间的竞争、传统证券交易所相对于衍生品交易所营利水平的下滑等因素,导致两类交易所的合并成为近年来的一个流行趋势。严格来说,这种合并主要是在交易所的控股公司组织层面完成的,旗下的不同交易板块仍然保持相对独立、边界清晰的交易路径与风险控制机制,合并主要是通过整合不同交易品种在证券(现货)、衍生品(期货)交易板块之间的分布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在此,纽约证券交易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在过去的近四十年间经历了一个从证券扩展到期货、放弃期货交易而专司证券交易、与衍生品交易所合并的“之”型发展轨迹。早在1979年,纽交所为应对新兴的金融期货同时避免干扰自身的交易秩序,创办了一家新的期货交易所——NYFE。经CFTC批准,NYFE上市了美国国债以及外汇的期货合约,后又采用纽交所综合指数及若干行业指数设计并推出股指期货合约。由于国债、外汇期货交易冷清,NYFE很快下架了这些合约;但纽交所综合指数期货合约却非常成功。该股指期货合约在1982年5月上市,仅比CME的标准普尔500股指期货晚一个月,很快成为与标普500以及价值线指数并驾齐驱的三大股指期货合约之一。然而,考虑到风险控制措施的成本以及比较竞争优势,纽交所最终决定放弃衍生交易业务,在1993年将NYFE卖给了当时的棉花交易所(即今日纽约期货交易所的前身),1997年甚至将股票期权业务卖给了芝加哥期权交易所,专司于打造自身擅长的证券交易业务,在债券、基金和结构性产品(如ETFs)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③参见刘仲元:《纽约证券交易所缘何放弃股指期货》,载《期货日报》2005年9月22日。近年来,受到证券现货交易市场份额下滑的压力以及衍生交易市场兴盛的诱惑,纽交所又重张衍生交易。2006年,纽交所与泛欧交易所集团合并,从而拥有了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④参见毛小云:《强者恒强,大者恒大——纽约证券交易所与泛欧交易所合并案例研究》,上海期货交易所博士后工作站研究报告(2007)。2012年又完成了与洲际交易所的合并,后者作为能源期货与场外市场全球领先营运商,不仅拓展了纽交所集团的业务范围,而且提供了强大的衍生品清算能力,弥补了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无清算机构的短板。⑤参见廖士光:《洲际交易所并购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研究》,载《证券市场导报》2013年第10期。
五、对我国处理好期货法与证券法关系的启示
在市场自然演进的过程中,美国形成了期货业与证券业分离、期货法与证券法分立的格局,二者之间的分工大致遵循了“交易机制 +基础资产”双重标准,即期货法与证券法分别处理商品(期货)交易与证券(现货)交易。这种各自独立发展的状态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直到上世纪70年代金融期货的出现而中断,自此期货法与证券法在证券衍生品上发生重叠,监管与市场层面都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以确定二者之间的合理边界。尽管这个过程并不总是很顺畅,CFTC与SEC之间的监管竞争失控甚至被批评为导致2008年场外衍生交易危机的原因之一,但总体上看,美国期货立法演进的目标在于保护市场参与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利益,同时促进美国期货市场的顺利发展,避免对其参与全球化竞争带来消极影响。
归纳起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期货立法模式对我国的期货立法、特别是如何处理期货法与证券法的关系,提供了如下三方面的启示:
第一,独立于证券法,存在着一部综合性的期货法,它对商品期货、金融期货以及场外衍生交易、杠杆性外汇交易等进行统一监管。与这种立法模式对应,往往存在一个发达的期货市场,包括商品期货市场与金融期货市场。事实上,如果进一步从期货立法形态与期货市场结构之间相关性的视角观察其他国家的期货立法,可以发现,在商品期货比较发达或比较重要的国家,一般会有单独的期货法或至少是独立的商品期货法,如日本、新加坡、印度等都是如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商品期货市场的战略意义是争夺对大宗商品的定价权。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自不待言;日本、新加坡、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商品期货则更多地体现了对区域性特定农产品或矿产品的重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商品期货不发达或者明确地转向以发展金融期货为主要目标的国家或地区,立法上多采用“大证券法”、“大金融法”或“大公司法”的模式,将期货交易监管纳入统一的证券监管或金融监管框架。德国、韩国、英国、澳大利亚均如此。
以此观照,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多种大宗商品的最大消费国和进口国,期货市场的现状与我国实体经济的地位极不相称;期货法也是目前我国金融立法体系中最显眼的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制订一部独立的、能够充分反映期货交易独特机理的《期货法》势在必行。它一方面避免了在《证券法》中塞入过多的期货交易监管规则,从而破坏《证券法》自身逻辑与体例的严谨性;另一方面,一部独立的期货立法也能够包容商品交易的不同阶段,从而化解当前我国实践中大宗商品中远期电子盘交易的监管归属争议。这也是域外的普遍做法,例如印度《远期合约监管法案》甚至通过直接规定现货交易的最长交割期为11天而消除现货市场与远期市场之间的划界争议。更进一步,借鉴美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我国可以将以往作为“违法经营罪”打击的地下炒金、炒汇交易等作为外汇、黄金的杠杆交易或按金交易正式纳入期货法的调整范围,避免运动式执法或单纯追究刑事责任的弊端。
第二,期货法与证券法的分立通常意味着证券衍生品在立法与监管上的交叉,从而需要期货监管者与证券监管者的分工与配合。在美国,它不仅包括SEC与CFTC之间的分工合作,还可能涉及到其他有权对特定大宗商品或金融工具进行监管的机构,如美联储、财政部、能源部等。当然,期货法、证券法分立模式下的监管机构也可能为一家,如我国台湾地区就在证券、期货分别立法的基础上实行金融统一监管,由“行政院”下属的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银行、证券、保险、期货在内的整个金融业进行监管。一个现实因素是,目前台湾地区的期货交易仅有金融衍生交易,尚未有商品期货交易。这或许使得台湾对证券、期货统一监管比较顺理成章。
在我国,我国期货监管机构与证券监管机构的合一已经消除了类似美国SEC、CFTC之间监管冲突的最大风险,但证监会与场外衍生品市场现有的监管者——如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商务部或者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笔者以为,这种监管交叉本质上属于功能监管与机构(行业)监管之间的重叠,应根据各自的监管目的尽可能有效地进行分工与协作,一方面避免市场监管套利,另一方面降低监管成本。
第三,在交易所层面,期货交易所与证券交易所通常根据各自的交易机制和风险控制措施的比较优势,分别上市不同的证券衍生品;跨界上市交易品种往往通过设立独立的子公司来进行。这种安排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市场参与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在我国,交易所层面的交叉在上市品种严格管制的背景下仅在局部发生。即便如此,既往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衍生品出现的问题(如三二七国债事件、备兑权证争议等)还是值得重视,它反映出衍生交易机理与证券现货交易机理共存于一个市场中时给投资者可能带来的混淆以及对监管提出的挑战。目前,我国法律不允许交易所设立子公司,导致推出股票期权交易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无法另行设立一个衍生品交易所来与证券交易进行物理区隔,因此它主要通过筛选有资格参与股票期权的投资者(即设置交易门槛为50万元的投资者适当性要求)来应对这一问题,相当于在市场内部做系统上的分离。这一安排最终的实践效果如何,尚待时日证明。
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的上市品种高度管制的局面非长久之策。顺应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要求,应适度放开衍生品交易所的设立,或者建立从合格中远期大宗商品市场向期货交易所转型的通道。同时,在交易所保持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应赋予交易所上市品种方面更大的自主权。从长期来看,交易所之间的竞争也将使得不同交易品种出现群聚效应,集中于最有特色的、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最佳服务的交易所中。立法与监管需要密切关注的,则是相关交易所在风险控制与投资者保护等方面的措施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