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有盛宴
2015-04-15吴惠子
吴惠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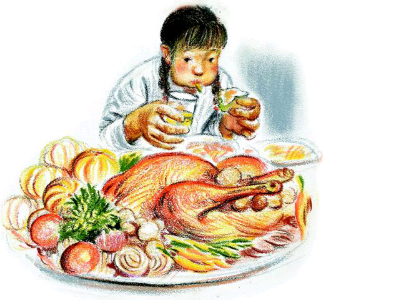
直到十一岁,我才吃到这辈子第一个汉堡包。
其实也不难想象,我出生的南方小县城,面积小,人口少。县城小到每年春节扫墓,都能在公墓大门口不费吹灰之力地碰到好几个同班同学。所以十一岁能吃上汉堡,在我们班已经相当时髦。
这要归功于我妈,她年轻的时候卖烟,天南海北基本都去过,那几年分管东北三省的业务,常驻北京办事处。我妈卖烟卖得风生水起,因为见多识广,所以一直走在时尚前沿,逛赛特,烫卷发,穿短裙,背名牌包。十一岁那年,我刚刚开始发育,挑肥拣瘦,有的衣服开始不爱穿。我妈明察秋毫,看出了我臭美的苗头。有一回她出差回来,突然觉得我很土,便二话不说买了两张火车票,让我跟她去北京见见大世面。
火车北上,我妈说,女孩子应该多出去走走,眼界宽,气质自然就好了。她问我到了北京最想干吗,我冥思苦想,憋了半天,说:“爬长城,吃汉堡。”
我妈惊愕,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她哪知道,爬长城和吃汉堡,已经是我对北京这座大都市所有想象力的极限。我妈也同样突破了自己的极限,意识到我比她想象中还要土一万倍,于是我们下了火车还没来得及放下行李,她就冲到麦当劳给我买了我这辈子第一个汉堡。
汉堡是胡椒味的,我怀着忐忑激动的新鲜劲儿,像加入少先队第一次佩戴红领巾时一样。我捧着软软的汉堡认真地咬了一口,又认真地咬了第二口。
崩溃!又黑又黏的胡椒酱,滋味奇怪,难以下咽。我抬头看看我妈,再看看周围,大家分明都吃得比我香。由于担心我妈再次嫌我土,我勇敢地把汉堡吃完了,心情非常复杂。
可谁知道这种被全世界背叛的感觉,竟接踵而至。
第一次喝到固体状的酸奶,第一次吃到从水里捞出来的不仅不带汤还要蘸醋的饺子,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除了有尖椒肉丝还有甜甜腻腻的京酱肉丝,第一次端起撒了葱花和香菜的咸豆腐脑,第一次遇到放糖不放盐的西红柿炒鸡蛋,我狭隘的味觉突然就慌了,心里也慌了。
当我第一次涮北方的清汤火锅,发现锅底居然没有猪蹄和土鸡时,我不屑一顾,心想:这清澈见底的一锅水,也能算火锅?但是新鲜的羊肉放在铜锅里烫一烫,在芝麻酱里蜻蜓点水地一蘸,味道还真是绝了。
我妈带着我吃遍了北京,又一路北上,吃到沈阳、长春、哈尔滨,从中国人开的小馆子吃到俄罗斯人开的西餐厅,口味跨区域、跨民族,食材上天又入地。那个寒假,我的每顿饭都像盛宴。我鼓励自己在带着冰碴的生拌牛肉里振作,也纵容自己在晶莹剔透的锅包肉里沉沦,彻底明白了我妈为什么说我土。
我梳着两条麻花辫儿,穿着我妈在赛特给我买的羽绒背心,站在八达岭长城上,第一次和两名陌生的外国友人合影。我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横扫全球,吃遍天下所有的飞禽走兽。回家的火车上,我妈给我买了一包真空包装的卤鹌鹑,啃起来奇香。
我妈看着我,就像端详一件艺术品,她说我出去见了世面,马上就洋气多了。
我光顾着吃,一心恳求我妈以后每次出差坐火车,都要给我买两包卤鹌鹑。
我回味着北方才有的盛宴,胃口大开,正值青春期长身体,无肉不欢。初中毕业时,学校体检,班主任语重心长地提醒我注意身材,让我考虑减肥,我觉得他多管闲事,一笑而过。
中考后的那个暑假,我住的小县城终于开了一家叫“麦琪汉堡”的餐厅,生意奇好。我第一时间去吃了一回,香辣脆鸡堡的味道甩出胡椒汉堡好几条街。我看着餐厅里络绎不绝的人,盯着他们的嘴,捕捉他们吃这辈子第一个汉堡的表情,有种扬眉吐气的自豪感。我打包了一个汉堡给我外婆,让她也赶赶时髦,可她咬了一口,摆摆手说太难吃了,问我中间的菜为什么是生的,说外面的饼还不如烧饼。我偷笑,觉得外婆比我还土。
后来我妈因为工作变动,被调到了粤东,再次刷新了我对食物想象力的极限。我虽然天生好吃,从不挑食,也自认为见过世面,所以胆大包天,但广东人还是让我觉得自己太孤陋寡闻。有一回跟我妈去汕头,听到我妈的客户们说要吃猴子,我问了我妈三遍是不是动物园里的那种猴子,我妈说是。那一瞬间,我还是崩溃了,彻底忘掉了自己要吃遍飞禽走兽的誓言。我偷偷跟我妈说:“你可别吃猴子。”我妈说:“你放心,我不吃,吃了要遭报应。”
我长大了,胆子反倒小了,干锅野兔已经到了我敢吃的哺乳动物的极限。
高中学习压力大,食量也大。我妈跟单位申请,出差的时间缩减了一半,所以总能在家里给我做饭。她去过的地方多,做菜又有天赋,可将南北口味融会贯通。但凡她吃到好吃的,就会默默地把食材和味道记下来,遇到吃不明白的,还会跑到厨房去找师傅耐心请教,然后回家第一时间做给我吃。
我家虽然深居内陆小县城,但米缸里永远都是我妈从东北运回来的香喷喷的大米,饭桌上随时都能从平平淡淡的鄂西风味变成精致的粤式小炒。原本我妈是为了让我吃饱了好好读书,可是由于我妈做的饭实在太好吃,以至于我每天吃饱了就困,根本没办法好好上课。我经常因为中午吃得太饱,下午的数学课上大脑缺氧,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晚自习下课后回家,我还要风卷残云,就着中午的剩饭剩菜饱餐一顿。有一回我一口气吃了半锅饭,我妈忍不住大发雷霆。
她说我成绩不好,饭都白吃了。
可是饭怎么会白吃呢!我胖了,真胖了。
高考前夕,当别人的妈妈都给自己孩子买各种补脑口服液的时候,我妈看电视购物,给我买了一种非常甜的进口减肥食品,我吃了半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抑制食欲对我来说就是胡扯。我妈只好勒令我每顿最多吃一碗饭,还不让我压得太实,并没收了我的全部零食。
但为时已晚。高中毕业,还是学校体检,身高一米六刚出头的我,再次称体重,我以为秤坏了。最后好话说尽,医生才勉强答应我在体检表上少写六斤,说那就凑个整数,一百二吧。我看着镜子里的姑娘,粗腿圆脸,虎背熊腰,一点也不好看。这才后知后觉,意识到高中这几年给我写情书的男生,欣赏的原来是我秀气的灵魂,而不是我的脸。
伤心之余,再想想自己以前总是以貌取人的行为,觉得十分肤浅。
那一阵儿,每当我端起碗,我妈就会问我:“你要吃,还是要美?”我就如鲠在喉,第一次隐隐约约觉察到,最接地气的价值观,其实就是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做出的那个选择。
虽然胖是一种无法呼吸的痛,但是一想到没肉吃,我便更加心痛。思忖再三,我意识到自己的内心始终无法割舍年少记忆里的铜锅涮肉,觉得“人生得意须尽欢”,便毅然决然离开小县城,到北京念大学。
北方虽有盛宴,但气候干燥。我因为水土不服,刚到北京的那一年,几乎每个月都去医院报到。发烧输液,体重直线下降,减肥效果强过任何减肥药。人一瘦,肆无忌惮,吃得更多,常常跟朋友三五成群,在大街小巷胡吃海喝。
可我们都是吃不了猴子的同类人,最大的出息,就是经常跨越半个北京,去西四北大街排队买煎饼,或是开着车从望京跑到南小街吃卤煮,夏天晚上的据点,通常都在对外经贸大学对面的车棚烧烤摊,冬天沿着东河沿,去南门涮肉、喝啤酒,清新脱俗。铜锅咕嘟咕嘟冒着泡,窗户上雾气蒙蒙,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影影绰绰,肉吃腻了,就来头糖蒜,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吹牛不胖,又幸福又满足。
朋友笑我吃起肉来像个男人,成本太高不太好嫁人,问我如果一顿没肉还能不能吃下饭,我光是听就急了,说不能,绝对不能没肉吃。我外婆总说,人有多大胃,就吃多少饭,饭可以乱吃,话却不能乱讲,世事无常,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
外婆说得对。
我妈得了癌症,整整十八个月,我一口肉都没吃过,也照样把每顿饭都吃下去了。那时候病急乱投医,我束手无策跑到雍和宫跪了三个小时,发愿说只要我妈身体健康,我愿意吃素不杀生。我妈知道后气急败坏,说我书都白读了,太愚昧。
我妈问我:“人如果不吃肉,身体还能好吗?女人不喝猪脚汤,皮肤还能好吗?如果吃素就能治病,还要医生干吗?”她一口气说了三个排比句,气势磅礴,听起来都很有道理。但是我固执,觉得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我说我在雍和宫见佛就跪,跪一次就说一遍心愿,绝对不能食言。最后我妈还是没拗过我,接受了我不吃肉的决心。
我妈配合医生,积极治疗。我遵守诺言,不吃肉也不杀生,连家里过路的小蚂蚁也不碰。刚开始吃素很痛苦,因为没有动物脂肪,饿得很快,经常刚吃完饭马上就饿,半夜有时候还会饿得睡不着,人一下子变得很焦虑,瘦了好多。有一回我馋得不行,做梦吃饭,夹了一块蒜香排骨,结果又在梦里清楚地告诉自己不能吃,于是放进嘴里的排骨,又被我吐了出去。早晨饿醒后我坐在床上大哭一场,觉得没肉吃的日子真的好辛苦。那时候每天早晨路过包子铺,看到店里的人吃肉馅儿的小笼包,真的就会多瞄两眼,羡慕得一塌糊涂,觉得要是能进去吃上半屉,简直就是人生第二大梦想。
现在两个梦想都实现了。
首先,医生妙手回春,我妈的病彻底好了,她的精神甚至好过从前;其次,我在朋友和我妈的反复劝说下,终于开了荤。但因为太久不吃肉,第一口老鸭汤,确实感觉很腥。朋友带着我连吃了三天肉,可是真的也就新鲜了不到一个礼拜,我发现,肉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有时候青菜煮面,似乎更爽口一点。
现在跟客户吃饭,山珍海味满满一桌,大家你来我往把酒言欢,但我的食欲却大不如从前,味同嚼蜡,经常走神。奇怪,这不就是我曾经心心念念的北方盛宴吗?高朋满座,热闹非凡,但盘子里的菜,味道怎么像是变了。
心口仿佛有一束光,沿着喉咙撞过来,把舌头上的麻辣鲜香都冲淡了。才明白,人最先变老的原来是味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天南海北的缤纷筵席,吃份儿新鲜,吃不出团圆。
小时候我信誓旦旦要吃遍全球,可眼下,走到北京,已经是我能从家里走出来的最远的距离。风风光光的北方盛宴,恐怕再使劲也推不到高潮了吧,因为生命里真正的高潮早就出现了:
我妈撸起袖子,在厨房三下五除二露一手——凉拌木耳、白灼芥蓝、丝瓜炒蛋、清蒸老虎斑,配一碗干贝白菜汤,添一碗喷香的白米饭。
四菜一汤,尽是滋味,千金不换。
(雨 涛摘自《ONE·一个》,李小光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