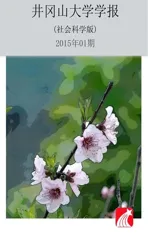胡风何以将鲁迅的“转变”提前到1919年
2015-04-15魏邦良
魏邦良
(安徽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0)
胡风何以将鲁迅的“转变”提前到1919年
魏邦良
(安徽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0)
胡风不认可学界关于鲁迅思想在1927年左右有较大转变这一说法,他认为,早在1919年,鲁迅已经接受了无产阶级思想。胡风强调鲁迅转变在1919年而非1928年,是为了突出鲁迅是通过创作实践,完成了思想改造——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而不是像邵荃麟、何其芳等人说的那样,是通过攻读马列主义文艺理论 “不得已才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
胡风;鲁迅;创作实践;思想改造
一
学界普遍认为,鲁迅是在1928年后,由一位进化论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茅盾、周扬、何其芳、邵荃麟等人均持此种观点。
茅盾说:“一九二六年,在广州,代表大地主买办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如何投降帝国主义而出卖革命,而血腥屠杀当年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员,鲁迅是目睹的,是万分愤慨的。当其时,同是青年而或者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卖友求荣;或者慷慨就义,宁死不屈,鲁迅也是目睹,是万分愤慨的。这些血的教训,最终轰毁了他多年来据以观察、分析事物的进化论思想,转而求索那解决人类命运的普遍真理,他开始阅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九二六年以后,短短数年内,鲁迅通过勤奋的学习和英勇的斗争实践,终于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飞跃。”[1](P196)
何其芳说,1927年,鲁迅在广州,目睹青年分成两大阵营,“对于进化论的相信就动摇了”,后来,又因翻译科学的文艺理论而接受了无产阶级的思想,“而坚信只有无产阶级才有将来,而参加了无产阶级的营垒”。[2](P144)
持此观点者,其依据便是鲁迅《三闲集》、《二心集》序言中的几句话。在《三闲集》的序中,鲁迅写道:“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在《二心集》的序里,鲁迅说:“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仅凭这几句话就证明鲁迅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恐难令人信服。
那么,茅盾、何其芳等人为何坚称,鲁迅是在1928年后才转变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想了解根本原因,还得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那段论述说起。
在《讲话》中,说到知识分子如何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说:“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毛泽东以自己为例,讲述了这种“磨练”的艰苦与曲折:
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3](P53)
那么如何才能完成这个改造呢?毛泽东说:“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3](P53)
可见,如果鲁迅是在1928年思想开始转变,那他的转变,就完全暗合了毛泽东《讲话》中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论述:一是在广州目睹革命阵营的分化而舍弃了进化论(就是毛泽东说的“学习社会”);二是因文学论争开始读马列著作(就是毛泽东说的“学习马列主义”)。于是鲁迅的方向就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向”,何其芳说:“鲁迅的方向正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向。……新文化若不与人民群众结合,那就不能完成这个任务。而要达到新文化真正成为人民自己的东西,并又动员他们起来打倒中华民族的两大敌人,则又非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之下是绝对不能成功的。”[2](P146)
这样,茅盾、何其芳等人的意图就很明显了,他们把鲁迅转变的时间确定在1928年后,不过是借鲁迅的转变宣传毛泽东《讲话》的英明,或者是把鲁迅树立为学习《讲话》的标兵和模范。其实,毛泽东在《讲话》中已经这么做了。毛泽东在《讲话》中引用了鲁迅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诗,并对此作了如下解释:“(这两句诗)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3](P82)
经毛泽东的诠释,原本涵义丰富的“千夫”和“孺子”就完全成了政治符号。当“诗”变成了“座右铭”,鲁迅也由文学大家变成了思想改造的“急先锋”。
二
1980年,胡风出狱,从四川回到北京不久,“被通知听了一位文艺工作领导人的报告录音”。当他再次听到这种观点时,忍不住写了一篇文章,予以反驳。
胡风认为,不能因为鲁迅《三闲集》、《二心集》的序言中的几句话,就断定鲁迅此前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说他读了一些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解决了一些文学史上的问题,并没有说他的全部思想‘转变’。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在具体问题上取得了创造性的解决,不但不能据此就断定这以前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相反,这正是总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应有的结果。”[4](P151)胡风的结论是:“在五四的十多年后还说在鲁迅精神里还有一个思想‘转变’问题,那完全违反实际,不过是批判者们冒充无产阶级代表发出的‘官话’而已。”
胡风承认,鲁迅思想发生过转变,但他认为,鲁迅在1919年写出《“圣武”》后就已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了。胡风在文章中引用了《“圣武”》中的一段话:
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我们这单有“我”,单想“取彼”,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实没有插足的余地。
因此,只须防那“来了”便够了。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5](P356)
根据这段话,胡风得出结论:“鲁迅在1919年就是这样迎接了十月革命的。”胡风对鲁迅的上述引文作了逐字逐句的分析:
一、他说的各种“外来的思想”实际上是指当时在中国开始了的社会主义运动说的。这种革命,在俄国已经胜利了。
二、他说的“有主义的人民”是包括革命领导者和有组织的人民以至其他无组织的劳动人民说的。他这种思想是超过了当时一切革命者的认识的,是符合毛主席从宣传、组织到行动的群众路线的大原则的。
三、他这种认识是和马克思主义的武装人民夺取政权的思想完全一致的。他把十月革命看做“新世纪的曙光”。
四、他说的“物质的闪光”,是指当时“实业救国”、武器救国,搞官僚买办阶级的立宪国会,完全脱离历史实际和脱离人民的那些思想说的。他所确信的是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五、他号召人民向“新世纪的曙光”抬起头来。这足以说明他的战斗是为革命,但并没有把自己放在“教师”的地位上,只是由衷地希望人民的觉醒,并不是用超出于群众的领导者说话,他自己也只是群众的一员,不过是对历史发展的要求在某些点上认识得较早而已。[4](P152)
胡风在文中还引用了李大钊对子女说的一句话:“鲁迅更和我们一致了”,并由此推断:“鲁迅在那时(1919年)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甚至是超过当时一般马克思主义者之上的。”
胡风对《“圣武”》的解读明显过度。在《“圣武”》中,鲁迅虽然赞颂了 “别国”、“有主义的人民”、“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从而让新世纪露出了曙光。但鲁迅在文中明确表示,外来思想是进入不了中国的:“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信息,在我们这单有‘我’,单想‘取彼’,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实没有插足的余地。”[5](P356)鲁迅还指出,外来思想即便偶或来到中国,也会“变了颜色”:“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的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若再留心看看别国的国民性格,国民文学,再翻一本文人的评传,便更能明白别国著作里写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几乎全不是中国所有。”[5](P354)对于新主义为何不能在中国扎根的原因,鲁迅也作了剖析:“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生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5](P354)可见,鲁迅这篇文章,明显是在批评当时的中国统治者“圣武”,最高理想也就是满足其“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而底层人民则麻木死寂毫无生机。胡风根据一己的需要,以过度诠释的方法,拔高了此文的主旨,让鲁迅穿上时尚而堂皇的马克思主义的大氅。显然,胡风此文也染上时代病:牵强附会,上纲上线。
三
鲁迅是在1919年左右还是在1928年之后思想发生了转变?弄清这一问题很重要吗?是什么原因促使胡风在衰老之年,抱病撰写长文,澄清此事?在胡风给一位日本友人的信中,我们或许能找到部分原因。
在给日本友人釜屋修的一封信中,胡风谈到鲁迅思想的转变:
……到1919年,他就认定了“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事实”就是十月革命,他就由空想的社会主义者转变为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了。他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有主义的人民”的胜利,是“新世纪的曙光”,他号召中国人民向这个曙光抬起头来。[6](P92)
胡风在信中强调:“我认为这一点在鲁迅研究上非常重要,提给日本同志们参考。直到现在,还有人想歪曲鲁迅,认为鲁迅是在1928-1929年受创造社、太阳社的围攻,不得已才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
根据此信,我们得知,胡风强调鲁迅转变在1919年而非1928年,是为了突出鲁迅是通过创作实践,完成了思想改造——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而不是像邵荃麟、何其芳等人说的那样是通过攻读马列主义文艺理论 “不得已才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
胡风强调鲁迅在1919年写出《“圣武”》后,思想即发生转变,也与毛泽东《讲话》中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论述有很大关联。
出于对《讲话》的生吞活剥,何其芳、周扬等坚持认为,知识分子要完成思想改造,必须按《讲话》的要求,直接参加革命斗争,学习马列著作,深入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所以,五四时期的作家(包括五四时期的鲁迅)以及国统区的作家,就存在着缺陷,由于时空条件的限制,他们在学习马列著作,深入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方面做得不够,在思想改造方面就不如延安知识分子,所以需要补上这一课。
胡风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延安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方面不应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越感,而五四时期的作家、国统区的作家,虽没有时空方面的优势,但他们照样可以通过创作实践完成思想改造:
就那些和人民有着联系,争取着深入人民的内容的作家们说,他们的创作实践原就是克服着本身的二重人格,追求着和人民结合的自我改造的过程。已有的成果是这样获得的,应有的发展是只能这样达到的。因为,历史现实的发展中的存在,作家的反映历史现实的创作实践(把握客观对象或深入人民的内容)并不是只须一次的“取得资格”的结果所能保证的。[7](P529)
胡风这一观点,遭到何其芳的讥嘲,何其芳说:“这岂不是一条最省事的思想改造的道路?”因为何其芳认为,“改造的道路只能是参加实际斗争和学习马列主义。”[8](P23-24)
在这种背景下,胡风通过对鲁迅《“圣武”》的分析,证明鲁迅在写作此文时思想发生了转变,其意图再明显不过,他要据此证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如鲁迅,完全可以通过创作实践完成思想改造:“他们的创作实践原就是克服着本身的二重人格,追求着和人民结合的自我改造的过程”,因为,“已有的成果”如鲁迅的优秀作品,“是这样获得的”。
倘若胡风的推断成立,那么五四时期的不少优秀作家——只要 “和人民有着联系,争取着深入人民的内容”,都可以像鲁迅那样不必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也可完成思想改造的。而国统区的作家如胡风及其友人也可通过同样的途径完成思想改造。
这就是胡风为何把鲁迅思想转变提前十年的真实原因。
鲁迅是否在1919年写下《“圣武”》就完成了思想转变,关乎胡风文艺理论是否成立,关乎胡风对鲁迅的总体评价,难怪胡风言词激烈,寸步不让。
四
围绕鲁迅的思想转变,胡风与茅盾、何其芳们争论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先后问题,而是如何借助鲁迅,夯实自己的理论。兹事体大,双方当然要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了。
在《二心集》序中,鲁迅明明说过:“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这句话,茅盾,何其芳等却视而不见。显然,在序言中,鲁迅表达的意思是:他虽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但他本人不一定非得要跻身“无产者”行列。由于鲁迅这句话,与何其芳等人力图论证的观点不相符,他们只能以一叶障目的方式将其忽略了。
而胡风在过度诠释《“圣武”》时,上纲上线,牵强附会,丝毫不输何其芳等人。双方为了以鲁迅作品验证自己的观点,在分析鲁迅作品时,不约而同,都犯了以偏概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毛病。
鲁迅在《二心集》的序言中还有一段更为意味深长的话: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了。[9](P191)
对何其芳等动辄喜欢引鲁迅为同道者的人们来说,鲁迅这句话是预先的警告:即使你我身处同一阵营,我也会对你格外警惕,因为“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
对胡风,这段话更是预先的提醒:倘若固执己见,特立独行,那你很可能被视为 “最可恶的叛逆”,有被除掉的危险。遗憾的是,胡风并没有读出鲁迅这句话的玄机,没有及时改变自己 “不满现状”的态度,写几篇歌功颂德的“表态”文章,而是本着对真理的赤忱追求,坚守阵地,强硬回击,不屈不挠,愈挫愈勇,终让自己陷入灭顶之灾。
胡风一再夸赞鲁迅有政治预见力,但鲁迅的这个本事,作为弟子的胡风似乎没有学到手。
胡风曾在文章中提到一位 “一只手拿法币一只手拿手枪的特字号教授老爷”对鲁迅对中共的攻击:“他(鲁迅)底享盛名不在于‘阿Q’是成功的作品,不在于他晚年以随笔杂感痛骂腐化势力和政敌,而在于一封回‘陈某’的信,内中大骂‘托派’为汉奸,恰适合第三国际的需要。第三国际常用的政治公式:先造成死者的偶像,而后引用他生前的话,满足自己的政治要求。中共不过是这公式之忠实执行者,但这却便宜了鲁迅。”[4](P42)
遗憾的是,胡风和他的论争对手们(周扬、何其芳等),或多或少,似乎都犯了这样的错误:“先造成死者的偶像,而后引用他生前的话,满足自己的政治要求。”
胡风的文艺理论有一个重要观点,“主观战斗精神”。在《以〈狂人日记〉为起点》一文中,胡风引用了鲁迅随感录《生命的路》中的一段话,证明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与鲁迅的精神是相通的。
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7](P419)
胡风这样评析这段话:“我也痛恨唯心论,但这一段用着好像是 ‘唯心论’的说法所写出的文字,可以说是对于三十年以来的革命斗争的真情的颂歌。你看‘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生命是乐观的’,对照着后来的历史发展底实际内容,这些诗的语言,包含了多么强的现实斗争的人生意义。”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说受到了邵荃麟、何其芳等人的批评。邵荃麟说,由于胡风离开了社会阶级的观点,仅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方面去认识主观问题,就产生了一连串的的错误。邵荃麟认为,胡风对主观的片面强调,多少受到了鲁迅早期思想的影响。不过,邵荃麟又指出胡风等主观论者和鲁迅的不同之处:“但是鲁迅先生却明白指出,这是叔本华,尼采等的学说,而主观论者,俨然以马列主义自命,这是他们真伪不同之点;其次,鲁迅先生思想正如瞿秋白所说:‘在当时尚有革命意义’,而主观论者今天重来提倡此种思想,则就远落于现实要求之后,而和鲁迅先生整个的精神是相反的了。”[10](P76)
对于胡风喜欢引用鲁迅的话,何其芳也做了批评:“这些人喜欢以鲁迅先生为例子来证明他们的论点,仿佛鲁迅先生就是像他们那样就无产阶级化了似的。但鲁迅先生却从来没有夸说过自己一贯正确,也从来也没有夸说过自己如何无产阶级化,相反地,他倒是谦逊地检讨自己过去的缺点,并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在他思想变化上所起的作用的。”[2](P10)
邵荃麟和何其芳在文章里都指出鲁迅早期思想的局限性,比如强调个性,信仰进化论等。但同时他们又表明,在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鲁迅的这种还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是进步的,具有积极意义的。这样,既维护了鲁迅的权威,也指出了鲁迅早期思想与毛泽东后来的指示和号召还存在相左之处。
现在,倘若胡风根据对《“圣武”》的分析,推断鲁迅在1919年就已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一方面,当年邵荃麟说他的思想受鲁迅早期思想影响,就不是批评而是表扬了。因为,既然鲁迅早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甚至是超过当时一般马克思主义者之上的”,那受其影响的胡风,又何错之有?另一方面,何其芳对他的指责也失去了威力。
这是胡风将鲁迅思想转变提前至1919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胡风也承认,鲁迅在1918年之前,服膺进化论,是人道主义者,但在给朋友书信中,他坚称,鲁迅的人道主义具有“战斗性”和“人民性”:“人道主义出发,真诚地进入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内容,进化论的武器达到了阶级论的内容,这就获得了深刻的人民性。”“进化论在鲁迅是成了肯定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武器,肯定人类解放的武器。”[6](P103)
周扬、何其芳等人只肯定1928年之后的鲁迅,认为那时的鲁迅具备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胡风不这样看,他认为,早期鲁迅,虽未接触马克思主义,但因具备“主观战斗精神”,通过创作实践,使鲁迅精神和毛泽东思想得以汇合。比如,通过描写阿Q的朦胧的革命要求,鲁迅肯定武装斗争,并进而“由于对于历史上阶级斗争和现实阶级关系(农民潜在的反抗要求)的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得到了和斯大林、毛泽东相同的结论”。
所以,胡风承认鲁迅的斗争策略和思想内容是有发展的,但这个发展是前后相承的,不应该机械地分为前期后期。
胡风喜欢引用鲁迅的一句名言来说明自己的文艺观:“喷泉里流出的是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他认为,鲁迅首先是一个具备“主观战斗精神”的战士,然后,才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而“主观战斗精神”几乎贯穿了鲁迅的一生,所以,鲁迅的人生之路和创作之路不应机械地被分为前期后期。而周扬、何其芳等人则认为,鲁迅只有在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后,才成为伟大的作家,至此,“鲁迅的方向”才成为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向”、“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所以,鲁迅的前期后期,判然有别。
这,就是胡风和他的论争对手最大的分歧所在。
[1]茅盾.学习鲁迅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精神[A].瞿秋白,等.红色光环下的鲁迅[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2]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4]萧军,等.如果现在他还活着——后期弟子忆鲁迅[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6]胡风.胡风全集(9)[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7]胡风.胡风全集(3)[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8]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四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9]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0]荃麟,胡绳,等.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C].北京:新中国书局,1949.
Why Hu Feng Put the Year 1919 as the Time of Lu Xun's Thought"Transition"?
WEI Bang-l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Maanshan 243000,China)
Hu Feng disagrees with the scholar community's argument that Lu Xu underwent an apparent thought transition in 1927,and believes that Lu Xu accepted proletarian thoughts as early as in 1919.Hu Feng's emphasis on 1919 instead of 1928 aimed to highlight that Lu Xu completed his thought transition through his literary practices;in other words,he actively accepted Marxism and socialist thoughts,contrary to what Shao Quanlin and He Qifang said that Lu Xu"reluctantly accepted those thoughts"through reading of Marxist and Leninist literary theories.
Hu Feng;Lu Xun;literary creative practice;thoughts reformation
I206.7
A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5.01.016
1674-8107(2015)01-0089-06
(责任编辑:刘伙根,庄暨军)
2014-11-12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胡风办刊的实践与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3YJA751050)。
魏邦良(1966-),男,安徽和县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